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智慧的时代,这是愚蠢的时代;这是信仰的时期,这是怀疑的时期;这是光明的季节,这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之春,这是失望之冬;人们面前有着各样事物,人们面前一无所有;人们正在直登天堂;人们正在直下地狱。
这里是纽约,也是北京、上海、巴黎、东京。
在这篇文章里,作者以纽约为蓝本,讨论生活在世界超级大城市必然面临的种种困境,由今日之纽约,窥视每座现代都市的明日面貌。

几年前,我用奶奶留给我的遗产在曼哈顿买下了一间公寓。我奶奶的父亲曾经是美孚石油公司的律师。奶奶的寿命长过她的三任丈夫,而且理财有方,她在坟墓里“大笔一挥”就把我的社会地位提升了一个档次。
与此同时,在这座城市的另一头,我弟弟生活在一个流浪者收容所里。
他住得不远——我们相隔不到一英里。搬来纽约后,这已经是他第二或第三个落脚点了。多数情况下,谈钱总是一件使人尴尬的事,要是发生在家庭成员之间,那就更尴尬了。所以,请允许我先简单地介绍一下情况:我弟弟并非没有获得遗产,他只是不能立即动用那笔钱而已,因为他患有精神疾病。他与疾病做着勇敢的斗争,也采取了各种手段来管理自己的健康。来纽约后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用医保卡在医院里配了处方药。
然而,搬来这座城市对他而言实在是个很糟糕的主意。从长远看这个决定,就好比看一场慢镜头的车祸。我哥、我爸,还有我,我们都提醒甚至恳求过他别搬来纽约。我爸对他说了自从我们在20世纪70年代搬来这里后,发生过的那些恐怖的事情。我告诉他,就算只在这里住几个晚上也是一件够折磨人的事,因为这座城市燥热、喧嚣,一刻不歇地脉动着。我大哥告诉他在这里找工作有多么不容易,这一点我弟弟了解得很清楚,他曾有一年多一直在找工作的经历。助教、工艺员、图书馆管理员......他找了几乎所有跟文字打交道的工作,只要薪酬高于最低工资标准。他有学士学位,还在报纸上发表过文章。
最终,所有的劝说都无济于事。他找不到工作,觉得在老地方——尤蒂卡——待不下去了,于是他乘上火车直奔纽约,然后在一家流浪者收容所报了个到。他几乎没带任何行李。他的家当不是送人就是卖掉了。他随身带了一只行李箱,一台手提电脑——为防失窃晚上就枕在上面睡,以及一部用充值卡充值的手机。这些物品也许在世界上很多地方都算得上奢侈品,但我可以打包票,对我弟弟而言,它们不过是联结他与外部世界的一条纤细的线;而他与身边的亲人却连这微乎其微的联系都没有。我们只能通过脸谱网得知他的行踪:他因为和人吵架或大打出手而被赶出了哪家收容所,他昨晚睡在哪里——也许是斯塔滕岛的一艘渡轮上,或者是奥尔巴尼汽车站的一个卫生间里。
最后,他终于找到了这家收容所,从某种角度来说,这已是他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他在那里住了一段时间,并参加了他们的职业技术培训。
在我弟弟作为一个无家可归者的这整段时间里,我从没邀请他来我家住,甚至没让他进过门。我爱我弟弟。他是个很好心、很有趣的人;他很善良,对老年人很有礼貌。他在年收入连一万美金都不到的时候,每个礼拜还要花上几个小时教人家英语。他是我认识的最聪明的人之一。我每次看到他都会想,有这样一个弟弟是多么幸运。
我还会想,另一个幸运之处是,出于某种我弄不明白的原因,我和他的基因构造天生就略有不同,以至于在同样的压力下,我的生活蒸蒸日上,而他的却惨不忍睹。这是不公平的,但我在很久以前就已决定不再费力去填平我们之间的鸿沟,因为我知道这是一场不可能获胜的战役,其中也包括帮他解决食宿问题。我曾经与他合住过,但最后得出结论我们俩还是分开住更合适。当时,我和女友正考虑把我们毗邻的两间公寓打通后住在一起,我的愧疚感最终没能战胜我想要避免麻烦的决心,我担心接纳了他会对我和女友的关系造成威胁。我曾见识过他给我父母造成的压力。我知道弟弟自己也意识到了他造成的问题,明白那样的话对他也不好。至少我是这样来说服我自己的。
于是,我们平时通过脸谱网和电子邮件互相联系,偶尔在餐馆里一起吃顿午饭。碰面时,他整个人十分消瘦,但却比这几年里任何时候我见到的他都更有活力。我几乎都要认不出他了。他的足迹遍布纽约的每个角落,收容所里的伙食非常糟糕,他的体重减轻了四十磅。他看上去不再忧郁,更像是在加利福尼亚和我一起长大的那个弟弟了,那时的他英俊潇洒,有大把的女朋友,是大家眼里的“金童”。如今的他精力充沛,对环境的适应能力更强,在社会保障局里跟人家斗起嘴来也更老练了。他申请了低收入者的廉租房,并给图书馆寄了一份应聘简历。与此同时,他还在哈莱姆区打零工,负责在地铁口分发免费的报纸。我意识到,抛给他一条救生索,跟他商量让他到我家来住,是一个不明智的想法。不论有多难,他都想向我们证明,更重要的是,向他自己证明,他能够靠自己的力量解决此事。不过,我还是觉得我有义务给他几百块钱,然后他就回到了自己的生活里。
出乎我的预料,他居然成功了。我弟弟走出了收容所。他通过了廉租房申请审核,找到了一间公寓,在一段时间里,实现了他的梦想。他靠自己的力量,在纽约住了下来。一开始,他热爱自己的新生活。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各方面的优惠政策的力度日渐减小,城市的压力——它使人举步维艰,在你想要得到帮助的时候,这种感觉会特别强烈——让他越来越喘不过气来。最后,他搬回了尤蒂卡,后来又去了达拉斯,如今他似乎在那里过着幸福的生活。那里气候宜人,他有了一辆汽车,也有了工作。他过着相对平静的生活,压力不大,尽管如今他已成了一个共和党人,我还是爱他。至今我仍常给他发布在脸谱网上的照片点“赞”。
我没有想好该如何评价他在纽约的这段时间,我想我是永远也无法做出评价的,因为我们的命运有着天壤之别,这让我如何评价呢?太不平等了。
在他来这儿的那段时间里,我每天早晨基本6点不到就起床。当时我在一家英国杂志社工作,必须常常去伦敦长期出差,我有一半时间是住在伦敦的,每个月都要在两地间飞来飞去,有时甚至是每个礼拜,这样的生活打乱了我的生物钟。与此同时,他就住在离我四条马路远的收容所里。在我住在纽约的日子里,有时候我在早晨站在公寓的窗口,喝着第一杯咖啡,看着曙光照耀在街对面停车场的围墙上。肯定有那么几个早晨,他刚好从我的窗口走过,从收容所走向地铁1号线车站,去分发报纸,但他没有按我们的门铃。他曾经抬头望过我的窗口吗?他知道我站在那里为他担心,想着他是否因为和人家打架而又一次被赶出了收容所吗?我有一次问他,为什么离开收容所、住进自己的公寓后也不来我家玩,他回答说:“天太冷了,而且我也不想上班迟到。”

我之所以讲上述这个故事,是因为我觉得有必要改变一下我们讨论“不平等”这一话题的方式。它的存在理由是非常复杂的,就像我弟弟最后住进了收容所的理由一样。不平等并不是一个我们和他们——富人和穷人——之间的问题。我们常常在同一个家庭里看到这种所谓的“区别”,就像我家。我的本能告诉我应该在这里为我的这番话表示一下歉意,要补充说明的一点是,我只是见证了我弟弟无家可归的一段日子,实际上他遭受到的困厄远甚于我的想象,而且我确信比我们俩更遭罪的还大有人在。这一切都是真实的,我想,但它却把我们引入了一条死胡同。给苦难分级是一种错误的做法,就好像我们有办法正确地衡量和评价这些苦难,比如肉体的痛苦、工作上的挫折,或绝望的心理。从某种程度来说,这种做法会引出一个错误的结论:认为有些苦难是可以忽略的,而另一些苦难是不可忽略的。
城市生活是由人群的邻近程度来定义的,当一部分人觉得住在这座城市里日子不好过,就会对城市里的每个人造成压力。比尔·德布拉西奥能当选为市长,部分原因就是他在竞选演讲中将纽约比作“双面之城”,这句话触动了生活在这座城市里的人们的心弦,他称之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核心问题”。纽约人能够感悟他的挫折与激情,也能理解他的“城市可以变得更好”的梦想。也可以说,他们是被他在竞选活动中所表达的一种看法给激发了,那个看法就是由于贫富之间、有产者和无产者之间的差异正变得越来越大,纽约成为了一座不宜居住的城市。这座城市的神话——这是一个特别的地方,一座梦想之城——在现实面前崩塌了:纽约人的收入差距达到了有史以来的最高水平。
我觉得有必要在这里提一下几个数字,以防万一你不怎么关注新闻。几乎有半数纽约人生活在赤贫状态,在过去的二十年里,纽约人的收入差距已经回到了大萧条时期之前的水平。位于收入最顶层的1%的纽约富豪,在1990年到2010年之间,平均收入从四十五万两千美元增加到了七十一万七千美元。与此同时,收入最低的10%的纽约人收入增长幅度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从1990年的八千五百美元仅仅上升到2010年的九千五百美元。这一时期的财富汇聚明显是向富豪们倾斜的。在1990年,最顶层的10%的家庭拥有整个纽约收入的31%;到了2010年,这一数字增加到37%。而且在这一群体中,超级富豪占了很大的比例:2009年,顶层1%的人群拥有的收入超过城市总收入的三分之一。这个信息明确地告诉我们:如今富人越来越富,穷人越来越穷。
中产阶级正在全速消失,尽管他们在美国历史中确实存在过一段时期。
就在德布拉西奥参加竞选前,詹姆斯·苏罗维奇为《纽约客》写了一则有先见之明的专栏,分析了这一切发生的大致原因。这座城市在很大程度上依赖金融业来为它创收——顶层1%的人群所缴纳的所得税令人难以置信地占到了所得税总数的43%——但同时,金融业也是造成收入不均的主要推手。再加上,支撑起中产阶级的那一类工作——比如制造业——已经消亡了。在2001年到2011年间,这座城市已经丧失了51%的制造业工作。苏罗维奇指出,在纽约做生意的成本实在是太高了,以至于工厂、手工作坊、造船厂什么的都搬去了别的地方。
这些数字极端地反映出许多美国城市中正在发生的事情:人们从郊区搬到城市里生活,迅速抬高了城市的房价和房租。纽约以一种夸张的方式见证了这一趋势。不属于顶层10%的纽约人发现自己的收入略有增加,但他们必须面对的是直升机螺旋上升式的房租上涨。2002年到2012年间,房租平均上涨了75%。如今的纽约房租已经是全国平均水平的三倍,其结果就是,几乎三分之一的纽约人的年收入中,有超过一半是用于房租支出的。许多纽约人连租房都租不起,更别提买房了。
居住在纽约市区的人们所付的房租占收入比例最高——比如,在布朗克斯区,一个普通家庭要花上66%的收入去租一套三居室的公寓——因此他们也是最穷的。顺便一提,那里就是我弟弟租下一间公寓住了一段时间的地方。

这样的现状是不可能长久的。而且,纽约的传奇——它的神话和流行文化;我们去那里旅行时留下的印象;描写它的文学作品——和现实之间的强烈落差,也是不会长久的。如果这本文集能有助于填平这座城市里有产者和无产者之间的鸿沟,我将感到十分高兴。通过描摹这道鸿沟,通过思考和想象今日纽约的生活,或许能实现这个目的。人们对纽约有什么感觉,人们在纽约看见了什么,人们讲了什么关于自己的故事,以及,如果可能的话,收入不均是如何改变这座城市的?
在2014年1月,我联系了数十位作家,他们都居住或曾经居住在纽约,又或者觉得那里是他们的精神家园。其中有二十八位回应了我。你正在读的这本文集就是他们参与讨论这个主题的成果,而他们的回应也是各式各样的,其中有回忆录和短篇小说;一篇杂文;几篇报告文学;一篇谈论酒吧侍者的小品文;一篇城市游记;一些住房纠纷的法庭记录;一篇口述历史;一首诗;甚至还包括推特网上的一系列推文,该系列推文从1912年的头条新闻说起,最后发展为像一首交响诗般的内容,它的主题是暴力和城市对维护自身形象的倾向。
这是一座现代的城市,就如你我今日的感受一样,许多遥远往昔的、更为鱼龙混杂的鬼魂和酒吧都已消失。房租更为亲民的时代已经远去——至少目前如此——有些作家写了随廉价房租而去的一些东西,当然,除了可支配收入以外。汉娜·汀婷深情怀念她在下东区租下的第一套廉租房,那里有一个开朗的、有良心的、持枪的莫霍克人在保护着那套房子。要不是廉租房政策,她会遇上他吗?士绅化——常被贴上“纽约的一大祸患”的标贴,但它其实仅仅描述了一种经济情况——是一把双刃剑;大家都在梦想着北迁,哪怕这意味着不得不抛弃一些东西。十五岁的夏沙达雅·杰克逊,作为布鲁克林一家免费学习辅导中心的一名学生,讲述了她家从皇冠高地搬迁至公园坡的经历,以及她的朋友对她在新地方的生活的一些臆测。戴夫·艾格斯介绍了夏沙达雅写的这篇散文,并说明了为什么他的出版社愿意为此类作品提供一个平台。与此同时,莎拉·贾菲进行着从公园坡到皇冠高地的反方向迁移,皇冠高地的租客们为了获得公寓里的基本服务必须奋力搏斗,这刺激她去旁听了一场纽约市住房委员会的听证会,其内容是讨论关于是否提高固定租金公寓房的租赁价的问题。
这本书里的一篇篇文章,一再重复着同一个主题,这个主题直击今日纽约的核心问题,明确地指出了人们所感受到的压力的来源。住房是人们永远都会关注的一个话题。我把这篇引言的草稿给我弟弟看了,然后他写了一篇散文来回应我,这篇文章也收录在本书中,他在文章里描述了他在纽约流落街头的那痛苦的七个月。几乎要无家可归的威胁也能够造成一种压力。珍妮·桑顿在一篇诙谐、感人的回忆录里写到,为了保住一间公寓她不得不坚守一份天天加班的出版工作,这样她的那位无家可归的朋友就也有了一个歇脚的地方。在一篇伤心的口述文章中,DW吉布森再现了一位处理租赁纠纷的辩护律师的真实心声,他的主要工作是为权益受到侵害的租客代言。他有一个和房东发生矛盾的女客户,那位房东打着重新装修的幌子,砸掉了租客们的卫生间,使他们无法继续租住,其目的就是把租客们赶走。“谁会对别人采取如此手段?”她问,“我们都是人啊,这太可怕了。”
阅读这样的文章,你想不对现代城市进行一番思考都很难。也许,如今世界上的任何一座城市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那就是位于社会底层的人们想要获得最基本的生存权利和尊严都要付出艰苦卓绝的努力。迪奈·门格斯图在他的文章里指出,为了让他那个患有自闭症的儿子获得更好的治疗,他想要搬到纽约来;这样的困境对于有些人来说是个难以逾越的坎,对另一些人来说却并不是什么大问题。玛利亚·贝内加斯回忆起她在布鲁克林的一家晚托班的工作经历时,进一步证实了门格斯图的观点,当时正是她的学生们因承受不住压力而纷纷选择自杀的一个时期。父母们被迫做出的牺牲,是别人很难了解的,甚至是超乎人们的想象的,这一点在泰耶·塞拉西的短篇小说里得到了很好的表现,她讲述了发生在一个俄罗斯男子、他的女儿、一个亚洲裔的出租车司机以及一个妓女之间的故事。
然而,这座城市还在继续为人们供应着希望,对所有初来乍到者来说,它还是一座指引方向的灯塔。就像大卫·拜恩所指出的,正是这种源源不断的人口涌入使得这座城市充满了创造力和活力。在一篇介绍一位莫扎特的剧本作者——此人在19世纪初来到纽约——的文章中,埃德蒙·怀特提醒我们,无论在哪个年代迁居到这里都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尤其是当一个人来到美国后想要用外国文化来感化它时。阿基尔·夏尔马一家在20世纪70年代从印度移民来到美国。他在一篇短文里写到,他在印度度过童年时所感受到的那种贫穷程度使他在纽约生活时无论如何也不会觉得穷。这种善于嘲讽的天赋使他在几十年后选择放弃在金融业的一份报酬丰厚的工作,转而成为了一名专职作家,哪怕它并没能完全弥补他在名望和高薪方面的损失。
你无论是往南、往北搬,还是往东、往西搬,抑或只是搬到街对面,都会感受到一种将自己置身于竞争激烈的生活中而形成的紧张感。这种紧张感使得人们在纽约的遭遇显得特别,有时甚至会令人感到危险。
乔纳森·迪描写了在2013年那个漫长冬季的一场暴风雪中,一对富有的夫妇近距离接触到了一个属于“社会中的99%”的普通人,此人是一个想要利用社会顶层1%人群的那种内疚和贪婪的心理来趁机获利的男人。科伦·麦凯恩回忆他走入曼哈顿的地下隧道,只为亲身体验一下他写的故事里发生的情节。他以友好的态度小心翼翼地接近了一个住在隧道里的女人,然而在他想要帮助她的时候,他发现了人们收到礼物时心生谢意与感觉被剥夺了尊严的心情之间的那根极细的线。
这样的遭遇也并非一定要在巨大的阶级差异下才会发生。在蒂亚·奥布莱特的故事里,一个东欧人在一次交通事故中碰到了一个和他有着相同背景的人,从而放松了警惕,结果后悔不迭。迈克尔·萨鲁第一次从伦敦来纽约旅行,通过他拍的照片,我们可以发现这座城市在以一种奇怪的方式传播着流行文化。他去了别人在家里举办的派对,去了博物馆和夜总会,听到了他喜爱的音乐,这让他认识到作为一个黑人如何在这座城市生活,尽管“黑人”在这里的意思和在他的家乡是完全不同的。
每个人都想寻找自己可以归属的群体,这是很自然的一件事,但纽约是一个奇异的大熔炉——那么多人,拥有不同的社会背景,财富分配如此不均——这迫使人们更加努力地去寻找归属,而且必须去一些特别的地方寻找。罗西·沙普描述了一个好的酒吧是如何演变为一个社区的,只要人们尊重在那里工作的服务员,那么可以说那里在经济上是属于公平竞争的。帕特里克·瑞恩回忆起在一家联合律师事务所上夜班的经历,与他打交道的是一些不适应社会的人、演员,和一个勉强维持生计的人。维克托·拉瓦尔在文章里讲述了他在少年时代逃离教堂,长大成人后又皈依宗教的经历,因为他既想拥有信仰,也想找到一个归宿。
这些归属感无论多么强大,都是不牢固的,它们随时都能发生改变,也许是因为你家隔壁的邻居换了人,也许是因为财富的增减,或者是还贷压力越来越大,到了无法忍受的程度。胡诺特·迪亚斯回忆他在工人阶级家庭长大,身边小朋友们的父母都为了各种账单苦斗。他们的命运休戚相关,哪怕有些小伙伴还在他家里偷过东西。贫穷会使人做出卑劣之事。郑元彪回忆起自己因为经济拮据而产生的自暴自弃和孤独感。最后他甚至觉得自己失去了做人的尊严,别人脸上的表情能使他意识到自身条件的改变。
一个穷光蛋住在纽约会觉得生活特别残忍,因为到处都是奢华的东西,就像劳伦斯·约瑟夫在一首描述“911”袭击过去十年后的纽约的诗中告诉我们的一样。“911事件”是对财富不均采取的暴力行为,它产生了全球性的影响。事情永远都是这样的,就像特居·科尔在“小死亡”这一系列推特文字中曝光出来的,这些文字带我们回看1912年的头条新闻。这样的事足够使我们就像乔纳森·萨弗兰·弗尔所想象的那样,祈望在靠近曼哈顿湾的地方有个第六区,那里有足够的空间让我们安身立命,也让这座城市能够自由呼吸。

这是一个令人吃惊的设想——把城市想象得比实际更大,为了能让你在那里过上悠然自得的日子。为了实现它,必须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呢?
政客们为了解决税收、最低工资、廉租房、社会保障的分配等问题苦苦搏斗,作家们也可以加入这一场战斗,用他们的想象力和经验来提出更有远见的主张,为从本质上努力改良城市助一臂之力。就像加尼特·卡多根在他的文章里指出的,城市和城市之间的差别其实并不大,如果一座城市不再美好,那么所有人的生活都会陷入困窘。
本书可以说是梦想着城市能变得更为宽容的人们的大本营。如果能把书籍比喻为庙堂,那我希望这座庙堂能有一个更为宽广的屋顶,为人们遮风挡雨,给人们带来慰藉。就像把纽约比喻为“双面之城”般令人耳目一新,纽约把许多城市集于一身的这个事实,在本书里也有明确的反映。彼此间的不平等使得怀着共同理想的人们很难生活在一起。
我喜欢这样想,正是这样的斗争塑造了我们——现实并非命中注定,我们可以做得更好,城市也能够变得更好。在本书里,我们的二十八位作者告诉了我们,正在这座城市里挣扎着的人们的现实感受。
(节选自《双城故事》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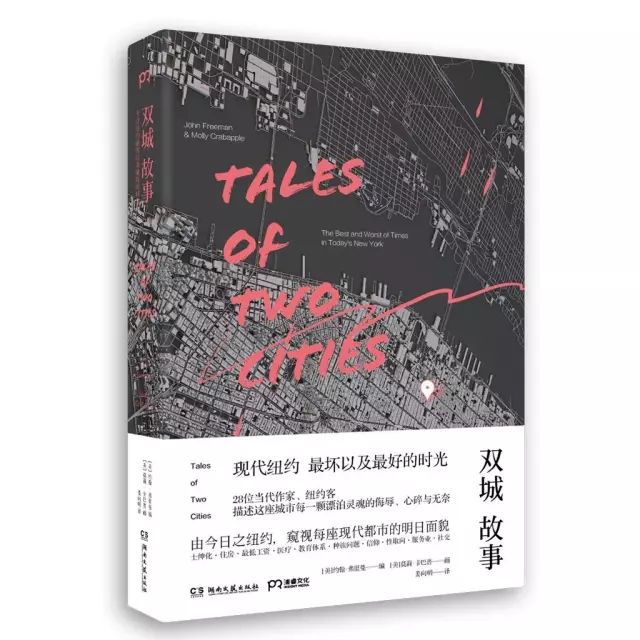
《双城故事》
[美]约翰•弗里曼 编/姜向明 译
浦睿文化 出品/湖南文艺出版社
欢迎来到纽约,这座充满诱惑又极度分裂的“双面之城”:它有令人眼花缭乱的百老汇、高雅的林肯中心、喧闹沸腾的第五大道,也有飞奔过地铁轨道的老鼠、脏乱的后街、随处可见的流浪汉。
金字塔顶端1%的人拥有超过城市总收入1/3的财富,与此同时,上千名儿童仍在街头流浪:对于生活在富裕与贫穷之间悬崖般断层上的纽约市民来说,到底是什么感受?
在这里,你能读到每夜在地道里入眠的流浪汉的命运与传说;士绅化给布鲁克林某个街区带来的沉重压力;被极度边缘化的事务所夜班助理们自娱自乐上演的闹剧;忍无可忍的房客为维护自身权益诉诸法庭的审判;亿万富翁被困在暴风雪而造成的愤怒一幕;人们走过装饰奢华的宠物店与瑜伽教室,它们讽刺般地开在廉价发廊以及戒瘾诊所旁边。
这本绝妙的、动人的纽约故事集,正是向这座危机中的城市发出的警铃,令人反思大都市的发展前景及未来。

长按图片 识别二维码
购买《双城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