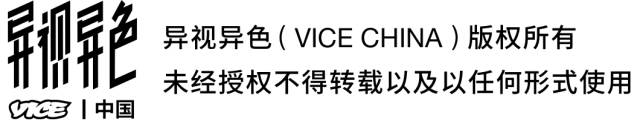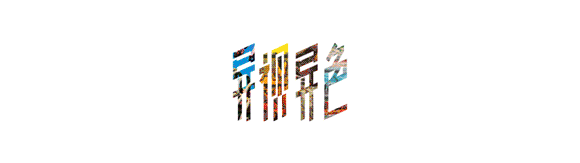

金子
我和一个英国护士根据 GPS,在杂草丛生,沙化严重的土路上开了半个小时。手机信号从塞尔维亚变成了匈牙利,我们认为铁定迷路了。这时,左手边突然出现两间破旧不堪,塌了半面墙的民房,外面是无数的生活垃圾。我们立刻确定,没迷路,这儿就是难民聚点。果然,里面大概有四五十个难民居住。
这些人是非法移民,试图从巴尔干之路进入欧盟。欧洲的难民签证分为战争难民和经济难民,战争难民 (比如叙利亚) 申请比较容易,而经济难民就会长达4、5年,甚至10年。这些人就是战争难民。我在塞尔维亚做过一段时间的难民医疗志愿者,和另外一个医疗组织轮流给难民看病,了解给药情况,是否需要随访,有没有可疑传染病。最开始接到 offer 的志愿者手册,上面写着 “help refugees who living rough”,我还以为这个 rough 指的是难民营脏乱差。来了以后才发现,rough 是指睡在玉米地和森林。
这四五十个难民里,有几个皮肤脓肿非常严重,需要就医。一个给非法移民派发食物的合作组织便给我下了指示帮助他们。其实这次有车开都算好的了,夏天的时候,我们经常要在40度的高温下暴走,有时还需要翻墙。其次,非法移民的聚点很偏僻,靠近边境线,却又尽可能远离审查,所以非常难找。
他们住在破旧的聚点而非官方难民营,是因为不想留在塞尔维亚。根据政策,在哪个国家取了指纹,就必须在哪个国家申请避难签证。要想进入官方难民营,自然只能申请这个国家的难民签证。而塞尔维亚是这条路的必经之地,非法移民们要想进入欧洲,就只能躲在靠近匈牙利或克罗地亚边境的树林、玉米地里露天睡觉,或者在人贩子的帮助下找个废弃民房席地,伺机越境。

本文所有图片由作者提供
有几个阿富汗的难民跟我说他们交了人贩子5000欧元,从土耳其坐船偷渡到希腊的莱斯沃斯,登陆的时候被警察取了指纹了。但他们嫌希腊穷,想去德国。就又交了人贩子一大笔钱,坐船去了雅典。之所以不选飞机,也是多亏了前人。申根国本来不查护照,但现在因为难民危机和恐怖袭击,有些地方查的很严,比如莱斯沃斯到雅典这条线。
到了雅典后,这几个阿富汗的小伙儿迈开大步一路走,被保加利亚扔回希腊好几次,还吃了不少打,现在总算到了塞尔维亚。到塞尔维亚后,他们也注册了首都贝尔格莱德的政府难民营,在里面歇了几天。然后坐着大巴(塞尔维亚的大巴基本不查护照)到了匈牙利边境。幸运的话,只需要徒步一晚上就能越境了。
我问他们,既然希腊都取了指纹,还去德国干嘛?去了不是也要被扔回希腊吗?他们耸耸肩,“到时候看呗。”

“感谢所有前来帮助的志愿者”
据一位难民的法律援助人士,在奥地利,如果非法移民在其他欧盟成员国取了指纹,但后来离开了欧盟区三个月以上,在律师的帮助下还是有希望申请到奥地利避难签证。其中最大的挑战是如何证明 “离开了欧盟区三个月以上”。这些难民都是偷渡越境的,自然没有边检人员在他们的护照上盖出入境章。为了有效凭证,一些人会把塞尔维亚的难民营注册手续作为证据。即使有风险被迫申请到塞尔维亚避难签证,也阻挡不了大家前往欧盟区的决心。
其实,塞尔维亚政府也不想接收难民。就算表面上接受正经注册的官方难民,还是摆出极大的力不从心。难民营里腐败横行,即使砸锅卖铁稍微有点儿积蓄的难民,也都舍不得自己购买吃喝,非要等着非政府组织发放。省下的钱要么给人贩子要么贿赂警察,剩下的就给自己买烟买酒。
当然, 这些是已经达到富裕阶段的叙利亚难民,不仅有钱有教养,日子也过得好好的,只是因为打仗,不得不走。他们塞钱给人贩子后,通常很快就能到自己想到的国家。避难签证申请也很快,拿身份不是难事。塞尔维亚根本见不到他们,只有生活没什么希望,受过的教育也不多,不知道从哪儿得到的信息,认定了走上这段漫长的征程的穷人。有时候他们掏给人贩子的钱也打了水漂,只能一边被警察打、被狗追,一边尝试 “游戏”。
难民们都管尝试非法越境行为叫 “游戏”。有时候我叫病人过两天再找我们随访,不少人都会说那时候不知道还在不在,因为晚上要去玩 “游戏”。幸运的话就越境到匈牙利甚至奥地利,没过关的也不一定就回这片林子,没准儿添了新伤,没准儿被抓,都有可能。
有一次有个头皮外伤的病人消失了好长时间,突然又出现了,伤口都化脓感染了。说是成功越境到克罗地亚,马上进入意大利了,却被克罗地亚警察抓到后送了回来,这么多路全白走了。但这其实并不算坏运气, 有天晚上,几个难民尝试扒火车去克罗地亚,结果一个触电身亡,一个休克,一个左眼失明。休克的病人烧伤的体表面积大概有30%,超过一半为深II度及以上,已经被几个西班牙志愿者转运到100公里以外的重症监护室抢救。
这种故事挺多的,每个人的旅程都能拍个电影。虽然每个月都有死讯,但也不全是因为游戏。难民们的精神状态非常令人担忧。

“边境放行吧”
我接触到的难民清一色为男性,大部分为20到30岁之间,有的十三四岁就踏上了征程。虽然每次去给他们看病,都笑容满面,非常友好,但是他们对烟草的依赖程度几乎是100%,酒精依赖(不是单纯饮酒)则有大概50%,自残自伤大概30%。这也意味着,每次出诊,3分之1的病人主要就诊目的是为了寻求止痛药。更令人担忧的是,难民中寻求可卡因的并不在少数。对这点我并不意外,但可卡因并不便宜,我并不认为大部分的难民可以负担的起。那他们的可卡因是哪里来的呢?
一部分的难民是因为人贩子画的饼,也有一些是因为信息的封闭,在出发之前并不了解自己将要面对的是什么。但我相信,这些人为了虚无缥缈的希望,就冒着生命危险倾家荡产,踏上遥遥无期的旅程,一定有必须离开的理由。只是这些青少年,因为旅程永久地丧失了接受教育的时机,并承受着巨大的生存压力。

唯一的意外是,我竟然还碰到了一名中国难民,我叫他王二。王二既不是经济难民,也不是战争难民,完全没有任何希望得到难民身份。但他觉得自己没有任何技能,在深圳随便找个工作只能赚3000多人民币,生活没有希望。自己长这么大了还没出过国,想去国外看看。今年三月申请美国签证被拒后又想去法国,但是听朋友说欧洲的签证更难申请,在报纸上看到了一些关于欧洲难民的报道,就萌生了跟着难民混进法国的想法。
王二先申请了个土耳其的电子签,飞到土耳其转了一圈,然后从土耳其又飞到免签的塞尔维亚,坐大巴来了克罗地亚边境,混进了难民的聚点。跟难民们一起尝试过两次游戏,都未成功。幸运的是王二还没有受伤,就是鞋坏了。
王二说没想到游戏这么难,而且最近老下雨,越境的路非常不好走,想等过几天晴天后再试试。
我问他知不知道中国人是没有希望得到难民签证的,王二说他知道,但他听朋友说在国外打黑工也能过得不错。虽然法语、英语都不会讲,但他觉得应该哪儿都能碰上会说中文的。
“你看,我现在不就碰上你了吗?可以说中文”。 王二很高兴。
也许王二和其他难民最终的结局完全不同,但相同的是,每个人都想要追求更好的生活。但相比于学会一门技术,难道这个艰辛的游戏,会更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