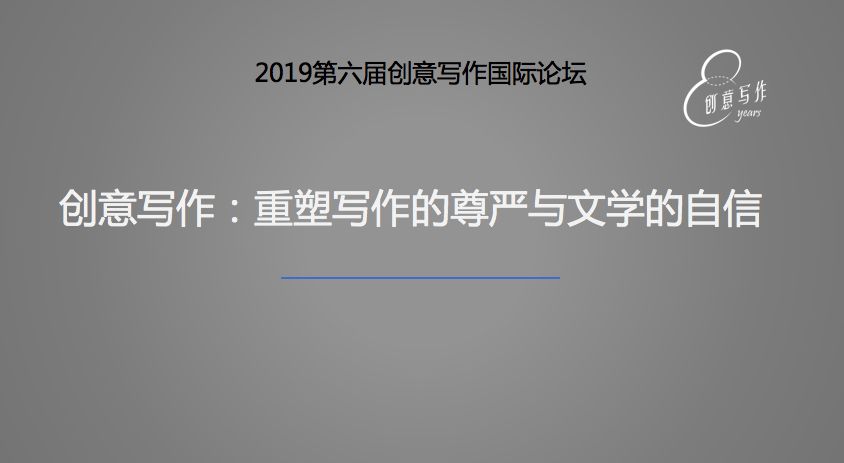
“小说的核心是发现,发现靠的是什么?靠的是想象。想象靠的是什么?靠的是经验。”——宁肯

宁肯,1959年生于北京,小说家,散文家,1982年在上海《萌芽》发表诗歌处女作《积雪之梦》。曾旅居西藏,创作长篇系列散文《沉默的彼岸》,系中国“新散文”运动代表作品之一。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致力长篇小说创作,现已出版长篇小说《天·藏》《蒙面之城》《三个三重奏》《沉默之门》《环形山》。另有散文集《说吧,西藏》《北京:城与年》《我的二十世纪》。曾获老舍文学奖长篇小说奖,首届施耐庵文学奖,鲁迅文学奖。作品翻译成英语、法语、捷克语,意大利语。
宁肯:
个人经验的想象与发现
2019第六届创意写作国际论坛发言
01 文学的“发现”与现实的“发现”
当我们谈起小说时,一定要把中、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分开,不能笼统的讲小说如何如何。因为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太不一样,它有自己的一套理论,一套工艺,一套认识,一套独特的操作过程。所以当我们谈论短篇小说经验时,它不一定适合长篇小说。
所以我今天谈论的一切都只在短篇小说范畴中。
我讲的题目和我最近的写作非常接近——个人经验的想象与发现。
这里面有非常明显的三个关键词:
经验、想象、发现
,这三个词正是短篇小说的核心。
在我曾经的写作中确实在这三个词上面碰到了问题,却来不及去系统地总结。恰好昨天在来的火车上,我与一位《收获》杂志的年轻编辑聊得非常投机。
我在给他发的一段微信里是这么说的,“小说的核心是发现,发现靠的什么?靠的是想象。想象靠的什么?靠的是经验。”
“发现”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就是你究竟要表达的是什么,你发现了什么。这里的“发现”和创意写作中的“创意”两个字有一点相似,但是它的路径却又不尽相同。创意具有很强的主体性,人们根据自己的经验去主动寻找一个创意、一个好的想法、一个灵感,但是短篇小说里面的“发现”有非常大的区别。
对于短篇小说来讲,经验到发现不是一个直通车,很多时候发现具有隐蔽性,这也是写作小说的一个特别大的难题。
我们生活中有怎样的经验就想到要表达怎样的东西,于是,我们就误以为自己找到了创意,再急忙忙地去加工、组织,表达那些经验中已成型的东西。然而,这样写作的结果大多数是失败的。
有时候我的写作非常容易陷入苦恼,经过虚构、加工却没有超出经验的范畴,然而,好小说要突破经验的禁锢。
如何突破呢?这时候就需要想象。
面对经验,我们能够升华出什么样的东西来,想象出什么样的故事来,这个阶段往往是最考验一位作家的能力。
所以小说创作需要经过想象,想象之后才能发现。如何通过想象就达到这种发现?这里面确实需要灵感,需要非常复杂的个人经验,包括技巧、阅读等等,也就是我们统称的文学修养。

2019年第六届创意写作国际论坛现场
02
从个人经验到小说创作
下面我想结合我的创作经历来谈论——经验如何唤醒自我表达,自我的表达又如何转化成小说的表达。
虽然我一直在从事长篇小说创作,但我认为一个作家不写短篇小说是非常大的遗憾,是不能充分体会到小说乐趣的,于是,我开始写短篇小说,可是,我已经60岁了,到这个年龄该如何重新开始写短篇小说?是零敲碎打还是来了灵感再写?
所以,我给自己做了一个规划,先把自己直接的经验记录下来,写了一本散文,把我童年的往事,我生活的北京胡同,我上学的经历,把我关于70年代北京胡同的记忆一篇篇的写出来,后来起了一个名字叫《北京:城与年》(还意外得了鲁迅杂文奖)。

2018年8月11日,
《北京:
城与年》获第七届鲁迅文学奖散文杂文奖
我的目的是先把这个经验记录下来,然后在这个基础之上判断哪些经验可以转化为小说。
其实,在做札记的过程中,一些地方就已经让我有了写短篇小说的冲动。
我举一个例子,比如 “九一三事件”对我的震动非常大。那时我正在上小学五、六年级,事发当天我们谁都不知道,不像现在,发生一个事情全世界都知道。那个事情是盖着的,直到“十·一”前后的游行,大家才知道出事了。
这个例子里的直接经验是什么?是震撼,是分裂,这些主题就足够我进行一个文学的表达,但是,从技巧上来讲我发现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实际在9月13号当天什么都没有发生。真正的9月13号是大家得到消息的那一天才叫9月13号。所以,我就写9月13号那天去上学的两个学生,那一天干了什么,经历了哪些东西,之后再跳到真正的9月13号,
将一个什么都没有发生的日子和另外一个重大的日子结合在一起。
两个平行的时间进行对比,以此来表达这种震撼。
起初创作这篇小说时有三个要素:
第一,写了一个白痴学生,矮矮的个子、穿着大背心、背着大书包。主角是白痴,叙述者是伙伴。
第二,政治事件,人们接到消息的震撼过程就像一个葬礼的过程。一个时代的葬礼。
第三,光有一个政治事件是不够的,因为我想表达这个白痴孩子被震撼到疯狂、崩溃。他本来精神就有问题,结果听完这个事情就裸奔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