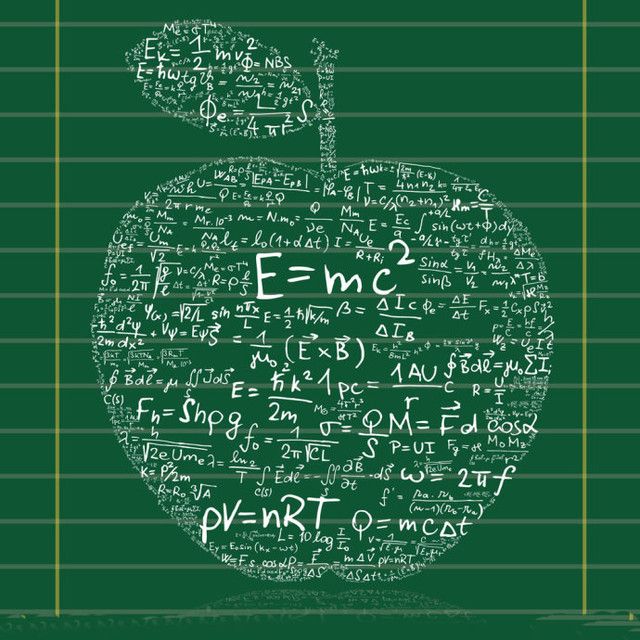两位同时代的数学大师
来源: 蔡天新 哆嗒数学网
编辑:Gemini
太湖的西北和东南
在十九世纪后期和二十世纪初期,中国东部太湖流域人才辈出,诞生了许多位大师级的人物,犹如两宋时期的鄱阳湖流域。太湖的北岸和南岸分别是江苏的苏、锡、常和浙江的杭、嘉、湖这六座城市,可谓是中国百姓口中传诵的“鱼米之乡”,也是文人墨客诗词里所赞美的“江南”。
一九一○年十一月十二日,数学奇才华罗庚出生在常州市金坛县的一个小商人家庭。他的父亲出身学徒,经过多年艰苦努力,拥有了三家规模不等的商店,一度担任县商业丝会的董事。不料后来一场大火把大店烧个精光,接着中店也倒闭了。等到罗庚出世时,华家只剩下一爿经营棉花的小店了。
金坛在太湖西北方向,而在太湖东南方向,一个叫秀水(嘉兴)的县城里,在罗庚出世不到一年,即一九一一年十月二十八日,也诞生了一位非凡的天才,日后注定要成为罗庚的室友、同行和竞争对手。此人姓陈,名省身。与罗庚的家庭背景不同,省身的父亲是个读书人,中过秀才。有了儿子以后,做父亲的考入了杭州的法政学校。毕业后进入司法界工作,很少回家。省身跟着疼爱他的祖母和小姑识字读文。有一次父亲回嘉兴过年,教会他阿拉伯数字和四则运算,并留下了一套传教士编的《笔算数学》,没想到小小年纪的省身竟然能做出书中的大部分习题,并由此对数学产生了兴趣。 由于家庭的溺爱,省身只读了一天小学。进入秀州中学高小部后,除了能做相当复杂的数学题以外,省身也非常喜欢国文,课余还能读些《封神榜》等闲书,文学气质获得熏陶,他甚至在校刊上发表了两首自由体的诗作。一九二二年,他的父亲转任天津法院,全家从此离开了嘉兴。
就在陈家北上的那年,罗庚进入了金坛初级中学。他在小学时因为淘气成绩有点糟糕,只拿到一张修业证书。不过,从第二年开始,数学老师便对罗庚另眼相看了。三年级时,罗庚已着力简化书中的习题解法,他在国文方面同样有所长进,并对古体诗歌感兴趣。初中毕业,罗庚考进了教育家黄炎培在上海办的中华职业学校商科,相当于今天的初中中专,学费全免,只需付食宿和杂费。
那一年是一九二六年,小一岁的省身在天津从詹天佑任董事的扶轮中学(今天津铁路一中)毕业,他跳过大学预科,直接进入南开大学。而罗庚虽在上海市珠算比赛中获得第一名,却由于家庭经济困难辍学,回家帮父亲站柜台。十六岁那年,他与同城的一位吴姓姑娘成了亲,而省身完婚已二十八岁,早获得洋博士并荣任大学教授了。值得一提的是,年轻时的罗庚相貌周正、身材魁梧。婚后第二年,妻子生下一个女儿,可是,罗庚依然喜欢看数学书和演算习题,有时看书入迷忘了接待顾客,老父知道后不由得怒火中烧。
又过了一年,以前赏识罗庚的初中老师王维克从巴黎大学留学归来,担任金坛中学校长,他看到罗庚家庭困难同时又好学,便聘请他担任学校会计。这位王校长虽然学理,曾听过居里夫人的课,却也是个有成就的翻译家,是意大利诗人但丁的《神曲》和印度史诗《沙恭达罗》的第一个中文译者。那时的中学老师不仅学识高,且对学生有一颗真诚的爱心。此前的校长韩大受也出版过《训诂学概论》等多部著作,在做人学习等方面循循教导学生。现在罗庚被认为是自学成才的典范,其实他在初中阶段就已广受教益,这一点是如今的教育制度难望其项背的。
可是,正当王校长准备提拔罗庚,让他担任补习班的数学教员时,华家的不幸却接踵而至。先是母亲得了子宫癌去世,接着罗庚患上伤寒症,卧病在床半年,后来虽然被救活,却落下了残疾,走路需要左腿先画个圆圈,右腿才能跟上,被人戏称为“圆规与直尺”。可是,也正因为腿的残疾,更坚定了罗庚攻读数学的决心。否则的话,聪明的罗庚对自己的人生之路也许另做抉择。那年十二月,上海的《科学》杂志以读者来信的方式发表了罗庚的论文《苏家驹之代数的五次方程式解法不能成立之理由》,从此改变了他的命运。
说到五次方程的一般解,自从十六世纪的几个意大利人解出了三、四次方程以后,便成为数学家最渴望解破的难题。直到一八二四年,挪威青年阿贝尔证明此类一般解并不存在。可是到了一九二九年,上海的《学艺》杂志却刊登了一篇论文《代数的五次方程式之解法》。行家一看就知道不对,但却没人去挑毛病。年轻无名的罗庚却认真地拜读并琢磨,终于发现有一个十二阶的行列式计算有误,遂撰文陈述理由并否定了“苏文”的结果,他也因此一举成名。清华大学算学系主任熊庆来读到罗庚的文章,和同事们暗自高兴,经过打探,找到罗庚并向他发出了邀请。
那年罗庚年方二十,而十九岁的省身即将从南开大学毕业。入读南开之前,省身便因为该校的同乡老师、数学史家钱宝琮的缘故,与数学更亲近了。钱宝琮和省身父亲是中学同学,后来留学英国。那时的南开理学院新生不分系,有一次上化学课,老师要求吹玻璃管,省身面对玻璃片和火焰一筹莫展,后来虽勉强吹成,但他却嫌太热用冷水去冲,结果玻璃管当即粉碎。这件事对省身触动很大,他发现自己动手能力差,于是决心放弃理化献身数学。很快,省身得到了系主任、哈佛大学博士姜立夫先生的赏识,对几何学萌生了兴趣。毕业前夕,他考上清华大学,成为中国第一个研究生。
从清华园到欧罗巴
旧中国的科学底子薄弱,尤其在一九三○年以前,当时只要是在外国取得博士学位回来的人,统统被聘为教授。这些教授待遇优厚、衣食无忧,加上教学繁忙、资料匮乏,缺少良好的环境和氛围,基本上放弃了学术研究。以姜立夫为例,在南开数学系最初的四年里,只有他一个教师,什么课都得他亲自讲授。一九四九年以后,他又在广州创建了岭南大学数学系(后并入中山大学)。而清华大学算学系主任熊庆来当时只有法国的硕士学位,却是东南大学(后改名中央大学)、清华大学两所大学数学系的创建人和首任主任。
清华大学毕竟是“皇家学院”,美国退回的“庚子赔款”除了资助姜立夫这样的青年才俊留学以外,还用以创办和扶持清华学校。清华学校请来了美国康奈尔大学数学硕士郑桐荪(后成为陈省身的岳父),由他担任大学部算学系主任。一九二八年,正是在郑桐荪的举荐下,熊庆来出任更名为清华大学的算学系主任,不久又有芝加哥大学博士孙光远和杨武之(杨振宁的父亲)加盟。可是这四位教授中,只有孙光远仍在继续做研究,他的主攻方向是微分几何。孙光远是浙江杭州人,与省身算是半个同乡。省身进入清华大学以后,成为孙光远的研究生。那年清华算学系共录取两位研究生,另一位吴大任因为家庭原因推迟入学,系里决定让省身先做一年的助教。
次年八月,正当省身开始读研究生之际,罗庚来到了清华大学。作为一名助理员,罗庚的办公室就在系主任熊庆来的办公室外面,无论谁来找主任,都会见到他。罗庚性格外向,说话风趣,很快与大家熟悉了,包括省身。那时罗庚的薪水只有助教的一半,略高于工友,与省身的研究生津贴相差不多,罗庚的家属仍留在老家金坛,那年夫人又生了个儿子。因为经济困难,清华五年他只有在寒暑假才回老家。王元在《华罗庚》里,记载了恩师晚年的一次回忆:“每当我寒暑假回家乡探亲时,熊庆来先生总是依依不舍,他生怕我嫌钱少不肯再回来了。他哪里知道,清华给我的钱比金坛中学给我的钱优厚多了,清华对我来说是求之不得的。”
虽然罗庚来清华那年,借着成名作的光在《科学》上一气发表了四篇论文,但那些工作都是原来在家乡完成的,属于低水平的初等数学。到清华以后,他如饥似渴地听课和钻研高等数学,接下来的两年里没有发表论文。省身后来写道:“这个时期是罗庚自学最主要和最成功的一段。在那几年里,他把大学的功课学完了,并开始做文章。”从一九三四年开始,罗庚的数学潜能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他每年都发表六到八篇论文,其中大多是在国外刊物,包括德国的权威杂志《数学年刊》,一时声誉鹊起。这些论文大多是数论方面(杨武之是他的引路人),也有的是代数和分析,显示了他多方面的兴趣和才华。他甚至在自学英语上也有一套奇特的方法。
正当罗庚开始大显身手的时候,自小目标远大的省身已通过硕士学位论文答辩,准备出国留学了。省身将赴汉堡大学,随布拉施克教授研究几何。说到这位德国导师,省身与他的结识要归功于同城的北京大学。
就在财源充足的清华大学修筑大楼、广招贤能的时候,历史悠久的北京大学却人心涣散、纪律松弛,经常拖欠教授薪水。待到文学院院长胡适出任掌管“庚子赔款”退款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董事之后,力促其通过了资助北大的“特款办法”,情况才有了改变。北大研究院也在清华研究院成立两年之后挂牌,同时开始邀请外国专家来校讲学。布拉施克便是最早来到北大的数学家之一,他的系列讲座题目是“微分几何的拓扑问题”。每次听课省身都没有落下,得以结缘这位数学大家。
易北河与剑河之水
晚年的陈老谈到自己成功的秘诀时,认为一半是天分,一半是运气。可以说,省身最初的运气便是在北大结识布拉施克教授。他抵达汉堡是在一九三四年秋天,此时希特勒已经上台,所谓的“公务员法”也已颁布,规定犹太人不能当大学教授,哥廷根这类名校首当其冲受到冲击。而汉堡这所新大学因为没有犹太教授相安无事,可以继续做学问。等到一九三七年,“新公务员法”颁布,连犹太人的配偶也不能当教授时,省身早已获得博士学位,被导师推荐到巴黎跟大数学家嘉当深造去了。
省身在汉堡期间,并没有埋头写论文,而是把重点放在学习和掌握最前沿的几何学方法上,同时与一些大家建立起比较广泛的联系。除了布拉施克和嘉当以外,省身还与法国布尔巴基学派的代表人物韦伊、美国普林斯顿的维布伦等有了交流。这就像长距离的跑步或划船比赛,必须紧紧跟上第一梯队,才能伺机突破并超越。
相比之下,自小苦出身、又缺乏家长和名师指点的罗庚更多地依靠个人奋斗和自学,因此也特别刻苦。被清华破格聘为职位较低的助理员后,特别珍惜也更加努力地钻研学问,他在短时期里便在国内外发表了数量可观的研究论文,这与“名门出身”的省身风格不同。不过,在布拉施克访问北大三年之后,清华也邀请到了两位级别更高的大数学家,那便是法国数学家哈达玛和美国数学家维纳,他们在北京停留的时间也更久。
哈达玛在数学的许多领域都有开创性的工作,其中在解析数论方面尤为出色,他率先证明了素数定理,那是“数学王子”高斯梦寐以求的结果。那项工作是在十九世纪末完成的,即使半个多世纪以后,因为这个定理的一个初等证明,又颁发了一项菲尔兹奖和一项沃尔夫奖。哈达玛来中国时年事已高,不在前沿做学问了,而维纳那会儿年富力强。作为控制论的发明人,维纳为数学史书写了光辉的一页。维纳对罗庚极为欣赏,推荐他去自己年轻时求学的剑桥大学,跟随当年的老师哈代。不用说,罗庚留英的奖学金也是来自那笔“庚子赔款”。
罗庚沿着西伯利亚铁路,经莫斯科来到柏林,省身从汉堡赶来相聚。那会儿正逢夏季奥运会在柏林举行,两人兴致盎然地一起观看比赛。当年秋天,省身离开汉堡转道伦敦去巴黎时,也曾特意到剑桥看望罗庚。当然,从省身轻松面对学问这一点来看,他到柏林和剑桥并非单纯去见罗庚,而与他比较贪玩也有关系。这里需要提及,据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的档案记载,在罗庚到剑桥访学之前,曾两度获得该基金会到汉堡大学研修的资助,但他都没有成行。倘若那时罗庚来汉堡,可能会随赫克或阿廷研究前途无量的代数数论,那样的话,后来中国数学的面貌将会有较大的不同。
罗庚抵达剑桥时,哈代正在美国讲学,行前他看过维纳的推荐信和罗庚的论文,留下一封短函。哈代在信中告诉罗庚,他可以在两年内拿到博士学位。可是,罗庚为了节省学费和时间,放弃了学位攻读,他专心于听课、参加讨论班和做论文。一年以后,哈代旅行归来,似乎也没有给罗庚以指导。可以说,罗庚又一次依靠自学。他在剑桥的两年时间里,写出了十多篇堪称一流的论文,大大超出了以前的水准。用王元的话讲就是,“已经脱胎换骨,成为一个成熟的数学家了”。当然,这与剑桥拥有非常强的解析数论研究团队不无关系,他们与当时顶尖的数论学家、苏联的维诺格拉朵夫联系密切。这是罗庚的另一大收获,他与苏联数学家建立了学术联系,这对他以后的研究尤其重要。
两年以后,罗庚启程回国,当他向哈代辞行时,大师问他在剑桥都做了哪些工作,罗庚一一道来。惊讶之余,哈代告诉罗庚自己正在写一本书,会把他的一些结果收录其中。这本书便是剑桥出版社出版的《数论导引》(一九三八),罗庚的那些结果可能是近代中国数学家最早被外国名家引用的成果。罗庚在剑桥取得的主要成就表现在,完整三角和的估计、圆法和华林问题、布劳赫-塔内问题以及哥德巴赫猜想等方面。与此同时,罗庚有了后来成为他代表作的《堆垒素数论》的腹稿。
从昆明到普林斯顿
一九三七年,即罗庚从英国回国的前一年,省身便准备从巴黎启程了,那时他已经在欧洲居留了三年,母校清华大学聘他为教授。没想到就在启程前三天,爆发了“七七事变”,日本人占领了北京城。虽然前途未卜,可是省身却不顾危险依旧踏上回程。当邮轮抵达长江口时,却发现岸上火光冲天,原来上海刚被日本人占领。不得已,邮轮掉头向南去了香港。到达香港后又滞留了一个多月,方才得知清华与北京、南开大学已搬到湖南,组成长沙联合大学。省身赶在开学前抵达。战火迅速向南蔓延,省身在长沙只待了两个多月,便又随学校南迁至昆明。
就在省身抵达昆明的那一年,罗庚从英国回来了,他也被破格聘请为西南联大的教授,两人当时年纪只有二十七八岁。在罗庚辗转从香港、西贡和河内抵达之前,他的夫人和孩子们已先期来到,一家团聚之后住在郊区,以避开日军飞机的轰炸。“联大”也坐落在郊区,但离华家比较远,罗庚每次坐着颠簸的牛车去上课。后来,在有课的时候罗庚就住到学校里,和另外两个单身汉同居一室,其中就有省身。
在西南联大的那些年里,罗庚和省身的数学研究都取得了新的突破。两人有一年时间住在一个房间里,每人一张床、一张书桌和一把椅子。那时“联大”的教授尽管生活清贫、工作条件艰苦,教书和研究热情却异常高涨,还有许多出类拔萃的学生,如杨振宁、邓稼先、李政道等。一段时间里,罗庚和省身一早起来有说有笑的,然后便沉浸在各自的数学空间里,直到深夜。虽然两人从未合作写过论文,但他们在“联大”联合举办过“李群”讨论班,这在当时全世界都十分先进。
在“联大”期间,罗庚在数论方面的研究主要与获得牛津大学博士并在普林斯顿做过博士后的闵嗣鹤合作,同时努力完成自己的第一本专著《堆垒素数论》。其时罗庚已是这个领域的领袖级人物了,但他并不满足于此,而是另辟蹊径,在自守函数和矩阵几何领域均做出了出色的工作,前者至今仍是研究热点,后者与省身老师嘉当的工作有关。罗庚在一篇论文的尾末还提到省身,感谢他提供嘉当论文的抽印本。此外,他还研究了代数学中的若干问题,如有限群、辛群的自同构性质,后者在不久的将来引导他深入研究典型群论。
与此同时,省身的学术研究也取得了新的进展。回国第二年,他便在美国的《数学年刊》上发表了一篇论文,这家由普林斯顿大学与高等研究院联合主办的刊物今天仍是全世界数学领域里的重镇。几年以后,省身又两度在《数学年刊》上露面,他在克莱因空间的积分几何等领域做出了出色的工作。法国数学家韦伊在《数学评论》上撰写长文,予以高度评价,认为此文超越了布拉施克学派原有的成就。这些工作为省身后来进入并立足美国铺平了道路,也正是在那段时间,他对高斯-博内公式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一九四三年夏天,省身应邀赴美访学,在普林斯顿逗留了两年半,完成了一生中最出色的工作,包括给出高斯-博内公式的内蕴证明,这标志着整体微分几何新时代的来临。这项工作是在抵达美国最初三个月内完成的,足见他在昆明时已做了充分准备。两年后,在接获母亲病危消息回国前夕,省身又提出了现在被称作“陈示性类”的不变量理论。那时抗战已取得胜利,罗庚在国内以其个人的成就和交游能力,可谓如鱼得水。他先是应邀访苏,接着又被选入赴美考察团。一九四六年春天,正当罗庚准备出发去美国时,省身回国了,两人在上海得以晤面。按照省身的回忆,“他(罗庚)负有使命,但我们仍谈了不少数学,我们的数学兴趣逐渐接近”。
天各一方瑜亮无争
华罗庚访苏是当年中国知识界无人不晓的事件,因为他撰写的三万字日记在上海《时与文》周刊上连载了四期,这家杂志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十分红火。在苏联,罗庚见到神交已久的维诺格拉朵夫。几年前,罗庚和省身早年的得意门生、数学家徐利治谈到两位恩师时认为,他们都是入世的。也就是说,他们都对政治比较感兴趣。相比之下,徐利治认为西南联大“三杰”之一的许宝騄是出世的。
许宝騄与罗庚同年,祖籍杭州,出生在北京,祖父曾任苏州知府,父亲是两浙盐运使,姐夫俞平伯是著名的红学家。从清华毕业以后,宝留学伦敦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回国任西南联大教授。他被公认为是在数理统计和概率论方面第一个获得国际声望的中国数学家,可惜在“文革”期间英年早逝。
罗庚在普林斯顿期间,在代数学尤其是典型群论和体(无限维代数)方面做了很多出色的工作,特别是得到了被阿廷称为“华氏定理”的半自同构方面的重要结果,并给出了被后人称为“嘉当—布劳韦尔—华定理”的一个直接简单的证明。一位美国同行说过:“华罗庚有抓住别人最好的工作的不可思议的能力,并能准确地指出这些结果可以改进的地方。”一九四八年,罗庚被美国伊利诺伊大学聘为教授。
罗庚把妻子和三个儿子接到美国,但已上大学且政治上要求进步的大女儿留在中国,出生不久的小女儿则被外婆接回金坛老家。那年中央研究院公布了首批院士,罗庚和省身榜上有名,另外三位当选的数学家是姜立夫、许宝騄和苏步青。
就在罗庚抵达伊利诺伊那年,即一九四八年的最后一天,省身率领全家离开了上海,搭乘泛美航空公司的班机抵美。此前一个多月,省身接到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院长奥本海姆的电邀,在洞察到南京国民党政府即将垮台之后,便做出了携家赴美的决定。自从一年多以前回国以来,省身忙于筹备成立中央研究院数学研究所。该所成立前后,作为实际主持人,省身广泛吸纳年轻人,他网罗的人才包括吴文俊、廖山涛、周毓麟、曹锡华、杨忠道等。省身亲自讲授拓扑学,其间他先后婉拒普林斯顿、哥伦比亚等大学和印度塔塔研究所的正式聘请。
秋天来临,随着新中国成立并定都北京,中国数学界面临同时失去两位领军人物的危险。庆幸的是,一年以后,罗庚决定放弃美国的高薪,率领全家返回中国。至于罗庚回国的原因,虽有种种猜疑和分析,但无论如何,他满怀报效祖国的热情,他的行动对中国数学界是个福音。多年以后,挪威出生的美国数论学家、菲尔兹奖得主赛尔贝格这样评价说:“很难想象,如果他(罗庚)不曾回国,中国数学会怎么样?”而省身则选择留在美国生活,成为中国数学家在美国的标志性人物,他对中国数学更多的帮助和贡献,要等到退休以后。
太平洋西岸的所长
罗庚回到北京以后,先是在清华大学任教,接着很快经受了“三反”与思想改造运动的洗礼,他与蒋介石的一张合影给他带来了很大麻烦。可是,罗庚毕竟是个值得团结的名人,此前毛泽东还宴请过他,最后顺利过关,但因为相互揭发造成了同事之间难以消除的隔膜。直到第二年,政务院会议决定,罗庚担任新成立的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所长,他的心情才豁然开朗。数学所筹备处的主任委员原是苏步青,罗庚是四位副主任委员之一。
接下来的几年,罗庚在数学所大展宏图。在组织工作方面,罗庚从全国各地广罗人才,调集了数十位有成就或年轻有为的数学工作者,既重视基础理论,又注重应用数学,并成立了微分方程和数论两个专门组,还鼓励其他人员钻研自己的方向。与此同时,罗庚主持召开了中国数学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当选为理事长),并创办了《数学学报》(任总编辑)。
一九五五年,中国科学院建立学部,罗庚成为首批学部委员。在学术研究和教学上,罗庚和他的数学所都卓有成效。他亲自组织“数论导引”和“哥德巴赫猜想”两个讨论班,第一个讨论班形成了后来的数学名著《数论导引》,第二个讨论班的成就之一是王元证明了“3+4”和“2+3”。这里所谓“a+b”是指每个充分大偶数都可以表示成两个奇数之和,它们的素因子分别不超过a个和b个。如果能证明“1+1”,那就几乎等同于原始的哥德巴赫猜想了,即:
每个大于或等于6的偶数均可以表示成两个奇素数之和。
值得一提的是,第二个讨论班吸引了北大数学系闵嗣鹤教授的研究生,其中就有笔者的导师潘承洞。那时清华数学系因为“院系调整”被解散,精华部分都到了北大。几年以后,已是山东大学讲师的潘承洞证明了“1+5”和“1+4”。而证明“1+2”的陈景润是由罗庚亲自出面从厦门大学调来的,之前,他写信把自己取得的一些成果告诉心中无比敬仰的罗庚,其间和后来发生的一些事情被徐迟写进了那篇著名的报告文学。直到今天,哥德巴赫猜想依然悬而未决,陈氏定理依然无人超越。
除了数论以外,罗庚还在代数和函数论领域取得重要成就,尤其在典型群和多复变函数论方面,这两个领域培养出的人才和主要助手有万哲先、陆启铿和龚升等,其中“典型域上的多元复变数函数论”让罗庚获得了以郭沫若院长名义颁发的一九五六年度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多年以后,罗庚的弟子陈景润、王元和潘承洞也因为哥德巴赫猜想研究获得了同一殊荣。罗庚发现了一组与调和算子有类似性质的微分算子,后来被国际上称为“华氏算子”。
在罗庚麾下,还有一批数学工作者从事其他方向的研究,最突出的要数吴文俊和冯康,他们分别在拓扑学和计算数学方向取得世人瞩目的成就。早在省身领导“中研院”数学所期间,吴文俊的工作便已十分优异,后来赴巴黎留学,取得博士学位后回到北京。他在示性类和示嵌类方面的出色工作,使其与罗庚同年获得自然科学一等奖。相比之下,作为有限元方法创立者之一的冯康除了在苏联斯捷克洛夫研究所进修两年以外,一直在国内从事研究。正是在罗庚的建议下,他从纯粹数学转向计算数学研究,后来成为这个领域当之无愧的学术带头人,并在去世四年后因为“哈密尔顿系统的辛几何算法”被追授自然科学一等奖。
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不可能不卷入政治活动,何况罗庚是个有热情,喜欢和需要交际的人。早在金坛中学工作时,罗庚就加入了国民党,清华时期他积极投身“一二·九”运动,到了西南联大,他又成了左翼诗人闻一多教授的密友。后来,罗庚长期担任民盟中央的领导人。一九五七年,罗庚与民盟的曾昭抡、千家驹、童第周、钱伟长响应“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号召,联名向国务院提出了关于科学体制改革的几点意见,不料却闯下大祸。幸好化学家曾昭抡主动承担责任,加上罗庚后来在报上认错,他和经济学家千家驹免戴“右派”帽子。
“反右”过后,接下来是大跃进。罗庚提出,在十二个数学问题上要在十年内赶上美国,并且要把计算技术、人造卫星、大水坝等方面的数学问题统统包下来。显而易见,作为一个大数学家,罗庚说这些话已违心地自夸了,但在当时的形势下,还被认为不够“先进”,所内甚至有年轻人提出,在偏微分方程领域赶超美国只需两年。罗庚又被列入了“保守派”,加上他在旧中国和海外的经历,屡次要求加入共产党的申请均在所里和科学院内部遭到否决。
那时中国已与西方割断了联系,一九五四、一九五八和一九七四年,罗庚均接到国际数学家大会做四十五分钟报告的邀请,但因未获得政府批准而作罢。迫于形势,加上年龄的增大,罗庚在“文革”前夕转向应用数学,这导致他晚年主要致力于推广统筹法和优选法,并取得了不俗的成绩,这也让他相对安全地度过了“十年浩劫”。
太平洋东岸的所长
正当罗庚在中国领导数学事业、历经磨难而生命力依然旺盛的时候,省身在美国一心一意地研究几何学,并渐入佳境。一九五○年夏天,国际数学家大会相隔十四年后在哈佛召开,省身被邀请做一小时的报告,他演讲的题目是《纤维丛的微分几何》。一九七○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在法国尼斯召开时,省身再度获得邀请做一小时大会报告,演讲的题目是《微分几何的过去和未来》。可以说,在这些年里,陈省身是风光无限的现代微分几何的代言人。不过,省身初到美国时,情况却并非如此。那时这门学科被认为已进入死胡同,甚至不出现在大学课程里。省身将拓扑学的精髓应用其中,形成了所谓的整体微分几何。
芝加哥的十年,陈省身可谓“复兴了美国的微分几何,形成了美国的微分几何学派”。接下来,省身移师西海岸气候宜人的伯克利加州大学,帮助这所公立大学的数学学科从全美排名第四跃居第一。省身与不少同行们合作过,其中包括后来担任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院长的格里菲斯和堪称传奇人物的西蒙斯。省身和格里菲斯的合作主要表现在网几何和外微分几何,因为省身的原因,格里菲斯后来多次造访中国。
省身与西蒙斯则合作完成了“陈—西蒙斯不变量”,它至今仍是理论物理的研究热点,曾被物理学家、菲尔兹奖得主威藤应用到他的量子场论研究中去。后来西蒙斯当了纽约大学石溪分校数学系主任,与物理学家杨振宁共事,在一次演讲之后杨先生终于明白,原来他和合作者米尔斯当年建立起来的规范场理论的数学对应物正好是省身建立的纤维丛理论,只不过后者比前者早十年出现罢了。
西蒙斯在达到数学盛名以后放弃了教授职位,转向金融投资并大获成功。眼下这场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中,作为文艺复兴公司总裁,西蒙斯的年收入一举超越金融大鳄索罗斯,高居全球“对冲基金”经理之榜首,同时进入《福布斯》全球富豪榜的前一百位。
省身还为加州大学培养了三十一名博士,其中最负盛名、最有成就的当数后来获得菲尔兹奖的丘成桐,他解决了包括卡拉比猜想和正质量猜想等多项世界难题。在伯克利期间,陈省身当选为美国科学院院士,为此只得在那之前一个月加入美国籍;获得象征终身成就的沃尔夫奖,这也是迄今为止唯一获此殊荣的华人数学家;还获得美国国家科学奖。
当进入花甲之年,对故乡的怀念之情油然而生,省身携带妻女回到了阔别已久的祖国,受到了高规格的接待,也见到了罗庚。那时罗庚正在外地推广“双法”,一纸电报把他召回了北京。那该是怎样一幕场景呢,在“文革”的悠悠岁月里,两家人一起吃了一顿烤鸭。
古稀之年,已经从加州大学退休的省身生活又到了转折点。那年春天,他与母校南开大学的领导和老友商议,准备建立南开数学研究所,为自己的回归做好准备。可是秋天,美国国家数学研究所却在伯克利成立,发起人之一的省身被任命为首任所长,回国定居的日期只得向后推延。直到三年后他任期届满,才接受邀请担任南开大学数学所所长。以笔者之见,当初省身之所以没有与另一所母校清华合作的原因恐怕在于,他不愿意与仍然担任中科院数学所所长职位的罗庚同城竞争。
在省身担任美国国家数学所所长期间,他频频寻找机会返回中国,与邓小平等国家领导人多次会面,利用自己的个人影响力,为提高中国数学的水准做出努力。比如,他倡导的“微分方程和微分几何国际讨论会”连续举办了七年,南开的学术年活动则连续举办了十一届。在省身的建议之下,还举办了“暑假研究生讲习班”,他本人亲自授课。在收揽和关爱人才方面,省身更是不遗余力,其中包括龙以明和张伟平,后者是现任南开数学所所长。在陈老先生去世之后,他俩双双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成为最近一次院士增选中仅有的两位数学家。
纪念和祈愿
一九八五年初夏,罗庚应邀访问日本。他在东京大学发表演讲,回顾了五十年代回国以后所做的工作,按年代分成四个部分,其中七八十年代主要用做数学普及工作。或许是因为回顾往事,罗庚头天晚上兴奋过度,靠吃安眠药勉强得以休息片刻,第二天他坚持要求脱离轮椅,站着做完一个多小时的报告。当他在暴风雨般的掌声中坐下来,准备接受一位女士的鲜花时,却突然从椅子上滑落。几个小时以后,东大附属医院宣布华老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他死于心肌梗塞,享年七十五岁。
此时,省身正在天津,为即将成立的南开数学所忙碌。当他得知罗庚逝世的噩耗,随即致电北京有关方面,要求参加骨灰安放仪式,却被告知,外地宾客一概不邀请来京。罗庚生前是全国政协副主席,追悼仪式规格非常高。但笔者相信,作为一个数学家,假如罗庚灵魂有知,必定希望省身这位相知半个世纪的同行和老友能来送行。就在两年前,罗庚到洛杉矶访问,省身从四百多公里外的伯克利驱车前往相聚,这是他们的最后一面。正是在那一年,在菲利克斯·白劳德(他的父亲曾担任美国共产党总书记,他和弟弟威廉都曾担任美国数学会主席)和省身联合提名和推荐下,罗庚当选为美国科学院的外籍院士,省身为这份提名撰写了学术介绍。
在罗庚去世以后将近二十年中,省身仍在思考微分几何领域的重大问题,例如六维球上复结构的存在性,但更多的时候,他是在享受数学人生,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和号召力推动中国数学。他帮助申办成功二○○二年北京国际数学家大会。随着暮年的来临,省身收获了各种各样的荣誉,包括一百万美元的首届邵逸夫科学奖,俄罗斯颁发的以非欧几何学创始人命名的罗巴切夫斯基奖章,当选法国科学院和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中国数学会设立陈省身数学奖(华罗庚奖已先期设立),美国数学研究所新建主楼命名为“陈楼”,而即将到来的二○一○年印度海德拉巴国际数学家大会上,要颁发一个世界性的“陈省身奖”。
在中国历史上,数学家的政治地位向来比较低微。在二十世纪以前,能被最高统治者接见的实属罕见,十三世纪的李冶可能是唯一的例外。他出身书香门第,本名李治,与唐高宗同名,不得不去掉一点。李冶考中辞赋科进士后,蒙古大军侵入,历经磨难的他没有逃往南方,而是留在蒙古人统治下的北方。元世祖忽必烈礼遇他,曾三度召见他,并封其为翰林学士,但那是看中他人文领域的才学。李冶虽著有诗文无数,并有《文集》四十卷,最有价值的却是一部冠名《测原海镜》的数学著作。此书在中国数学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他也因此被尊列“宋元四大家”之一。
相比之下,二十世纪的罗庚和省身处境大为不同。罗庚曾先后受到蒋介石、毛泽东、华国锋、胡耀邦等不同时期政党首脑的礼遇,而省身接受的荣誉则超出了国界,除了邓小平、江泽民多次单独会面以外,还被美国总统和以色列总统授过勋。说实话,如此“殊荣”在世界数学史上也只有十八世纪的欧拉等极少数人才享受过。不过,他俩面对政治领袖的心态有所不同。罗庚更像是旧时代过来的人,有着诚惶诚恐的一面,而省身则处身任何场合都比较自如。这从省身少年时写下的自由诗和罗庚后来与毛泽东交流的古体诗词中可以看出,这种差别应与两个人的出身、经历、所受的教育和环境有关,也造成了他们治学之路和研究风格的差异。
遗憾的是,即便是接受过东西方名校熏陶的省身,也只是忙忙碌碌地度过一生,未能像他当年师从嘉当时逗留的城市巴黎所熏陶出来的那些伟大的数学先辈那样,在研究之余做一些哲学方面的深入思考。从笛卡儿到庞加莱,法国数学的人文主义传统绵延不绝,这两位几何学和拓扑学的开拓者也是哲学家。其结果是,几乎每隔十年八载,法国都会产生一位享誉世界的数学大师。相比之下,我们更多地依赖天才人物的出现,这一点在罗庚身上尤为明显,而省身的教育并非都在国内完成。在罗庚和省身(还有许宝騄)一百周年诞辰之际,我们在缅怀和纪念他们的同时,也由衷地祈愿,下一个或更多的罗庚、省身早日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