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认识一个腼腆内敛的姑娘珊珊。不知是生性如此,还是后天使然,她的楚楚可怜,满心满眼,即便我是女性,也深感难以招架。
她的那种内向,让人打心眼里渗出一种心疼感。
她总是低着头,耷着眼,身体呈现扭曲的拘谨姿态,她是封闭的,向任何人,甚至向她自己。
我不敢和她说话,怕惊扰了她的小世界,但我觉得她的世界一定有故事,封闭的人,总会有封闭的理由,总不会扭捏做作。
她看起来不算消极,但惯于躲避,喜欢用冷漠气场逼走众人。
所有人都以为她高冷,不愿与她共事,更不屑和这般林妹妹似的清高人物打交道,她被孤立,被嘲讽,被暗地里揣测缘由。
但在一次聚餐上,我看到和我相隔一个座位的她,在翻看短信后,眼圈明显的红了。她使劲忽闪睫毛把泪憋回去,脸都憋得通红。可是,仍然没有一个人注意到她。
她太小了,无论个头,声音,还是气场,都小到容易被人忽略。
可我看到她,却觉得她有心事。
饭后我找到她,她却不愿和我有任何过多的接触,只一门心思想要离开,身体散发出强烈的驱逐意味。
我不勉强她,轻轻问她,姗姗,如果你想找我谈心的话,我随时奉陪,我是个很好的倾听者。
姗姗抬头看了我一眼,有点怯生生,但眼神中似乎多了些真诚,她说,你把电话留我。
那天以后,我没再见过姗姗,我对她全部的印象,就停留在饭桌上那个默默吞咽泪水的清秀女孩和她那双防备心极强的眼睛。
几个月后,阴差阳错的,我加了她好友,看到她朋友圈里发文字用省略号,发图片用省略号,转发文章也用省略号,我就知道,她有多少省略号,就有多少的难言之隐。
她不愿意说,我就要主动引导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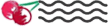
我问她,想好了么?要不要告诉我。
姗姗沉默了很久,回了我一个字,嗯。
于是我们约在茶馆,我听她讲故事,听她讲隐藏在心底最深处的故事。
她说,你准备好了么?这是个悲剧。
我点点头。
她开始讲,她说自己很悲催,她的家族是医学世家,按照父母的要求和期望,她一定是要传承家业的。
可姗姗说,我有我自己的想法和规划,我不喜欢医学,不喜欢医院的味道和药的味道,我想找一份自己喜欢的工作,认真地去做。
说到这里,她异常痛苦,眼中有泪珠游荡。
她说,我和我爸无法沟通,他甚至无条件地命令我,我的任何想法,在他那里都一文不值,都成了不孝的代名词。
她说,你知道么?当那么大一顶道德帽子扣在你头上的时候,你就不得不屈服了。
我问,因为你不想背负不孝的恶名?
姗姗说,对。
那你现在是一名医生?我问她。
护士。她说。
因为我排斥学习和进入医学领域,工作的时候,总带着情绪。一次扎针时,因为不专注,给病人用错了药,导致了一场医疗事故。虽然病人最后被抢救回来,但得知消息回家的时候,我还是觉得天都塌了。除了不能面对自己外,最大的恐惧来自于父母,我完全不知道等待我的是什么。姗姗说。
此时的她,已经哭得一塌糊涂,几度哽咽讲不下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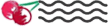
等稍微平复一些,她才接着说,回到家,我爸已经从医院同事那里知道了这件事,他非常生气,我从来没见他那么生气过。
他说我给他丢脸,给家族丢脸,不配做他女儿。
我的怒火也终于爆发,我吵他,说,本来这就是我不愿意做的事,我不喜欢医学,你非要把我按在这个位置上,我不情愿,出了责任还要我承担,是不是我的人生,连自己都根本没有支配权?
说完这段话,我爸惊讶,同时暴怒,让我滚出去。
我脑袋一热,没管那么多,直接开门出去。出了门我最大的感觉不是后悔,而是无法面对,自己犯的错,我不知道是不是该自己承担,因为这条路,对我而言本来就是错的。
姗姗哭成泪人,她说,我怎么办?我现在该怎么办?
我问她,你多久没回过家了?
她说,一个月,只和家人短信联系,我不敢回家。
我问她,你担心什么?担心他们把你的过错挑明,担心他们对你从医的命令,还是担心自己想离开医学却碍于父母不敢离开的两难境地?
姗姗说,都有,但更担心的是两难。
我告诉她,别把两难想得太难,我经历过,慢慢剥离,两难归根结底是一个难题。
她说,什么?
我说,你和你爸价值观的冲突。
姗姗苦笑着说,这冲突就够大了,根本没法解决。
我说,有办法,你慢慢想,会有办法的。
一直到谈话结束,她都仍没法面对这件事,总觉得无法解决,总觉得需要逃避。
所以她常哭,在她看来,这是表达和发泄自己的最好渠道。
不被理解的委屈,似乎只有哭能宣泄,而她,也不愿意主动去找一个能够理解自己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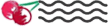
但她终于变了,也许那次谈话给了她些微的灵感,也许是她自己再也无法承受困窘。一年的时间里,姗姗的情绪在朋友圈里渐渐好转,我能感觉到她开始面对。
后来她找到我,说,我在想办法,我不想一味妥协。妥协,是对自己不负责任,对父母不负责任,也是对病人的不负责任。
我通过朋友知道了她现在的情况,在一家外企做白领,找到一个疼爱自己的男朋友,和父母的关系也不再僵持。
但我好奇,她究竟是怎么做到的?
我打电话过去,姗姗说,恰好,我也想打电话给你呢。
她说,她听了我的话,真的绞尽脑汁在想,想各式各样能够解决问题的办法,不再逃避。逃避对她来说,只能带来更大的问题。
她说,我为自己争取,但并不和父母直接对抗。我告诉他们,给我三个月时间,如果我能找到一份自己喜爱的工作,挣到比医院更多的钱,能让他们感受到一如既往的踏实和安稳,那我按照自己的路来走。
如果找不到呢?我问。
找不到,就待在医院里,一辈子,遂了他们的愿。姗姗说。
这个赌注,有点大吧。我说。
姗姗说,这是我唯一的机会,只有这样,他们才愿意让我去尝试。
父母也同意了?
姗姗说,我刚在医院捅了篓子,他们也得考虑考虑我是不是真的适合。
她那三个月跑前跑后,投了上百份简历,面了一次又一次试,终于找到一份还算满意的工作。
她说,外企虽然累,但我喜欢,我看起来内向,其实战斗力很强。
姗姗终于不再是一把鼻涕一把泪的爱哭小妞,在外企工作一段时间后,她的气质有了很大改观。果断利落自信大方,她成了不再惯常躲避的女孩子。
后来她问我,当初你为什么要帮我?
我笑,说,因为你的眼睛那么美,不该用来盛眼泪。
姗姗笑得灿然,她说,眼睛是用来呈现明媚的,就像我的现在。
内容经作者授权发布
畅销书作家,讲师,“鱼群心智成长营”创始人。新书《别轻易放过自己》火热上市,
微信公众号:鱼樵

编辑:静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