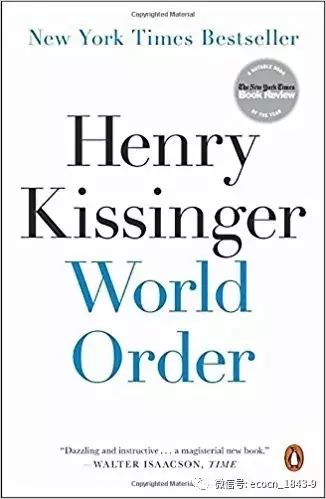
如果你想理解亨利·基辛格的观点,不妨玩玩下面这个头脑游戏:假设,自2001年9月11日以后,掌管美国外交政策的是一位现今年逾90的老人,而不是把过去25年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指责他上面的两伙人。这两伙人,先是新保守主义者,他们四处兜售民主,视这位老人的现实政治为姑息纵容;如今则是民主党人,这些自由派固执地认为,治理国家须从内政着手,因而,他们最痛恨的就是介入外部事务,更别提有什么大战略了。
对伊拉克采取些现实主义是不是比小布什时代的“下不为例”的外行做法更有用吗?一位读过温斯顿·丘吉尔有关阿富汗文章(“除了在收获季节 . . . . . . ,普什图人不是忙着私人战争就是公共战争”)的政治家会让美国致力于在喀布尔建立一个“照顾到两性比例. . . . . .且具有完全代表性”的政府吗?基辛格会先给叙利亚划定一条红线,然后又在阿萨德使用化学武器时任其不受惩罚吗?他会任由普京在边界问题上的权力真空逐渐膨胀吗?他会眼看着南中国海变成地区冲突的战场吗?
若你认为美国现在做得很好,那么,就请你跳过这篇文章,直接去看文艺评论。然而,如果你对这个正在旋转着失去控制的世界感到忧心忡忡,那么,《世界秩序》就是为你准备的。该书融容历史、地理和现代政治于一炉,并且丝毫不缺少激情。对,就是激情。因为它是一位著名的悲观者发出的内心呐喊,它是一位熟知历史的老人对子孙后代的警告。尽管这本书有不足之处——因为作者在意自己的遗产,因为他不想不必要地去惹恼他仍然想施加影响的小人国领导人而有所言不由衷。同时,本书还重复了之前著作中的某些立场。但是,这仍然是一本每一位国会议员都应当在宣誓就职前强迫自己关起门来去阅读的著作。
本书立论的前提是:我们生活在的一个失序的世界中。“就在当今‘国际社会’之被不断提及可能超过任何时代之际,‘国际社会’却没有一整套明确一致的目标、方式和限制⋯⋯一边是混乱所带来的种种威胁,一边是相互依存达到了史无前例的程度。”因此,有必要构建一种秩序,一种能够平衡各国互相抵触的欲求的秩序,一种能够同时让制定了现存国际“规则”的西方守成大国(主要是美国)与以中国、俄罗斯和伊斯兰世界为代表的不接受这些规则的新兴国家达成均势的秩序。
这会因为从未有存在过一种真正的世界秩序而变得困难。相反,不同的文明始终都在倡导自己的世界秩序版本。伊斯兰世界和中国的版本几乎完全以自己为中心。也就是说,倘若你不是穆斯林,或者视没有得到皇权的庇护,那么,你就是异教徒或者蛮族。均势的概念没有进入过他们的版本。美国的版本,尽管在时间上比上两种版本要晚一些,在内容方面也考虑得更周到,但也是一种多少以自我为中心的版本。也就是说,这是一种道德秩序:一旦这个世界理解了它的含义,并且像美国人那样去思考,一切都会好起来。因此,最佳出发点仍是欧洲的版本,即“威斯特伐利亚式”的权力均势。
几个世纪以来,多元化既是欧洲的力量之所在,也是它的软弱之体现。自罗马帝国在476年灭亡后,没有一个大国统治过整个欧洲。彼时的生存之道就是竞争——敌人的敌人就是你的朋友。因此,天主教的法国联合了新教的德国和荷兰的小公国,甚至是奥斯曼帝国,以防止天主教的神圣罗马帝国称霸。这种合纵连横的结果就是残酷的“三十年战争”,各方结成同盟,战争不断。这同当代的中东非常相似。最后,在1648年,235名特使齐聚威斯特伐利亚周边的几个小城镇中,制定出了三份不同的协议。
这三分协议的基础契约就是“教随国定”。一国的统治者可以确定他的国家的宗教,但是,它也令作为欧洲秩序之基石的民族国家获得了至高无上的地位。凡是国王必称之为“陛下”,且地位都是平等的。“教随国定”开启了一个外交的时代(在那之前,只有威尼斯人才有所谓的外交官)。均势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因为它既要容纳正在崛起的大国,也要不可避免地去容纳不理性行为的激增,如法国大革命那种想把平等带给所有人的诉求。滑铁卢战役之后,占据主导地位的英国,通过倒向一方的方式,给欧洲带来了均势。
这是基辛格熟悉的领域,讲此类故事是他的拿手好戏。他的英雄,不可避免地,都是现实政治的践行者。如在1624年至1642年间担任法国宰相的红衣主教黎塞留,他在解释自己同新教徒联手的原因时曾说过这样一句话:“人之永恒在于来世之拯救,而国家不是永恒的,若现在得不到拯救,就永远也得不到拯救。”除此之外,他的英雄还有维也纳会议的缔造者,奥地利的克莱门斯·冯·梅特涅,以及信奉实用主义的英国人帕默斯顿爵士(“我们没有永远的盟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读读基辛格关于塔列朗的描写,最后,你就会把这位贵族出身的法国外交官当作是那位带着厚厚的眼睛,讲起话来带着德国喉音的老人:
“他以欧坦主教的身份开始了他的仕途。之后,他离开了教会,转而支持大革命。再往后,他抛弃了大革命,当上了拿破仑的外交部长;最后,他又抛弃了的拿破仑,去参加恢复法国君主制的谈判,并以路易十八的外交部长身份出现在维也纳。许多人会把塔列朗当作是一个机会主义者。对此,塔列朗可能会反驳说:他的目标是法国和欧洲的稳定,他利用了一切可能的机会去实现这些目标。他的确曾千方百计地为了地位而去钻营,但是他这样做是为了在不受任何权力约束的情况下,近距离地学习有关权力和合法性的各种知识。只有人格如此强大的人,才能投身于如此之多的伟大而又利益相冲突的事件中去。”
因此,欧洲给我们提供了最合理的历史模式。但是,现在的欧洲已经不再是雕塑者了。它已经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失势了,并非真心实意地接受了后威斯特伐利亚时代的联盟思想,他们正沉迷于建设欧洲联盟的内部事务之中。除非他们解决了内部的争论,不然的话,将成为世界舞台上的一个小角色。正如基辛格在他那更加一针见血的一处旁注中所指出的那样,欧洲的统一,有且只有在一个强大如意大利的皮埃蒙特和德国的普鲁士那样的统一者的身上才能实现。
基辛格还对俄罗斯进行了精心的梳理。一旦你对普京所肩负的历史筹码以及这个国家长达数百年的无情扩张————在1552年至1917年间,俄罗斯的领土面积平均每年增加100000平方公里——有所了解,就会对他的民族主义有一个更清醒的认识。
该书也把一部分内容给了伊斯兰教。宗教曾是基辛格的一个盲点,仅从“宗教”一词没有出现在《大外交》一书的目录中即可知道。如今,基辛格似乎已在另一条道路上走得太远了。伊斯兰教在将宗教与国家分离问题上的失败,突然间就成为了解释一切世俗问题的原因(尽管解释不了世界上最大的穆斯林国家印度尼西亚的成功)。伊朗所代表的是背信弃义。相比之下,以色列是一个受害者,是一个非理性时代的“一个威斯特伐利亚式的国家”。他没有提及以色列建设定居点的无助于事,也没有考察这个犹太人国家自身的极端分子(刺杀其时正在谋求和平的伊扎克·拉宾的人只是一名“激进的以色列学生”)。所有这些给人的感觉是,它们是对以色列右翼以及支持他们的美国国会议员伸出的一个来得太迟的橄榄枝。
该书的亚洲部分较为简略。基辛格所比较的是英国对印度的影响和拿破仑对德国的影响:在这两个例子中,曾经视自己仅为地理存在的两个多民族国家,双双找到了自己民族身份。尽管该书有部分内容书同他上一本著作《论中国》是重复的,但是,他仍然对这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中央王国的历史进行了一番快速梳理。在这个国家,外交政策的主要工作就是通过礼部来收受贡品。至于军事,那是不被看重的(“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1893年,就在西方军队迅速占领这个国家时,清朝政府仍就把军费花在了修复颐和园中的一艘大理石船上面。
这样,问题的全貌以及与美国有关的内容就慢慢地变得清晰起来。在亚洲,两个权力均势正在若隐若现地形成之中,且都同中国有关,一个在南亚,一个在东亚。但是,这两个均势,当前都缺乏制衡者。也就是说,缺乏一个像当年的英国之于欧洲那样,能够将其重心转向较弱一方的国家。至于中国,尽管她有时候也在利用国际规则,但是这个国家“始终没有忘记,当初她是以一种与其历史形象完全不符的方式,被迫接受了现存的国际秩序。”从历史上来看,崛起之国与守成大国之间的位置互换共发生过15次,其中有10次是以战争来完成的。一般的看法是,中国和美国是伙伴。但是,“伙伴关系不可能通过声明来实现。”
当代的美国能够带领世界走出这种模式吗?基辛格从未直接回答这个问题,但是书中论及他自己国家的章节,读起来就如同是对十分珍视但又心胸狭隘的朋友的谆谆告诫。美国是带着两个深深的性格缺陷接手这个任务的。首先,受地理位置的限制,美国人有这样一种想法:外交政策是“一种可为可不为的行为”。直到1890年,该国的军队规模,在世界上还只排在第14位,比保加利亚的还小。这是一个已经不光彩地从她主动所挑起的上五次战争中撤退了三次——越南战争,小布什版的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的超级大国。其次,那些造就了一个伟大国家的理念让这个国家经常对外交政策有一种厌倦感,这尤其体现在这样一种观念上:“国内优先原则具有不证自明地普遍性。任何时候将它们运用于实践都是有益的”。这种观念的直接体现就是伍德罗·威尔逊在国联问题上的天真幼稚,以及新保守主义者在伊斯兰世界的冒险之旅。
状态好的时候,美国是不可阻挡的。例如,当年的西奥多·罗斯福就对需要他的国家借入国际局势有着清醒的认识,并且竭尽全力去美国的理想主义去适应务实的世界。在冷战中,美国的道德秩序曾经发挥了作用:有一个可以最终为其超级力量所战胜的明确的对手,有听从她的盟友,以及一整套的结盟规则。但是,当今的失序更加复杂。既有中东的混乱,核武器的传播,还有网络空间作为一个不受监督的军事竞技场的出现,以及亚洲的重新排序。挑战“不是简单的权力多极化,而是一个对抗的现实越来越多的世界,”基辛格写道。“绝对不能再做这样的假设:只要任其发展,这些趋势将在某个节点上,自动地调和为一个均势的世界,一个合作的世界,甚至是一个有序的世界。”
与此同时,“解决”这些问题的为政之道,正在变得越来越难。有一种网络乌托邦观点认为,随着国与国之间的了解的加深,以及关联性和透明性的增加,这会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安全。在基辛格看来,这种观点是可笑的。他写道:“自文明出现之日起,社会内部的和各个社会之间的冲突就存在了。这些冲突的起因始终没有受到信息的缺失的制约,也没有因为分享信息的能力不足而受到限制。”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事件的即时性就如同斯一场考试。事件瞬间传遍整个世界,一切皆成为内政的一部分,仕途皆由公众所塑造。胆魄、领导力和秘密,所有这一切都在变得越来越难。
当今美国领导人的表现如何呢?在这个问题上,该书既有令人恼火的含糊其辞,也具有隐藏在语言背后的打击力。书中没有对奥巴马政府的直接批评,基辛格甚至还在论述小布什对外交政策的无知时,在一段略带讥讽的内容中,表达了他对这位前总统的个人崇拜之情。但是,在含糊其辞和谄媚的后面,传达却是这样一种明确的,甚至是愤怒的信息:世界正在脱离正轨,得不呵护。与此同时,作为任何一种新秩序不可或缺一部分的美国,甚至尚未对一些基本的问题做出回答。如“我们该防止什么?”,“我们该达到什么目标?”这个国家的政客和民众都没有为今后的世纪最好准备。阅读此书会成为向前迈出的第一步,同时也是有用的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