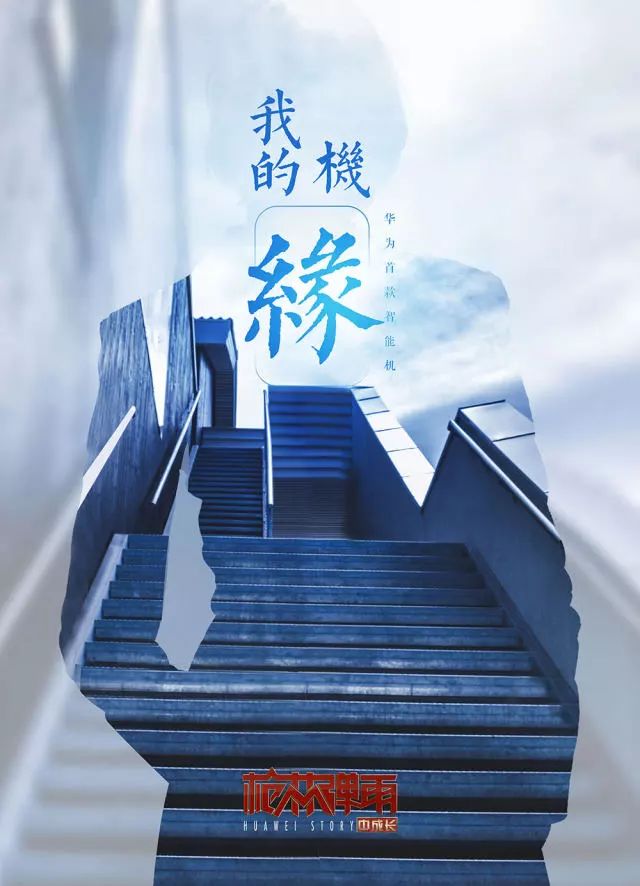
说起华为手机,很多人的印象也许是从2014年Mate7开始的,其实追溯我们做手机的历程,早在十多年前就开始了。那时手机行业基本被外国厂商垄断,华为做第一款终端产品,是为了配合无线基站设备的销售。
2002年,中国很多地广人稀的农村市场都还是通信盲区,为实现广覆盖,华为推出了无线设备CDMA 450,发现还需要有配套的终端产品才能提供完整的服务。
我那时正在无线产品线做与3G系统配套的测试UE相关的工作,公司一声令下,我就和王银峰等人被划分出来,在北京组建了华为终端业务的第一支研发团队——“无线固定台开发团队”。当时我们就十来个人,团队聚餐时一桌就坐满了。我们做的第一款终端产品,名字就叫做“村村通”。
第一代“村村通”是一个可以外接电话的无线终端产品,上面带一个天线,也叫T型固定台。最初我负责软件,因为从未接触过手机芯片,华为和手机芯片供应商的合作协议还处在签署过程中,为了加快产品的开发进度,我就联系上了外地一家手机终端厂商,去别人那里看了一天的手机芯片代码,然后回来搞开发,可以说是“现学现卖”。
团队其他成员也都是边学边干。就这样我们用三四个月的时间做出了产品原型,还记得有个射频通路问题,我们在实验室里封闭攻关了半个月才解决,和无线设备打通第一个电话那天正好是2002年的大年三十,大家兴奋地击掌欢庆“终于可以过个好年了!”
过完年回来继续产品的调测开发时,就遇到了非典。2003年4月我和几个兄弟正在深圳出差,本打算月底返京,结果非典蔓延到了北京,大家回去了就会被“隔离”。为了能持续开发,于是都继续留在深圳。
那时北京的疫情已经很严重了,很多地方停工停课,但我们的开发工作一直都没有停歇。大家心里都憋着一股劲儿,想把华为终端产品的“第一炮”打响。
2003年中,我们终于成功研发出了产品,去西藏开了“村村通”的第一个试验局。当时西藏的牧区还没有通电话,我们坐了一天的车,把“村村通”产品送到牧民家里时,他们都很惊讶,有的牧民还拿出厚厚的红布想把产品包起来,生怕这个“宝贝疙瘩”磕着碰着或者弄脏了。我们连忙告诉他们,这样不利于散热,让产品“裸着”就好了。看着他们小心翼翼又欣喜又惊奇的样子,我们心里的成就感油然而生。
随后我们又推出了长得像电话机的“村村通”,并把型号扩充到多制式,产品先后突破了阿尔及利亚、印度等海外市场。
这个不错的开端证明了我们具有做手机的能力。于是华为终端公司顺势成立了,我也正式成为了华为终端公司的一员。
华为终端一直在探索华为手机之路,坚持在功能机等产品上持续投入。就在这时,发生了一件大事——2008年,Google整合并推出了安卓平台。
这件事让整个手机行业都震动了,也让在功能机市场苦苦挣扎的华为终端看到了一线曙光——我们手机研发最大的短板就是软件平台,现在有了安卓这样一个全新的、开源的、并能与IOS匹敌的平台,让华为能和其他早期智能机厂商站在同一起跑线上,这时不拼,更待何时?
因为我有固定台和功能手机的开发经历,公司领导就让我牵头负责做基于安卓平台的手机开发。
我刚接到任务时心情很复杂。那年我33岁,本想稍微歇歇要个孩子,却没想到领导突然给我派了这么一个艰巨的任务。
智能机对华为终端团队来说是完全陌生的新领域,我们没有业务方向,没有固定的市场,分给我的“预研”小组也没几个人,我都不知道怎么能带着这样的团队走向光明。
要拒绝这个任务吗?我动摇过,但看着领导信任的目光,我又把拒绝的话语咽了下去。就这样,我接下了“军令状”。
开发产品不是纸上谈兵,我首先要回答问题就是华为能不能进入安卓联盟?这个问题在现在看来简直匪夷所思,但在当时的确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难关。
那时华为在手机市场上还没什么知名度,我去见Google的安卓主管时,他开口就问:“华为是什么公司?华为还做手机?”然后,任我说破了嘴皮,他对与华为的合作也丝毫没有兴致。
怎么向Google证明我们的能力呢?我带领团队冥思苦想,在当时每台手机都需要AP+Modem两个芯片时,我们把安卓系统移植到了只有Modem芯片的手机上,这种技术当时在业界是非常难的。当我把这款手机演示给Google的安卓主管看时,他在惊讶之余,终于承认华为在手机技术上的确“有两把刷子”,打开了Google和华为合作的大门。
拿到了安卓的许可证,我开始招兵买马,却遇到了困境。那时Google对于大家来说还是一个互联网公司,因此公司内部很多人对安卓未来的发展并不看好,或持观望态度。我四处动员,七拼八凑拉起了第一支做智能机的队伍。
队伍建起来,只是万里长征第一步。要留住人得有“粮食”,我又开始思考——“粮食”从哪儿来?我们做出来的产品能卖给谁?
多年的通信行业经验让我感觉到欧洲市场应该有机会,因为欧洲的运营商在通信业务上的拓展比较激进,也容易接受新事物和新技术。于是我就联合市场找到了德国电信(T-Mobile),向他们推广华为的智能手机产品理念。我做了一整套PPT讲述我们对安卓的理解,我们的产品概念,以及“强大”的组织阵型。我们推出了一个类似苹果的3.5英寸直板大屏安卓手机,并与最早可以支持虚拟键盘输入的输入法创新公司合作,还引入了世界顶级的设计公司与我们一起进行界面的创新。这些与众不同的思路与创新的想法,最终引起了德国电信的合作兴趣。
2009年2月,在巴塞罗那“世界移动通信大会”上,德国电信宣布和华为合作。我当时心情真是既兴奋又紧张,兴奋的是终于有客户了,紧张的是这个项目7个月后就得发货交付了,而那时我们只有一个产品概念,整个开发团队也不到50人,要运作这样的项目简直是不可能的。
但项目签了,就必须得保证交付,而且要交付真正有竞争力的产品,才能让客户能持续给我们“粮食”。
除了人力上巨大的压力,另一个交付阻力来自公司内部。采购部认为我们的产品不应该选择电容式触摸屏,因为华为从来没有和电容屏供应商合作过,而且电容屏里有很多专利,这里面隐藏的专利风险、交付风险、新供应商的供应风险都太大了。
但我坚持要用电容屏,原因很简单——智能机代表未来,电阻屏(需要用触控笔的屏幕)却是过去的原始体验。如果我们在这上面妥协,那我们的产品从出生开始,就注定看不到未来了。
所以,必须要用电容屏,有风险,就想办法解决。我拉着当时终端的总裁与采购一起讨论,怎么解决专利风险、预防供应风险。我们找了两家供应商并行验证,和他们一起解决了很多电容屏中的问题,并推动采购部成立了专门的小组去应对可能会发生的风险。
为了让产品更有竞争力,我还私下拉了其他团队的一些“业余工作者”,和我们一起做架构设计,互相PK,互相讨论,就是想弄明白,在当时的硬件基础上,怎么做出一个更优化的架构。
而我们在项目中遇到的最大挑战,是德国电信提出的定制需求。当时德国电信为了给用户带来创新业务体验,提出了很多从未成熟商用过的定制业务需求。我们只能组织研发骨干、产品经理、系统组专家等与德国电信反复讨论,深入分析业务需求并做市场调研,一边开发一边测试,一点点地摸着石头过河。
华为算是第一批做安卓手机的厂商,和Google之间也有很多的磨合问题。客户也和我们一起努力,找Google寻求和合作与支持,协助我们进行手机开发。团队人力有限,能力也有限,每天我们都是凌晨一两点回家,连续几个月在黑暗中挣扎,而光明看似遥不可及。
我四处奔走疾呼,说智能机一定是华为的未来,我们现在做的就是打下华为智能机的基础,希望大家能够多一点投入。
我动用了自己所有的关系找人、找资源,甚至还把印度软件团队的十几个人也召唤来了北京,发动五湖四海的兄弟们一起来战斗。
最后就靠着这样的人拉肩扛,
我们如期开发出了华为第一款智能机Pulse,得到以严谨苛刻著称的德国客户的高度认同
,表示“我们对华为的及时交付非常满意,这证明我们选择华为作为T-Mobile自有品牌安卓手机的合作伙伴是正确的。”
后来,我们继续拓展欧洲市场,在两个月内拿到了10万台的订单。随后同系列产品又突破了美国市场,销售近300万台,逐渐打开了华为智能机的市场局面。
第一款智能机系列虽然卖了几百万台,也得到了客户的认可,但我们离真正站稳脚跟还有很大的距离。那时华为手机多是运营商定制,运营商的要求是高性价比,价格要低,性能要好。而我们遇到的第一个困难就是——手机芯片厂家不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