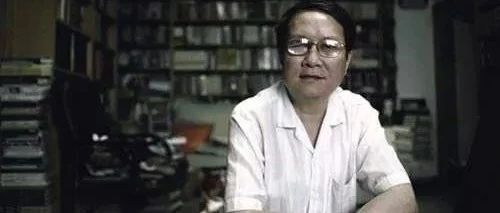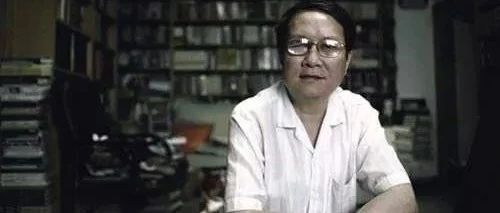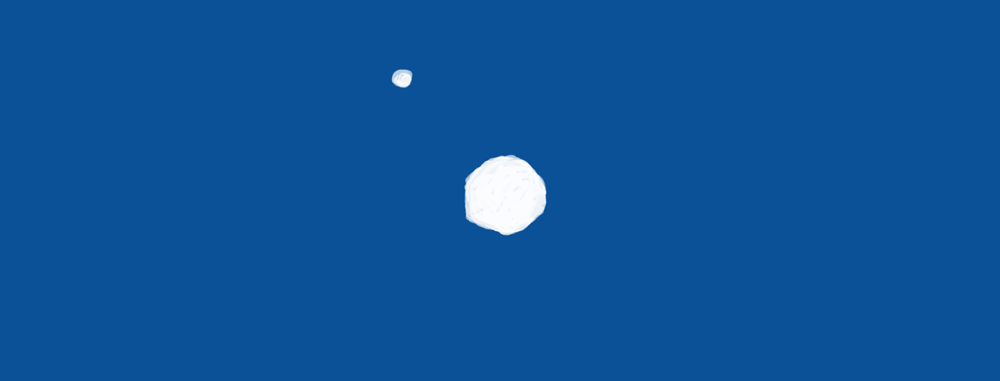
清代两江总督,这个
曾经的东南第一要缺
,
在晚清已是一块
烫手山芋
。
当两江总督是份美差时,咸丰皇帝当然不会想到曾国藩,可当它是
高危职业
时,咸丰皇帝第一个想到了
曾国藩
。
接任两江总督,就意味着要完成一个沉重如山的任务——拿下金陵城,平定太平军。
眼看半壁江山摇摇欲坠,
两江成为风暴的中心
,曾国藩在此时不得不接任两江总督。
至此,曾国藩的总督生涯在生死之间拉开了帷幕。
“
19
世纪五六十年代风云动荡,两江地区就是彼时的暴风眼,清军与太平军,绿营与湘勇,朝廷与督抚……一种势力挤压着另一种势力,一个派系排挤着另一个派系,它们相互缠绕、斗争,挤出一道道夹缝,把两江总督夹在其中,为中年曾国藩制造出险象环生的生死局。
”

多隆阿的离开对曾国藩无疑是重大打击,他的部署失去了一支劲旅,曾国荃陷入了孤军深入的境地。在庞大的金陵城下,曾国荃、曾贞干兄弟只能靠他们自己来抵御强敌了。
弟弟在前线浴血奋战,哥哥在阵后焦头烂额,考验曾家兄弟们的时刻又到了。他们即将面临的是李秀成数十万大军的轮番攻击。不过,还没有等李秀成到来,更为强大的敌人却从天而降,使得整个湘军大幅度减员,士兵们无法正常行动。他们必须先处理一场天灾。
同治元年
(1862 年)
七月二十八日,安庆衙署。
夜晚,曾国藩来到庭院,观看星象。一颗彗星出现在北极星座间,此非吉象,曾国藩心以为忧。其实这颗彗星在四天前就出现了,那时光芒尚小,尾芒也弱,但直逼北极星座。这里的北极星座不是现在的北极星,而是古代星象家极为关注的在北方夜空的五颗星。这五颗星各有代表,第一颗星代表太子,第二颗星为帝星,代表皇帝,第三颗星代表庶子,其后代表后宫。彗犯北极,为不祥之兆,尤指宫中之变。这一年里京城政治事变迭出,先有咸丰皇帝驾崩,后有辛酉政变,因此当曾国藩看到这颗有芒的彗星直逼北极时,“心窃骇之”。
近些日子以来,他每晚都邀来幕僚,同观天象。从二十四日开始,他就注意到了一颗彗星。二十六日,彗星光芒渐大,直射帝星。二十七日夜阴云,不见。二十八日这天,彗星已过北极星座中的第一颗星,距离帝星不远。不过有幕僚说,这颗彗星光芒还小,应该不会有什么灾祸。
“
天意茫茫”,曾国藩摸不透这颗彗星到底预示着什么,是人祸,还是天灾?然而,确实有一场灾祸悄然而至 —大瘟疫正在席卷江南各处。
家人、幕僚、各路将帅相继倒下。陈妾日夜咳嗽,病已深笃。季弟曾贞干得了疟疾,上吐下泻,身体虚弱。曾国藩拿出去年花了一百九十两买的鹿茸,派人送到金陵军营中,让弟弟们配制服用,希望季弟的疟疾病情能有好转。七月初四,曾国藩从书信中得知,皖北的李续宜病得必须扶杖出入;七月十七,他又得信知吴彤云已经疟病垂危。不仅如此,鲍超、唐义训、朱品隆等各处将领都相继病倒。
这是一场波及范围很大、持续时间很长、破坏性很强的瘟疫,史称“咸同之际江南瘟疫”。它从咸丰十年
(1860 年)
夏天开始,到同治元年达到高潮,之后又断断续续地持续到同治三年,主要发生在江苏、浙江和安徽之间。
这场瘟疫的流行病不止一种,而是霍乱、疟疾、天花、百日咳等多种疾病混合并行,因此它的传播性极强,致死率很高,造成的人口锐减用“十室九空”形容一点也不夸张。有学者统计,这是清代江南历次瘟疫中疫死率最高的一次,“疫病死亡人口所占比率大约在
8% ~ 15%
之间,一般不会超过 20%”。但也有极个别地区疫死率高达
40% ~ 50%
。按这个死亡率(
8% ~ 15%
)计算,江南十府一州约有数百万人死于疫病。
疫病伴随着旱灾、水灾以及兵祸,对当地百姓的影响极大,关于疫情的记载遍布江南各地的地方志。同治元年四月间,嘉兴有吐泻等病,不及一昼夜即死。夏五月,多地大疫:娄县、上海、川沙、南汇、嘉定、江浦大疫,其中上海霍乱大流行,死者数千人;江浦暴发瘟疫,城乡多狼,食人无算。夏秋以来,常熟时疫流行。六月、七月,孝丰瘟疫,民遭兵戈者半,遭瘟疫者亦半。绍兴六月大水成灾,七月,疫大作,加以穷饿,民死者益多。
据学者考证,这场瘟疫持续五年之久,前后波及三十二县次,疫情主要集中在江宁府、苏州府、松江府、嘉兴府、湖州府和杭州府等地。而这些地区正好是湘军与太平军反复争夺的府县。战争无疑加剧了疫病的传播,病毒随着双方部队的行军和战争难民的流动而传至各地。交通较为闭塞、以往瘟疫较少波及的浙西一带也因数次被太平军攻入而成为重灾区,上海则因为难民大量涌入也不断暴发疫情。这场瘟疫基本随着战场的出现和转移而不断被引发和传播。
战争也自然受到疫情的严重影响。军队中由于人员聚集和卫生条件差,士兵的感染率和死亡率极高,史料记载:“秋八月,江南大疫,南京军中尤甚……” 尤其湘军的情况更为严重,太平军因有军医防护而情况稍好。
曾国藩这样描述湘军中的疫情:“兄病而弟染,朝笑而夕僵,十幕而五不常爨;一夫暴毙,数人送葬,比其反而半殕于途。” 在军营里,哥哥一得病,马上就传染给弟弟;早上还有说有笑,晚上就撒手人寰。十个营帐中有五个都没有办法生火做饭。一个人突然病逝,其他人前往送葬,返回时有一半人也都倒在路上。
也许曾国藩的描述有些文学的夸张,但是霍乱、疟疾、天花、百日咳等混合起来的多种疫病让湘军兵勇不是上吐下泻,就是高烧不止,或者咳嗽泣血,却也是事实。大批大批的士兵倒下了。
曾国藩络绎不绝收到各处湘军将领发来的疫情报告。在宁国附近的鲍超军中疾疫大作,勇夫感染生病达一万多人,每日病死者多达几十人。在婺源一带防守徽州后路的张运兰、朱品隆、唐义训各军中的感染率为百分之六七十,连张运兰的弟弟张运桂都已经病死。在金陵雨花台曾国荃的部队中也有上万人感染生病。浙江的左宗棠部超过一半的人也在生病,每次出队不满五成。到了深秋之时,各军将领也或病或亡,李续宜病得身体虚弱,只能拄杖出入;鲍超染病甚重,被送往芜湖养病;张运兰护送弟弟灵柩到祁门,也一病不起;水师大将杨载福也抱重病;自己的季弟曾贞干在金陵城外染病,上吐下泻,卧床不起。更有甚者如猛将黄庆、伍华瀚等都已经病逝。
曾国藩十分忧虑和焦急,他在给朝廷的奏折里写道:“天降大戾,近世罕闻。噩耗频来,心胆俱碎!”
他最担心疫情打乱军事部署,让千辛万苦争来的战果毁于一旦。他本希望鲍超攻下宁国后迅速由南进军金陵,缓解曾国荃孤军深入的局面,然而鲍超此时一病不起。他本想让张运兰等部兵驻皖南,抵挡太平军侵入安徽,进攻江西后路,然而张运兰却病倒在祁门,不能回营。
曾国藩束手无策,焦灼万分,“竟日绕屋旁皇,不能作事”。
湘军的医疗体系并不完善,也没有切实可行的防疫治病方法,面对疫情几乎无招架之力。他们能做的只有举行最原始的且带有迷信色彩的“傩礼”。曾国藩不知道这是否有效,不过他觉得聊胜于无,对弟弟说:“大傩礼神,以驱厉气而鼓众心,或亦足以却病。” 于是,曾国荃、曾贞干在军营中“前建清蘸,后又陈龙灯狮子诸戏,仿古大傩之礼”。如今艰危时刻,军队士气最为重要,身能倒,但军心一定不能倒。
当然,此时他最担心的还是九弟曾国荃,如果他也染病,攻克金陵就彻底没了指望。不过上天眷顾曾国荃,“营哨官无不病者,惟统帅曾国荃日夜拊循,独无恙”。很快季弟曾贞干也幸运地从疟疾中康复过来。

金陵困局不是曾国藩第一次应对的生死困局,也不是最后一次。
之前还有三次困局:
兵败靖港
,跳河自裁;
九江又败
,二度投湖;
兵困祁门
,悬剑帐中,随时自裁;之后还有一次:
平捻无功,河遇风暴
,又
处置天津教案,饱受清议煎熬
,写下遗嘱备后事。
曾国藩担任总督的前后二十年间,深陷生死困局不下五次
,
这是由他身处晚清大变局的夹缝中所导致的。
《夹缝中的总督》
以曾国藩为圆心,以曾国藩的五大生死困局为五个同心圆,随着每一局半径的增长,圆面积不断增大,曾国藩要处理的局面也越复杂,同心圆覆盖的
晚清人物、政局、战场、人事、亲族等关系
也就越多、越复杂。
本书用精巧的叙事,通过奏折、日记一层层揭示出晚清督帅如何处理自身与时代、家事与国事、欲望与权力的复杂关系,以此
从总督之死的视角考察晚清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