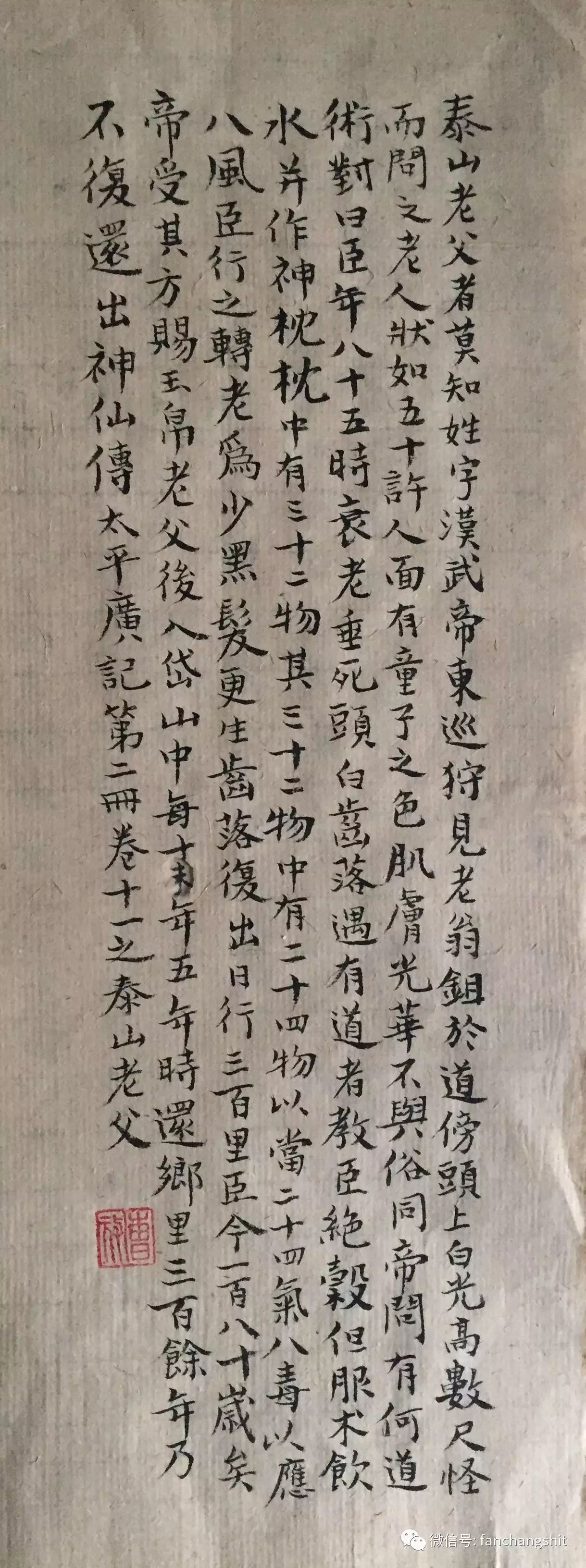
1985年夏天的某一天晚上,我们一家人在外面吃晚饭。也没有什么有包浆的四四方方的小桌子,就凉床(竹制的,一米宽,两米长吧),父母子女一溜小板凳围坐着。上面摆放着黑乎乎的几碗菜,不外乎茄子苋菜之类的。做茄子,应该剖开来,放盐放蒜,最重要的是放猪油,再搁饭锅里蒸,那才好吃。但猪还小,与一个营养不良的儿童无异,正在猪笼里饿得直哼哼,显然不是猪油时节。饭也不行,一半米,另一半搞不清楚什么东西。总之,真鸡巴难吃。可耻在于,这么难吃的东西还是每次都能被我们一家人吃个狗日干净。
我家的饭桌按下不表。旁边,是另外一个凉床。一个人盘着腿坐在上面吃。那是我祖父,他和祖母单过,所以单吃,但祖母是童养媳,吃饭从来不上桌,所以也不上凉床。我没有看到她,我想她应该在黑洞洞的屋里摸黑吃饭。因为靠儿子赡养,早年就好吃嫖赌的祖父现在更不用干活了,白天抹抹小纸牌,输赢几个蚕豆(相当于赌场筹码)。没有牌局,他就坐在河岸上钓鱼,翘嘴巴鱼参(can)鱼、鲫鱼,还有昂刺鱼。那晚他吃的应该是昂刺鱼,我能闻出味。也知道怎么做,还是蒸,放盐、浇点香油、撒一把葱的事。我当然想象着端着碗过去分到点鱼刺放嘴里唆唆,但我了解祖父的为人,知道去了也白搭,只好狠狠扒几口自家的饭菜。
饭吃完,碗筷收拾了到河边洗,凉床也用河水擦干净了,我们就坐上去乘凉。有没有讲故事?有可能讲了,但谁他妈真的爱听那些破逼玩意呢。至今我也无法理解一个儿童真的能享受父母长辈讲的那些故事?我也很明确的知道一点,夏夜乘凉这事乏善可陈。还是热,最好每过十分钟就到河边擦一把。另外,蚊子太多,睾丸都能叫它们叮肿了。我们之所以如此热爱夏夜乘凉,是我们没有电风扇,更没有空调。哪怕我们想回家写一写寒假作业而打开了电灯,也准叫父亲在脑袋上凿出一个包来。电也是钱嘛。啊,俯视三十多年前的夏夜,家家户户门前都是乘凉的人:男的光膀子,女的也差不多,我这样的无不光着屁股,噼里啪啦打蚊子的声音此起彼伏,场面十分壮观。
我要说的是半夜。我醒来发现自己躺在自家的凉床上,应该是冷醒了,因为起了风,身上是一层露水。父母和兄弟姐妹都到屋里睡觉了,他们没有叫我。这是不可原谅的。在不远处的祖父的凉床上也无声无息地躺着一个体积庞大的黑乎乎的影子,与粮食麻袋很像。我不确定那是祖父,他平常让人听了犯恶心的鼾声呢?我没有走过去看,我不敢。不敢的原因是他的凉床下有一堆惨白的火焰。我听说过鬼火,也听说过我那个在小学当老师的叔叔解释过鬼火的原理。但我还是无法解释眼前的景象。我带着一身鸡皮疙瘩回了家,爬上了床,我和哥哥共有的一张床。我们一人睡一头。随着我们越长越大,床越来越小。如果我俩都直挺挺地躺着,勉强能容得下我们。但他喜欢蜷曲着睡。这总是让我的脚无处可放,只好放他身上,而每次醒来,都是他的脚放在我身上。这一睡姿可能是我们兄弟整个童年都很不和的主要原因。可这一晚,当我掀开蚊帐的时候,借着夏夜固有的清光,我发现我的哥哥直挺挺地躺着。
大概是秋天的时候,祖父死了。2005年秋天,祖母死了。2006年元月,父亲死了。我不知道自己哪天会死,但铁一般的事实告诉我,我总有一天也会死的。而唯一让我感到安慰的是,读过这篇文章的人都会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