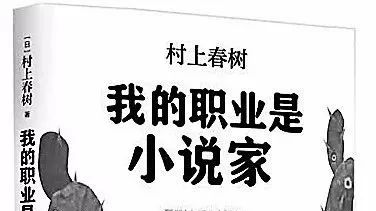第二场
【卡图兰讲述故事,小女孩和父母表演。同一对夫妇,从亲生父母变为养父母,服装稍变。
卡图兰:从前,在不远的地方住着一个小姑娘,虽然疼爱她的父母在对她的教养中并没有宗教上的严厉苛求,她却笃信自己是耶稣基督的第二次再生。(女孩带上一撮假胡子,套上一双拖鞋,四处为人们祝福、祈祷)
六岁的孩子这样行事好生奇怪。她戴上一撮假胡子,套上一双拖鞋,到处祈祷祝福。她总在访贫问苦,安抚乞讨者、酒鬼和吸毒上瘾者,六岁的她总同那些她父母觉得不该来往的人混在一处。
每次她父母把她从那些人中拉回家后她总会跺脚、尖叫、摔她的玩具;她的父母就会说……
父母:基督从来不会跺脚、尖叫、摔他的玩具。
卡图兰:她回答说,“那是老基督!懂吗?”
一天,小姑娘又溜了出去,可怕的是整整两天她父母找不到她的踪影,直到一位陌生的教士恼怒地打来电话,“你们最好到教堂来。你女儿在这里胡闹。开头还好,现在开始撒野了。”(善良的父母微笑着,灯光渐暗。)
听到她还平安地活着,她父母如释重负,别的都不计较了。父母二人急急忙忙开车去接她,匆忙中撞上了了一辆装肉的大卡车,两人头破血流地死去。(灯光照着血泊中这对善良的夫妇。)
小姑娘听到这个消息,只流了一滴眼泪。她没有第二滴眼泪,因为她觉得如果基督的父母在车祸中丧生也会这样;政府用船把她送往住在森林中的养父母的住处……(邪恶的养父母上,牵着女孩的手,紧紧地拉着。)
这对凶狠的夫妻……在向政府申请的表格中隐瞒了他们的虐待前科;他们恨宗教,恨基督,恨任何人,事实上他们也没恨任何人,就是恨这个小姑娘。(养父母扯下她的胡子扔在地上。)
小姑娘以一颗快乐的心容忍了他们的仇恨,她宽恕了他们,但这似乎毫无用处。当她坚持在礼拜天去教堂时,他们夺走她的拖鞋,让她赤脚踩着石子和碎玻璃的路去教堂;
她几小时地跪在教堂里,祈求天父宽恕她的养父母,教堂的地面上到处流着她脚上的鲜血。他们不说时间,但她回去晚了要挨打;把饭分给穷苦同学吃要挨打;为那些丑孩子叫好要挨打;跟麻风病人来往要挨打。
她的生活就是不断地被折磨虐待,但她微笑地忍受着并变得越来越坚强,直到有一天,她遇到一位在路边乞讨的瞎子……(卡图兰扮作瞎子。她将尘土与唾沫擦在他的眼皮上。)。
她将一点尘土与她的唾沫拌在一起抹在他的眼睛上。瞎子向警察告发了她。当她的养父母将她从警察局领回家后,他们说……
养父母:你要像基督一样,对吗?
卡图兰:她说,“你们总算明白了!”(停顿)
他们瞪了她片刻。开始折磨她。(骇人的情景过程在舞台上展现。)养母将一顶铁丝缠绕的荆棘头冠箍在小姑娘的头上,而养父用一根九尾鞭抽打她。两小时后,当她苏醒过来,他们问她……
养父母:你还要像基督一样吗?
卡图兰:她虽然流着泪,但她说,“是的,我还要。”(养父母将一具沉重的十字架放在她背上。她背负着它痛苦地挪动着步子。)
于是,他们强迫她背着一具沉重的木十字架在客厅里走一百圈,直到她腿弯胫折无法动弹,只能盯着自己那双已经麻木的细腿,他们问她……
养父母:你还要像基督一样吗?
卡图兰:她几乎晕厥了,但她忍着自己的虚弱,直视着他们的眼睛,她说,“是的,我还要。”
他们把她双手用钉子钉在十字架上,再把她双腿朝右弯后把她双脚也钉在架上。然后他们把她和十字架竖起靠在后墙上。他们开始看电视。当看完所有的节目,关了电视机后,他们操起一把磨得锋利无比的匕首走到她面前问道……
养父母:你还要像基督一样吗?
卡图兰:小姑娘强咽泪水,深深地吸了口气,说,“不要了,我不要像基督一样,我就是基督!”(停顿)
养父母将那把匕首刺入她的体侧……
(两人作此状。)……他们扔下将要死去的她,自己去睡了。(女孩的头慢慢垂下,闭上了双眼。清晨的曙光,养父母上。)
早晨,他们十分惊奇地发现小姑娘还没有死……(女孩缓缓地睁开双眼,向他们点头问好。他们轻轻地将女孩从十字架上放下。她摸着他们的脸好象是她宽恕了他们。他们将她放入一个玻璃棺材然后封上了棺盖。)
于是他们把她从十字架上放下来,放入一个玻璃棺材,活埋了她,留了能让她再活三天的空气……(他们将土铲在棺材盖上。)……在地下的她听到了她养父母最后的声音,他们喊道……
养父母:嘿,如果你是基督,三天后你就能爬出来,你会吗?
卡图兰:小姑娘想了一会儿,对自己微笑着,她轻轻地说,“我会的,我会的。”(停顿)于是,她等啊。等啊。等啊。(当女孩缓缓地用手指抠着棺盖时,照着棺材的灯光渐暗。卡图兰走上前来。)
三天后,一个走过树林的汉子被一座小小的新坟绊倒,可这汉子是个什么也看不见的瞎子,他爬起来继续走,没有听到他身后一具尸骨在抠挖棺盖的可怕的声音,抠挖声渐渐远去,永远消逝在这空旷、荒凉、冷漠的树林里那漆黑漆黑的深处。(暗场)
第三幕
【审讯室。卡图兰匆匆写就一篇长长的认罪书。他将第一页递给端坐着的图波斯基。埃里尔站在一旁,抽着烟。
图波斯基:“我供认我参与谋杀六人的罪行;其中三人被杀是我的个人行为,另外三人是被我和我哥哥模仿我所写的一系列残忍而变态的小说的内容所杀。”
括号,“附上相关小说”,括号。(停顿)我最后谋杀了我哥哥,迈克尔……”没错,谢谢你,卡图兰。不然,我们将永远无法给你定这项谋杀案。“用枕头压住他的头……”等等,等等,等等……“让他免受遭到处决的恐惧与折磨……”
等等,等等,等等。关于他是如何热爱他哥哥的话。是的,你确实展示了这一感情。“在最后的这次谋杀之前我还谋杀了一个哑巴小女孩,大约三天前。我不知道她的姓名。这个小女孩……是……
埃里尔:(停顿)这个小女孩怎样?
图波斯基:在这一页的结尾。
埃里尔:写快些。
图波斯基:写快些。(停顿)还是“再写快些”?“写快些。”“写再快些。”
埃里尔:是“写快些”……
图波斯基:是“写快些。”(埃里尔扭着脖子,倒看着卡图兰写的第二页。卡图兰几乎本能地用手捂住他写的内容。埃里尔在他后脑上扇了一巴掌。)
埃里尔:你他妈的没在考试!
卡图兰:对不起……(埃里尔从他肩后看着他写的内容。)
埃里尔:“按照一篇叫《小基督》的故事里的方式……杀害的。”哪篇叫《小基督》?我没见到那篇……
图波斯基:什么?(埃里尔翻找着纸箱中的稿件,他找出了《小基督》的故事。)
埃里尔:他说他们像《小基督》的故事里那样杀害她的。你见到这篇故事了吗?
图波斯基:(厌恶、悲哀地)我看到了。(埃里尔开始读那篇故事。卡图兰瞥了一眼图波斯基,图波斯基盯视的眼神令他惊恐。把认罪书的第二页递给图波斯基之后,他继续写着)你把她的尸体放在何处?
卡图兰:我画了张地图。在卡梅尼斯森林我们家后院约一百码外有一口许愿井。她的尸体就埋在那口井的后面。同另外两人埋在一处。两个成人。
图波斯基:哪两个成年人?
卡图兰:我正在写。(图波斯基查看他的手枪,卡图兰留意到了,但继续写着。)
图波斯基:(对埃里尔)你看到哪了?
埃里尔:“她会带上一撮胡子并穿着拖鞋四处走动。”
图波斯基:埃里尔,如果你读故事只是为了发现一个孩子如何被谋杀,干嘛不直接跳到故事的结尾?
埃里尔:哦。对。
图波斯基:比如,跳到“荆棘头冠”或者“背着十字架在屋内兜圈直到两腿弯折”那一段,或者后面紧接的一段。(停顿)
我得让他们派法医去,把尸体弄回来。(图波斯基持卡图兰的地图下。读完故事的埃里尔开始无声地流泪哭泣。卡图兰看了他片刻,又继续写认罪书。埃里尔坐着,面露厌恶的神色。)
埃里尔:这世上怎么会有你这种人?
(卡图兰写完一页,又开始另一页。埃里尔读着第一页)“我按住他,我哥把他的脚趾头切下来,这法子来自小说《河边小城的故事》。附上小说。”(停顿)
“我按住她,他逼着她吞下两个肚里塞了剃刀片小苹果人,这法子来自小说《小苹果人》。附上小说。”(停顿)你真地以为你死后我们不会烧掉你所有的故事吗?
卡图兰:我按照我的许诺,如实地供认了一切罪行。我相信你们会按照你们的许诺,保存好我的小说和档案,在我死后五十年内不予泄露。
埃里尔:你凭什么相信我们会信守诺言?
卡图兰:因为我相信,在你们内心深处,你们是正直的人。
埃里尔:(站起来,激愤地)内心深处?!内心他妈的深处?!
卡图兰:等我写完这页你再拷打我好吗?我已经写到我如何谋杀我父母,(卡图兰继续写着,埃里尔点了支烟)谢谢。
埃里尔:(停顿)你杀了你父母?(卡图兰点头)这似乎问得荒唐,但是,呃,为什么?
卡图兰:嗯……我有一篇小说叫《作者和作者的兄弟》。我不知道你是否看过……
埃里尔:我看过。
卡图兰:噢……我讨厌那种变相自传体作品。我认为那些只写自己经历的写家是因为他们实在太愚蠢而缺乏任何创造构思,但《作者和作者的兄弟》,我认为,是我唯一的非虚构作品。
埃里尔:哦。(停顿)他多大年纪?他们开始的时候。
卡图兰:他八岁。我七岁。
埃里尔:事情持续多久?
卡图兰:七年。
埃里尔:那几年你一直清楚这事?
卡图兰:我开始不太确切,直到最后,但应该是。
埃里尔:然后你杀了他们?(卡图兰点头,将写完的认罪书交给埃里尔。)
卡图兰:我用枕头压在他们的头上,然后把他们埋在我们家屋后的许愿井的后面。我觉得许愿井那儿合适。反正,那个聋哑女孩也埋在同样的地点。(埃里尔在文件箱里翻找着。)
埃里尔:你知道,你的童年遭遇在法庭上可成为有力的辩护。当然,如果我们不准备立马处决你,那就难免麻烦的法庭程序。
卡图兰:我不要任何麻烦的程序。我只要你们信守诺言。就按原来说的杀了我,保管好我的小说。
埃里尔:好,你当然可以对我们半信半疑。
卡图兰:我能相信你。
埃里尔:你怎么知道你能相信我?
卡图兰:我不知道。你牵涉到某种事情。我不清楚那是什么。
埃里尔:哦,真的?好,你知道,我来告诉你关于我的事情。那就是我有着压倒一切的,根深蒂固的仇恨……对你这种人……仇恨。那种哪怕是对孩子……碰一手指头的人。我每天带着这种仇恨醒来,它把我唤醒。
它跟着我坐车上班。它在我耳边说,“他们别想溜掉。”我早早上班。准备好所有的刑具绳索和电源,免得我们……浪费时间。我承认,有时候,我使用过度暴力。有时候我对一个完全无辜的人使用过度暴力。
但我要告诉你,一个完全无辜的人走出这个房间到了外面的世界,他们想都不敢再想对孩子提高他们的嗓门,就怕被我听见了拖回来再给一顿过度暴力。那么在执法机构,这种行为是否构成道德问题呢?
当然是!但你知道吗?我根本不在乎!因为当我上了年纪时,你知道吗?孩子们将围着我,他们将知道我是谁,知道我坚守了什么,他们会感谢地送给我他们的糖果,我会接受这些糖果,谢谢他们,祝福他们平安地回家。
我会很快乐。不是为了这糖果,我并不真的喜欢这糖果,但是,我明白……我心中明白,如果没有我,他们中有的孩子就没法来了。所以我是个好警察。并不是说我有多大能力,因为我没有,但我坚守着我的位置。
我坚守着我的位置。我站在正义的一边。我也许并不永远正确,但我站在正义的一边。孩子们的一边。站在你的对立面。所以,当我听到一个孩子被那样的方式残杀……就像《小基督》故事中的那种方式……
你知道吗?就凭你写这个故事,我非把你弄死,更别说还动手杀了孩子!所以,你知道吗?(从橱中取出一笨重、形状可怖的电刑具和接插头。)
去他妈的你父母对你和你哥干的事。去他妈的。如果我抓住他们我也弄死他们,就像我现在弄死你一样。因为以牙还牙一样犯罪。以牙还牙一样犯罪。现在请你跪下,我要给你上电刑。(卡图兰往后退着。)
卡图兰:够了,别再来了……
埃里尔:来这儿,请,我说过……(图波斯基上)
图波斯基:出了什么事?
埃里尔:我正要给他过电。
图波斯基:天哪,你们怎么了?
埃里尔:我们谈话呢。
图波斯基:谈什么?
埃里尔:没谈什么。
图波斯基:你在作你“等我老了孩子们会过来送我糖果”的讲话?
埃里尔:你混蛋。
图波斯基:(吃惊地)对不起?今天你这是第二次……
埃里尔:(对卡图兰)你!跪这儿,请。我已经客气地告诉你了。(卡图兰缓缓走到埃里尔面前。图波斯基在桌前坐下,扫视着认罪书的另外几页。卡图兰跪下。)
卡图兰:第一个让你下跪的人是谁?你母亲还是你父亲?(埃里尔死寂般地不吭声。图波斯基张着嘴。)
图波斯基:我混蛋。
卡图兰:我猜想是你父亲,对吗?
图波斯基:你没有对他说过你父亲的那些破事,你说了吗,埃里尔?上帝!
埃里尔:没有,图波斯基,我没对他说过我父亲的那些破事。
图波斯基:什么?哦,垃圾。那个老毛病。
埃里尔:(对图波斯基)你没完没了地挖苦那破事,你是不是?挖苦那“问题童年”的破事?
图波斯基:我没有没完没了挖苦任何事情。是你自己老把你那问题童年兜出来。
埃里尔:我从来一字不提我的童年问题。我不会用“问题童年”这个词来描述我的童年。
图波斯基:你会用什么词?“被你爹糟践的”童年?那不是一个词。(埃里尔开始微微颤抖。)
埃里尔:你想对罪犯透露更多信息吗,图波斯基?
图波斯基:我只是厌倦了所有人都在这儿用他们童年的破事为他们自己的丑恶行为辩护。我父亲是个狂暴的酒鬼。我是个狂暴的酒鬼吗?是的,我是,但那是我的个人选择。我毫不隐瞒地承认。
埃里尔:现在还是让我拷打这罪犯吧。
图波斯基:你还是拷打罪犯吧。你让他等得够久了。(埃里尔一边说一边用电线接头拴住卡图兰。)
埃里尔:今天你踩过了线,图波斯基。
图波斯基:我在读罪犯的认罪书,埃里尔,保证我们对此案的处理没有任何漏洞。我在做我的工作。我没有用拷打一个已定罪的智力犯人来满足我自己施虐狂的复仇心理。
埃里尔:你踩过了线。
图波斯基:请你赶紧折磨罪犯吧,埃里尔。还有半小时我们就得处决他。(埃里尔在将电极接通电池。)
卡图兰:现在你父亲在何处,埃里尔?
埃里尔:一个字也别说,图波斯基!一个字也别说!
图波斯基:我一个字也不说。我在读他的认罪书。我在做我的工作。就像我说的。
卡图兰:他在监狱里吗?
埃里尔:你给我闭嘴,变态狂。
卡图兰:不然你想怎样?你想折磨我处决我?(停顿)他在监狱里吗?
埃里尔:嘘,嘘,嘘,让我集中……
图波斯基:他没在监狱里,没有。
埃里尔:我刚才怎么说的?
卡图兰:他们从来没有逮捕他?
图波斯基:他们没法逮捕他。
埃里尔:图波斯基!对于所有当事人来说你太恶劣了,继续这种……这种谈话。
图波斯基:我有一种可怕的感觉——你是对的。
埃里尔:所以我要接通这最后一根电极,我要接通这最后一根电极……
卡图兰:他们干嘛不逮捕他?
埃里尔:嘘,嘘,嘘……
卡图兰:他们干嘛不逮捕他?(埃里尔接通了电极,正当他要启动电源时,图波斯基在这最后一刻开口了。)
图波斯基:因为埃里尔已经谋杀了他,当然喽。(埃里尔轻声笑了,他又颤抖起来。他没有启动电源。)当然,这不是真正的谋杀,对吗?更像是自卫,正当防卫,等等。我称之为谋杀是取笑他。
嘿,如果我父亲在我八岁起每星期跟我上床我也会杀了他,你明白吗?(停顿)嗯,趁他父亲睡觉时他用枕头压在他头上。我发现你们这俩小子有许多共同之处。(图波斯基将认罪书平摊在桌上。停顿。)
埃里尔:我要向局长报告,报告你此案整个侦讯过程中的行为。侦讯从开头起就毫无目标毫无头绪。从开头起。比如那个“侧视角度”的东西?那个“你眼睛下方的侧视角度”的东西?那到底是什么?
图波斯基:用胡言乱语来打乱及破坏罪犯的心理状态是所有侦讯条例中的内容之一,埃里尔,现在我希望在不用你的电刑的状态下继续审问罪犯,你不介意解除卡图兰先生身上的电极吧,我希望他能够专注。
埃里尔:我将要求局长由我来代替你担任此案的一号侦讯,再说这不是第一次了,对吧,局长信任我,他曾这么说过,一号也多次被撤换过,你会遭到申斥,这案子将由我来结案。由我来根据种种线索和物证对此案做出最后决定。由我来定案。
图波斯基:那你定案过程的第一步是什么?
埃里尔:我计划是,在你进来说这么一大堆之前,我的第一步就是用电刑拷问犯人,对吗?
图波斯基:为什么?
埃里尔:为什么?因为他杀了那帮孩子!
图波斯基:你看,我的第一步是讯问他一系列关于杀害哑巴女孩的问题。
埃里尔:嗯哼?
图波斯基:我的第一个问题“这是否属实,卡图兰先生……”我会以这种,正式的口气。“这是否属实,卡图兰先生,你同你哥哥,以《小基督》故事中的方式,将一顶带刺的头冠套在女孩的头上?”
卡图兰:是的,情况属实。
图波斯基:情况属实。我的第二个问题,“在此之后还是之前你用九尾鞭抽她?”
卡图兰:之后。
埃里尔:这些我们都知道。
图波斯基:我的第三个问题,“你是否逼迫她背负一个沉重的木十字架绕圈走动,然后将她钉在十字架上?
卡图兰:是的,我们是那样干的。
图波斯基:你们是那样干的。最后,你们是否将一把匕首插入她瘦弱身体的一侧?
卡图兰:是的,我们是那样干的。我感到耻辱。
图波斯基:然后你们是否掩埋了女孩?
卡图兰:是的。
埃里尔:我说过了,这些我们都知道。
图波斯基:在故事的原文中,掩埋她的时候,小女孩还活着。在你们掩埋那哑巴女孩的时候,她是活着还是已经死去?
卡图兰:(停顿)什么?
图波斯基:在你们掩埋那小女孩时,她是活着还是已经死去?(卡图兰寻思着答案,但想不出来。)
卡图兰:(轻声)我不知道。
图波斯基:你说什么?
卡图兰:我不知道。
图波斯基:你不知道。你不知道她是死是活。
嗯,埃里尔?你去见你的局长朋友时,顺便给搜救队打个电话,让他们赶紧过去,如果那哑巴小女孩还活着,能否让他们就挖出来?谢了,哥们。(埃里尔注视了他一眼,冲出门去。图波斯基踱步到跪在电刑刑具前的卡图兰面前。)你怎么会不知道?
卡图兰:很难说清。她没什么呼吸了。我想她死了。她是死了。她现在应该死了,还没死?埋在土里还能活吗?
图波斯基:她死了吗?她应该死了?我不知道。我从没把一个孩子钉在十字架上再用棺材埋掉。我不知道。(图波斯基开始摆弄电刑的接线。卡图兰定了定身子准备承受电击。图波斯基切断电源回到桌前坐下)
我估计她死了。我估计。但我不知道。我突然觉得我像是在同法律学生交谈。你只说你模仿《小基督》。那也许能蒙混埃里尔。“对不起,警官,是我干的。”结了!可蒙混不了我。明白吗,埃里尔是个警察。他执警。警犬也执警。我是个警探。我,有时候,喜欢侦查。
卡图兰:我肯定她已经死了。
图波斯基:不太肯定,对吗?(停顿)
你知道吗,我曾经写过一篇小小说。它多少表达了我的某种世界观。不,它没真正表达我的世界观。我没有世界观。我觉得世界就是一堆垃圾。那不是真正的世界观,对吗?或者是一种世界观?
嗯。(停顿)总之。我写了这篇小故事,而且……等等,没错,不,如果说它没有表达我的世界观,那它表达了我对警探工作以及警探工作与整个世界的关系的观点。对,就是这样。你干嘛还跪着?
卡图兰:我不知道。
图波斯基:样子很傻。
卡图兰:是的。(图波斯基示意他坐回椅子。卡图兰解去手上最后一个电极,在椅子上坐下。)
图波斯基:那么,你要听我的故事吗?
卡图兰:要。
图波斯基:你不愿说不要,是吗?
卡图兰:不是。
图波斯基:不是。那好,我的故事叫……它叫什么来着?它叫……《一个聋子小男孩在铁道上行走的故事——在中国》(停顿)怎么样?
卡图兰:什么?
图波斯基:你觉得这故事名字好吗?
卡图兰:我觉得这名字好,是的。
图波斯基:(停顿)你的真实想法是什么?我允许你绝对地说真话,哪怕这话会伤我的心。
卡图兰:我觉得它应该是我听到过的最差的名字。它需要两个逗号。你不能在一个题目中用两个逗号。你不能在一个题目中有一个逗号。这题目中甚至可能还有一个句号,这个题目。这题目近乎愚蠢。
图波斯基:(停顿)也许这个题目的形式正好比较超前。
卡图兰:也许是。也许那些糟糕的题目形式都比较超前。也许这将成为新潮流。
图波斯基:也许会的。
卡图兰:我只是觉得这是个糟糕的题目。
图波斯基:我们对此取得了共识!现在我收回我让你实话实说的许可,你很幸运我没赏你一个大头耳光!(停顿)好。我说到哪了?
卡图兰:聋哑男孩,长长的铁路。(停顿)抱歉。
图波斯基:(停顿)好,那么,从前有个聋子小男孩,什么也听不到,聋子男孩都那样。哦,对了,故事发生在中国,所以,它是个聋了的的中国男孩。我不知道我为什么选择中国。哦,我知道了。
我就喜欢那些中国孩子的眼神,很滑稽。(大笑)反正,有一次他从某个地方沿着铁道走回家;他走在平原上伸向远方的铁轨上,那中国的平原,你明白吗?没有树,只有光秃秃的大地,什么也没有,只有他,走在铁轨的枕木上。
也许他有点弱智,这小孩,也许他是个有点弱智的聋子中国小男孩,因为,我是说,他是聋子,走在那种铁道上,那是很危险的。如果火车从他身后开来会怎样?他听不见,他会被碾得粉碎。所以,没错,也许他弱智。
好,一个弱智的中国聋孩子正沿着长长的铁道走回家,你猜怎样?一列火车正沿着铁道向他身后开来。因为,铁道是那么长,火车是那么远,所以火车一时还撞不到他,但会撞到他的。这火车开得如此之快即便司机看到他也来不及刹车。
而且这孩子不起眼,你明白吗?他就像,你见过那种矮小乖巧的中国孩子吗?头发长长的?对,就那种。所以司机甚至可能看不到他。不管怎样,有人看到了这孩子。你知道谁看到了他?嗯,就在孩子前方两里路外的铁路边,
有一座奇怪的古塔,这塔也许有一百英尺高,塔顶住着一个奇怪的老人,这奇怪的老人留着那种长长的中国胡子,你知道的,还有那眯缝着的眼睛,还有那种滑稽的小帽子。有人觉得他极有智慧,也有人觉得他有点可怕,
因为,你知道,他住在这座高塔的塔顶。不管怎样,多少年来没人跟他说过话。人们甚至不知道他是死是活。当然,他还活着,不然故事里就没这人了。所以他就待在那塔顶上,他做数学计算,他画各种设计图纸,
他搞各式各样的发明,发明那些还没被发明的东西。在他房间里,堆在地上、钉在墙上的资料有一百万页,而所有这一切就是他全部的生活。世界就在他脚下。这些设计、这些计算是他唯一的寄托。
当他从他那拱形的小窗往外眺望时,他看到一英里外,现在是半英里了,那聋子小男孩正在走来,在男孩身后仅仅两英里之外,也许三英里,一列火车呼啸而来。
那老人对他眼前的状况看得很准确,“一个聋子男孩走在铁道上。这个聋子男孩将听不到他身后的火车。这男孩会被轧得粉身碎骨。”于是……
卡图兰:他怎会知道小男孩是个聋子?
图波斯基:(停顿)啊?
卡图兰:他怎会知道小男孩是个聋子?
图波斯基:(想了一下)他看到他的助听器。
(卡图兰微笑着点头。图波斯基松了口气。)孩子从书包里拿出助听器……当然他看到这聋孩子,也看到了火车,但他没有像平常人那样,冲下塔去救孩子,当然他愿意的话他来得及。那他做什么呢?他什么也没做。
他什么也没做,他只是开始在一张纸上计算着,自得其乐。我想那计算是关于火车的速度,铁道的距离,还有小男孩那两条细腿行走的速度。他要算出铁轨上火车飞速碾向那可怜男孩后背的确切时刻。
那男孩继续走着,显然毫无知觉,火车呼啸而来,越来越靠近他,当男孩走到离高塔塔底大约三十码处时,老人完成了计算,他发现火车将分秒不差地在距离塔底十码处碾过男孩。距离塔底十码处。老人显得毫无兴致,
他漫不经心将那张写着算式的稿纸折成一只飞机后将它仍出窗外。他回到桌前继续他的研究,把那聋子男孩的事全忘了。(停顿)在距离塔底十一码处,那小男孩跳下铁道去抓那只纸飞机。火车在他身后呼啸而过。(卡图兰微笑着)
卡图兰:相当不错。
图波斯基:“相当不错。”你所有的垃圾故事加起来也不如它。“一百零一种法子来杀害一个五岁孩子”?
卡图兰:不,它比不上我写的那些的故事,但它相当不错。
图波斯基:对不起,我已经收回我让你泼我脏水的许可,对吗?我的故事要好于你所有的故事。
卡图兰:是,没错。我再次感谢你保存我档案中那些微不足道的故事。
图波斯基:嗯。
卡图兰:(停顿)但是,不管怎样,这故事如何体现了你的世界观?或者你对警探工作,或任何事情的观点?
图波斯基:哦,你没理解吗?(自豪地)
你看,那智慧的老人,明白吗,他代表我。他整天坐在塔顶,他计算着,他和他的同胞们并无太多的亲密关系。这又聋又傻的男孩路过,他代表了我的同胞,明白吗?他这么过来,显然,毫无知觉,甚至不知道火车在过来,
但我知道,而根据我的精密计算,我在那精确的时刻扔出我的纸飞机,我将从火车轮下救出这傻瓜,我将从罪犯的手下救出我的同胞,我甚至得不到一句感谢的话。那聋子男孩并没感谢那老人,对吗?他只是玩他的纸飞机。
但那不要紧,我不需要感谢。我需要知道的就是由于我的辛勤侦查,那孩子没被火车伤害。(停顿)如果是你这种案例,那我就必须追查轧死这穷孩子的火车司机,然后倒过来追查他的混账同伙。
卡图兰:(停顿)那么这个老人就是要这聋子男孩去接他的纸飞机?
图波斯基:是的。
卡图兰:噢。
图波斯基:怎么,你不明白?
卡图兰:不,我只是以为男孩碰巧去接了那飞机,像是一个巧合。
图波斯基:不。不,老人就是要救那男孩。所以他扔出了那纸飞机。
卡图兰:噢呵。
图波斯基:他确实擅长于扔纸飞机。他确实擅长于一切。
卡图兰:但他不是转过身来就好像忘了这件事吗?
图波斯基:不。他,喜欢,转过身去,因为他是如此擅长于扔纸飞机,他甚至不需要看它落在何处,他明白这一前提:“哇呜,傻小子。他们喜欢纸飞机,对嘛。他一定会跳起来去接它。”(停顿)这还不清楚吗?
卡图兰:我觉得它还可以更清楚。(图波斯基点着头,思考着,他好像突然想起了他的身份。)
图波斯基:闭嘴!我用不着听你什么狗屁的创作指导!
卡图兰:不,我只是想……
图波斯基:我觉得你们将三天前虐杀的小女孩埋到土里时,她的死活你应该写得清楚。我觉得你应该交代得更清楚。你要不要我说得更明白,就算我们答应过你,我一怒之下照样一把火烧掉你所有的故事?(图波斯基一手拿着故事的文稿,一手拿起火柴。)要不要我说得更明白?
卡图兰:求求你,图波斯基。你的故事真的很好。
图波斯基:我的故事好过你所有的故事。
卡图兰:你的故事好过我所有的故事。
图波斯基:故事很清楚,老人要救那个聋哑小男孩。
卡图兰:绝对清楚。
图波斯基:(停顿)你只是不喜欢那个聋哑小男孩最终没有死去!
卡图兰:我喜欢这故事,图波斯基。这跟别的事情毫无关系。跟烧掉我的故事或其他事情毫无关系。我真的喜欢你这故事。如果我写了这故事我会自豪的。我会的。
图波斯基:(停顿)是吗?
卡图兰:是的。(图波斯基放下手中的故事文稿。)
图波斯基:不管怎样,我不会烧掉它们。我是个守信用的人。如果别人信守诺言,我也信守诺言。
卡图兰:我知道你这点。我尊重你这点。我也知道你不在乎我是否尊重这点,但无论你在乎与否,我尊重你这点。
图波斯基:但我尊重你尊重我这点。呵,那我们不是很默契了吗?不过真是太糟了,还有二十分钟我就得向你的脑袋开枪。(图波斯基微笑着。卡图兰第一次对自己的死亡思考了片刻。)
卡图兰:嗯。(图波斯基停住微笑。停顿。)
图波斯基:不,我……你有些故事也非常出色。有些故事我不喜欢。
卡图兰:哪些?
图波斯基:(停顿)我忘不了那个《枕头人》故事中的某些东西。某些温暖的感觉。(停顿)那个主题,一个孩子死去,孤独地,出了事故,他并不真的孤独。他有这么个,善良的人伴随着他,牵着他的手或怎么样的。而那正是孩子的选择,不管怎样。这多少让人感到欣慰,无论如何。这决不是无聊的胡说。
卡图兰:(点头、停顿)你失去过一个孩子?
图波斯基:(停顿)我不像老埃里尔,不会跟犯人计较那一类事情。(卡图兰点头。悲哀的停顿。)我儿子淹死了。(停顿)自己去钓鱼。(停顿)傻瓜。(卡图兰点头。图波斯基将电刑具放回橱里。)
卡图兰:下面该怎样?
图波斯基:我们等待那个哑巴女孩的消息……(图波斯基从橱里拿出一个黑色的头套,优雅的比试给卡图兰看,前前后后。)……我们把它套在你头上,带你到隔壁房间,对着你的脑袋开枪。(停顿)
明白了吗?不对,我们带你到隔壁房间,然后给你戴上头套,再朝你的脑袋开枪。你知道吗,如果先给你套上头套再带你去隔壁房间,你可能撞上什么,伤了你自己。
卡图兰:干嘛去隔壁房间?干嘛不在这儿?
图波斯基:隔壁房间,比较容易清理。
卡图兰:(停顿)你是突然开枪呢,就是突然向我开枪呢,还是给我一分钟祈祷之类的?
图波斯基:嗯,首先我唱一首关于小马的歌,然后埃里尔拿出他的刺猬弹。你知道他行刑用的刺猬弹吗?拿出刺猬弹后,嗯,你还有十三秒到二十七秒的时间,要看他的刺猬弹的大小。(停顿)
如果我突然开枪,我不会告诉你我将突然开枪,对吗?!上帝!作为一个天才的作家-杀手-心理-杀手,你也太蠢了点!(停顿)从你套上头套到开枪大约十秒钟吧。所以,你的祷告词要尽量的短。
卡图兰:谢谢你。
图波斯基:别客气。(图波斯基将头套扔在卡图兰面前的桌上。停顿。)
卡图兰:我只是想追忆一下我哥哥。
图波斯基:哦?想你的哥哥,是吗?不想那三个被你杀害的孩子,只想你哥哥。
卡图兰:没错。不想那三个被我杀害的孩子,只想我哥哥。(门开了,埃里尔目瞪口呆地走进来,满脸茫然。他慢步走向卡图兰。)
图波斯基:他们找到她了?(埃里尔走到一脸恐惧的卡图兰面前。埃里尔将一只手放在卡图兰的头顶,抓住他的头发,轻轻地仰起卡图兰的头,俯视着他。)
埃里尔:(轻声地。)你到底干了什么?老实说你到底干了什么?(卡图兰无法回答。埃里尔轻轻地放了他,慢慢走回门口。)
图波斯基:埃里尔?
埃里尔:嗯?
图波斯基:他们找到她了?
埃里尔:是的,他们找到她了。
图波斯基:她已经死了,对吗?(埃里尔站在门口。)
埃里尔:没有。(卡图兰恐惧地将头埋入双手。)
图波斯基:她还活着?(埃里尔朝门外打着招呼。一个八岁左右的哑巴女孩走了进来,她的脸、头发、衣裙和鞋都都漆成了鲜绿色,她快乐地微笑着,用手语向两人问好。)
埃里尔:他们在许愿井那儿找到了她,在一间小小的儿童游戏室里。她身旁还有三头小猪。她有足够的食物和水。小猪也是。她似乎对这一切感到很快乐,对吗,玛丽娅?(埃里尔对她比划“你快乐吗?”她微笑着,用手语比划着。)
她说是的,她很快乐,但它能带走那些小猪吗?(停顿)我说,我得问你。(图波斯基盯着他们两人,目瞪口呆。停顿。)我说我得问你小猪的事。
图波斯基:什么?噢,是的,她可以带走小猪。(埃里尔对她竖起拇指。她跳了起来,快乐地尖叫着。卡图兰微微一笑。)
埃里尔:好,好,让我们现在带你去洗干净,再送你见你妈妈和爸爸。他们一直在担心你。(埃里尔牵着她的手,她快乐地向每个人挥手道别。埃里尔带她出了门。图波斯基和卡图兰缓缓地别过脸来相互对视着。顷刻,埃里尔缓缓走进,将身后的门掩上。)
他们发现她身旁还有一大桶绿色的漆,你知道那种铁路隧道里暗中闪光的漆吗?所以,需要的话可以漆好多。在他说的地方他们还发现了父母亲的尸骨,在许愿井边。所以他供认他谋杀了我们完全不知道的两个人,他还供认他谋杀了一个没有被谋杀的女孩。
图波斯基:为什么?
埃里尔:为什么?你在问我为什么?
图波斯基:是的,我在问你。
埃里尔:噢?图波斯基,你知道吗?你是一号,你自己回答。
图波斯基:埃里尔,今天我不希望看到你的违抗。
埃里尔:呃,行,你说了算。
图波斯基:这个案子,到此为止,你可以向局长汇报了。
埃里尔:小女孩还活着你似乎并不高兴!可小女孩活着连这个家伙都很高兴!不高兴不就是他作弄你的笔录嘛!(图波斯基在故事稿件里翻找着那一篇。)
图波斯基:显然这女孩被漆成绿色并放在小猪一起是为了模仿……
埃里尔:是模仿《小绿猪》那故事。太棒了,图波斯基。你的想法肯定来自绿漆和小猪。问题在于,为什么?为什么他们没有也杀了她?而他为什么说他杀了?
图波斯基:嘘,我在细读这故事,看看有没有任何线索。
埃里尔:(大笑)我们只要问他!
图波斯基:我说了,我在细读这故事。
埃里尔:(对卡图兰)你能告诉我们那哑巴女孩为什么还活着吗?
卡图兰:(停顿)不。不能,我没法说。但我很高兴她活着。我很高兴。
埃里尔:我相信你很高兴她活着。我相信你很高兴她活着。我相信你比他更高兴她活着。我要问你另一个问题,凭我刚才的一点直感,因为现在我也有了直感。我觉得图波斯基先生的侦案才华正影响着我。那个你们割掉他脚趾,让他流血致死的犹太小男孩,他的头发什么颜色?
卡图兰:什么?
埃里尔:他的头发什么颜色?
卡图兰:棕黑色。是那种棕黑的颜色。
埃里尔:“是那种棕黑的颜色。”很好。考虑到他是个犹太男孩,“是那种棕黑的颜色。”很好。可惜他的妈妈是个爱尔兰人,所以她儿子完全象个红发的混血。你还要我问你那个死在野地里的女孩吗?
卡图兰:不要。
埃里尔:不要。因为这两个孩子你一个也没杀,对吗?
卡图兰:是的。
埃里尔:你甚至从来也没见过这两个孩子,对吗?
卡图兰:是的。
埃里尔:是你指示你哥哥杀了他们吗?
卡图兰:我根本不知道这一切,今天才知道。
埃里尔:你哥哥还杀了你父母?
卡图兰:我杀了我父母。
埃里尔:你杀了你哥哥,这是我们唯一能够确凿指控你的谋杀罪。根据罪行已减轻的情况,我非常怀疑你会被处决。所以我认为你应该极为谨慎,承认杀了……
卡图兰:我杀了我父母。(停顿)我杀了我父母。
埃里尔:我相信你杀了。(停顿)但你没有杀任何孩子,对吗?(卡图兰点头,他垂着头。)你作证,图波斯基。(埃里尔点了支烟,图波斯基恢复了他的神情,在桌前坐下)
图波斯基:干得漂亮,埃里尔。
埃里尔:谢谢,图波斯基。
图波斯基:还有,我刚才很高兴小女孩还活着。我只是不想在办案时流露自己的真实情感,就是这样。
埃里尔:哦,我明白……
图波斯基:你明白吗?(停顿)哼。那么,嗯,只是出于我个人的好奇,在你因谋杀另外三人而被处决之前,卡图兰先生,你为何要供认你杀了那些孩子呢?
卡图兰:是你们逼我杀了迈克尔。当你们发现第三个孩子时,你们会发现我杀了我父母。我觉得如果我自己承担这一切,正像你所希望那样,我至少能保住我的小说。至少我的小说还在。(停顿)至少我的小说还存在。
图波斯基:哼。那真是太遗憾了,对吗?
卡图兰:什么遗憾?
图波斯基:我们保留你小说的先决条件是你老老实实地坦白犯罪的整个过程。现在你没有杀害另外两个孩子的供词以及我的地板上踩满的这混帐的绿色油漆,确凿地证明了你原先的供认不符合事实,对吗?这样的话,显然,由于你的供认与事实不符,你的小说就得烧掉。(图波斯基搬过垃圾桶,往里浇了些汽油,拿起了火柴。)
卡图兰:你不是在开玩笑吧。
图波斯基:这是你的头套。请你套上。我把火点上。
卡图兰:埃里尔,这是……?
图波斯基:埃里尔?作为信守诺言的人,我们曾许诺,如果他如实供认,我们将不烧掉他的小说,这是否属实?
埃里尔:天哪,图波斯基……
图波斯基:这是否属实,我们曾许诺,如果他如实供认,我们将不烧掉他的小说是或不是?
埃里尔:是的,情况属实。
图波斯基:他是否供认他杀了一个犹太男孩而事实上他并没有杀?
埃里尔:是的,他供认了。
图波斯基:他是否供认他用剃刀片杀了一个女孩而事实上他并没有杀?
埃里尔:是的,他供认了。
图波斯基:他是否供认他杀了那绿得刺眼的孩子而那孩子根本就没死?
埃里尔:是的,他的确供认了。
图波斯基:那么,作为信守诺言的人,我们是否有权烧掉卡图兰先生的所有小说?
卡图兰:埃里尔……
埃里尔:(悲哀的)是的。
图波斯基:我们是有这权力。我们这里大约有四百篇故事,如果把刊载了他一篇故事那些本《解放》收缴过来,那就是他一生的作品,对吗?那就是他一生的作品。(图波斯基掂了掂他手中的小说。)合在一起也没多少。我是否该在他的小说上再浇点汽油,是否有点危险?我担心会烧到我自己。
卡图兰:埃里尔,请……
图波斯基:套上头套,我说过了。(图波斯基点燃了桶中的火,小说文稿还在他手中。)
埃里尔:埃里尔!
图波斯基:(停顿)埃里尔?
埃里尔:(停顿)我知道这一切都不是你的过错。我知道你没有杀那些孩子。我知道你不想杀你的哥哥,我知道你杀你的父母完全有正当的理由,我为你难过,我真的为你难过,我过去从不对任何被拘留者说这种话。
但这最后一刻,我要告诉你,我从来就没喜欢过你的故事。你知道吗?(埃里尔将图波斯基手中的小说文稿拿了过去。)你还是把头套套上吧。(卡图兰走上前去带头套,但他停住了。)
卡图兰:我记得你说你要带我去隔壁房间,你要我在那里带上头套,对吗?
图波斯基:不,不,我们就在这里枪毙你。我刚才在胡说。就跪在那儿什么地方,别让你的血溅我身上。
卡图兰:但你说带上头套后你给我十秒钟,你这也是胡说吗?
图波斯基:嗯……
埃里尔:我们给你十秒钟……
图波斯基:我们给你十秒钟,我开玩笑,我开玩笑。(卡图兰跪在地上,图波斯基掏出手枪,上膛。卡图兰悲哀地盯着埃里尔。)
卡图兰:我曾经是个好作家。(停顿)这是我唯一的愿望。(停顿)我曾经是。我曾经是。
图波斯基:“曾经是”是个关键词。
卡图兰:(停顿)是的。“曾经是”是个关键词。(卡图兰套上头套。图波斯基瞄准他。)
图波斯基:十、九、八、七、六、五、四……(图波斯基击中了卡图兰的脑袋。他倒在地上,死去,鲜血渐渐渗出头套。)
埃里尔:喂,你干嘛干那种事?
图波斯基:我干了哪种事?
埃里尔:你说过你给他十秒钟。那不地道。
图波斯基:埃里尔,让他跪着,头上套着套子,枪毙他,这还有什么地道不地道?
埃里尔:那也得干得地道。
图波斯基:听着,我今天听够了你的牢骚话。你怎么啦?你用那种方式看待它,我们破了这个案子,对吗?嗯,对不对?
埃里尔:我想是的。
图波斯基:那就是你七十岁时更多的糖果,是不是?(埃里尔叹息)听着,把手续表格做好,把房间冲洗干净,把这些小说烧了。好吗?我得去同哑巴女孩的父母谈一下,警告他们小猪的事。
(图波斯基下。埃里尔朝桶里加了些汽油,然后看着手中的一叠小说手稿。死去的卡图兰慢慢地站了起来,脱下头套,露出鲜血淋漓、弹孔炸开的额头,他注视着桌前的埃里尔,说……)
卡图兰:在临死前给他的七又四分之三秒的那一刻,卡图兰构思着最后一篇故事来为他的哥哥祈祷。他的构思更像是一篇故事的脚注,那脚注说……(迈克尔出现在门口的弱光中。)
一个名叫迈克尔•卡图兰的健康快乐的男孩,在即将要遭受他父母连续七年拷打折磨的那个夜晚,见到了一个长着一张微笑大嘴的的枕头人。他同迈克尔坐在一起,聊了一会儿。
枕头人告诉孩子他将面临的可怕生活以及他将死在他唯一最亲密的弟弟手中,被闷死在监牢冰冷的地面上。枕头人建议,为了避免这恐怖的一切,迈克尔最好自己结束自己的生命。而迈克尔说……
迈克尔:但如果我自杀的话,我弟弟就永远听不到我被拷打的惨叫,对吗?
卡图兰:“是的”,枕头人说。
迈克尔:如果我弟弟从未听到我被拷打而惨叫,他可能永远不会写那些他要写的小说,对吗?
卡图兰:“是的”,枕头人说。于是迈克尔想了一会儿后说……
迈克尔:那么,我想我们应该保持事情的原样,我被拷打而他听到了我惨叫的整个过程,因为我想我会喜欢我弟弟的小说。我想我会喜欢它们。(迈克尔在追光中暗转。)
卡图兰:故事以一种时尚的悲凉结尾,迈克尔受尽了折磨,卡图兰写下了那全部的小说,可是被一位冷血的警察将它们一烧而光而永绝于世。故事原本该这样结束,可突然被打断,因为一颗子弹提早两秒钟打穿了卡图兰的脑袋。
也许故事不那样结束更好,因为那个结尾并不确切。这位冷血的警察,出于只有他自己知道的原因,没有将那些小说稿付之一炬,而是小心翼翼地把它们放进了卡图兰的档案,贴上封条,以便将它们封存到五十年后。
(埃里尔将小说稿放进档案箱。)
这一变故搅乱了作者原本时尚的悲凉结尾,但不管怎样……不管怎样……它多少保存了这一事件的精神本质。(埃里尔用水浇灭了桶中的火苗,灯光缓缓变暗至暗场。)(全剧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