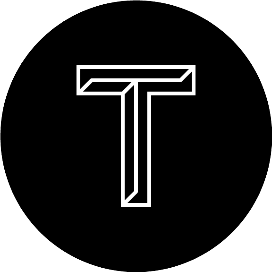《人海同游》是一部讲述导演蔡杰追寻家族和个人情感的电影。因台风天气而延误拍摄,但最终成功完成。电影涉及多个角色和情节,包括导演和演员之间的交流和合作。电影的制作过程中经历了许多挑战和困难,但最终完成并上映。电影的主题涉及家庭、情感、人生等。
电影原计划在香港拍摄,因天气原因延误。导演蔡杰和他的团队经历了长时间的等待和准备,最终成功完成拍摄。
电影的制作过程经历了许多挑战和困难,包括资金问题、选角问题等。导演蔡杰和他的团队克服了这些困难,最终完成了电影的制作。
电影探讨了家庭、情感、人生等主题。通过讲述主人公们的经历和成长,电影表达了人生的无常和变化,以及面对困境时的坚持和努力。

2021 年 10 月 9 日,台风 8 号风球正式登陆中国香港。
凌晨五六点,天朦朦亮。和往常一样,导演蔡杰习带着相机,只身前往码头,准备抓点空镜。空旷的街道上,一只红色塑料袋被人挂在树梢,随风狂舞,喇叭里循环播放着台风警报,提醒路人小心风雨和积水 —— 这是电影《人海同游》的最后一个镜头,结束得安静、轻巧和日常。
为了这场风雨戏,5 位内地主创在香港等待了太久。
2021 年 8 月底,《人海同游》剧组前往香港筹备拍摄。奇怪的是,
整个 9 月香港都未曾「打风」,平静得异常 —— 上一次出现这种情况还是 6 年前的夏天,当时因厄尔尼诺现象的影响,香港度过了 70 年以来首个未经台风侵袭的八九月。
没有准确的天气预报、没有工业化的制作流程、没有充足的预算,但蔡杰不想改戏。
对他而言,台风天的画面从写剧本开始,甚至是孩童时期,就已经刻在脑子里了。

南方长大的孩子一谈到台风,总带点特殊的情感。蔡杰记得,台风天就意味着放假,风力不那么强烈的时候,他还可以一边吹风一边玩。制片人莫津津的台风记忆则伴随着气味 —— 危险的气息恰好被方便面和罐头鱼的飘香掩盖,这些平日里的「稀客」唯有在台风天才得以上桌。台风过境,大人不便出门买菜,幼年的她却心甘情愿被这样「打发」。
这部电影也事关女主人公「麦婉婷」情感世界的一场台风。来得再激烈,过境之后,人们依然会继续原本的生活轨迹 —— 它不停留,也不改变什么。影片气质基本确定后,前期筹备便开始了。
没有人为制造台风的资金,就只能靠天吃饭。为了实地考察剧本中的想象能否落地,从 2018 年到 2020 年,每逢夏天台风季,蔡杰一定会赶回广东,一个人拿着相机去郊区的荔枝林等待。他承认,这是一种最笨的方式,但好在等待对他而言不算陌生 —— 超乎常人的耐性只是他作为创作者,或者说纪录片导演的基本功之一。

严格算起来,在香港的正式拍摄时间只有不到 10 天。整整 3 个月,一群人就这样硬生生地从夏末等到初秋。这段日子过得紧密又松散,如今回想起来,莫津津才意识到:那时全组没有一个人考虑过预备方案,偶发类似「如果拍不到台风该怎么办」的忧虑,大家也会立刻打岔:「没事儿,一定会有的。」盲目的乐观既是虔诚的祈祷,也带有一丝赌徒般的侥幸 —— 好在老天爷最终还是给足了面子。
首日台风戏拍摄结束后,监制关锦鹏致电问候:「今天拍得怎么样,这下是要风有风,要雨有雨了哦!」莫津津笑着回复,是的,老天爷突然间什么都给了。
天色将晚,空荡荡的新居卧室,麦婉婷躺在熟睡的男友身旁,陷入了回忆。远方
城中村的灯火隐隐现现,屋内萦绕着她的独白和啜泣,「爸爸小时候明明对我那么好,为什么说走就走?」没有答案,甚至没有被枕边人听清,问题就这样掉在了地上 —— 如同掷出窗外的一块石头,不起眼,孤零零,却是麦婉婷全片唯一一处情绪出口。一念这句台词,女演员林冬萍就无法抑制情感,仿佛替麦婉婷把多年积攒的委屈尽泄而出。
打口碟和父亲的往日来信不断撬动着麦婉婷的思绪,海浪声与风声交织,梦境和现实缠绕,雾气在台风天弥散开来,连同回忆,
把荔枝林
一起铺成了幽蓝色。带着对过去、代际、自我的种种疑问,麦婉婷踏上了前往香港的旅途。
《人海同游》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寻父之旅」。现实中,蔡杰身边的朋友大多在 25 岁到 30 岁期间迅速稳定下来。他们在工作上慢慢晋升,不再更换居住的城市与生活方式。这种看似稳定的生活,曾给他们带去一些恍惚和迟疑 —— 仿佛一眼望到头,人生就这样了。这些瞬间,麦婉婷也有过,她中学时憧憬的未来并不是眼前的样子:她也曾渴望冒险,去不同的地方看不同的风景。
蔡杰和编剧王寅不满足于单纯的家庭伦理叙事,于是,一个和麦婉婷截然不同的角色 —— 人类学家「鱼生」诞生了。他如同一阵台风,席卷了麦婉婷的生活。「
(在香港寻找父亲的)
这段时间本不属于麦婉婷,她只是借来体验,然后又还了回去。」蔡杰说。
2015 年在《南方都市报》工作的经历,也像蔡杰过往的一段「借来的时间」—— 与《人海同游》的英文片名「Borrowed Time」对应。白天,他忙着跑突发现场,被要求
以「短平快」的风
格输出大量的信息,
这对
蔡杰而言有些困难:
「那阵子,每天交完稿已经晚上八九点了,回到出租屋睡几个小时,起来之后就会问自己要干什么,
创作要怎么继续?
」他一心想着结束这样的日子,重新开始创作。
林冬萍最早接触表演是在高中的话剧社,后来在大学认识了蔡杰和王寅,三人常常搭档拍摄短片作业。本科毕业后,她先后从事过电视新闻和广告营销,其间也会偶尔「上镜」,但始终和表演不太一样。她遗憾自己非科班出身,没有在最合适的年纪入行。「某些时刻,我也想离开南方,去北京,尝试正儿八经地进入这个圈子。」当时,林冬萍已经有了稳定的家庭,远游并非一件易事。
2017 年,《人海同游》刚进入创投阶段,剧本引起了业内广泛关注。铁三角 —— 蔡杰、王寅、林冬萍 —— 原以为能彼此陪伴,走完长片创作的全程,但林冬萍选择了先行暂别。
蔡杰坚持要为
林冬萍走完
选角面试
流程,
他
带着相机从
深圳赶
来广州,
为她录下了
一段试戏视频。
他们都以为,林冬萍和麦婉婷的缘分结
束在了
那个傍晚。

2019 年年底,《人海同游》的投资款基本筹齐,约定和投资公司年后签约,不料疫情来袭,电影业停摆,加上演员档期迟迟未能协调,项目陷入停滞。「当然我也可以选择一直等待,但时间是会消磨人的。我怕再等下去,就不想讲述这个故事了。」蔡杰说,「人总是在慢慢变化的,现在让你特别动情的故事也可能不再是你下一个阶段的人生课题。所以我一定要去完成它,不管怎么样,它会产生一个结果。」
疫情让蔡杰放弃了工业化的制作流程。他独自承担了绝大多数资金风险,在妻子和最亲密的朋友的支持下,完成了第一笔拍摄经费的筹措。资金问题解决了,还剩麦婉婷的选角没有敲定。蔡杰想到了林冬萍,「那阵子,她已经过上了完全不一样的生活,我好像也觉得她跟表演或者这部片子没什么关系了。但等到要拍的时候,好像一切机缘又让我把她抓了回来。」
过去两年,林冬萍的重心在家庭生活,离开了职场,也很久不再接触拍摄。面对蔡杰的再度邀请,她也有过片刻迟疑,但最终被老友的一席话打动:「他说,很难、没钱、没环境,整个社会也在停摆。但是他还想继续。这个项目已经走了太久了,不知道疫情什么时候能结束。如果他这个时候不动起来的话,这个项目可能就胎死腹中了。」
蔡杰最后问,「你愿不愿意一起,把这个事情继续下去?」
「只要你觉得 OK 的话,我没问题的啊。」林冬萍答应下来。
有段时间,朋友圈隔三差五出现林冬萍的健身视频,朋友们知道,这个项目再次启动了。

「故事
从更远的地方重说。」雷光夏在片尾曲《小故事》中浅浅吟唱着,关于《人海同游》的起源,还能追溯到更早的日子。
2014 年,中秋前夕,还在中国传媒大学读研的蔡杰拍了部剧情短片《归省》:一台机器,两页 12 号字体的剧本,两三天时间,两三千预算,三四个朋友的剧组 —— 这是他的首部剧情作品。完成后,很快有了一些回响,这部作品被评为第 11 届中国独立影像展的最佳短片。「原来剧情片这么简单,那是不是也可以再拍部长片?」蔡杰笑着回忆道。
《归省》的灵感源于王寅的一位女性朋友:年轻的她没和家人商量,就决定远嫁日本。

这个选择让蔡杰感到有趣。生于南方,他乡求学,奔波四处的拍摄经历,让二十出头的他因乡愁生发了许多关于家庭羁绊的思索。
「对我而言,《归省》更多在讲述一个回家的故事。
在那个年纪,让我感怀的是无论外面的生活怎样,最重要的是有家可以回。
」短片借中秋团圆,讲述了回国探亲的女主角与父辈和同辈之间的关系变化。
「往后再过渡差不多五六年,就到了《人海同游》的年龄阶段。」近 30 岁的年纪,蔡杰对婚姻、代际等问题有了新的观察和思考。还在报社工作的他,和彼时正在日本读研的王寅有一搭没一搭地聊起了剧本,一个新的故事渐渐有了雏形。「我们配合的方式就是在微信上相互『丢』灵感,然后找时间约电话会议,两三个小时漫无目的地聊人物、家庭、剧情的走向。」
作为潮州人,地缘和文化上的暧昧让他对香港有天然的亲近感。几乎每个潮汕家族中都有一位香港的「远房亲戚」,每逢过年,便会带着各种礼物返乡,连同带回的还有孩子们对大都市的初次想象。「1997 年的香港回归也是我们这一代人挺重要的集体回忆。」蔡杰说,「我家甚至还特意买了一盘香港回归大型文艺汇演的 DVD。」

世纪交接的数十年中,翡翠台、凤凰台带来了两岸三地的文娱内容,蔡杰的电影启蒙也从那时正式开启。「我在广东潮汕的农村长大,小时候那边虽然比较闭塞,但还是可以搜到凤凰卫视电影台。我记得当时每天都在播放各种各样的香港电影,一开始对电影的认知也是从那时候开始的。」
当一个孩子每天接触的都是 TVB 或香港新闻时,香港其实就成了生活的一部分。和多数广东孩子一样,蔡杰的粤语习得是一个自然的过程。「那个时候开始,就已经能听懂这门语言了。再等到大学,去到了广府文化,在大家都说粤语的环境里,你也会试着开始和别人用粤语沟通。」
直到 2008 年,蔡杰才第一次踏足香港。他没做任何准备,刚过罗湖口岸手机就没了信号。突然间与原有世界断联的陌生体验让他感到新鲜,兴奋或是警惕之下,人总会本能地放大对眼前环境的打量。「一个人在陌生的环境里打探,那种感觉特别像《人海同游》中麦婉婷去香港的状态。」

香港带给他新奇的体验:维港,东环,狭小的民居,以及日后成为《人海同游》取景地的油麻地水果贸易档口 —— 一切都像极了儿时轮播了几十遍的《开心鬼》那么具体。
2018 年,为了更好地投入剧本创作,王寅回国,和蔡杰开始一起实地调研。「当时我们去油麻地果栏。一天 24 小时,我们中午去看一下,傍晚去看一下,深夜再看一下 —— 发现深夜还有好多人,我们就继续从深夜等到凌晨,等他们忙完之后,我们再跟上去问,能不能跟他们一起去喝杯茶。」从一个个群体开始,再到一个个空间,这一过程恰如王寅研究生专业社会学的田野调查。调研结束后,二人根据所得,继续修改剧本。
《人海同游》创作初期,蔡杰也曾困惑于找寻这个故事的切入角度。18 岁后离开家乡,等他真正拍摄长片时,反而产生了一种「近乡情更怯」的感受。但不同于他的原生文化,广府文化与他保持着一种恰当的距离,让他持有一种「亲近的旁观」,「以一个广东作者的视角去拍香港」因此成为蔡杰和王寅的创作起点。
「我们能不能就去拍一种粤港的关系?」如同对广府人的贴身旁观,亦近亦远的香
港给了蔡杰一个靠近的理由。

2011 年夏天,刚考完研的蔡杰闲来无事,和两个朋友约着一起前往藏区寺庙支教。
那年,丁真的笑容和歌声还未走红,理塘也没有成为 5A 级景区。3 个年轻人搭火车到成都,再坐大巴进山,最后转摩托到达目的地。高原反应第一天就来了,头晕呕吐,疲劳乏力,蔡杰在床上度过了进藏的第一周。
一对双胞胎很快引起了蔡杰的兴趣。两兄弟年纪不大,性格不同,却被众人共同期许着成为转世活佛。人群之中,蔡杰也在等一个答案。
「拍之前,我也没有意识到会跟那么久。只是他们实在太耀眼了,你一眼就会看见这两个小孩。」第二年,他独自回到理塘,开启纪录片《云上佛童》的拍摄。蔡杰不曾料到自己与这对双胞胎的缘分将从 22 岁开始持续整整 9 年 —— 从研一到毕业,工作换了两三份,但只要夏天一到,蔡杰总会带着相机如期而至。

两兄
弟在镜头注视下慢慢长大,陆续还俗,最终在「做活佛」和「做自己」之间选择了后者。蔡杰知道,这段拍摄关系将随着答案的浮现暂告一段落。谈到分别,蔡杰说,「拍纪录片其实就是一个和人打交道的过程,只是有的交集快,有的慢。大家有过相互陪伴,彼此打动的时刻就够了。」
最后一次拍摄结束,他将相机留下作为礼物。次年,《人海同游》正式开机。
蔡杰形容自己性格温吞,不似王寅那般冷静坚决。
在永别与永恒之间,他更习惯停留在意味模糊的灰色地带,「所有关系都有结束的一天,但这不影响你去感怀它,享受它。
」这句话恰当地概括了蔡杰的处世哲学,也带出了《人海同游》的世界观 —— 在不同的风景中,遇见不同的人,穿过了那片雾,你就不再是原来的那个人。
《人海同
游》上映不久,一则豆瓣短评引人注目:「这个导演就是靠人脉在拍片」。朋友们揶揄蔡杰,他也觉得好笑,「恰恰因为是新人导演,我什么权力和人脉都没有。
」主创团队的搭建过程其实很简单 —— 剧本和角色固然重要,但更离不开人与人之间的同频相吸,监制关锦鹏便是被蔡杰吸引而来的前辈之一。
筹备期间,关锦鹏陪蔡杰试镜,现场聊完后,演员推掉了角色。蔡杰没有太放在心上,猜想对方可能是不喜欢剧本。当晚,关锦鹏打来电话,主动问起蔡杰为什么明明觉得合适,却没有尽力说服对方,并以他多年的经验,带着蔡杰一五一十分析失败的原因 —— 究竟是某方面准备的缺失,还是现场游说的态度不够坚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