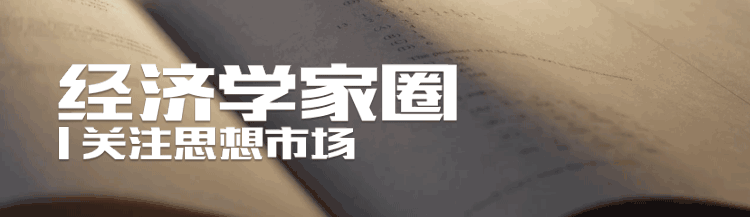

本文源自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智库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资本论》研究室主办的“智库名家论坛“的发言整理。
何祚庥首先回顾了物理学历史上那场旷日持久的关于光的本质争论。在物理学史上有一个长期争议的重大理论问题:光是粒子,还是波?这两种理论,整整争吵了200多年。最后是在1905年,在爱因斯坦讨论光电效应的一篇论文里,引入普朗克常数h,统一为光的波粒二象性的理论。而更重要的是,正是由于人们对光的本质有了更深的理解,由波和微粒的分歧,走向“波粒二象性”的统一。这就导致20世纪物理学的大革命,出现了相对论和量子力学。何祚庥进而指出,经济学或政治经济学里的纷争,至今已有150年。那么,人们能否借鉴物理学“从争论到统一”的历史经验,构建一个新的理论,解决已持续150年之久的争论。他指出,这并不是人们第一次提出这一问题。在中国,樊纲教授著有《现代三大经济理论体系的比较与综合》一书;在西方,萨缪尔森在《经济学》(第19版)中写了一篇《一个折衷主义者的宣言》。
对于如何折衷或统一,何祚庥指出,以劳动价值论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仍然停留在只讨论“三要素”的水平,人们能否建立一个包括知识或科技进步和市场进步在内的马克思主义“四要素”的“新”政治经济学?这种“新”政治经济学建立在一个劳动和效用相统一的新劳动价值论框架下:效用≡使用价值WS=社会平均必要简单劳动所创造的价值WJ×广义科技效率因子N。为了使大家理解这一新的框架,何祚庥结合物理学的“无量纲”概念对其进行了详细的讲解,并对丁堡骏等学者的批判进行了回应。
何祚庥在对马克思、瓦尔拉斯、凯恩斯三大理论体系比较和综合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新颖又值得深思的问题:为什么经济学的左派和右派不能统一在一个旗帜下,共同为中国经济发展服务?在何祚庥激情澎湃的演讲之后,樊纲、杨春学和李帮喜作为嘉宾进行了发言。
著名经济学家樊纲首先对何老九十高龄仍坚持在科研一线表示钦佩。随后,樊纲回顾了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学习期间写作《现代三大经济理论体系的比较与综合》的情景,指出2017正好是这本书写作完成30周年,在这30年中,他虽然一直希望对于这个主题进行更深入的研究,但是,由于对中国经济现实问题的研究投入了太多精力,以致这个愿望一直没有实现。何老的研究重新引起了他的兴趣,并借此机会对何老等给予他支持和帮助的学者表示感谢。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智库副理事长、首都经贸大学教授杨春学对何祚庥的演讲进行了评述。杨春学指出,何老将物理学中的无量纲系数引入经济学,这一方法探讨了效用理论的两个著名问题。一是效用计量问题。按照基数效用论的基本观点,效用的大小可以用Util这一类似无量纲的计数单位进行测度。二是人际效用比较问题。如果个人效用可以用一种绝对尺度在基数上进行测量,就可以确信人际间效用的可比较性。杨春学在发言中还对何祚庥夫人庆承瑞借助于“功率”“能量”等概念深入浅出地讲解物理学方法在经济学上应用的补充发言给予了高度评价。
青年学者李帮喜指出,何老今天讲的关于使用价值(或效用)的度量问题,其实日本著名数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越村信三郎早年也作过相关研究,但其对于效用的度量研究最终并未取得成功。众所周知,日本关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数理研究有着很好的传统,三位数理政经学者森岛通夫、置盐信雄、越村信三郎因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数理研究的卓越贡献获得过诺贝尔经济学奖提名。这三位日本学者至今仍对数理政经学者产生影响。国内一些学者也在从事关于数理政经方面的研究,何老提出的这个问题其实也应属于数理政经的研究范畴。李帮喜在发言时还讲述了一个鲜为人知的故事:华罗庚晚年对数理政经有深入的研究,八十年代华老在《科学通报》发表过关于大规模经济规划与矩阵理论的系列文章,通过Perron-Frobenius定理证明了华氏命题(对偶不稳定性定理)。
在三位嘉宾发言后,经济研究所资深研究员刘霞辉和赵志君作了精彩点评。
刘霞辉指出,对于何老所讲的科技进步项A,西方经济增长模型发展是以解释A展开的。其中,以罗默和卢卡斯为代表的“新增长理论”利用人力资本解释经济增长中的A。新经济增长理论的重要内容之一是把新古典增长模型中“劳动力”的定义扩大为“人力资本投资”,即人力不仅包括绝对的劳动力数量和该国所处的平均技术水平,而且还包括劳动力的教育水平、生产技能训练和相互协作能力的培养等等,这些统称为“人力资本”。正是人力资本理论的提出,西方经济增长理论得以完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剩余价值理论,认为劳动创造剩余价值。而现代社会,劳动形式和复杂程度与马克思时代完全不同,这就需要对劳动的内涵加以拓展,如具有人力资本的劳动应获取人力资本的补偿,而剩余价值中也包含人力资本创造的价值。在现代社会中有必要对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理论进行创新。
赵志君在点评中分享了其利用量子力学和热力学方法研究经济学的心得体会。对于何院士提出的问题,他指出,何老提出了很有意义的研究方向,但劳动价值论不仅从计算方法上是社会平均的统计概念,实际上价值论是一个宏观概念,从方法论上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论属于整体主义的,目前没有公认的最优化方法问题,对应的数理方法是概率统计。劳动价值论还存在一个问题是其涉及的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的概念都是相对的、时变的,很难给出一个客观基准,所以劳动价值的计算不具有很强的操作性。效用价值论是个人主义的概念,有公认的个人主义的最优化方法,对应的数量方法是微积分。效用的评判在市场条件下有客观标准,可以通过市场交易发现效用或使用价值。
就何院士提出的效用价值论和劳动价值论相统一的计算公式,我认为首先存在量纲和价值尺度的统一问题,效用的单位是什么?如何转化成劳动价值的单位?在何老那里似乎没有得到解决。其次,西方经济学的效用函数是消费品的非线性函数,如何通过效率因子转换成劳动的线性函数,本身是一个需要回答的问题。再次,何老没有在市场经济的框架下探讨效用价值和劳动价值的统一问题。我认为要实现两个概念两种理论的统一,必须将两者换算成统一的尺度,这个尺度只能是货币。即只有将效用和劳动都换算成货币之后才能比较,否则两派无对话的语言基础。最后,效用论的可比性建立在边际的基础上,而劳动价值论的万比性建在社会平均的基础上,不能做简单乘法,只有在方法论上实现突破,才可能找到效用论和劳动价值论统一的办法。如果能将效用价值论和劳动价值论统一起来,也就实现了宏微观的统一。从方法论上,统计热力学、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方法论值得经济学家借鉴。
随后,经济研究所《资本论》研究室研究员陈昌兵和副研究员王瑶也进行了点评。
陈昌兵指出,何老分析探索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劳动价值论和西方经济学中的效用论相统一的问题,这对于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很有启发。西方经济学运用效用、成本等概念构建了微观经济分析框架,具有较强的实用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尤其《资本论》是以劳动、价值等概念为基础构建了分析资本主义社会运行的理论框架,具有内在一致的逻辑性、抽象性,能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对于解决我国社会现实的经济问题,西方经济学具有工具方面的优势,而对于解释经济运行中存在的本质问题,西方经济学却无能为力,而这却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最有优势的地方。因此,在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应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核心,吸收西方经济学的研究成果,更好地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
王瑶指出,何老用现代物理学方法建立劳动和效用相统一的价值论,试图从逻辑起点上探索构建新的经济理论体系的可行性。在经济思想史上,马歇尔在构建新古典主义理论体系时,曾将牛顿力学的经典术语引入到经济学概念之中,“价格弹性”“货币流通速度” “通货膨胀” “均衡”等用语深入人心。马歇尔晚年提出“经济学家的圣地在于经济生物学而非经济动力学”,他赞赏的“经济发展有机观”与生物学中的“达尔文主义”类似。鉴于此,王瑶提出在构建新的经济学理论体系时生物学方法可以作为物理学方法有益补充的设想。
最后,经济研究所《资本论》研究室主任、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智库办公室主任郭冠清代表论坛主办方作了总结发言。郭冠清指出,经济研究所非常重视物理学方法在经济学上的应用,曾邀请两位经济学家就量子力学、热力学在经济学应用进行过讲解,这次更有幸邀请到何院士作专题讲座。我们希望借助物理学方法,像萨缪尔森利用比较静态均衡方法奠定现代经济学大厦基础一样,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作出有益的探索。
相关阅读
《杨振宁当年回国已经做好回不去的准备》
作者刘全慧,湖南大学理论物理研究所所长
十年前,我带女儿回科学院理论物理所,拜见了许多科学家。见到何祚庥先生时,叫她叫喊爷爷,何先生说,“只能叫伯伯!”。这位老伯伯,今年开始步入“90”后。据我所知,他和科学网的陈方培先生一起,可能是科学网的庞大队伍中仅有的两位奔百者。今年,我在湖南大学担任“岳麓论坛”的坛主,希望请何祚庥先生过来开个讲座。他回了一句,大意是,你敢请“90”后? 但是,话音未落,5月20日-28日,他和庆先生就在国防科大讲了一周的课,主题是经济学!6月13日,他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开坛设讲。他说:“我现在感兴趣的问题是。能否建立一个经济热力学的新体系?已做的事情是:1)已弄清楚何谓市场经济的均衡态。2)已找到一个守恆律,劳动价值守恒定律。3)接下来,当然是能否建立一熵增加的定律,以便解答经济系统的发展方向问题了。…”何先生现在每天刷微信,有时一天会超过10条。相比较而言,我一个月也未必会写一条。在他和庆先生离开长沙前一晚,我和黄明球教授(戴元本先生的高足)过去看他,相谈甚欢。纵然青春不老的杨振宁先生,不仅斑斑点点,而且步履蹒跚。我仔细端详了他们二老的手和脸,不但没有老年斑、连普通的斑纹也少,从心态到身态,就是两位伯伯(南方人有尊称伯母为伯伯的习惯)。孙昌璞老师的评价是:“他们是特殊材料做成的!”我个人的总结是:物理研究是最好的春药。当然,我口袋里有很多佐证材料。
都是杨振宁的铁粉。我于是乘机自我吹嘘为“杨学”的创立者。何先生立即戏称我为“杨学大师”。他对杨先生的评价如下,在物理学上,“杨振宁是爱因斯坦之后,贡献最大的物理学家”;对中国社会的贡献,“他推动了中国的改革开放。”“杨振宁当年回国,已经做好回不去的准备!”在1970年代起,杨先生不但自己回国,还起劲地推动中美之间的科学、文化的交流等。杨先生破冰之后,海外华裔回国的人流开始喷涌,1972年林家翘带领了20多人的代表团访问中,1972年,尼克松访华。1978年,改革开放。
杨先生在1971年的破冰之旅时,和何祚庥先生等中国内地理论物理研究队伍的代表有过座谈。回美国后,杨先生迫不及待地会见了Physics Today的编辑,11月份就发表了长篇谈话《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物理的印象》。特别提到“杨会晤了该小组(层子模型小组)的李炳安和何祚庥。”我问何先生是否知道此事,他说不知道。我觉得两方面的奇怪,杨先生返回美国后,难道我们没有收集杨先生回美国后的谈话? 第二,何先生不会去在意杨先生对“层子模型”的评价? 我立即把有关文章的照片发给了何先生。何先生的回复如下:“我从未读过杨先生的回美后的讲话。只记得那时,第一次见杨时,大家决定由李炳安讲层子模型,由我讲这一模型的场论基础,即复合场量子场论。当然,我会用到推广了的杨-费尔德曼方程。所以,杨就记住了我。”
顺便提到,杨先生肯定不会欣赏“层子模型”,因为他对“层子模型”的兄长“夸克模型”都不是很感冒。这一点在他2014年的文章中,有清晰的表达:“Despite its impressive success, the standard model is not the final story. To start with, dozens of constants need to enter the model. More important, one of its chief ingredients, the symmetry- breaking mechanism, is a phenomenological construct that in many respects is similar to Fermi's proposed “four-ψ interaction” to explain beta decay. That 1934 theory was also successful for almost 40 years. But it was finally replaced by the deeper U(1) × SU(2) electroweak theory.”Chen NingYang,The conceptual origins of Maxwell's equations and gauge theory Physics Today, 67(11), 45 (2014); doi: 10.1063/PT.3.2585. 除了杨先生对标准模型中的唯象部分不太满意外,我猜测,杨先生可能是物理世界之本源是场而非粒子论者。
和何先生的交往,可以追溯到28年前。1986年我进入郑州大学物理系,跟随赵祖森先生学习粒子物理。赵先生算得上一位隐士,除了读文献上课培养学生,澹泊寡欲,几乎不和外人交往,也从不出门参加学术会议。很久以后,我才知道他和周光召先生、何祚庥先生都是清华的同班同学。当时,张立仕教授是《广义相对论》课程的老师,不过我们经常在课后一起讨论量子力学,好几次师母过来找他回家吃饭。在1989年6月以前,我已经炮制出了一两篇文章。有一次,张立仕老师带我出去参加学术会议,似乎是承德师范学院主持的一次讨论量子力学基础问题的会议,会议上,第一次碰到了何祚庥先生。记得,我在会议上有个简短发言,然后和何先生有过短叙,他用铅笔给我导师赵祖森先生写了一封信,大意说,刘全慧手上的东西拿个硕士学位足够了,不必要另外再做硕士论文了。但是,导师赵先生觉得,还是应该再做一篇论文,而当我的论文完成的时候,《高能物理与核物理》发表了一篇题目完全一样的文章。感谢答辩委员会宽宏大量,还是让我毕业了。我毕业的时候,拿的是同济大学的学位,答辩委员会主席是华东师范大学的徐在新教授,主要成员有上海物理学界的前辈,当时在同济大学物理系的殷鹏程教授。答辩通过后,赵老师特别说,听说你有点酒量,今天聚餐就上点白酒吧。我大概灌了一瓶左右。当时,这点酒,还不在话下,现在已经畏酒如虎。上海答辩之后,我就去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做客座研究,当时,北京的气氛还是有点紧张。那个时候,理论物理所,还在两层楼的小房子里。当时,也见过何先生,但是聊得不多。很可惜,导师赵祖森先生在长期病疼的折磨之后,两周前(6月12日)驾鹤西归了。他去世前一月,我去郑州看老人,他躺在病床上,已经脱了人形,浑身僵硬,对外界没有反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