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托马斯·沃尔夫(Thomas
Wolfe,
1900—1938),二十世纪美国文学最重要的小说家之一,是第一位超越地区而广受好评的美国作家。1900年他生于北卡罗莱纳州阿什维尔,毕业于北卡罗莱纳州大学,在哈佛大学获得剧本写作硕士学位,后在纽约大学任教。沃尔夫创作于大萧条时期的作品描述了美国文化的变化和多样。他在短暂的一生中创作了四部长篇小说,分别是《天使望故乡》、《时间与河流》、《网与石》和《你不能再回家》,并以这些作品在美国文学史上获得与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刘易斯、福克纳和海明威差不多同等的地位。沃尔夫的作品感情奔放,文字流畅,气势磅礴;作者的主观感受强烈,以暗示和象征的手法有力地感染读者。1938年沃尔夫去世后,威廉·福克纳将他列为他们那一代最出色的作家,而自己则甘拜其下风。“垮掉派”作家杰克·凯鲁亚克也将沃尔夫视为自己的文学偶像。
“天使,望故乡!”这是英国诗人弥尔顿的一句诗,美国作家托马斯·沃尔夫借用它作为书名,写了一本关于故乡、关于成长的书:《天使望故乡》。小说中,尤金对家庭的冷漠、无情和家乡的偏狭、闭塞深恶痛绝,心中不时泛起“逃出”这种环境的冲动。而小说最后他选择了离开家庭,继续去哈佛深造,渴望去体验一种新的人生。就这样,很多时候,故乡真的只能遥望。而每一位对它充满眷恋的人,都拥有一颗天使一样念旧而纯真的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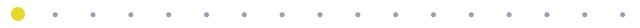
《天使,望故乡 》(节选)
托马斯·沃尔夫/文
朱小凡/译
······一石,一叶,一扇未曾找到的门:这石,这叶,这门。以及还有那些被遗忘的面庞。
赤条条地,我们被孤身放逐到这里。在母亲幽暗的子宫里,我们不识得她的面容;从她血肉牢笼中,我们来到这个莫可名状、无法言传的人间牢笼。
我们之中,有谁了解他的兄弟?有谁洞察过父亲的内心?有谁不是被囚禁终生?又有谁不是作为一个孤独的陌生人度过一生?
逝者已逝,在灼热的迷惘之中,失落,在暗淡余烬的点点星火之中,就这样失落了!无语地追忆着,我们寻找那种伟大而被遗忘的语言,寻找那条通往天堂的遗失的小路,一石,一叶,一扇未曾找到的门。何处?何时?
失落啊,风声悲泣,幽灵,归来吧。
.......
但是我知道,他冷漠空洞的眼神曾经变得幽深,泛起一种朦胧而强烈的渴望。这种渴望以前也曾经在一个死者的眼中浮现过,并把命运从芬切奇街引向费城。这个男孩手握石雕百合花茎的天使,心中荡起一股冷静而莫名的激情。他的一双大手上长长的手指握紧了。他觉得,在这个世界上他最想做的事情就是用一把凿子精雕细刻。他想把内心里某种幽暗而莫可名状的东西通过雕刻冰冷的石头派遣出来。他想雕一个天使的头像。
......
他始终没有找到。他始终没有学会雕刻天使的头像。他雕过鸽子、小羊、表示死亡的交叠在一起的大理石质的双手,还有严谨优美的字母——但是唯独没有天使。这些虚度着逝去的年月——巴尔的摩放纵的岁月,工作与狂欢,还有布斯与萨尔维尼戏院,对石匠产生了灾难性的影响。他熟记了激昂的台词中每一个腔调,诵读着在街道上阔步穿行,双手舞动着种种激烈的手势——正是我们在放逐中盲目的前行与摸索,表达着我们的渴望。这时,无语地追忆着,我们寻找那伟大而被遗忘的语言,寻找那条通完天堂的遗失的小路,一石,一叶,一扇未曾找到的门。何处?何时?

他刚刚三十出头,但看上去要老得多。他的面容枯黄塌陷;蜡色的鼻梁像鸟嘴一样突出。长长的棕色胡须愁苦地耸拉着。
一次次狂饮搞垮了他的身体。他瘦得像根棍子,而且咳嗽不止。如今,在孤独而充满敌意的城镇里,他想到辛西亚,不禁害怕起来。他觉得自己得了肺病,快要死了。
他又一次孤身一人,满心失落。在这个世纪上,他既没有找到秩序,也没有获得安定,连立足之地也失去了。于是,奥弗利又开始在大路上漫无目的地漂泊。他向西面安然矗立的群山走去,心想那里不会有人知道他的恶名,同时希望在那个于此隔绝的天地里开始新的生活并恢复健康。
......
他们坐在热气腾腾的小屋里,周围弥漫着正在变熟的苹果暖洋洋的气味,这时,大风从山上呼啸而来,松林怒吼,遥远而狂野,光秃的树枝碰撞在一起,噼啪作响。他们一边削着、刮着、剥着手里的东西,话题从粗劣的插科打诨转到了死亡与葬礼:他们缓慢而单调地说着,带着一种邪恶的饥渴聊着命运,和刚刚入土的人们。他们继续聊着,而甘特则倾听着风声幽灵般的呜咽,被失落与黑暗所埋葬,他的灵魂沉入了黑夜的深渊,因为他看到,他必将死为一个陌生人——除了把死亡作为盛宴来享受的兴高采烈的潘特兰一家——所有的人都必将一死。
他像一个在极夜里渐渐死去的人,想到了自己青年时代的如茵绿草:那玉米、那李子树,还有成熟的庄稼。怎么会到了这里呢?失落啊!
......
他在一片黑暗中躺在摇篮里,洗过澡,擦过粉,喂得饱饱的,静静地思索着很多事情,最后沉沉睡去——无休止的睡眠消磨了他的时间,使他感觉到灿烂生命中的一天就这样一去不复返了。每当这种时候,他只要一想到,在获得与别人同样的身体上的自由之前,必须忍受各种不便、身体的虚弱、无法言语以及无尽的误解,他的心里会被一种无奈的恐惧所折磨。他想到面前令人心焦的漫漫长路,身体控制系统缺乏协作,膀胱不听号令地自行其是,还有他不得不与满脸傻笑、笨手笨脚地摆布他的哥哥姐姐们为伍,浑身被收拾得既干爽又干净,被大家围绕着,身不由己地抛头露面。一想到这些,他的心里就越发难受了。
他对自己语言符号的贫乏深感痛苦:因为没有办法使用词汇,他的心灵被绑缚了。他连身边事物的名字都叫不出来:他可能用一些杜撰出来的声音为它们命名,而这些词汇都是他从周围的谈话中胡乱吸收来的。日复一日,他专心致志地倾听身边的谈话,认识到只有通过语言才能实现自己的第一次逃离。
......
他独自睡在关上了百叶窗的房间里,昏暗的阳光一缕一缕投射在地板上,他慢慢沉浸在深不见底的孤独和悲伤之中:他看到自己的生活沿着森林中一条昏暗的小路向前延伸,他知道自己将始终是一个悲伤的人:桎梏在这小小的头颅之中,囚禁在这颗搏动而极其隐秘的心里,他的生活必定始终沿着孤独的道路前行。失落啊。他懂得,人与人之间永远是陌生的,一个人永远不可能真正了解另一个人,囚禁在母亲幽暗的子宫之中,我们出世时还没有见过她的面容,我们被递送到她的怀抱中时其实只是个陌生人;而且,囚禁在这难以打破的现世的牢笼里,我们永远无法逃脱,无论是谁的臂膀紧紧抱着我们,谁的嘴亲吻着我们,谁的心温暖我们。永远,永远,永远,永远,永远。
......
这个男孩的心像一座残酷的火山,他对偶像的崇拜就像小小的飞蛾,义无反顾地投入之后,最终却烧成了灰烬。无情的岁月一个又一个击碎了他的神灵与英雄。什么才能满足他的期望?什么才能经受住成长与记忆的考验?昔日的黄金现在为何黯然失色?似乎在他的一生之中,他所无限景仰的人到头来都变成了雕像;他所依赖的活生生的生命在他身体下融化,低头一看,发现自己拥抱的只是一尊泥塑;但是,在他阴霾笼罩的心灵之中,只有她依然如故,持久而真切,正是她用光芒照亮了他昏盲的双眼,正是她为他无家可归的茫然的灵魂提供了归宿。她依然如故。
啊,生命中的死亡把人变成了石头!啊,我们的神明颓然退位!如果人能够继续活下去,超越了岁月的磨蚀的灰烬,那么尘土难道不能复苏,死去的信仰难道不能重生,我们难道不能重见那曾在清晨山顶上显现的上帝吗?谁与我们同行在群山之上?
......
他站在黑暗边缘,脑子里只有对城市的梦想,无数的书籍,和众多幽灵般的幻象,他爱的人,爱他的人,曾经认识却又失去的人们。他们再也不会来了。他们永远不会再回来了。
他的双脚站在黑暗的悬崖边,抬眼望去,看不到任何城市的灯火。这就是,他想,猛烈而灵验的死亡之药。
“这就是终结吗?”他说。“难道我已经耗尽了生命,却还没有找到他?要是这样,那我就再也不会开始我的旅程了。”
“傻瓜,”本说。“这就是生活呀。你还哪里都没有去过呢。”
“可是在那些城市里呢?”
“根本没有什么城市。只有一次旅程,最初的,最后的,唯一的一次。”
“就算是比西潘古更陌生的海岸,比非斯更遥远的地方,我也要追寻到他,我自己的萦绕不去的幽灵。我已经失去了滋养我的血液:在通往生活的道路上,我已经死去了一百次。靠着缓慢的隆隆鼓声,靠着垂死的城市闪耀的光芒,我已经来到这个黑暗的地方。这是一次真正的旅程,一次美好的旅程,最好的旅程。现在准备好吧,我的灵魂,准备开始去追寻。我要探索的那些海洋,将比盘旋着信天翁的海洋更加陌生奇妙。”
他赤裸着,孤身一人站在黑暗之中,远离了那个充满街道和面孔的失落的世界;他站在自己灵魂的堡垒上,面对着自己失落的土地;他听见失落的海洋在内陆的嗫嚅,听到号角在内心里奏响遥远的音调。最后的旅程,最长的旅程,最美的旅程。
-end-

回复以下关键词,送你一篇歌苓美文:新作|自由| 戒荤| 跑爱| 婚姻| 善良|
爱| 婚姻| 善良| 萌娘生命| 女郎| 信仰| 建筑败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