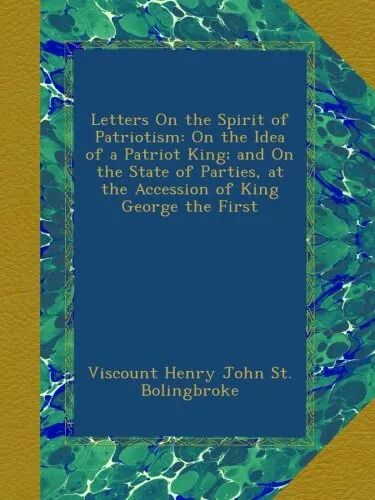
博林布鲁克圈子同沃尔波、丹尼尔·笛福阵营之间带有历史范例性质的斗争,之所以呈现出异常胶着的悬疑局面,很显然是因为
沃尔波
-
佩尔海姆体制
引领的这个时代,还没有呈现出明晰的
道德图景
,无论宪政层面、经济层面,还是帝国层面,都是如此。
确切地说,夹在宗教和政治革命的十七世纪以及工业革命的十九世纪之间的十八世纪英格兰,正待
在十八世纪完成自我界定
。正如拉斯莱特所论:
“经济人这个充满阳刚之气、东征西略的英雄,是
19
世纪工业化的一首幻想曲,可是他的
18
前辈,大体上却被视为一个女性化的、甚至是柔弱的形象,他仍然在与自己的欲望和歇斯底里、与其他的幻想和嗜好释放出的内在和外在的力量抗争,这些力量是以打破秩序的女神形象作为象征的:‘命运’、‘奢侈’以及刚刚出现的‘信用’。潘多拉乃是先于普罗米修斯登场的;首先,追求欲望并因此成为欲望的牺牲品,这在传统上被视为女性扮演的角色,或是让据有阳刚之气的‘德性’屈从于‘命运女神’的角色;其次,投机性的新经济人形象,是与本质上据有父权制和古典特点的公民爱国者形象相对立的。因此,
18
世纪有关政体同经济、生产和交换之新关系的辩论,经常被认为是欲望和女性远离,占了上风。这些关系被强行赋予了新的历史角色……于是,在
18
世纪下半叶,出现了诸如‘爱国者’与‘商人’这样的概念对峙。”(波科克,《德行、商业与历史》,北京三联,
2012
年,第
168-169
页)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博林布鲁克集团以超议会的方式提起了那个时代欧洲到处都在盛行的二元论历史论题,将沃尔波视为明确且单一的政治和文化天敌,以先知的嗅觉从沃尔波体制当中嗅出了种种的危险信息:
“危险来自那些大大小小的资本所有者,他们投资于公共信用体系,从而把政府和公民的关系、因而也意味着把全体公民和全体臣民的关系,变成了债权人和债务人的关系。不是市场而是股票市场,使英格兰人在
1700
年前后突然意识到,政治关系正处于变为资本主义关系的边缘;假如没有非专业化的农业社会的爱国者理想这一反题,这种意识是根本不可能形成的。”(波科克,《德行、商业与历史》,北京三联,
2012
年,第
163
页)
显然,在博林布鲁克集团看来,道德的动机并不在于人类自身的道德意识,而在于对上帝意志和上帝的“更大荣耀”的服从和体现;不信仰上帝,便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道德可言;在历尽千年的传统中,道德不过是人类对上帝的信仰仪式的可怜的组成部分,远非人类自身的终极要求。这是博林布鲁克自然法观念之根本信条,这一观念在
18
世纪的启蒙家那里发生了决定性转变。
在经历了数个世纪之久的禁欲主义之后,享乐在人类苦难和不幸的道德氛围中已经变得不可理解了。然而,随着个体权利的确立,有关幸福和享乐的观念则开始被确立为自然权利之一。
18
世纪的
自然神论和伊壁鸠鲁主义者
执掌时代潮流,他们都认为,依据自然和理性,人类是可以向上帝提出合理要求的,就如同同一时代的自由经济理论一样,这中间的过程似乎也是一个可以公平地进行讨价还价的交易过程,其中,寻求尘世自身的幸福便是首要的合理诉求;这便导致了现代道德意识同古代美德观念之间的决定性差别。
古代美德观念并不包含权利和责任之间的两元区分,而现代的权利观念则导致了权利和责任之间的两元区分。由于权利和幸福观念取代上帝的位置,成为人类道德意识的首要原则,便很难再将自爱与他爱、德性与幸福协调起来,同时也无法像古人那样对人类道德采取灵活的态度,比如雅典的民主政体就是以公民道德上的灵活分级为基础的,正如
伯利克里在葬礼演说词
中暗示的那样,只有公民
-
士兵才能够在城邦获得自己的一块墓地和神灵,非公民阶层以及外邦人在雅典人的道德意识中则无权享有此等权利。
无论是柏拉图在
《理想国》
中,还是亚里士多德在
《政治学》
中,都将不同的道德体系赋予不同的社会阶层。现代的自由主义者则将权利和责任判然割裂,由此造成的首要逻辑结果便是德行与幸福之间的绝对对立,并认定责任与幸福同样也是对立的。因此,在确立个体自然权利的同时,也将责任绝对化。在他看来,古代道德历来重视从“敬畏”当中获得快乐和幸福,比如当一个希腊的牧人在翠绿的原野上倾听到雷声之时,他会立刻认为这是宙斯发出的召唤,这样的召唤既包含有作为城邦公民的幸福感,也包含有同等的责任感。因此,古代的道德意识并不是建立在作为绝对的权利主体的个体的内省之上,而是建立在公民彼此之间的沟通之上,尤其是建立在公民同诸神之间外向的交往之上。
因此,毫不奇怪,古代的道德意识中不曾诞生权利主体这样的观念。诸神对人类的召唤乃是建基于丰沛而灵活的自然和城邦生活,其中既不包含类似
基督教禁欲主义的律法元素
,也不包含绝对的主体权利意识。
与此相反,现代道德意识由于主体权利的绝对化,从而也导致了无条件的和僵硬的责任意识。只有现代人才会为自己开列一份长长的、无条件的责任清单;正是现代道德意识的这种绝对化境况,催生了
历史主义当中的英雄意识
;个人主义纯洁并升华了的道德律令,远远超出了人类能力的一般性极限;单纯顺应一种严厉的内在要求,绝对的责任信仰便很可能在人类当中催生一系类的非凡举措,不停地剥夺自然权利方面的自利要求。
从根本上讲,这仍然是一种全然个体的伦理责任形式,它以无条件的、无限制的献身意识和天命意识,试图重振荣耀、自豪和贵族阶层的成功等
人文主义价值观
,而实际上在德皇威廉二世所开启的大众政治时代,这只能导致具有民主本质的、新式的、普罗米修斯式的政治伟大和理性的堕落;在这种新式的政治伟大当中,根本的要义就在于:绝对的奉献和战胜自我成了绝对伦理原则所要求的严厉的造物主。
一个像
色诺芬
那样,能够恰如其分地权衡手段与目的、能够灵活地游弋在善恶、人神之间、并在诸神战争中找到审慎均衡点的人物,在现代道德意识中将只能呈现为败坏和罪恶的形象。这种民主伦理不再建基于
18
晚期和
19
世纪人们对普遍选举之合理性的深刻意识之上,而是建立在
宪政主义和自由至上
的习俗之上,依据此一习俗,司法机构应当正式取得针对国家的独立地位,这是因为在宪政主义和协商性民主看来,司法独立的立意之本乃在于司法乃是单纯的社会和经济利益的调节者。
这样的民主伦理虽然少了一份英雄主义诉求,并因此拒绝了跨越式发展的可能,但毕竟多出了一份对制度和利益多元化的关爱;它以牺牲政治生活中的唯意志主义而获取了更大程度的权力分散;它弱化了人们对民主政体本身的信仰,但强化了民主政体的制度形式;麻木的民主得到长足发展,人文主义的价值观则相应地风光不再,
百姓的和平意识和协商意识成为政治的主流
,这种主流的和平意识所要求的只是权利形式的不断推陈出新以及公共平衡的调节机制的日常轮换,而所有这一切都只能一味着处于绝对化地位的政治伦理意识最终都无法在任何民主政体中取得实质上的胜利。
博林布鲁克正是在欧洲、尤其是英格兰民主进程的这段至关重要的但也极为晦暗的关键期,提起了自己的
反霍布斯
式的自然法教义:
“不妨考量一下心灵是如何构成的……又是将我们引向怎样的目标。我们不应当像自然法学家建议的那样,信任纯粹的理智,我们应当更多地信从我们的感官。倘若我们能够对感官接收的信息进行考察和比较,并以后天归纳之法从诸般作品推及上帝的意志,从上帝令我们置身其中的体制推及我们在其中的利益和职责,我们就等于是将道德之根基系于磐石,而非流沙或者空洞的地面,形而上学家们倒是颇为擅长将流沙之地或者空洞之地指点给我们。”(
Isaac Kramnick,
Bolingbroke and His Circle
, Harvard, 1968,
第
87
页)
很显然,博林布鲁克在自然法问题上的真正关切并非像西塞罗、格劳秀斯乃至洛克那样,去找寻或者发现理性的道德法则,相反,他是要着力伸张如下观念:自然法和道德法则乃是先于人类意志而存在,因此也就是先于一切的人间立法实体而存在的。
博林布鲁克此论的主要攻击矛头乃是指向霍布斯的。在博林布鲁克的自然法景图景当中,最为突出的特质就在于:人间立法者是完全有可能误读误解自然法的,并且也正是因此,催生并巩固了众多背离自然的制度、习俗以及偏见,这一切毫无疑问都策源于欺骗和无知。
切不可因此就认为博林布鲁克是汲取了法国启蒙运动之血液的乐观的理性主义者。他的确说过虚假的表象往往会欺骗人的理智,但这样的话必须放在他同沃尔波体制为敌的时代背景中去理解。而且,他还进一步地认肯了至关重要的一点:上帝创造的人就是如此,激情、欲望、愚蠢和无知的力量要远远胜过理性,由此令非理性的意志往往成为最终的胜利者;上帝规定的人类状态,绝无可能是霍布斯式的理性自然法的完满状态,一切的完满规划都不契合人类之不完满的状态,这正是
《爱国者君主》
之自然法观念的核心要义;据此要义,道德法则的根基只能是人在上帝那无可理解的秩序面前采纳永恒的恭顺和谦卑。
霍布斯之
《法律要素论》
的本质要素就在于:
“人无优劣之别,然而非但无知群氓,就连其学说迄今不衰之大家(亚里士多德)亦以为可自人之血统而别其贵贱。”
这在博林布鲁克看来,乃全然是犯下了希腊人所谓的“傲慢”大罪,这罪行的根本则在于毁灭了“
伟大的宇宙存在之链
”的保守精神和秩序诉求,由此建构起来的秩序不会是别的,只能是“反秩序”;由此也便昭然若揭,博林布鲁克心目中的理想秩序并不一定要落定于一个虚幻的黄金时代,甚至也不一定就是他字面上常常提起的“撒克逊的过去”,确切地说,
他所谓的宇宙秩序不过是莎士比亚和培根所处的两个极具动力和张力的英格兰帝国时段之间的那段平缓期,所酝酿的安闲甜美的诗性时期
,显然,在博林布鲁克看来,那才是不列颠民族性的精髓所在。
“塞西尔
1559
年的所谓的工业计划是谨慎而保守的,它为大多数这一时期的社会立法定下了基调。普通的道德考虑仍然被作为一种出发点,即‘使青年习惯并从事劳动和工作,以免他们成为游手好闲的无赖
......
’然而,道德考虑往往具有社会目的:维护秩序
......
社会秩序反映着宇宙自身的秩序,诗人和哲学家的主题也是立法者的主题。他们的目的在于阻止社会演变,防止一个阶层对另一个阶层的侵蚀,警惕技术创新所可能造成的社会影响。一句话,在于稳定和保护现有的社会秩序。”(《剑桥欧洲经济史》第四卷“
16
世纪、
17
世纪不断扩张的欧洲经济”,张锦冬等译本,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492
页)
由此观之,重要的不是托利党或者乡村辉格党所谓的宪政自由和宪政平衡,重要的是那古老且美好的“文化理想”。由此便可以解释,像博林布鲁克这样一个深染启蒙教养并以“天然贵族”为政治诉求的人,竟然会诉求那个时代的个体商业者阶层和乡绅阶层的政治盲从力量,也就是今天人们所谓的民粹主义力量,去对抗这些人眼中那神秘且可怕的公共信贷和国债体系;并以极具激情和偏见的方式,去体现、抒发并引领一个疾进社会当中没落阶层的情绪、态度、内心渴望以及社会挫折感。
很明显,面对沃尔波体制的斗争乃是一场实实在在的政治较量,博林布鲁克是需要现实的政治力量和政治利益来完成这一轮较量的,因此,他愿意而且也在有计划地扮演
保守主义
-
民粹主义
政治领袖的角色,在这方面,可以说,以保守自居的博林布鲁克恰恰是这条最具现代特质的政治道路的最早先驱。
波科克认为,在这个问题上,博林布鲁克乃“借用”了
哈灵顿
的理论,这可以说是点出了博林布鲁克政治诉求的要义。
哈灵顿之乡绅
-
利益理论,乃是以古典雅典和罗马的公民军为基础融构而出的
,拥有土地的公民
-
士兵阶层乃是共和国利益格局据以维系的支柱,同时也是据以调整和变幻的标尺;历史乃是在背离和复归此一理想标尺的过程当中伸展开来的;确切地说,哈灵顿据此建构的乃是一种古典气息已然大为削弱的二元历史循环论,并且据此二元循环的永恒历史过程,哈灵顿在那么一个因清教徒精神和自然权利之强力伸张而造成的变乱格局当中,成功地重建了历史一致性、连续性和稳定性之法则。
霍布斯当然是此一变乱格局最为透辟的观察者,他的诉求并不像评论者们常常认为的那样,乃是要依托一个人间的主权立法者来重建稳定和秩序,至少,这并不是霍布斯的终极诉求;确切地说,霍布斯的终极关切跟哈灵顿不会不在一个层面上,同样是历史之一致性和连续性法则;只不过,跟哈灵顿这类很难摆脱古典束缚的人物不一样,
霍布斯乃全然挣脱了古典的循环论历史框架,转而诉求一种有着单一且恒定力量源泉的历史法则;在霍布斯看来,此一法则的根基并不在于任何的先验秩序,而在于绝对的自然权利个体之间绝对且普遍的冲撞格局当中,这样的冲突在击碎那“伟大的宇宙存在之链”的同时,在制造出普遍混乱格局的同时,也蕴涵着极具潜能的历史法则之重建能量
,因为,惟有在这样的普遍变乱格局当中,才能令绝对的自然权利个体同“利维坦”建立无需任何中介的直接联系和互动。
说白了,
“利维坦”背后的至深精神图景乃是英格兰人从日耳曼丛林当中的原始自由民向着拥有强劲进取精神的现代帝国个体公民转变的精神图景
。
沃尔波首创的“首相”体制自然是深得“利维坦”真义。
不过,博林布鲁克并不这么看待问题,严格来说,在这个问题上,博林布鲁克乃接纳了哈灵顿的历史二元论这样一个准古典的观念。在他看来,
1688
年革命不但没有实现自己的政治承诺,反而逐渐背离了此一政治承诺,那就是重建古老的宪政自由,这其中的原因有社会结构性质的,也有人性方面的。
社会结构方面的情由主要在于财产结构的变化,税收之征收和运用体制、公债体制以及以英格兰银行和东印度公司为核心组件的金融利益集团,乃从根本上改变、甚至可以说是置换了英格兰传统的乡绅利益阶层在议会决策中的分量。不过,博林布鲁克很快便将笔锋从财产结构转向人性,转向文化
-
德性政治论式,他据此指出,新的财产形态乃是潘多拉的魔盒,在整个英格兰社会散布腐败和邪恶。
确切地说,他一方面遵循
哈灵顿的“大洋国”共和思路
,敏锐地指出,“当今之世,金钱的力量乃是真正的力量”,另一方面,他又迅速背离了哈灵顿的共和思路,决绝否认金钱的力量可以成为正当的政治力量,并将这种力量称之为“影响力”,而非真正意义上的政治变革应当予以考量的体制要素。
由此,博林布鲁克便成功地完成了自己的历史哲学图示,此一图示依然是二元的,一边是“超出记忆”的
撒克逊黄金时代
,
1688
年的政治承诺在博林布鲁克看来,恰恰就是系于对这个“超出记忆”的时代的记忆,另一边则是
1688
年之后展开的那么一个逐渐背离的历史过程。
在这个过程当中,辉格党和托利党在观念和原则上的传统分野,也就是
前
1688
年代“乡村派”和“宫廷派”的那种带有强烈清教主义精神气息的分野
,已然消散,取而代之的则是一种变乱驳杂的派系格局。显然,博林布鲁克的政治思维框架是极为类同于
19
世纪后半叶
帝国没落时期的那种文化政治思维
,他不能接受那种建基于现实利益诉求的党派格局,也正是因此,他拒绝将“派系”视为“党派”。
沿此思路,在现实利益诉求之间居中引领的“首相
-
内阁”体制便成为博林布鲁克攻击的核心点;在博林布鲁克看来,这样的体制既是缺乏一切“自然正当性”的
人造体制
,也是一种于乱世当中崛起的
暴君体制
,就如同撒旦同地狱崛起一般。
延伸阅读
英国史短章 | 一
英国史短章 | 二
英国史短章 | 三
英国史短章 | 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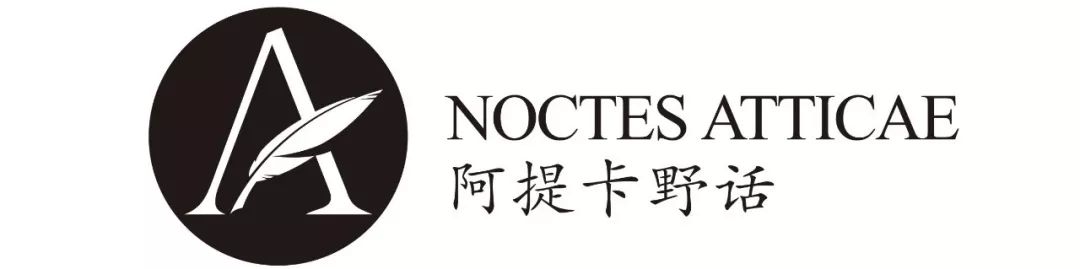

漫漫冬夜,阿提卡乡野蛰居的日子,草草写下这些笔记,是为“阿提卡之夜”。
Aulus Gellius,
Noctes
Atticae
,Praef, 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