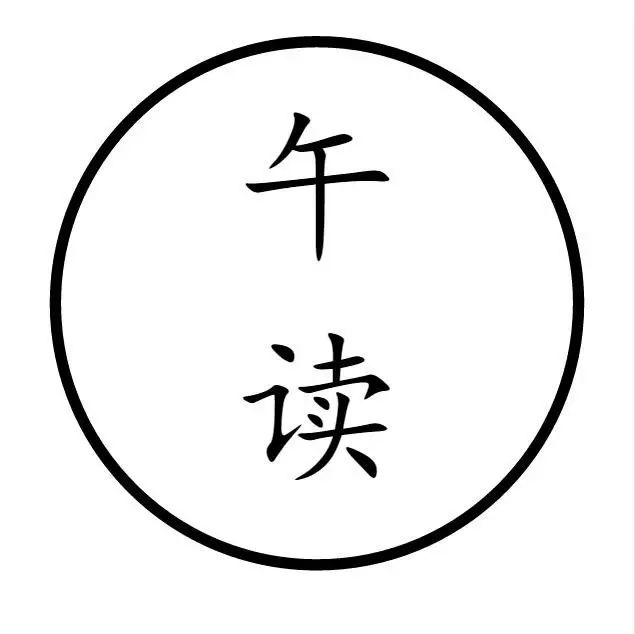位于西子湖畔、灵隐寺边的飞来峰,是江南文化乃至中华文化的珍奇瑰宝。400多尊姿态各异的佛教造像,300多处精工细作的摩崖石刻,既温润亲和又遥远神秘,构成了中国佛教艺术史上的宝库。浙江广播电视集团与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管委会联合出品的纪录片《飞来峰》穿越存世千年的造像题刻,穿透风云际会的历史尘烟,以影像美学表达方式的创新,为观众描绘出一幅深邃而迷人的中华文化记忆图景,赋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
在推进文化强国建设,推动文化传承发展的大背景下,纪录片因其非虚构性、人文性和艺术性兼具的特征,是记录文化、传承文化的重要内容载体,亦成为彰显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真实影像文本。《飞来峰》虽为个案题材,但能由点及面、见微知著,显现了作品高远的格局和立意。
纪录片通过展示从五代到元代初期在飞来峰开凿的大量造像和题刻,及其延绵存续至今,成为千年西湖“石质史书”的历程,鲜明体现了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创作者不仅讲述历史故事,而且记录了对文物的传播与推广,使其在现代社会依然焕发生机、发挥效用,具象折射了中华文明的创新性;作品呈现汉式造像与藏式造像的相遇,中原元素与江南景观的融合,客观印证了中华文明的统一性;该片借助飞来峰石窟勾勒出佛教中国化的演变,天竺法师来到烟雨江南传法,梵文和汉文同现崖面相互凝望,生动凸显了中华文明的包容性;片中佛陀造像温润圆融、荡涤人心的微笑表情,以及从周伯琦《理公岩记》到飞来峰山石中的历代题刻,隐含了文人巧匠们对美好安居生活的向往,巧妙表达了中华文明的和平性。
石窟造像、摩崖题刻均是静态的、古老的、沉默的,代表着文化遗址的基本状态。如何使之“活化”?是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一个重要命题。对于纪录片创作而言,首先必须植入动感、现代的元素,使观众感知到其历经千年而未消弭的活力。主创团队将佛陀的“微笑”视作中华文明精神标识的一种表征,亦将其作为这部纪录片的核心意象符号。片中通过运动镜头、延时拍摄、光影设计、三维动画等多种手段,努力使每一尊佛像、每一处题刻都灵动起来,具有生命力与诉说感,将其所蕴含的温暖与智慧,将中华文化深邃而包容的精神鲜活地传递给观众。
为使飞来峰及文化遗产得以“活化”,该片还运用了一种可称之为“古今对话”的叙事结构和策略,将古人的寻觅留记、传奇掌故,与今人的游历观瞻、研究保护穿插呼应、并行不悖,使同一处文化景观、物质场景在古往今来、荏苒代谢的流动叙事中得以活态呈现。观众仿如以飞来峰为媒介,与古人甚或诸佛文字相通、笑容神会,共享桂子飘香、山色空蒙的千年景致,进行了一场跨越时空的心灵对话与互动。由此,身处网络社会的现代人亦能从历史积淀中获得直面人生风雨的精神慰藉和心理疗愈,并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厚重底蕴与无穷魅力。
江南美学是中国美学、东方美学的重要构成,广泛表现在江南地区的自然美、艺术美和社会美之中。古典江南美学可追溯至远古的良渚文化,到南宋时期以都城临安(即今杭州)为中心全面形成。飞来峰的题刻与诗文,成为东方智慧与浪漫的象征,也是江南文化的地标符号。从白居易到苏东坡,历任的杭州主官将山水园林的美学与人工治理理念相结合,塑造了这座城市的文化气质。以此为表现对象的纪录片亦饱含浓厚的江南美学旨趣,呈现出诗意雅致、意境幽深的风格。从《孤山路31号》《西泠印社》到《飞来峰》,体现了浙派历史文化类纪录片特有风格的承继与发展。
该片总体上呈现出散文诗般的典雅简约格调。女声解说温婉含蓄,思绪静水深流,画面精致唯美,音乐神秘舒缓,辅以诗词美文、佳句摘录,反映文人情怀得以在江南抒发的欢喜与和谐,及其心灵与外部世界的交融,体现出江南美学诗意栖居的感性。创作团队在内容叙事上不求集中完整,放弃了专家访谈等强逻辑性的表述方式,而是通过对日常的观赏、雅集、拓印、数字扫描等现场的纪实性摄录,以及虚实相生的情景再现演绎,强化了作品自然优美的诗意。
意境是中国古典艺术理论的重要范畴,它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审美意识。在这部作品中,情景再现影像多采用中国画式构图和从容舒缓的升格镜头,并不追求写实式的摹仿,而是探寻一种写意传神、带有禅意的素描,将江南美学以虚代实、追求意境之美的旨趣融入到作品之中。如此,在讲述古代人物故事时,观众犹如在欣赏一幅以形写神的影音山水画,虽不能看明画中人的面容表情,却能够在影像符号营造的幽深朦胧、情景交融之意境中,体味到文人骚客间的惺惺相惜,及其与飞来峰、杭州城之间深沉的情感连接。片中还将佛教造像和历史人物的水面、镜面倒影与实景相结合,升华了文化遗产的神圣感,予人以意在言外、境生象外的高层次审美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