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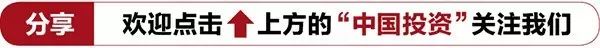
欢迎读者朋友在文末“
写留言
”处,给我们评论建议,精彩言论本刊将会赠送精美杂志一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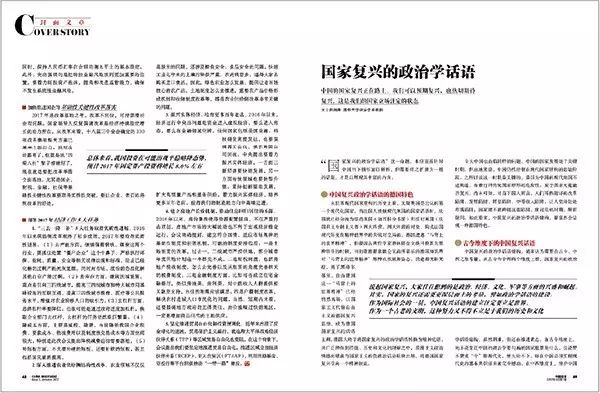
 中国的国家复兴正在路上。我们可以预期复兴,也热切期待复兴,这是我们的国家立场注定的状态。
中国的国家复兴正在路上。我们可以预期复兴,也热切期待复兴,这是我们的国家立场注定的状态。

●
中国复兴政治学话语的德国特色
●
古今维度下的中国复兴话语
●
中西维度下的中国复兴话语
●
理性确定国家愿景
“国家复兴的政治学话语”这一命题,本应直接针对中国当下情形加以解析,但需要将之扩展为一般的话题,才足以展现其丰富的内含。
中国复兴政治学话语的德国特色
从世界现代国家建构的历史上看,无疑英国是公认的第一个现代化国家。当法国人接触现代英国的国家话语时,法国就已经分流为崇尚英国(如百科全书派)和反对英国(法国君主专制主义者)两大阵营。两大阵营的对垒,构成法国现代转变在精神世界中的尖锐对立局面。德国遭遇“马背上的世界精神”,但德国古典哲学家群体将金戈铁马换算为思辨哲学的时候,当初歌德跟拿破仑见面所显示的德国知识界对“马背上的世界精神”那种欢欣鼓舞姿态,消逝得无影无踪。到了黑格尔那里,自由建国这一“马背上的世界精神”已经悄然离场,以国家主义代替自由主义的德国复兴思维,成为德国国家复兴的话语主调。德国人终于将国家复兴的政治学话语转换为精神呓语,并广泛伸张到传统、历史和文化的理解之中,浪漫主义政治情感的肆虐与国家主义的伪政治话语联袂出场,将德国国家复兴引向一个精神歧途。
今天中国也面临同样的问题。中国的国家发展处于关键时期。但总地来说,中国仍然徘徊在现代国家建构的起始阶段。之所以说这一时期是关键的,是因为中国的现代建国不进则退,有着打回传统国家原形的危险性。至于国家究竟能否复兴,尚未可知。对当下国人而言,人们耳熟能详的改革陷阱、发展陷阱、转型陷阱、中等收入陷阱,让人觉得处处布满陷阱,国家能不能跨越这些陷阱,度过危机时期,颇有疑问。如此看来,中国复兴的政治学话语建构,很显然会呈现一种德国特色。
说起国家复兴,大家往往想到的是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的兴盛和崛起。其实,国家的复兴还需要更深层面上的考量
,譬如政治学话语的建设。作为国际社会的一员,中国复兴话语的建立注定要立足世界。作为一个古老的文明,这种努力又不得不立足于我们的历史和文化。
古今维度下的中国复兴话语
中国复兴的政治学话语建构,通常认为需要在古今、中西之维考量。从古今和中西两个维度上看,国家复兴的政治学话语建构,虽然困难,但还在推进状态。在古今维度上,先不说变迁中国的政治学要勾画的国家愿景是什么,仅说赞不赞成“今”即现代化,便久讼不下。好在中国必须实现现代化的基本共识还未被完全撼动。在中西维度上,维护中国性,拒斥西方性,似乎一直是相关争论各方的基本倾向。幸运的是,各方在底线上支持现代化的趋同性立场,让各方力图在西方国家特殊的现代化进程中发现现代化的一般原理。但需要注意的是,“左右之争”插入相关争论以后,事情变得复杂多了。这一争论,让人处在捍卫中国既有政治秩序,或是进入规范现代状态的旋流中。中国复兴的政治学话语,因此很难凸显一个众所认同的话语体系。
先不讲今之中国。仅就古之中国而言,中国是“谁之中国”,就不好断然作答。当代大陆新儒家认为,中国就是铁板钉钉的儒家中国。但实际上儒家中国仅仅是政治社会面相的中国或教化面相的古代中国。即使不谈道家中国、佛家中国,儒家中国也是一个以偏概全的说法。况且这只是精神形态的中国之一方面,物质的中国呢?制度的中国呢?墨家、法家等等便粉墨登场,各显其能了。
讨论何谓中国的问题,涉及到至少
3
个“对子”:一是正统与异端。中国究竟是谁的中国,当然是居于正统者的中国。作为中国主体民族的汉族,自然有理由认定汉族居于统治地位的中国,才是正统中国。但清朝皇帝康熙特别辩护道,“自古得天下之正,莫如吾朝”。这就有点让人不知所措了。说起来,中国古代二十几个王朝,得权最不正的可能就是清朝。少数民族、野蛮民族、异端、靠武力打天下,这种种得天下之不正的因素,清都占全了。比较起来,它得权不正,尤甚蒙元。蒙元以其四书学,让正统象征的儒家迅速成为国家主流意识形态。清朝时,儒家进入国家层面较缓慢。而从儒家精神来讲,整个清朝主要讲小学少讲大学。但皇帝“得天下之正”的大言不惭,让正统和异端的争论变得是非莫辨。
二是中华与夷狄。华夷是个更复杂的问题。大陆新儒家认定汉民族天生是华,别人是夷。但在东亚儒学论述中,人们却发现日本和韩国,都曾竞争“中华”这个古典国家定位。日本东京大学著名教授渡边浩,就说他最遗憾的是,日本竟然不愿以中华自命。而韩国则成立有中华学会。中华天经地义属于政治意义上的中国吗?日韩两国学者的回答恐怕是否定的。如将“华”代表文明,“夷”代表野蛮。但华夷关系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中华”是一个可变的、可转移的文明定位。“华”“夷”并不是在古代定位不移的角度将“华”确凿无疑归属于中国,尤其是在中国显著衰颓之后。
三是王朝和帝国。由于新清史、新元史的兴起,让人们习以为常地认帝国为朝代的中国史观,受到挑战。尽管争论一时半会儿不会平息,也难以得出一致认同的结论,但对国人转换视角看待自己国家的历史,发挥了不小的驱动作用。近代以来,国人被动挨打,悲情宰制。因此常常只看到别的民族欺辱中华民族的痛史,而没有看到中华民族内外部冲突带给别的民族的痛苦。从汉与匈奴冲突始,落败的匈奴进入欧洲,欧洲人就体会到来自东方强大军事力量所具有的威胁。如果把匈奴跟汉之争算作中国朝代史的一部分,匈奴进入欧洲的中国人就不能全部推脱。此后蒙元王朝跟蒙元帝国、满清王朝跟满清帝国的联系与区别,也让国人面对同样的问题。西方学术界的新清史、新元史研究,打的正是国人烂熟于心的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旗帜。当今国内历史学界对国家复兴话语有高度的学术警惕,殊不知反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话语,却发挥出瓦解中国建构的国家复兴话语的效用。
当中国复兴的贫困国家话语试图成为一种世界性话语的时候,这似乎有一种“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添堵。中国一向以“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声索领土,如果按照这样的说法,从匈奴开始一直到蒙元、满清,从西欧往东都是中国的领土了。中国领土的帝国式诉求足以让欧亚大陆所有国家坐卧不安。与此相关,我们的国家复兴话语贫困,还表现在面对帝国史和朝代史,一再声称自己是爱好和平的。
从总体上讲,这也没有错。但对欧洲人来说,“黄祸论”这一历史学热门话题似乎一直在提醒他们,黄种人并不是爱好和平的民族。从古今维度讲“古”中国,国家复兴的政治学话语应搭挂在古代的哪个中国?这是难以断然回答的一问。
作为崛起大国,我们一方面努力保证复兴进程的持续性和稳定性,一方面也要着眼于未来,解决建设“一个什么样大国”的问题。国家复兴不仅仅依靠自我发展,还可能受制于外界影响。国家崛起之际,保持头脑冷静,理性应对内外之挑战尤其重要。
中西维度下的中国复兴话语
再一个是中西维度。中国致力建构国家复兴的政治学话语,对中西的复杂交错关联也很难清晰切割。挑战相应也有
3
个方面:一方面,中国能否将地方性知识与全球性知识区隔得非常清楚?如果决绝区隔开来,便对自己制造了障碍——中华文明之“华”就不能成立了。因为中国的“物华天宝,人杰地灵”也是地方性知识,并不是真正的“天下”知识。
我们认定西方的现代知识是地方性知识而非普世性知识,实际上同时把我们自己确立的“中华”知识的普适性否定掉了。国人凭什么自认中国的五服制度和天下体系普照全球,而西方的现代知识就一定是地方性知识?一个必须避免的反讽论断是,在中西维度致力瓦解西方话语的时候,千万不要同时瓦解了自己的相类论断。中华文明本是扩展性文明,也就是论者所谓的漩涡式结构。确实,直接塑造中华文明的周,“撮尔小国”,方圆不过几十华里,晚近阶段,中国地域之广袤,远非周人所可想象。须知现代“西方”早就不是一个单纯的“地方”,它提供了各国无法逃避的现代国家规范结构,其普适性已经为
500
余年的世界史所证明。在这点上国人没过心理关,反驳西方人时只顾将其归为地方性知识,殊不知把自己的普世也输掉了。
另一方面,中国的现代民族国家之形式结构和实质结构是疏离的。有论者强调今天的中国是一个文明性国家,不是一个民族国家。中国确实有鲜明的文明性国家特征,并同时伴有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支持的普世性国家。但即便如此,今天中国作为一个民族国家立于世界史不会有人质疑的。差别不在中国国家性质的文明性或民族性,而在中国能否体现出民族国家的规范性。从政治理论上讲,民族国家只是建立现代国家的第一步。第二步是把民族国家的国家权力结构、国家总体结构安顿到现代的规范国家结构上。规范的现代国家结构一定是立宪国家。中国肯定是一个制定了成文宪法的国家,否则就只好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废掉。确立立宪国家的前提是主权国家的建立,主权国家是立宪的主体。要不然国家超越民族国家宪法去制定万民法,为诸民族立宪。不过历史提醒国人,天朝体系时代,中国试图为其他民族立规,日本、韩国的不买账,应当是一剂清醒药。
今日不说全世界,仅论东亚,日本人也曾认定,古代东亚属于中国,近代东亚属于日本。尽管日本人建构的东亚体系——“大东亚共荣圈”,已经被中韩等国拒斥。但其日本复兴的政治学话语已经进入历史。相比而言,韩国作为古代中国的藩属国,在近代变成日本的殖民地,他们倒是非常坚决排拒中日两国的帝国冲动。对此,国内的新儒家朋友,在这方面视野稍微要广一点,一者固执“崖山之后无中国,明朝之后无华夏”,将中国性弄得无比狭隘;二者又对五服制度、天下体系极尽赞美,丝毫不顾及邻国感受,这种关起门来的自语,无助于中国建立现代国家。
再一方面是主权国家与国际秩序的不同取向。
中国复兴的国家话语之一,是要重建天下秩序。这就涉及到现存国际秩序的存废问题。
如果这仅仅限于学术界的争议,现实影响不会太大。假如付诸国家行动,一定让全球震惊。毫无疑问,中国最近
40
年
GDP
的迅速增长,就是因为依托于现存世界秩序。中国是现存世界秩序得利最大的国家。国人很清楚,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最愤怒,指责中国赚了美国人的钱,“偷”了美国人的工作机会。这种说法成不成立另说,但挠中了中国得益于现存世界秩序的痒处。假如中国不深明于此,竟然自己拆自己的国际舞台,不仅会危及本已脆弱的中国经济,也会因为没有设计好替代秩序就宣告现存秩序废弛,更将危及整个国家的安全。这需要中国政治学界全力以赴建构国家复兴话语的时候审慎以对。
至于左右维度,简单来说,极左与极右,都不是建构国家复兴的政治学话语适宜的进路,则是不争之论。
理性确定国家愿景
中国的国家复兴正在路上。我们可以预期复兴,也热切期待复兴,这是我们的国家立场注定的状态。但按照时髦的提问方式,不妨尾随一问:中国复兴,是谁之中国?何种复兴?回答“谁之中国”已属不易,论断是“何种复兴”,到底是国家融入平等的国际大家庭,还是耀武扬威、称霸世界的复兴,也是不能轻率回答的严肃问题。今时今日的中国,似乎倾向于后者居多,认同前者的甚少。这是不是需要国人警惕的复兴模式呢?开篇所论德国,其称霸世界的国家复兴导致的国际悲剧,能不能推动国人沉潜反思,理性确定国家复兴的愿景?中国自有国家的特殊国情,但在国情与世情之间,如何审时度势,择定国家发展进路,确立国家发展愿景,需要深入思考,审慎作答。即问即答,就显得相当轻率了。
(文|任剑涛 清华大学政治学系教授)
本文刊于《中国投资》
2017
年1月号。版权所有,侵权必究。欢迎个人分享,媒体转载请回复本微信号获得许可。

《中国投资》杂志以全球视角看中国投资,涵盖宏观经济、行业分析和企业投资案例,同时以全球市场为坐标,聚焦特定国家、地区和重大国际趋势。
自2016年起,中联部相关机构作为支持单位,与《中国投资》非洲版一道,为非洲各国与中国持久的大规模合作,提供一个专业而强大的对话平台。
China Investment
magazine, established in 1985, is a monthly at central government level
and China’s oldest media outlet concentrating on trends reporting in
the investment arena.
Starting
from April 2016 and under the auspices of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and International Department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hina Investment
African Edition will
create and provide a professional and powerful platform of dialogue for
the ever larger-scale but sustainable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African countries throughout the continent.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木樨地北里甲11号国宏大厦B座1805-1810室
Address: Room1805-1810 Guohong Building B. A-11 Muxidi Beili,Xicheng District.Beijing 10003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