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看点
在第27届国际哲学奥林匹克竞赛上,来自上海平和双语学校的林燕盈,为中国赢得了第一块奖牌。国际哲学奥林匹克竞赛是什么?林同学的哲学之旅如何开始?哲学对个人和社会有何作用?外滩君请来林燕盈,为读者们解答这些疑惑。
大家都知道国际上有一重大赛事,叫做奥林匹克竞赛。
除了我们所熟知的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会之外,国内的学生家长还耳熟能详的大约便是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即奥数了。
然而,国际奥林匹克竞赛
其实远不止这些。
鲜少有人知道,还有国际经济学奥林匹克和国际哲学奥林匹克等全球性重量级竞赛的存在。
在上个月于罗马举行的第27届国际哲学奥林匹克竞赛(InternationalPhilosophy Olympiad)中,来自上海市平和双语学校高中部十一年级的
林燕盈同学成功摘得了银牌
。
这也是有史以来,
中国在该竞赛中获得的第一块奖牌。

林燕盈(右)与
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施璇(
中)以及获得荣誉奖的王姝元(左)
近年来,在国际哲学奥林匹克竞赛中成绩最好的国家是土耳其、德国、波兰。
注:根据澎湃新闻报道,中国迄今参加哲学奥林匹克竞赛的学生选手只有四届共6人。
2017年第25届IPO在荷兰鹿特丹举行,中国去了两名高二学生,一名来自上海,一名在美国读书,分获30多名和50多名(参赛者共90多名)。上海这名学生2018年已被美国埃默里大学(美国排名前20)录取。
2018年5月,第26届IPO在欧洲黑山举行,国内自由报名学生有20-30名,其中有若干上海学生。
这个女孩究竟是何方神圣?“国际哲学奥林匹克竞赛”又是个什么样的竞赛?比赛流程是怎样的?在国际上地位几何?
带着这些问题,外滩君第一时间联系了这位获奖的“哲学女孩”来为我们分享她的经历。

2019年国际哲学奥林匹克现场

国际哲学奥林匹克是什么?
国际哲学奥林匹克是一项中学生哲学竞赛,为国际科学奥林匹克的一种,自1993年起每年举行。
比赛奖项依次有金奖、银奖、铜奖、优异奖,授予优秀论文的作者。
每年的全球决赛为期四到五天,每年会选在不同的国家与地区举行。
主办国可以派出十名参赛者,其余
参赛各国能派两名参赛者
。
比赛将拟四条题目,参赛者从中选一,在四小时内以
英文
、
法文
或
德文
写一篇论文,但不能使用
母语
或其国家的
官方语言
。
论文将由随队导师和国际哲学团体联合会的代表共同评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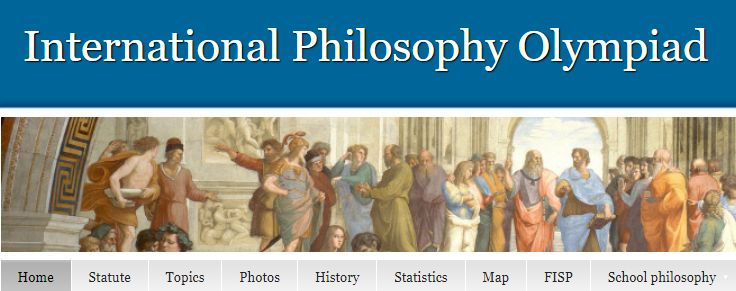
奥哲官网
去年10月左右,林燕盈在学长和老师的介绍下填了国际哲学奥林匹克竞赛(以下简称“奥哲”)的报名表。
年底,这一届奥哲的主题出炉——
文化遗产与公民身份(Cultural Heritage and Citizenship)
。
在这一阶段,林燕盈按照上一届参赛选手的经验从人物和主题两种划分角度入手,过了一遍哲学史。
据林燕盈自己说,比起奖牌,这段广泛地在哲学领域中探索与学习的时间里学到的知识,是她觉得从这次比赛中最大的收获。
12月,林燕盈参加了国内的奥哲初赛,并且获得金牌,晋级为决赛选手代表中国前往罗马参加奥哲的世界决赛。

林燕盈(前排右一)
“当时我看着那个主题其实是懵的,根本不知道从何入手,一切都要从头开始。
主要是因为我之前的兴趣比较集中在认识论上,没怎么了解政治哲学、伦理学等其他哲学分支,所以我能用以分析这个主题的概念工具是很少的。
不过,好在IPO出题没有局限在当年的主题上——国内的初赛中正好有一道题,讲的是柏拉图说知识是被证实过的真信念(justified true belief),这是一个比较经典的知识定义类题目。
我刚好在比赛前几天也看了类似主题的书,于是就写了篇文章,主要讨论了‘证成’这个方面,由此很幸运地拿到金牌,成为中国代表队的一员。”林燕盈如是说。

5月中旬,林燕盈启程前往罗马。
5月16日晚上,来自世界各地40多个国家的几十位参赛选手被安排到了一座罗马郊区的内政部府邸里入住。(据说那是个训练警察的基地,每次进出还有人检查护照,可见这一比赛的受重视程度)
那天晚上,所有选手都参加了开幕式,还听了当地学校乐队的古典音乐演出。
尽管由于国内接触哲学比较少,奥哲这一比赛在中国看来并不很受重视,但其实奥哲是一项不小的赛事。
除了每年的主办国享有十人名额之外,每个国家至多派出两人代表团参加奥哲的全球决赛。
在不少东欧国家,选手需要经过好几轮比赛与选拔,方能代表国家出赛。

林燕盈说,她发现相比中国,其他国家的选手在哲学上的积淀明显比较丰富。
相比赛前专程准备,然后临场学习内容;
对于不少欧洲国家的学生来说,诸多的哲学知识是成长过程中自然而然积累下来的。
因此,他们有着有扎实的哲学底子。
这背后可能是文化的原因,比如法国高考中本身就会要求学生掌握一些哲学史的内容。

5月17日上午,决赛正式进行。
选手们各自为营,在官方给出的4个选题中任选一个,并且自选角度进行观点性论文的写作,计时四小时。这对高中生们绝对是个巨大的挑战。
在比赛当场提供的四个选题中,林燕盈选择了一道有关艺术的。
“我选的题目是来自达芬奇的一句话,大概意思是
如果一个画家只依赖重复练习和经验观察,而不依靠理性,那么TA只能成为一面镜子,而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达芬奇的语气应该是说这种画家不是好的画家。
我觉得这句话挺有共鸣的,所以选择为达芬奇辩护。
答题时,我把画家普遍化成艺术家,把画家从事的创作过程普遍化成艺术的创作过程。
为了避免之后偏题进入对于艺术定义的讨论,在写的时候,我先把艺术的所指扩展得比较宽泛。

然后我首先问的问题是:
是不是存在一种没有理性参与的艺术创作?
我发现让这种艺术创作得以可能的方法之一,是把理性定义成judgement of form,对形式的判断。就像我可以判断逻辑推理是不是为真一样,我也可以判断艺术作品是不是美。
当然,这里是指广义上的美,我把它暂时粗泛地定义成艺术所追求的东西,并且是我对已有的一个东西进行认知。而这从某种意义上,是更高阶的,因为它和单纯的模仿区别了开来,是有意图的调配和组织。
接下来,我就讨论为什么没有前述那种理性参与的作品是不那么好的。
我给出了两个论证:
其一,是从德性伦理学的角度出发,指出这样的创作只是模仿,有碍于艺术家的自主性;
其二,是指出这样的创作很难有原创性
,这里我把原创性作为对艺术有价值的东西接受下来。”

在最后,林燕盈又论证了理性的加入,是可以解决这些问题的。
她将自己的论证联系到现代,提了一下理性可能可以成为人之为人,与机器区别的一个
关键,并稍微涉及了人格的问题。整篇文章写下来,大概三千字左右。
林燕盈觉得,与其说奥哲是一次“竞赛”,她会愿意把奥哲描述成一种“交流”——在四天的比赛行程中,其实真正意义上的“比赛”就只有这一上午。
比赛当天下午,组委会为选手们组织了一个达芬奇主题的庆祝活动来迎合达芬奇逝世500周年。遗憾的是,由于林燕盈在比赛前晚没睡好,那天下午她就留在了住处休息,并未参加这场活动。
为了这次500周年的纪念,意大利比赛组委会还让每个代表队做一个小视频来介绍达芬奇的某个方面,请了一位教授过来为选手们做了一场达芬奇作为一名跨学科全才,对于学科分化严重的现代意义的演讲。
“其实很多人不太知道达芬奇的哲学家身份。”至今,林燕盈仍有感叹。
晚上,选手们又被带去一个古罗马废墟看了一场纪录片性质的灯光秀。
除了去罗马的交通费用需要选手们自己承担之外,比赛期间全程的食宿都由组委会承担。

当外滩君问林燕盈她从这次比赛经历中收获了什么时,林燕盈的回答更多是
眼界的开阔与认知的提升。
从相处融洽,还毫无忌惮地拿两国关系开玩笑的以色列代表和马来西亚代表身上,她看到了超越国家政治的友谊。
站在罗马建筑面前时,她真正体会到了艺术史上学到的所谓石柱带来的恢宏感。


与哲学的不期而遇
提起自己怎么会喜欢上哲学的时候,林燕盈笑着说这一切其实都是机缘巧合。
在林燕盈初二初三的时候,她对于校内的学科学习并没有很高的兴趣,而是借着这个由头,自己去图书馆探索了一些平时在学校里没机会接触的学科。
一开始,
林燕盈
是被人类学、社会语言学这些学校里不教,看上去神秘,且似乎对人类本性和社会能提供更多洞察的学科所吸引。
在阅读的过程中,她发现有一些东西和学校里教的不太一样,于是就面临着选择相信什么的问题。
“比如说对于语言学里的语法来讲,学校会想说有一个绝对正确的英语语法,那就是高考书上的。
但是语言学会认为这样规定一个语法太过于normative(标准性)了,应该也要有descriptive(描述性)的语法。

比如说一句英语 I ain’t a white man,你能说这句话的语法是错的吗?不行啊,那人家的确是这么用的。
这时我就想:
我应该去接受我新看到的这些东西,还是去接受我学校里学到的东西?我要通过什么标准来判断什么是真的、值得相信的?
后来这个问题变成,我们说相信知识,知识又是什么?所以我和哲学的缘分,相对于具体的学科问题而言,更为根本的是从知识本身的问题开始的。
我到现在也还认为,
哲学最吸引我的地方就是它的根本性。
别的学科可能有一些假设是从事这个学科的人都要接受的,如果质疑它,可能就不再是在从事这个学科,而是在从事关于这个学科的哲学了。
但哲学对我来说是一个愿意而且能够检视自身基础,而不离开自身的学科,这种独特性和彻底性在我看来是很迷人的。”
在大学里,林燕盈仍然想选择哲学作为主修,并对这门学科进行更深层的探究。

除了本身的喜好,林燕盈的家长也给她了一定的支持。
和许多中国家长一样,几乎全是理科背景出身的林燕盈的家人,一开始也不理解为什么她会喜欢上这样一门“钻牛角尖”的学科,并不鼓励她往哲学的方向发展。
然而到现在,随着他们慢慢见证了林燕盈这一路的经历,他们对她研究哲学的态度也转变为“喜欢就去做吧”。
在林燕盈看来,她从家庭中得到的最大支持主要还是经济层面。
家里的经济条件让她可以去买书,可以去了解自己想了解的东西,也可以支付这次去罗马参加比赛的机票开销。
除此,林燕盈也很感激自己的父母能够允许她在高二这比较关键的一年(注:高中阶段的平时成绩,尤其是十一年级的成绩,在大学申请审核中会得到比较多的重视)去分出那么多精力来做奥哲。

林燕盈自己也承认,换做很多别的家长,他们不一定会同意自己孩子这样“冒险”。
“对我来说,他们不反对就已经是给我很大的支持了。”林燕盈如是说。
其实家人舒展的心态早有”表露“。林燕盈的父母没有很早就让她接触当时风靡的奥数。
在林燕盈的幼年阶段,她上的课外班主要是绘画,古筝等据林燕盈自己说更“感受型”的兴趣课程。一直到四五年级,林燕盈才开始学奥数。
学校方面也给了林燕盈不少支持。
一方面是哲学李彦老师在学术上的辅导与支持。
另一方面,在这次参赛过程中有过一些波折,导致林燕盈差点没能去参加决赛。但是当时老师们都很努力帮忙一起想办法,最终中国代表团成功成行。


哲学是对深度思维和推理能力的锻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