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过近十年编校、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新疆图志》整理本于5月22日在乌鲁木齐首发,引发关注。业内人士指出,新疆是丝绸之路上的明珠,该书的出版对新疆史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首发式仪式,图/新疆师范大学
《新疆图志》是目前所见新疆方志中分类最为丰富、体例最为完备的一种,被誉为清代新疆的“百科全书”。全书采用分志叙述的方式,分为二十九个门类,共一百二十卷、二百余万字、近百幅地图,全面记载了清代新疆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地理、物产等各个方面。
《新疆图志》的编纂始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宣统三年(1911年)完成,由时任新疆布政使的王树枬担任总纂。王树枬在内地任官之际,就以勇于改革、思想开明而闻名。《新疆图志》 不仅体例完备,而且多有创新。比如,该书在道路志中指出新疆深沟重堑,“不患其不能守,而患其不能通。通则富,不通则贫;通则强,不通则弱”,呼吁“他日铁路之兴,又将变而愈通。则开荒徼为康衢,化荆榛而文物,此固穷变通久之方所不能閟遏者”,表现了晚清知识分子对于发展交通为强国之策的充分认识。

新疆图志,清宣统三年木活字印本
《新疆图志》根据新疆地处边疆、多民族聚居的特征,创设了不少新的分志门类,比如设立国界、交涉诸志,对涉及国家利益的疆界、外交给予重点描述;设立藩部、礼俗诸志,对于多民族聚居地的民情风俗给予详细介绍;设立军制、民政诸志,对于边疆地区军队建设和民政举措给予具体罗列;设立沟渠、土壤诸志,对兴修水利、开垦土地情况给予翔实记载。《新疆图志》还抄录了十六卷涉及新疆地方行政事务的奏议,其中十五卷都是左宗棠收复新疆以及建省以来的内容,这个按年编排的档案,也是晚清新疆建设最基本的史料。而根据《新疆布政使司就纂修通省志事札吐鲁番厅文》记载,《新疆图志》编纂伊始,就先期“选派精于测绘之员赴南疆一带测量,并在省先绘总、分舆图,以为修志基础”。这些精绘的地图,分为两个部分,一是标志实业、盐产、邮政、电线分布和以府厅州为单位的道路交通示意图,共二十二幅;二是绘制有经纬度标志的全省地图,共五十八幅。
据史料记载,《新疆图志》全帙最早的印行本,是在宣统三年十二月,由新疆通志局在乌鲁木齐利用木活字排版刷印,简称“志局本”。因时间仓促,这一版本存在不少错误,在印行之后不得不另钤红色活字做旁改处理。《新疆图志》第二次印行在天津,时间为1923年,出版方东方学会对“志局本”的错误进行了修订,但在排版过程中也产生了不少新添的文字讹误。除了这两种刊印本,目前存世的还有一种抄本,分装为一百二十三册,每册以黄色绸缎包装,故称“黄册本”,里面有许多印本中未曾见到的图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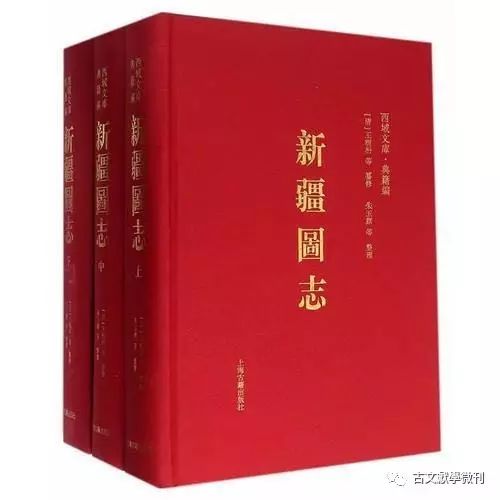
2009年,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新疆师范大学西域文史研究中心综合现有的三个版本,联手对《新疆图志》进行了全面的标点、校勘。经过近十年的编校,《新疆图志》整理本得以面世,使图志编纂中的所有文献得以尽可能全面的展示。据透露,该书第一次将分离的图、志合刊,并对图志中与新疆及其周边直接相关的人名、地名编制了详细索引。据上海古籍出版社社长高克勤透露,《新疆图志》是“西域文库”出版计划的开篇,接下来,该社将携手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新疆师范大学西域文史研究中心奉献更多的西域文献整理和研究成果,为“一带一路”倡议提供历史支撑和学术支持。
附:
《新疆图志》整理本前言(简约版)
文/朱玉麒
一
新疆古称西域。“西域”的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其范围也多有变化。用西域指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为核心的区域,从汉代以来一直延续到了清朝中期。乾隆年间经营西北,“西域”的概念过渡为“西域新疆”,并逐渐以“新疆”作为专有名词指称西域,故祁韵士在嘉庆年间撰着的《西陲要略》中,有“今之新疆即古西域”的定义。光绪年间,左宗棠收复天山南北失地,力主建省,于是从光绪十年(1884)起,“甘肃新疆省”及其简称“新疆”在行政称谓中完全替代了西域的旧名。
在乾隆经营西北以来,“盛世修志”的观念也体现在西域/新疆的文化建设中。有清一代新疆地区的通志纂修,前后凡三次四种。
清代前期,有乾隆年间的《钦定皇舆西域图志》(简称《西域图志》)五十二卷。这部志书乾隆四十七年(1782)告成,由武英殿刊刻并写入《四库全书》。由于乾隆皇帝的亲自过问、编纂人员倾全国之力、主纂人员又多参与西域平定的不同事务,《西域图志》因此比较全面、真实、详细地汇集了乾隆统一和经营西域的史料,成为清代边疆通志纂修的典范。
清代中期,又有嘉庆年间的《西陲总统事略》和《钦定新疆识略》(简称《新疆识略》)接续前志,成为新疆地区新的地方通志。这两部新的志书由伊犁将军承办,开创了新疆地方政府纂修通志的先河。注重文化建设的伊犁将军松筠为了总结统一以来几十年中的发展面貌,召集流放伊犁的文人先后纂修,于嘉庆十二年(1807)由祁韵士纂成了《伊犁总统事略》十三卷,后来多以《西陲总统事略》的名称刊行;嘉庆二十五年,又由徐松纂成新的《伊犁总统事略》十三卷,后出转精,在道光元年(1821)由松筠恭进清廷时,得到新即位的宣宗皇帝赏识,赐名《新疆识略》,并御制序文,道光二年由武英殿刊行。这是“新疆”作为一个省级行政区的专有地名,首次被政府在正式的文本中启用。
清代后期,《新疆图志》的编纂成为新疆地方通志在清代最后的总结。以王树枬为代表的清末新疆官员,承担起了为建省后的新疆谱写新志的重任。《新疆图志》从光绪三十三年开始编纂(1907),宣统三年(1911)完成,由新疆通志局活字印刷行世。因此,这部纂修于新疆建省以后、完成于辛亥革命期间的通志,也是中国封建王朝时代有关新疆的最后一部通志。《新疆图志》皇皇巨著,凡一百一十六卷、二百多万字,不仅在数量上超越了以往的志书,其承载时空的悠长、完备,编纂观念的守正、趋新,也都后来居上,成为新疆地方通志的殿军。
所以,在掀开中国现代史的篇章前,《新疆图志》堪称是一部为古代新疆做了全面总结的集大成的百科全书。
二
《新疆图志》的纂修,光绪三十三年由新疆布政使王树枬(1851—1936,枬字或作枏、楠)创议兴办,其时建立了新疆通志局的机构。树枬字晋卿,晚号陶庐老人,河北新城(今高碑店)人。光绪十二年(1886)进士,先后在四川、甘肃历任知县、道员等职。光绪三十二年至宣统三年(1906—1911),任新疆布政使。在任期间,除了改革币制、创设邮政、兴办实业等一系列使新疆走向近代化的作为之外,《新疆图志》的纂修,也是他在任上重要的文化建树之一。今存《新疆布政使司就纂修通省志事札吐鲁番厅文》对于纂修《新疆图志》的意义有明确的表述。在札饬中,表达了对清朝统有新疆而超迈汉唐的主权意识,并从建省以来“一切规模粗具,惟有志乘阙如”的表述中体现了为新疆建省而修志的明确目标。这份札饬于光绪三十三年十一月初九日下达到吐鲁番厅,已经开始了通志编纂的实际工作安排,并在来年的光绪三十四年成立了新疆通志局——通志纂修开始和通志局建立的年份,过去的研究多有误差,现在根据这份札饬档案,可以定案。
此外,根据饬后所钤“甘肃新疆布政使司之印”的印章,可知实际的执行机构是新疆布政使衙门;而具体纂修的倡议与组织者,是时任新疆布政使的王树枬。因此宣统三年《新疆图志》告成之际在新疆巡抚任上的袁大化就成为当然的修志“总裁”。但是王树枬的署名出现在“总纂”和“总办局务”中,可知居功甚伟。图志编纂的收尾工作由候选道王学曾完成,因此“总纂”衔名由王树枬、王学曾共同署名。按照地方志责任者常规的署名方式,《新疆图志》的作者是“袁大化修,王树枬、王学曾纂”。
王树枬在担任《新疆图志》总纂、总办期间,不仅手订志例、分门列目,还亲自参与了一些分志的纂修和修订,在为钟镛的《新疆备乘》所撰序言中,称“当时予所手订者凡十余篇”。也就是说,全部《新疆图志》二十九志中的三分之一,王树枬都参与了文字编纂。其中提及的《国界志》、《山脉志》、《兵事志》、《访古录》、《新疆小正》、《礼俗志》、《道路志》,后来也都以王树枬个人的名义有单行本刊印。
除了擘画有方、身体力行之外,《新疆图志》能在短短三五年之内就完成巨制,还依靠了一批履新的文人担任了分志的编纂工作。这其中有履新任官者如王学曾、郭鹏、李晋年、刘文龙、段永恩等,也有因事流放或寄寓新疆者如钟镛、裴景福、宋伯鲁等。据《新疆图志》卷首的“纂校衔名”记载,参与纂修图志的人员多达六十八人,但这还不是全部。
总之,是王树枬的号召力和乌鲁木齐丰富的人力资源库,成就了清末《新疆图志》实力雄厚的编纂团体。
三
作为清代边疆通志的典型和新疆地方志的集大成者,《新疆图志》在以下几个方面的突出特点,值得表彰:
1、观念进步
《新疆图志》的编纂,承袭传统通志为地方列传的观念和体例,是中国地方志中后来居上的重要典型。这种继承性,与王树枬等修撰官员在传统国学中的博学渊览有关。更重要的是,在中国近代变革的转型之际,他们的思想能够与时俱进,决定了新的地方通志在反映新疆建省后的面貌时,注入了新时代的编纂观念。具体的表现,是《新疆图志》的编纂顺应时势,具有晚清新政革命带来的强国富民理想。
王树枬在内地任官之际,就以关心国际局势、勇于改革而闻名。他曾着有《彼得兴俄记》、《欧州族类源流考》、《希腊春秋》、《希腊学案》,被伯希和称道为“反映了一名开放的思想家使用一种比较可靠的语言所进行的阐述”。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的乌鲁木齐,是东西方探险家穿梭往来的开放型城市,王树枬和《新疆图志》的其他编纂者,经常与这些海外人士切磋学问,在伯希和、马达汉、莫理循的游记中,都记载到王树枬等人正在编纂这部重要的地理著作而向他们求教西方政治、财经、科学方面的问题,以及打算利用他们的测绘数据到图志编纂中去的交往。
从思想到知识,《新疆图志》不忘主权意识与强国之梦、借他山之石以攻玉的编纂观念,保证了其在晚清方志中的进步性和科学性。
2、分类合理
《新疆图志》采用分志叙述的方式,共设立了建置、国界、天章、藩部、职官、实业、赋税、食货、祀典、学校、民政、礼俗、军制、物候、交涉、山脉、土壤、水道、沟渠、道路、古迹、金石、艺文、奏议、名宦、武功、忠节、人物、兵事二十九个门类,是所见新疆方志中分类最为丰富、体例最为完备的一种。
作为总纂官的王树枬在考取进士之前的青年时代,就参与了直隶总督李鸿章在保定创办的畿辅通志馆的纂修工作,因此对于方志纂修训练有素。在历代通志反映地方自然与社会状况最为基础和传统的门类中,也有纂修者因地制宜的创新之处,如学校一门,完全不同于内地围绕科举为中心的精英教育记录,而是偏重于新政革命以来对于基础教育建设的记载;其中对民族地区教育成败的反思和对策,也多有叙述。
更重要的是,新疆作为边疆、民族省份而不同于内地省区的特征,在《新疆图志》也受到重视,在编纂过程中创设了新的分志门类。如设立国界、交涉诸志,对涉及国家利益的疆界、外交给予重点描述;设立藩部、礼俗诸志,对于多民族聚居地的民情风俗给予详细介绍;设立军制、民政诸志,对于边疆地区军队建设和民政举措给予具体罗列;设立沟渠、土壤诸志,对建省以来兴修水利、开垦土地情况给予翔实记载。
因此,即使我们将在后面讨论《新疆图志》仓促编纂带来种种局部的失误,但都无法掩盖图志编纂中的体大思精和恢弘布局为地方志编纂所带来的方法论贡献。
3、史料丰富
《新疆图志》为后来者提供了新疆在帝制时代最为详赡的地方史料。图志的凡例专门提及:“各志记载攸关,凡得之前书者,必详举原书,附考于下;虽采取之各府厅州县乡土志及各项公牍者,亦必标题清晰。非仅求不掠人美,盖必如是而来历分明,近足以征信当时,远足备后来考证也。”这一宗旨表明了王树枬等在纂修之初就确定了无征不信的编纂目标。
图志编纂中的史料表现,一方面,在有关新疆历史的材料上,纂修者勤于翻检典籍,从丰富的中国古代史志和当代著述中比勘论证,进行叙述,所以《新疆图志》是一部考、述结合的史料库。虽然《新疆图志》卷首的“引用书目”只列出了五十种参考书目,而在具体的撰述中,随文出注的史料文献,据后来的研究者钩稽,竟达六百多种。
另一方面,清代建省以来的“当代史”记述,是《新疆图志》“详今略古”观念下编纂的最大宗。编纂者依据现存盘案、各地采访录、新编乡土志等来完成对当时建置、居民、贸易、物产等天地人事的记述,是保证《新疆图志》具有可信度的重要原因。
正因为《新疆图志》的编纂出自对当时文献的充分依赖,我们至今可以从中获得的一手数据。如有关新疆职官的史料,目前仍以《新疆职官志(1762-1949)》为最完备,而散处《新疆图志》各分志的地方职官可补《新疆职官志》之名录者,不下百处。
4、图表并重
在《新疆图志》卷首的八则凡例中,一共有三则凡例专门说明《新疆图志》的地图编纂,开篇即言“是书图志并重,不敢偏重于志而略于图”,可见对于地图绘制的重视。
这些精绘的地图,分为两个部分,一是标志实业、盐产、邮政、电线分布和以府厅州为单位的道路交通示意图,凡二十二幅,分别附录在宣统三年印行的《新疆图志》之《实业志》、《食货志》和《道路志》中,达到图文并茂、“以豁阅者之目”的目的。二是绘制有经纬度标志的全省地图,凡五十八幅,除了开篇的四幅地图各为一道而合为一省之图外,其余府厅州县地图各一幅,又有“伊犁将军辖境图”“阿尔泰山图”各一幅,其时伊犁将军主要管辖伊犁、塔城一带边防,而阿尔泰山地区当时还未在行政建制上归属新疆,但是由于塔阿借地等问题使之与新疆事务密不可分,《新疆图志》在建置、国界诸志中有关阿尔泰事务的记载以及地图的专门绘制,事实上也为民国年间阿山道的建置归属于新疆提供了理据。但是后来的收藏者和影印着不知就里,将其分别著录,造成了《新疆图志》并无地图而名不副实的印象。
另外,利用大量的表格来一目了然地反映新疆事务的纷繁内容和递进资料,也成为《新疆图志》的一大特色。在《藩部》、《职官》、《民政》、《道路》诸志中,表格呈现的方式多达七十余表,仅《藩部志》详明表述土尔扈特、和硕特、回部各族牧界、世次等内容,就制作了表格二十四种之多,成为方志叙述语言之外明晰的补充材料。
编纂于晚清动荡之际的《新疆图志》,因为时间仓促、书出众手,自然也免不了带来种种缺陷和失误。
约而言之,有以下数端。
1、引文失误。《新疆图志》讲求无征不信,大部分的引用文字,都标志出处。但是核对所引原书,则往往发现这些引文似是而非,多有讹误。
2、出处误记。《新疆图志》抄撮引文时,有误记出处而张冠李戴者;还有一些引文因为误标出处,以致难以覆按。
3、知识错误。《新疆图志》也有因为未经目验而误记史实、不谙民族语言而错标汉字,造成知识性的错误。凡此种种,提醒读者在使用《新疆图志》时,应该核验其所据引的原始典籍,以免以讹传讹。
4、重复叙述。《新疆图志》因为各志编纂出自不同的人员,总合、校勘难以面面俱到,遂至许多内容有重复之嫌。重复录文、重复列传不一而足。
四
《新疆图志》在编纂之初,定名为《新疆通志》,但最终可能因为丰富的地图绘制,使本书采用了传统的图志并称的书名,而改为《新疆图志》。
《新疆图志》最初可能印行过先期纂修好的个别分志单行本。因为《新疆图志》是按照二十九种分志分别纂修,所以各志完成的时间也不一致,提前完成的各志,似乎也都在全书印行之前有单册印行的情况。1910年莫理循经行西北,到达乌鲁木齐,就曾记录《新疆图志》已经完成了九卷的情况,以上的分志,估计就有莫理循所及见者。
这部《新疆图志》全帙最早的印行本,当在宣统三年十二月,即公元1912年1-2月间,由新疆通志局在乌鲁木齐利用木活字排版刷印(以下简称“志局本”)。该书一百一十六卷、卷首一卷,装订为一百一十七册。封面均有隶书“新疆图志少鲁题签 辛亥冬月”字样贴签,少鲁即王学曾的字,可知刷印装订的时间不早于宣统三年十月,而卷首袁大化的总序所署年代为“宣统三年岁次辛亥嘉平月上澣”,则全书最后印行完成也当在十二月底了。这部木活字本的印行,除了上节指出的失误之外,还留下不少制版错误,如植字颠倒、转向以及许多排版中的误植、脱讹,在印行之后不得不另钤红色活字做旁改处理,这种情况每卷都有。加之当时新疆的纸张、活字质量都难臻完美,印刷漫漶之处也在在多有。
《新疆图志》第二次印行,在民国十二年(1923)。其时罗振玉、王国维等发起在中国成立东方学会,于北京、天津设立总会所,并“设印书局以流通古今书籍并本会学术杂志”,于是在辛亥年间仓促印行的《新疆图志》得到东方学会的推荐,在天津得以重印。该书封面贴签题“新疆图志”,而内封题“重校订新疆图志百十六卷”,牌记题作“岁癸亥东方学会据志局本重校正增补天津博爱印刷局印行”,铅字排印,分装四函、三十二册,印刷精美,其铅字、用纸和装帧都堪称上乘,一改志局本的粗糙。东方学会本除了改正志局本上明显的红字所改正的错误外,对于志局本一些古雅生僻的用字,也往往改正为通行而易于理解的字词。此外,东方学会本还在具体的编排上做了修正。不过,东方学会本在排版过程中,也产生了不少新添的文字讹误,均以不熟悉西北史地而有鲁鱼亥豕之失。从整理本的校勘记可知,东方学会本改正志局本错误的功绩,适与其造成新的舛误可以等量齐观。
以上两种刊印本之外,天津图书馆还收藏有一种抄本,凡一百二十卷,卷首一卷,分装为一百二十三册,每册以黄色绸缎包装,故称“黄册本”。其书原为民国实业家、方志收藏名家任凤苞天春园旧藏,多被认为是宣统三年上呈军机处宪政编查馆的精抄本。与印本相较,也多有不同,如其第二册为《礼俗图》,为它本所无。黄册本在《建置志》中还有“两汉沿革图”、“三国西晋六朝沿革图”、“唐代沿革图”、“宋代沿革图”、“元代沿革图”、“明代沿革图”,《国界志》中有“钦差大臣长顺会同俄使佛哩得勘定伊犁中段图”等各图,可见即使在地图本身的制作上,原本也绘制了比现在所能见到者更多的地图。外如袁大化为《新疆图志》各分志撰写的序言,黄册本中除《水道志》前阙如外,其余二十八分志序言为各本中保留最多者。黄册本中,还保留了王学曾纂修的四卷“补编”,反映了辛亥革命前后新疆的社会状况,保留了那一时期珍贵的数据,不无参考价值。如补编二附录“铁路虚线全图”一幅,让我们了解到清末新政中新疆铁路建设的宏伟规划。
五
《新疆图志》作为古代新疆地方百科全书的集大成者,更是近代新疆地方史料的富矿,是西域/新疆史研究的重要资料。不过对于该书的利用,却受到多方面的限制:一是两次刊印的《新疆图志》都留下不少文字错误,难以卒读;二是后来的收藏将图、志分散,难窥全貌;三是相关的影印缩微夺漏,阅览维艰。对该书的点校整理成为我们充分使用这一重要文献的基础。
目前呈现给读者的这一点校本,主要做了如下的古籍整理工作:
1、第一次综合了上述三种《新疆图志》的全本,做全面的标点、校勘。我们以流传较广的东方学会本为底本,以志局本作为校本,并核对相关原始文献,尽可能避免了正文中的文字错讹,并通过校勘记的形式纠正了史实论述的错误。本书还增补了黄册本中为刊本所不载的袁大化分志序言和四卷补编的内容,使图志编纂中的所有文献得到了尽可能全面的展示。
2、第一次将分离的图、志合刊。图、志分排,造成了《新疆图志》纂修名不副实的错觉,也给阅读带来了很大不便。五十八幅的《新疆全省舆地图》,后来只有马大正等整理《新疆乡土志稿》时,曾经缩印单色附录,这个影印,不仅没有回复原貌,而且也混淆了图与志的关系。这次的整理,利用了国家图书馆藏东方学会版的彩印本,使之恢复了图、志并存的旧观。然因印制等技术合成上的困难,此《新疆全省舆地图》将与本书配套,另册出版。原来附录在通志局本正文中的二十二幅黑白地图,在东方学会本中被定名为《新疆实业盐产邮政电线道里图》单另成册,所惜该图册遗漏了《焉耆府总图》一幅,并删除了所有地图框外的绘制者人名。此次的整理本,为了尽可能地保存原图信息,仍以志局本的二十二幅地图插入正文,使之图文对应,方便读者。
3、第一次为本书配置了人名和地名索引。多民族聚居的新疆,丰富的语言带来了不同语种的人名和地名称谓,以及不同的名称构成,因此在使用汉语音译的过程中,也造成了大量同人同地异名,和异人异地同称现象;再加上排版植字者不知就里的刺剌、柘拓之混,称名现象的复杂程度,成为阅读的最大障碍。本书的人名、地名索引,对图志中与新疆及其周边直接相关的人名、地名编制了详细索引,尽量将异人异地的同名现象做出区分。而且通过这一索引汇总,也方便了对翻译名称的研究和统计。然本索引内容丰富、体量很大,亦将另册出版。
由于时间的仓促和整理水平的限制,本书的点校也留下很多遗憾。如:《新疆图志》的多种单行刻本、抄本以及稿本,此次没有列入校勘的范围;对黄册本《新疆图志》的版本价值,仅限于增补他本没有的文字部分内容,并没有将该本作全面的校本利用;而且黄册本中的《建置志》、《国界志》中的多幅沿革、边界图,整册的《礼俗图》,因为考虑到刻本的体例完整和一致性,此次也没有附入。对于《新疆图志》编纂过程中的史料发掘和细节研究的不足,也限制了我们的整理水平。凡此都期待读者的批评指正,以期将来的增订工作能够更加进步。
本书的整理工作缘起于2009年笔者在新疆师范大学主持西域文史研究中心工作期间。参加这一整理工作的,有新疆师范大学、新疆大学和石河子大学从事西域研究的教师与研究生。其后笔者奉调北大,这项整理工作也得到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的支持。因此这一典籍的整理,属于新疆师范大学西域文史研究中心和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共同的成果。对于《新疆图志》的编纂者及黄册本等珍稀版本的研究,也得到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清代新疆稀见史料调查与研究”(项目批准号11&ZD095)的资助,它也是以上这一重大项目的研究成果。
本书的完成,还要感谢以下单位和个人的支持:新疆大学图书馆提供底本与校本的复制,天津图书馆提供黄册本增补的扫描,中国国家图书馆提供《新疆全省舆地图》使用的授权;冯其庸先生始终关心图志的整理并欣然为本书题签,宁燕女士提示新疆档案有关《新疆图志》编纂的资料,北大中古史中心图书馆方平老师为编纂数据扫描和复制随时提供的各种方便。
自整理工作开始,上海古籍出版社就毅然签约出版这一整理成果。六年以来,本书的整理得到各届社领导的关注,责任编辑吕瑞锋一直尽责地承担本书的各种出版事务,出版社的审校人员出色的工作也帮助我们避免了很多校勘错误。这部书稿的成果,也凝聚了该社的心力,谨此向相关人员致以诚挚的谢意。
2015年11月24日于北大朗润园
(本文转载自上海古籍出版社)
来源:
文汇报、上海古籍出版社
策划:
文止
排版配图:
饮冰姑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