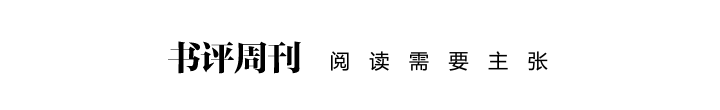
春暖花开,万物更新。书评君最近也推陈出新,开始了许多新的探索与尝试。
书评君近期推出了一个新栏目——“试读报告”。这个栏目的特点在于:
为书评君的读者们提供尚未开售的新书试读本,让大家抢先一步读到最新鲜、最难得的新书。
这些试读本都是书评君与各位出版界的好朋友们精心为书评读者们制作的,与市场上售卖的正式书籍不同,试读本更简洁、更直接,让你与文字进行更加原汁原味的亲密接触。
本期“试读报告”,我们选择的是学者、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洪子诚的著作《文学的阅读》。参加试读的小伙伴们都给书评君发回了热情、真诚又颇具启发的试读报告并给出了自己的试读评分(满分10分)。对洪子诚老师以及文学感兴趣的各位读者,他们的新鲜试读感受也是很珍贵的第一手反馈。
如果你感兴趣,想要参加我们的“试读报告”,请关注近期的书评公号,我们将很快公布下一期的试读书目。如果你对试读书目有建议,也欢迎留言给书评君。
本期试读书目
《文学的阅读》
《文学的阅读》
作者:洪子诚
版本:北京出版社 2017年4月
“洪先生给人印象深刻的,是某些不为“代”所囿的品质。他较少地受制于他成长的那个时代的学风与文风,赋有那一代人中较为稀有的对作品细腻的审美感觉,这种感觉曾经是备受压抑的。与自己生活的时代的风尚保持距离,毋宁说是一种罕见的禀赋与能力,禀赋系于先天,能力也赖有后天的努力,甚至是自觉的清醒的努力。洪先生常会说到自己的“怯懦”、“犹豫”,我却相信他的性情中有较为坚硬的东西,不易磨损,能抵抗外力的销蚀。这种“坚硬”在我们所处的环境中,尤其可贵。”
赵园老师在评价著名学者、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洪子诚老师的文章时,提到了洪老师个人的一些“坚硬”品质。这种“坚硬”的品质也渗透在洪老师这本《文学的阅读》的文字之中:那种缓缓又持久的精神之火,极度朴素又极度骄傲(爱伦堡写茨维塔耶娃的序言)的文字之光。洪老师在序言中讲到自己的个人阅读经验:
我们这些一辈子与书作伴,在书本中消耗大部生命的人,什么时候也能像纪德那样,说出“何时我们才能烧尽所有的书本”这样的话? 难道不是吗:“在书本中读到海滩上的沙土是轻柔的,这对我是不够的;我愿我赤裸的双足印在上面……。任何未经感觉的认识对我都是无用的。”(《地粮》纪德著 盛澄华 译)……现在我想,纪德的意思是,读书自然十分重要,但要走出书本,走向田野和广阔的生活,或者说,书本最主要的是教会、启发我们观看世界的热情和方法,也就是“重要性在你的目光中”。
这本书中的文字,大多是洪老师读一些作家作品的感受,但是会延伸到读作品时,阅读者所处的环境,阅读动机、心情和方法等的讨论;也就是读者和阅读对象建立怎样的关系的问题。这也是洪老师取名《文学的阅读》这个书名的原因。
洪子诚
,1939年生。广东揭阳人。1961年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后留校任教至今,1991年——1993年曾赴日本东京大学讲授中国当代文学。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当代文学教研室主任。著有《当代中国文学的艺术问题》、《作家的姿态与自我意识》、《当代中国文学概观》、《中国当代新诗史》。
霞天饛雀
(数学教师,喜欢写点什么)
试读评分:9分(满分10分)
“重要性在你的目光中”
阅读是人的精神食粮,更是我们观察世界的角度与方法。阅读别人的同时其实就是在阅读自己,寻找共鸣和知己的过程。
子诚老师在前言(按,其实是2010年为《我的阅读史》一书所写的结束语《为赞颂一切我所焚毁的……》)中讲到他自己的个人阅读经验:
『我们这些一辈子与书作伴,在书本中消耗大部生命的人,什么时候也能像纪德那样,说出“何时我们才能烧尽所有的书本”这样的话?难道不是吗:“在书本中读到海滩上的沙土是轻柔的,这对我是不够的;我愿我赤裸的双足印在上面……任何未经感觉的认识对我都是无用的。”(《地粮》,纪德著,盛澄华译)……现在我想,纪德的意思是,读书自然十分重要,但要走出书本,走向田野和广阔的生活,或者说,书本最主要的是教会、启发我们观看世界的热情和方法,也就是“重要性在你的目光中”。』
作为《大家小书》之一种,文集包含了子诚老师对于新诗的阅读,像北岛、牛汉、商禽、张枣、许世旭、纪弦、梁秉钧、牛汉、周梦蝶的诗歌阅读经验,分享了其个人感受;也包括他对于文学的阅读,像巴金、契诃夫、《鼠疫》的阅读经验等等,更多的是随感抒怀。书虽未读毕,但通过这位“性情中人”的阅读史,有心人依然可以窥见历史的横断面。
透过子诚老师的文章,给人印象最深刻的,是文字背后那些他特有的不为“代”所囿的品质。这种品质在我看来,是一种禀赋与能力,禀赋系先天,能力系后天。正如赵园老师所说,『洪先生常会说到自己的“怯懦”、“犹豫”,我却相信他的性情中有较为坚硬的东西,不易磨损,能抵抗外力的销蚀。这种“坚硬”在我们所处的环境中,尤其可贵。』
书中文字大多是子诚老师读一些作家、作品的真实感受,但读来常会感受到子诚老师在阅读作品时所处的环境,体会到其阅读动机、心情和对方法的思考,我想,这也是取名《文学的阅读》的原因罢!
翻开小书,品味大家,扑面而来的是朴素又傲骄的文字之光,更有缓慢又持久的精神之火。我始终相信,“重要性在你的目光中”。
天空之镜
(高中语文教师,希望自己的课堂能发散一点思想的光亮)
试读评分:8分
哪本书会给你轻盈的力量
春色渐深,坐在校园里的紫藤花架下,捧读洪子诚先生这本《文学的阅读》。春草绿的布质封面,隐隐发散春日气息。
在春天,适合读几首新诗,认识几位真正的诗人。
我喜欢书中这样的文章《一首诗可以从什么地方读起》。从什么地方读起呢?在我的语文课上,穆旦的《春》从“读懂了哪一句”的提问开始,诉诸学生的阅读经验;痖弦的《秋歌——给暖暖》从“暖暖是谁”进入讨论,探寻有魔法的意象;闻一多的《也许》从回忆童年入睡情景开始,诉诸日常体验……每首诗都有不同的进入通道。有时,我们得学会用耳朵看诗中的景象;有时,我们得学会用眼睛听诗中的声音。
我也心仪书中这样的观点:做一个“合格”的诗人固然不容易,做一个“合格”的读者同样不容易。读诗,要学会不断变换角色,进入另一个生命体,要习惯词的奇异用法,去倾听万物对话,去发现语言的秘密。还有这句话:对诗人的纪念,最好是去读他的一首诗。所以我愿意用整个春天的时间去读张枣的《镜中》,因为这样的句子它挥之不去啊:
只要想起一生中后悔的事,
梅花便落了下来……
很想知道,今天,哪一片梅花会无声无息落下?落下的那一片,会花多久时间零落成泥?
读这本书最快乐的时刻,是随同作者跟辛波斯卡一起诚恳地向这个世界道歉:
我为自己分分秒秒地疏漏了万物向时间致歉
……
我知道在有生之年无法找到任何理由替自己辩解
因为我便是我自己的障碍
虽然人人都是自己的障碍,好在《文学的阅读》让我轻盈了一点点……
阿芳这个名字有点单薄
(喜欢春树夏花秋叶冬雪暖阳寒星一切一切的我)
试读评分:10分
如何享受阅读
刚看到这本书的名字时我以为这是本“硬”书——讲怎么站在文学专业的角度上进行专业的阅读,当然我是臆测了。所以在看到前言第二段讲为什么取名《文学的阅读》时,内心是欣喜的,这正是我最近思考的和困惑的。读者与文本与阅读是何关系以及如何享受阅读?
关于第一个问题,可以从两方面理解,一方面是文本价值的实现。正如本书中引萨特的话:书要是不被人阅读,他就只是涂在白纸上的黑色污迹,而一旦被阅读就一定和特定读者建立与他人的不同关系。可见,书要实现自己的价值首先就要被阅读,而能多大程度上实现,就要看读者了。这里用了“特定读者”一词,即强调了阅读的主体,也就是你怎么看。这也就涉及到了本问题的另一方面,读者与阅读本身的关系。作为阅读的主体,读者是影响阅读的主要因素之一,读者所处的环境、个人经历,阅读的目的、方法、心情都会影响对文本的理解。就像我在中学时背《论语》,背是背会了,可除了考试不扣分外,对我而言论语与其他课文无甚区别。而随着经历的增长,现在再读论语,读到某些字句的时候会自然地联想到生活中遇到的一些事情,甚至会帮助指导生活,这大概也是洪教授强调书要重读的原因吧,虽然可能会破坏当年的阅读感受,但毕竟有些书是常读常新的。
其次是如何享受阅读?现在我们在生活中经常陷入自相矛盾的境地,读书也是其中之一。当读书变成任务具有功利目的时,就变成了一件使人拧眉的事。我们都不喜欢被要求读书,只享受于被吸引而读书,因此,多读书,对一些“闲书”有助于养成读书的习惯,享受读书的快乐。此外,阅读应是与生活相联系的,就像我喜欢三毛,喜欢杨绛,因为她们的作品有烟火气,能看到她们自己,是活生生的人!纪德说:“未经感觉的认识对我是无用的”,在我理解就是:不与生活发生联系的学问对我都是无用的。
洪子诚教授这本《文学的阅读》内容很广,后边新诗部分除了辛波斯卡稍有涉猎,其他的都没接触过,所以在这方面我只能说洪子诚教授给我扩展了一条新路,而不能对其做任何评价。但是在本书传达的主要内容——阅读、影响阅读的因素以及如何享受阅读这些问题上,我认为洪教授是有启迪、解惑之功的。最后用前言的一句话作结吧:书本最主要的是教会、启发我们观看世界的热情和方法,也就是“重要性在你的目光中”。
缪文培
(汉语言在读,无所事事的学生)
试读评分:8分
用了一天多读完洪子诚的文学的阅读。一行行的觉得读着很轻松。每个读者可能都有自己阅读的偏好或者对某个类型的作品怀有一种警惕性从而敬而远之的习惯吧。我历来对某一个作者谈论一本他们所读过的书而写出来的感想什么的,一直保持着距离感,毕竟对于我来说阅读真的是很个人的事情,大家追求不同,或者只是某个阅读时刻周围环境,心境的不同,都会导致最后每个读者抓到的那个和文章之间产生共鸣的点大不相同。而阅读,就是一个感动自己地过程。去看人家是怎样被感动的从而去强迫自己也有这样的心境,那无异于缘木求鱼。不可靠,也不现实。
但是读了这本书,觉得真的很好,那种放下身段的讲述和偶尔出现的幽默,都让你感觉到作者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他有自己的阅读偏好,也有自己这漫漫一生的积累和遗憾,而不是一个所谓的文学教授,高高早上,说一些完全理论化的东西。一个作者要是不可爱,那他写出来的东西是很难让人感到亲切的。作者,显然是个可爱的人。
里面说的话有很多都对我的胃口,例如文章开始就提出了一个人的阅读史是会记录下他的生命状态和变化,会在这个记录里留下痕迹。细细想来觉得很对,读什么书,什么时候读,对一个读者来说,真有一种冥冥中注定的感觉。总之看完全书,有一种感动在我的心头。毕竟,作者读一辈子的书,是在做一件他喜欢的事。嗯,读一辈子的书,在我看来是一件真是件愉快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