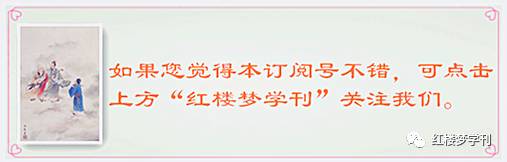

作者 关鹏飞
林黛玉与贾宝玉的第一次见面,后人喜欢概括为一见钟情。林黛玉觉得贾宝玉“何等眼熟”,贾宝玉觉得林黛玉“看着面善”,再加上书中为二人恋情所铺垫的木石前盟,得出这样的结论无可厚非。然而,当我们细读文本,抛开曹雪芹的主观阐释,而关注其精确描写,会发现林黛玉对贾宝玉的接受,即便从第一次见面的角度来看,也有一个走神与走心的过程。二者的分水岭,便是贾宝玉摔玉。
所谓走神,是指林黛玉初进贾府,因为小心谨慎而改俗从众,故其心思不在于如何表达、展现自我,而在于揣测、迎合别人意见,这种惯性延续到她与宝玉的初见前期。林黛玉孤身进府,多观察,少说话,唯唯诺诺,自是良策。但在迎合中难免受到影响,承袭一些偏见。比如对贾宝玉,就听信王夫人的交待,对其所问,答以冷语。这里尤其可以举出读书之问,略作比较。贾母和贾宝玉都问过这个问题。黛玉回答贾母之语为“只刚念了《四书》”,而回答宝玉则是“不曾读,只上了一年学,些许认得几个字”,变化之大,不过转瞬之间而已。原因在于,林黛玉问姐妹们读什么书的时候,贾母答以“读的是什么书,不过是认得两个字,不是睁眼的瞎子罢了”,她便现学现卖。虽然不能因此苛责林黛玉,但在分析过程中却也不能熟视无睹。
最要命的地方在于,看似用心,实则走神,貌合神离,弄巧成拙。贾宝玉问玉之际,林黛玉就是如此处理的。她心思缜密,先忖度一番,再答曰“想来那玉是一件罕物,岂能人人有的”。这话在贾母听来,主要表达“不便自己夸张之意”。林黛玉此答虽深得贾母之欢,却失宝玉之心。从儿童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宝玉不过想要跟看得上眼的伙伴分享美玉,但林黛玉所答既已引起误会,贾宝玉处在那样礼法森严的时代,又不会通过沟通很好地表达分享的意愿,只能通过极端的摔玉的方式来激烈地加以呈现,就不足为奇。
尽管现实的处境让林黛玉不得不走自己之神,猜他人之意,不可否认的是,在她内心深处却还是对宝玉有所好感。不妨从她眼中的宝玉形象出发,略加悬测。由于宝玉中途换衣,故有两处描写,具体内容不同,结构却甚相似,都是先写装扮,再写眉目。前者是身份地位的象征,后者才是本身心神的展现。这就告诉我们,林黛玉所见,是二者兼有的。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贾宝玉眼中的林黛玉,纯粹从眉目入手,深及于心。于此亦可见二人初见前期,态度迥然有异。除去前面所云黛玉初进贾府之因,或亦与男性直白、女性婉转之性别特点有关。
而打破这一层隔阂,让黛玉真正走心的,便是宝玉发疯引发的摔玉行为。

贾宝玉摔玉的原因,说起根由近乎荒唐,细按则深有其味。贾宝玉自己曾说:“什么罕物,连人之高低不择,还说通灵不通灵呢!我也不要这劳什子了!”首先,“罕物”一词,紧承黛玉之语,针锋相对,可见作者安排之用心。后面接以“人之高低”,越发可见宝玉之可爱。以他的身份,在贾府地位极高,他却自认低贱,这不是作践自己,而是平等之心的萌发。且这不是专属林黛玉者,而是贾宝玉普遍的为人准则。讲到“通灵”,这在书中有其特殊的语境,剥开曹雪芹的环节设计,我们不难明白,这种所谓的通灵,不过是打着人神相通的旗号,对礼法隔膜人心、知音难求现状的抗议,而具体到宝黛之间,则是呼吁坦诚相待。最后,贾宝玉决意不要这块劳什子,大有言外之旨。如果不能跟林黛玉心心相通,就算与全世界感同身受,如鲁迅先生所云“悲凉之雾,遍被华林,然呼吸而领会之者,独宝玉而已”,又有什么意义?不如斩断一切,获得耳根清净。
摔玉,看似疯狂的背后,实际上承载着青少年贾宝玉的心理诉求。从林黛玉事后的哭泣来看,贾宝玉达到目的,林黛玉对他的心理期许也发生了直接的变化,从走神一变而为走心。后续的故事也便在此基础上一一发展起来。
曹雪芹借鉴《左传》等史书中的预言表达,给宝黛恋情渲染神秘氛围,营造一种木石前盟、一见钟情的假象,与他隐晦地展现社会现实密不可分。这当然是一种策略而已。他的伟大不在于这些策略性的技巧上,而在于他敏锐感受到时代的新气息,并以充满文学性的叙事表达出来,至今仍然常读常新。以宝黛初见来看,贾宝玉通过发疯砸玉,成功吸引林黛玉,在林黛玉痛失母亲之后,迅速占领她的心灵空白,这类故事,在今天仍屡见不鲜,如法国电影《两小无猜》中失去母亲的男主人公和日本电影《情书》中失去父亲的女主人公等,爱情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亲情缺失。而从全书主人公贾宝玉的疯狂来看,其实疯狂的不是他,而是他所处的整个礼法社会,人心狡诈,真心难求,一旦出现贾宝玉这样的“赤子”,搅乱死水一般的等级森严的固态社会,自然人人喊打,称之疯子。这让我们不能不想起美国电影《飞越疯人院》。清亡已过百年,贾宝玉们的任务仍然任重道远。
从走神到走心,愿我们也能像林黛玉一样幸运地,由阅读,被唤醒。
欢迎长按下方二维码关注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