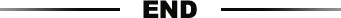于是,我强作镇静的唱起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一路豪歌,跌跌撞撞、趔趔趄趄地跑回了家里。
>>> 人人都有故事
这是有故事的人发表的第866个作品
作者:郭奇然
《生死之间》
(长篇连载 一)
一、我的梦想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在我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常听奶奶讲,我们家里经常闹鬼,每当黄昏降临时,此鬼就出来四处觅食,夜半三更时闯入院中,形体高大怪异,狰狞可怖,煞是吓人。那时,爹不知到了哪里,叔叔在一年前也消失得无影无踪,我们和爷爷奶奶住在一个院子里,半矮半破的院墙无法阻挡那恶魔的出入,所以,那鬼几乎天天来光顾我们的家门。不过奶奶又说,此鬼只是为的寻食,既不伤人,也不掠物,它若来到时,你千万不要喊叫,只用被子蒙住头,过一会儿就平安无事了。
当时,我们全家七口人,住在一间不过三十平米的土屋里。我与两个弟弟裹着一张破棉被,象蚯蚓似的蜷曲在一起,按理说,我们已形成了一个牢不可破的战斗整体,什么恶鬼也自会退避三舍的。可是在缺乏爹的保护下,我还是感到一种莫名的恐惧。我多么盼望爹能够早点回家啊。可是爹究竟去了哪里,爷爷奶奶和妈妈始终不肯告诉我这个秘密,我猜测,爹一定是做错了什么事情,离家出走了,否则,他不会忍心抛下我们不管的。一次偶然的机会,我终于知道了爹外出的原因。
在那天下午的语文课上,由于几个晚上连续的做着恶梦,妈妈做午饭只熬了一锅苦菜汤来喝,所以,刚一上课,我的肚子里就饥肠辘辘,脑子嗡嗡轰叫,不管老师如何严厉的盯着我,我还是趴在桌子上睡着了,不一会儿,我看见爹回来了,嘿,爹是那样的威风,他身穿虎皮铠子甲,手握一口鬼头大砍刀,大声呵斥那恶鬼,“你是何方妖道,竟敢趁爷离家出走之时,欺凌我孤儿寡母,老弱病残,我今天非把你碎尸万断不可 !”说着,爹就和那恶鬼打在了一起,好一场厮杀,我情不自禁地提起了一根哨棒,和爹并肩战斗在了一起,不到几个回合,那恶鬼就被打走了。我大叫一声,“爹,你真了不起!”
可是,课堂上却传来一片大笑,老师狠狠踢了我一脚,并忿忿地说,“ 你上课睡大觉还不过瘾,还居然大喊大叫扰乱课堂。你说说,刚才我都给你讲了什么内容?”我摇着头茫然不知所措。
“我知道你什么也听不进去,可是,严峻的国内外形势你为什么充耳不闻,视而不见,你不知道,国际上,苏修社会帝国主义正在卡我们的脖子,美国支持蒋介石梦想反攻大陆吗?你不知道国内的地富反坏右都在蠢蠢欲动,妄图恢复他们失去的天堂吗?你真是不争气,难道你也要学你老子的坏样子吗?”
我傻傻的看着老师,老师却越来越气,“你老子吃不下农田建设的苦,居然能跑在包头城里打工,还不向生产队交工钱,你知道不,就因为你爹的问题,公社才撤消了我们社会主义文明村的崇高荣誉,你老子真是我们村的千古罪人,我都替你害臊!”
我不知道该和老师如何分辨,反正,自己上课睡觉说梦话总是错误的,老师不管如何批评都是为了我好,我还能说什么呢,只是低下头来一个劲地哭。然而,我却意外地知道了爹的下落,原来他是在城里给我们挣钱,不管爹如何坏,如何丢人现眼,给生产队脸上抹黑,可我相信,爹回家时一定能带来米面的,到那时我就不会饿着肚子上课,昏昏沉沉地说梦话,让老师为我操心生气了,想到此,我心里反倒觉得一阵快慰和欢乐。
终于捱到了下午放学,老师罚完我值日后,已是临近黄昏了,我懒懒地顺着河边往回走。夕阳的余晖映照着熟悉的村巷小路,喧闹了一白天的村庄开始变得安静下来,此时的河边小道上,也只留下了我的孤身独影,心里不免有一股凉飕飕的感觉。我突然看见,在我前面出现了一位白发婆婆,她脚小笨拙,走起路来一颠一簸,很是吃力,这不是奶奶吗?我使劲地揉揉眼睛,证明了我的判断是完全正确的。
“奶奶,你等等我!”我一边喊着她,一边向她跑去。可奇怪的是,奶奶既不应声停下来,也不回头看我一眼,自顾慢慢腾腾地往前走,无论怎样追赶着她,她却始终在我前面走着,样子还是那么艰难颠簸。蓦然之间,从小路的西面猛的刮来一阵小小的旋风,顺着风势,奶奶连翻了几个筋斗,就倏然不见了。我拼命地喊着奶奶,差一点就要哭出了声来,可耳畔听到的只是凄凄阴风,汩汩流水,眼里看到的仅仅是前面的一座小小土庙。
★
这座土庙是我村唯一的河神庙。
我常常听奶奶说,每年秋季,大青山一带暴雨不绝,洪水滔天。一望无际的汪洋由北向南,转东折西地从村里横穿过去,肆虐的洪水无情地把一个村庄斩为两段,形成了南村与北村,每当洪水过后,村里不知有多少房屋夷为平地,多少人卷进大漠荒流,在洪水面前,不管你是佛教徒、道教徒、基督教徒亦或是伊斯兰教徒,都不能享有任何的特权,死亡与不幸都是人人平等的,这就形成了一个共识,固而在南村的河边上有了这座小小的河神庙。据说,有了这座河神庙后,洪水就不再向从前那样暴虐成灾了。自然,这座供奉着八位河神的小小土庙,就成了遐尔闻名的神庙,一年四季总是香火不断,连百里之外的人们都争相朝觐。
可是,虽然我每天不只三次的从它前面经过,但从来就没有进去过一回。因为奶奶常常告诫我,不到十二岁的小孩是灵魂不全的,灵魂不全的人进去后就会失魂落魄,而一旦魂魄走散了,就很难再把它找回来,所以,这不到三年的小学生涯里,每当我上学和回家经过这里时,总是屏声静气,连正眼也不敢往里瞅一下,有时,虽身不由已的窥探一眼,总会觉得里面有很多头颅在轻轻转动,绿眼睛忽闪忽闪的夺人心魄。现在,奶奶又是这样怪异的消失了,更增加了我莫名的恐惧:这座土庙里居住的大概不是什么河神地灵,而是一群吃人的魔鬼,我的腿颤抖的开始不听使唤了,连喊一声奶奶的胆量也没有。但我还是清醒的意识到,只有早一点回到家中,把奶奶失踪的情况及时告知爷爷和妈妈,才能有解决的办法。于是,我强作镇静的唱起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一路豪歌,跌跌撞撞、趔趔趄趄地跑回了家里。
可是,当我推开那扇破烂的栅门时,却看到奶奶在若无其事的喂猪洗菜,这使我更加诧异不安。我忙问奶奶是怎么回家的,奶奶居然说她一整个下午,从未离开院里半步,我慌忙顶住院门,放下书包,糊里糊涂的喝了一碗玉米煮菜汤,又强打精神,帮妈妈洗完了锅碗,就一骨碌蒙住头睡觉了。
★
这一天晚上,我真的像奶奶说的丢了魂魄一样,满脑子都是那连翻了几个筋斗的突然不见的奶奶。尽管我多次责备自己,不要疑神疑鬼,一定是在夕阳的回光返照中看花了眼睛,误把一棵摇摆不定的小树看成了奶奶,可无论如何就是消除不了历历在目,清晰可见的事实。难道说真的遇见了鬼?我不敢再往下想了,可越不敢往下想就越是要想。夜越来越深了,狂呼的北风穿过墙壁的裂缝,给屋里带来了丝丝阴风,仿佛像一个哀怨的女鬼在低声哭泣。妈妈在若明若暗的油灯下给我们缝补破了又破的书包,她软弱瘦长的身子随着扑朔迷离的光线不断变化着形象,一时间,我竟然把她看成了河神庙里的土地爷,吓得我大惊失色,呼叫不已。妈妈以为我中风患了感冒,急忙放下了手中的针线活,用手抚摸着我的额头,并问我什么地方难受。我怕妈妈花钱去找医生,更害怕她深更半夜离开这个黑屋子发生不测,急忙说没什么大不了的,只是心里有些害怕,过一会儿就好了。妈妈再没有说什么,赶忙吹灭了油灯,紧紧的搂着我睡下了。
一会儿,紧张劳累了一天的妈妈发出了轻微的鼾声,刚刚被我大呼小叫惊醒了的弟妹们又重新进入了梦乡。而我,虽然死死的抱住了妈妈,可还是久久不能入眠。强劲的北风照样呼啸不已,房顶上的几捆高梁杆子不时的被刮到院子里,发出喀嚓喀嚓的呼叫。我的心也仿佛被揪住似的,随着高梁杆子的呼叫一阵比一阵紧张,突然间,家门吱的一声被轻轻打开了,我猛得向门口看去,天哪,一个巨大的黑影正蠕动着向我们的土炕走来。我大喊一声,眼前变得一片昏暗。
不知有多少个日子,我一直昏昏沉沉地睡在了炕上,偶尔清醒,就立刻看到那个硕大无比的黑鬼在向我扑来,然后伸出像钢叉一样的魔爪,死死卡住我的脖子。我惨叫着,哭闹着,奋力挣扎着。家里人慌乱成了一团,奶奶给我连续请来了三位乡间大夫,可他们在诊断我的病情时,竟然说的南辕北辙,风马牛而不相及。爷爷奶奶和妈妈不知该听谁的为好,他们眼巴巴地看着我的高烧由38摄氏度上升到了42摄氏度。后来,各位大夫均已摇头无能为力,回天乏术,有的干脆明示尽快准备后事,以免祸及其它弟妹。全家人围着我只是一个劲地哭,两个小弟弟还跪在地上不停的祈祷,他们甚至承诺让魔鬼吃掉他们,以唤回我的生命。有些好心的邻居建议妈妈到旗医院治疗,可家里穷得连一个铜板也没有,拿什么去住院治疗呢?即使邻居们凑上几个小钱,也是杯水车薪,再用牛车拉到四十公里外的县城,恐怕半路上也就没命了。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时而长吁短叹,时而呜咽哭泣,他们愤愤的遣责老天的不公,一个十多岁的孩子就被无辜地送给阎王,还有什么天道可言。
三年级的全体同学也都轮番着地来看我,就连那位语文老师也来了。他站在我的面前,握住我滚烫的小手,已是潸然泪下了,“忠元,我那天下午是不应该批评你的,更不应该出手打你,你是班里学习最用功的同学,也是最遵守纪律的同学,怎么可能故意地上课睡觉呢?是老师不了解情况,一时错怪了你,请你原谅老师吧,老师给你赔罪了。”同学们也跟着哭成了一片。
忽然间,妈妈不知想起了什么,她大声地嚷道:“你们都不许哭,我的儿是不会死的,他是中邪了,是鬼迷了他的心窍,一会儿就会好起来的!”说着,妈妈就像发了疯似的跑出了家门。大约有一顿饭的功夫,请来了村南口住着的一位巫婆。那女巫翻看了一下我的眼皮,很快在土炕的一角设起了香案。她用白蓝紫黄四色纸各叠成了四个纸人,每个纸人的肚子上钉了一枚银针,分别置放在香案的四个方位,又在一张黄纸上写下了一大串符箓,在上面压着沉重的香炉,最后拿出一把短剑来,在我的右手食指上豁开了一道小口,把流出的鲜血轻轻的抹在了剑刃上,再用香灰止住了我的流血。这一切是那样的轻车熟路,快捷有序,人们不禁屏声静气,看着她的高招。只见那巫婆口中念念有词,似说似唱,忽而闭目沉语,相邀各路天兵神将,忽而怒目圆睁,断喝诸方魑魅魍魉,一把血剑在四个纸人旁边不停的挥舞辟刺,犹如一道彩虹。
妈妈在我的背上缝了很大的一块红布,她背着我跟随巫婆不断的跑动,由屋里到院内,由院内到村口,一直向我丢魂魄的地方——河神庙跑去,口里还不停的喊着“忠元魂回兮,我儿魂归兮,妖魔鬼怪快快躲开呀,天兵天将已经把你们包围了。”
当我被满头大汗的妈妈背进河神庙的时候,我的眼睛豁然亮堂了起来。多少年来,近在咫尺擦肩而过的河神庙,由于它的阴森可怖,神密莫测,更因为奶奶的灵魂不全理论,所以,从我记事起就未敢越雷池半步。今天,在巫婆和妈妈的帮助下,又在一大群善男信女的追随下,终于看清了它的庐山真面目,原来不过是几俱破损不堪的泥塑土像。尽管它们的面目狰狞可怖,但有的已是无头无足,有的也缺了胳膊少了腿,倒是在它们身上增加了一层厚厚的麻雀屎,仿佛像一群肮脏的乞丐,脚下却有成群结队的老鼠在肆无忌惮地争抢它们的一点可怜的供品。看来,河神地灵在这里也同样受到异类的排挤与欺辱,它们和我家的处境完全一样,毫无能力来保护自己的神圣殿堂,长期以来,对河神地煞形成的恐惧开始动摇了,我甚至象可怜母亲一悯起了它们。
回到家里后,巫婆将我背上的红布取下,擦掉了剑上的血迹挂在了门上,接着又是一通乱叫乱舞。当妈妈大声喊:“我儿回家了没有?”我脱口而出“妈妈,我已经回家了。”于是,我的灵魂就被招了回来,生命奇迹般的沿续了下去。
二、父亲的回归
父亲因在村里吃不饱肚子,偷偷的跑到包头的白云煤矿挖煤。他原以为到了城里能找份清闲的工作,多挣几个小钱,除了填饱自己的肚子外,还能养家糊口,聊以为生。可是,矿井里的临时工全是靠卖命挣钱,他们使用沉重的镐头刨煤,再用铁锹装在小煤车上,最后要推到井外五百米的地方卸掉,才算完成了一次性的任务。他们两人一个小组,实行了严格的计件工资,每推出卸掉一车煤,每人挣一角五分钱。这样,象爹这般的强壮劳动力,累死累活每天也只能挖上十车煤,获得一元五角的工资收入。而当时每天配给粮食仅八两棒子面,这在满强度超负荷苦力下,无论如何也是坚持不了,况且,井下因瓦斯爆炸引起的塌方与漏水事故不断地发生,临时矿工的年轻生命不明不白的就被埋在了下面,所以,父亲权衡再三,只好灰溜溜的回到了村里。
爹的回家,使我的睡眠状况得到了很大的改善,我第一次感到了父亲的伟大,他就象一道冲不垮的拦河大坝在保护着我的安全。很长时间,我再也看不到那个巨大的魔鬼破门而入了,每个夜晚都能甜蜜的进入童年的梦乡。在梦乡里,我吃着很大很大的馒头,穿着很白很白的足球鞋,尽情地跑向学校、村头与田野,向我的老师和小伙伴炫耀着我的富有和威风。
然而,仅仅维持了半个月的甜蜜梦境很快就因父母的不和而破灭了。母亲责难父亲老实得像个木头人,没有一家之主的能力,把个穷日子过得叮当乱响,家里常无隔夜粮,吃了上顿没下顿,一大群孩子嗷嗷待哺,为了活命,眼睁睁看着别人拿了四斗高梁买走了一岁的妹妹,象你这种男人活着还有什么意思,趁早不如死了的好。父亲也不甘示弱,大骂母亲作风不好,趁他在包头打工之际,不守妇道,与村东头的赵二小鬼混一处,忠元在那天晚上看到的哪里是鬼,分明就是魔头赵二小,为了讨一碗粥喝,你竟无耻到出卖自己的肉体,和你这种贱女人过日子,怎能有脸见人。
爷爷奶奶叔叔姑姑们自然是站在了父亲的立场上,大骂母亲不要脸,给门庭正派的老郭家出尽了丑,丢尽了人,丧尽了门风。愤怒的叔叔拿起棍子毫不客气的将母亲打翻在地,全家人在她瘦弱的身上踢来踢去,象教训一头野牛似的教训着她。围观的人群一阵一阵的高喊,“打的好,好好打,打死这个臭不要脸的,打死这个臭婊子!”我和弟妹们吓得只有嚎啕大哭的份。
★
那时,我还不明白什么叫婊子,只是人们动不动老叫我乌龟王八蛋时,才些微感到了其中的含义。总之,在以后上学和回家的路上再没有一个同学和我相随了,甚至,他们还在后面不时地用石块和牛粪打我。我无法忍受这种歧视和污辱,有一次竟仗着胆子请求父亲,“爹,你不要再和妈妈吵闹了,我宁可看到那个黑影,也不愿要你保护了。”父亲气得脸色铁青,说我不明事理,一定是跟着妈妈学坏了,否则,怎么能说出这样的混帐话来,他越说越气,竟然狠狠的打了我一记耳光,这是爹一生中,唯一打过我的一次耳光。随后,他就抱着我哭了,哭得竟是那样伤心。
其实,我和弟妹们对母亲的看法倒与别人完全不同,母亲是位极其善良明理而又忍辱负重的女人,父亲不在家时的那两年,她为了我们弟妹五人能喝上一碗小米稀饭,穿上不露肉体的土布,整天整夜地在拼命干活,有几次竟累得趴在地上无法站立起来。一天,我实在不忍心看下去了,就对母亲说:“妈妈,我不想念书了,我已经识了好多的字,还学会了打算盘,再不用受别人的愚弄了,就让我帮您做营生干家务吧,我一定会使弟弟妹妹念上更多的书,妈妈,您就同意我这样吧。”
谁知,妈妈竟扳起一幅异常凶狠的面孔,一伸手,对我就是重重的一记耳光,她颤抖着身子骂道:“你这不争气、不上进的东西,怎能说出这种胡话,妈一天到晚的劳累,为的是什么,难道就是为了你能记记工分,算算帐目吗?妈是盼望你们把书念完,将来好有个出息,妈就是累死饿死,也不能停止你念书啊!”这也是妈妈一生中唯一打过我的一记耳光,说着,她就紧紧地搂着我大哭了起来。
从那天起,我就暗暗地下定决心,一定要抽出时间,多帮妈妈干活,尽可能为她分忧解难。那时,我家的院门紧挨着饲养院的南墙根,在饲养院的牛圈里,残存着不少的干牛粪,而在马槽中也剩余着很多的干草秸,这些都是很好的烧材原料,我为什么不能利用它们呢?我发现,每天晚上在上灯的时候,两名饲养员填满马槽里的草料后,就要回家吃饭,我抓住这半小时的机会,悄没声的翻过断墙,在牛圈里摸索着干牛粪,在马槽中捡取着干草秸,捡满一筐后,再悄然翻回到家中。开始行窃时,我未免心惊胆战,拙手笨脚,又不熟悉里面的情况,曾有好几次被儿马踢倒,叫驴咬伤,为此,我一度心灰意冷,不知所措,准备洗手不干了。可每当看母亲佝偻着身体在地里捡干柴时的艰难,我的心里就酸楚的隐隐作痛,我不能退却,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也要帮助妈妈解决烧材的问题。那天晚上的电影《南征北战》,给了我很大的启发:高营长为什么带兵总是能打胜仗,连军长都表扬他,“仗使你越打越精了”,还不是因为他对敌情的了如指掌。第二天中午放学后,我佯装在饲养院里玩耍,心里却暗暗记住了每匹马和每头驴的位置,了解它们各自的性格特点,并有意的给它们加草,在它们身上搔痒,一连几天,所有的烈马和暴驴都成了我的要好朋友。奇迹终于出现了,以后每晚在它们的饭碗中取其剩下的食物时,它们就会默默地站在一边,十分友好的抬起头来停止咀嚼,任我分享它们的残羹剩汁。就这样,每晚总能取出一筐子干牛粪和两筐子干草秸,相当于母亲捡三天的干柴。对我的这种行为,开始时母亲还严厉的责骂一番,她要我堂堂正正的做人,清清白白的处事,不该从小就偷鸡摸狗,学坏了心术。可是,当她在半夜里看到弟妹们被寒风冻得直打哆嗦的时候,当她在我熟睡中轻轻解开我的衣服,看到我被牲口踢咬得伤痕累累血迹斑斑时,她竟然伤心地哭了。我想,母亲的眼泪大概就是默许了我的行为。
然而,使我不能理解的是,母亲为什么要和赵二小相好呢?据我所知,居住在村东头的赵二小,是个可恶的痞子和恶棍,他仗着在战场上立过三等军功的政治优势和国家每年补给二百元生活费的经济条件,在村里恣意欺男霸女,鱼肉乡人。乡亲们像躲避瘟神似的躲避着他,但是,他对我们家的态度却是十分友好的,还经常挑水和泥垒堵破烂的院墙,这可能就是因为母亲的缘故吧。我记得,在我刚上三年级的时候,因交不起两元钱的学费,学校一度停止了我的上课。赵二小知情后立刻找到了学校,不知什么原因,学校不但免去了我的学费,还提供一些必要的铅笔本子,以资助我的学业,这使我十分感激这位十恶不赦的恶人。每当我见到他的时候,还叫他一声赵叔叔。那年冬天,我全身没有一件棉衣,早上尽管是跑步上学,可到了教室后,都已经是手脚冰凉,呲牙咧嘴了,过上半天也握不住铅笔。又是这位大恶人,给我送来了一条棉裤,虽然十分的陈旧肥长,但我穿上后还是感到一股说不出的温暖。
★
一天下午,我正兴高采烈地拿着考了一百分的算术卷子回家报喜时,突然被一个小伙子抓住。他污言秽语,出言不逊,大骂我长了三只手,偷走了他的棉裤,勒令我立即脱下棉裤还他,否则就要砸烂我家的门窗。在大庭广众面前,我拒绝脱下棉裤,小伙子恼羞成怒,一拳将我打倒在地,然后骑在我身上,就要强行脱掉我的棉裤。我无力与他抗争,很快,裤带就被解开了,我闭起双眼,等待着这一屈辱时刻的到来。
正在此刻,赵二小不知从哪里喝酒经过,他不问情由,出手就是一连串的重拳,直打的那后生眼冒金星,鼻子里鲜血直淌。他像一头狮子在狂吼着“你他妈的睁大狗眼看一看,是哪个孬种偷了你的棉裤,你的棉裤上有你妈的什么记号,这个小娃娃穿的怎么是你狗日的东西。”
那后生直吓的丢了三魂,丧了七魄,忙不迭地跪在地上求饶,磕头犹如捣蒜,“大爷,请您老消消气,这条棉裤不是我的,就当我吃错了迷魂药,嘴里把不住门的胡说八道。您老大人不记小人过,就放过小的这一把吧,小的给您磕头,求大人高抬贵手了。”
围观的人群虽然犹如蜂蚁,其间也有那后生的一大堆亲戚朋友,但他们一个个就像秋后的蚂蚱,傻呆呆地站在一旁,既不出手相救,也不开口劝架,眼巴巴地看着赵二小往死里打他。
我实在不忍心看下去了,急忙提起裤子劝道:“赵叔叔,你就不要再打他了,既然他认了错,说这条裤子不是他的,你就饶他一码吧,你看,他的鲜血已经流了一大摊了。”
赵二小见状,又狠狠的踢了那后生的屁股一脚,然后回过头挑衅地对围观者说,“你们都看见了,以后谁他妈的狗吃耗子多管闲事,老子就剥了他的皮,抽了他的筋,叫他变成一个不男不女的二胰子。”
从此后,我就放心大胆的穿起了那条肥而且长的棉裤,堂而皇之地出入在校园里,家门口和田间的小路上,再也没有人敢欺凌我了,也再听不到人们说我是乌龟王八蛋了。看来世界上原本是没有真理的,真理就是强权,就是力量,就是血与火,火与水的一种较量。对于赵二小这样的恶徒,我非但无法恨得起来,反而倒生了一种感激与崇敬之情,而对于我的父亲,反倒是同情与怜悯多于感恩了,真是不孝之徒。
(连载中,请关注……)
责编:彭彭
本文版权归属有故事的人,转载请与后台联系
阅读更多故事,请关注有故事的人,ID:ifengsto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