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本文系读者来稿,感谢译者杨基先生的赐稿。文章译自卡森《重返基督与文化》(
Christ and Culture Revisited
)第四章第二节。提前声明一下,囿于卡森的神学家背景,本文的观点我们未必会完全赞同,不过,作者对民主脆弱性的分析,以及对神化民主的担忧,显然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全文近
4000
字。
………………………………

注:唐纳德·卡森(
Donald Arthur Carson,1946~
),
归正福音派神学家、新约研究教授。
多数西方人会毫不迟疑地说民主是个好东西。当然,美国人认为民主带来和平,所以民主是所有人的权利;这个想法已经影响美国政府的外交政策长达一个世纪——自从威尔逊(
Woodrow Wilson
)提出十四点计划至今。不可否认,民主制度的确立,已经带来很大的社会变革。从二战的废墟中,从“日出之地”(即日本)的集权主义政权和千年帝国(即纳粹德国)的失败中,崛起了两个强大的民主国家。民主制度继续在西欧推进:意大利、希腊、西班牙也纷纷加入民主阵营。民主在韩国取得了巨大成功。帮助推翻苏维埃帝国的各种伟大思想当中,民主是其中一个;苏维埃帝国的前卫星国家如今都在以不同的步伐走向较少集权、较多民主的理想。阿富汗和伊拉克当前军事冲突的部分驱动力,就是人们希望这两个国家建立良好民主体制,不仅克服它们内部的分裂,而且成为中东的进步磁石,吸引其他穆斯林国家走向民主政府、自由市场、相对自由、较少爆发狂热侵略的方向。
当然,在民主形式的政府环境下长大的人,没有一个人可以无视民主有许多问题——笨拙、低效、腐败等等;没有人可以无视民主与暴民政治之间的界限多么细微。
尽管如此,(
122
)我们如果不同意丘吉尔的著名判断,就是对历史的极端无知:“民主是糟糕的政府形式,但别的形式更糟糕”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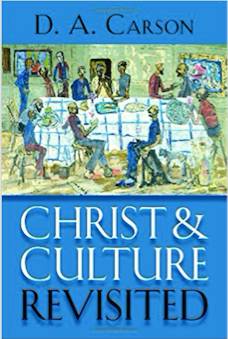
我们思考“民主如何帮助建立一种亲近基督教、有时又反对基督命令的文化”之前,
我们首先应该记得民主是一种复杂的现象。民主的复杂性表现在多个层面:从民主的表面形式,到作为民主基础的意识形态,再到民主实践的成熟程度。
古代雅典的那种相对直接但当然严格受限的民主,迥异于美国投票选举的复杂层级,美国连总统选举都要通过选举团这个中间机构进行。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神话解释自己的民主起源。英国总是提到
1215
年和大宪章,并且自夸威斯敏斯特是“一切议会之母”——尽管自从
13
世纪一来,英国已经经历了多场内战、一次弑君之变、奴隶制度的设立和废除、以及不列颠帝国的兴起和衰落。法国人喜欢夸耀
1789
年的大革命推翻了教权制度,以及倡导“自由、平等和博爱”——但是,法国大革命直接导致罗伯斯庇尔暴政,然后又引发拿破仑战争,而自从
1789
年之后,历史的波涛推动法国走过两个帝国、两个君主集权、两次独裁、以及五个共和国(到我上次数的时候)。美国夸耀自己的宪法和宪法所保障的权利法案,夸耀其明确分权的管制形式,但这种形式的民主并没有阻止内战爆发(美国历史上最血腥的战争),美国长期受困于奴隶制度和种族主义,总统多次遭到暗杀和未遂暗杀,并且,当然,还有常见的各种不公正、不平等、操纵民意和外交政策失误等等问题。
克钦(
Ketcham
)的新书仔细描绘了各个地区的民主(例如北美、欧洲和亚洲)具有相当不同的根源。这是这本书的一个长处。例如,儒家意识形态推动很多亚洲形式的民主走向金字塔式的、集体共享的理想,而远离多数西方形式的民主。(
123
)我们也会思想民主如何演变的问题。民主的演变可能是非常缓慢,我们可以合理地问这样的问题:“英国是何时成为一个民主国家的?”——并且意识到这个问题没有一个令人信服的简单回答。
我们也可以思想思想美国宪法的多数设计者预见到民主不是“智慧出于多数人意见”的政府形式,而是“确保政府必须向人民交账”的政府形式,这种政府形式有“定时淘汰”的机制,每隔几年就要甩掉那些“统治者”,免得他们的个人权力(更不用说政府本身的权力)变得迟钝和腐败。
与之相反,今天形形色色的政客则倾向于诉诸“美国【可以换作 ‘法国’、‘英国’、‘加拿大’等等】人民的智慧”。
然而,
更困难的是,西方传统上与“民主”相联系的那些自由和价值观,在另外一些“民主国家”几乎毫无踪影。
位于撒哈拉以南的黑非洲国家,很多统治者是通过选举产生的,选举程序也相当公正,而且他们上台之初都得到了多数人的真诚拥护,可是最后却变成了暴君,只能用政变赶下台。 伊拉克和阿富汗最近产生的民选政府仍然非常脆弱(尤其是前者),并且这两个政府都根本不支持西方民主国家那种“宗教自由”——但公平地讲,在阿富汗这样的国家,百分之九十九的人口是穆斯林,这里的“宗教自由”和西方世界大不一样。选举人为什么要信任这个或那个政府,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投票所要表明的公众意愿并非总是一目了然。例如,很多人说(讲得不无道理),最近的巴勒斯坦大选投票(
2006
)导致哈马斯掌权,选民投票给哈马斯,并非因为多数巴勒斯坦人想把以色列从地球上抹去,而是因为他们已经受够了阿拉法特和他死党的无耻腐败。(
124
)加拿大魁北克轰动一时的投票公决也是这样,魁北克人党掌权不是因为多数选民希望脱离加拿大(随后的公民投票证明了这点),而是因为多数投票人厌倦了其他传统政党的争吵、狭隘和腐败。换句话讲,民主真够乱的。
很多严肃的批评家已经注意到,要有一个比较稳定的、西方意义上的民主制度,必须满足一些前提条件。至少必须有一个独立的司法系统,有自由媒体,某种确保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制度(通常是被奉为神圣的宪法,和纪律严明的警力),某种确保军队服从平民控制的结构,以及一个和平更换领导人的制度(通常是一个稳定的两党轮换制或多党制)。我们还可以加上其他一些要素,例如民众有一定的教育水平;但有一点很明显:西方人所讲的“民主”,其实是“自由的民主”,而非“不自由的民主”,也就是世界其他很多地方涌现的民主实践。后面这种表达方式,“不自由的民主”,来自于扎卡瑞亚(
Zakaria
),
他在书里深刻地指出,在确保自由的措施真正到位之前,肤浅的民主政府形式很容易让位于极权主义
——二十世纪法西斯的崛起证明了这点。换句话讲,一两次民主选举并没什么用。这种投票,最理想的情况也只是某个更实质进程的第一步,
但一个不自由的民主国家也可能组织投票,甚至是相当干净的投票,而这种投票只是为了拥护某个暴君或屠夫或理论家(宗教理论家或别的什么理论家)。
没有证据表明最近的伊朗大选有严重的腐败问题,但是伊朗的新任总统内贾德是那种否认纳粹大屠杀的极少数人之一。他还发誓要把以色列从地图上抹去。随着内贾德在伊朗国内强力推行伊斯兰教法,伊朗的基督徒正在承受一轮又一轮凶猛逼迫的压力。那么,可见,(
125
)将来在伊朗,基督和文化必定发生大量冲突。但伊朗政府确实是民主选举的。那么,显然,有头脑的基督徒不可能兴高采烈地拥护一切民主诉求。
但是,让我们现在把讨论的范围局限于西方成功的民主国家;这些国家多年享受自由,我们已经对此习以为常,不觉得稀奇。从西方的角度看,名副其实的民主是拥有各种自由和保障的民主,就是扎卡瑞亚所说“自由的民主”。这种民主又如何呢?基督徒应当如何看待它呢?
几年前,我和斯洛伐克一位牧师谈话。他说,柏林墙一倒塌,各种全新自由就涌入斯洛伐克。仅仅三个星期之后,他有生以来第一次看见伯拉第斯拉瓦街上贩卖色情书刊。这不是基督徒鼓掌欢迎的进步——但基督徒也不希望政府完全压制媒体。简而言之,自由带来很多好东西,但正因为我们人类善于败坏任何体制,所以,自由必然也会带来很多邪恶的东西。专家说,北美的色情出版销售收入如今超过酒精饮料、毒品和香烟的总和。
问题比斯洛伐克这位牧师的故事所暗示的还要复杂得多。多数人掌权,意味着少数人不掌权。我们没有什么具体的理由可以认定多数人永远(甚至经常)赞同基督教理想。随着多数西方国家迅速自我脱离犹太—基督教传统,民主多数派的观点和基督教少数派(并且,同样地,当然与其他少数派)的观点越来越对立,极化现象日益尖锐。理论上,民主制度努力保护少数派的权利;但在现实中,这很难落到实处。有时候,立法者和法官只注意保护少数人,反而忽视多数人的观点。但是,一旦少数人的观点来自于他们的宗教信仰,(
1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