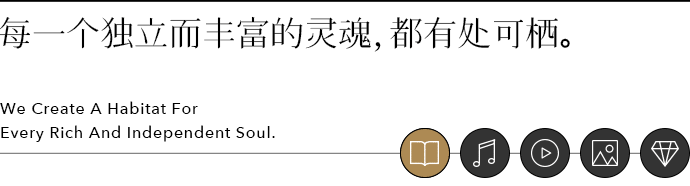

每到十一,单向街的编辑们总希望借长假在时间上带来的系列感,为读者朋友们呈现一些不一样的东西。从开篇的图中,大家也能看到,这次十一,我们将呈现一系列和“地点”相关的内容。这是第一篇,关于北京。
旅居中国 20 余年的意大利学者雷立柏在他的新书《我的灵都》中说,北京在地理上或许是找不到的,比如慈云寺、八王坟....很多地名真正的意义都消失殆尽。然而从古至今,北京一直是人之汇聚地,在城中生活亦是心之浪游,与其强行诉说对故都的眷恋,不如聊聊关乎心灵的有趣话题,比如——
在北京,有哪些地方可以一个人哭?
▼▼
“只要有手机信号的地方”
方可成 | 宾夕法尼亚大学传播学博士候选人,政见 CNPolitics 发起人
只要是有手机信号的地方,都适合一个人哭。因为几乎每个人的注意力都被自己手上的屏幕吸走了,他们真的不太可能会注意到你在哭还是在笑。
心理学研究发现,一个人哭确实有助益宣泄负面情绪、改善精神状态。相比起来,在很多人的注意之下哭,是不利于宣泄和改善的,原因有二:哭的人觉得尴尬,发泄得不彻底;围观的人多了,反而不会有人会上前给予认真而深度的安慰。
但是,最有利于宣泄和改善情绪的其实是在另外一个人面前哭——当然,这个人肯定是对你很重要的、能够给予你安慰、能帮你分析问题并且寻找解决方法的人。
所以,最适合一个人哭的地方应该是:有手机信号,并且能让另外某个人能够很方便地找到你的地方。

参考文献:Bylsma, L. M.,Vingerhoets, A. J., & Rottenberg, J. (2008). When is crying cathartic? Aninternational study. Journal of Social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27(10), 1165-1187.

“冬天的玉渊潭”
Yuda | 单向街主编
玉渊潭公园在今天的北京,也是鼎鼎大名的。尤其是春天,每一棵盛开的樱树下都站着一撮人,闹哄哄的拍照。赏樱赏樱,本是花之美艳与人之笑靥两相映照,但在这人间热闹中,花影人影不分,仿佛一下子欣赏力就下线了。
可是同一个公园,换个时间,便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面貌。
2012 年冬天,由于工作地点的关系,我得以常常出没于玉渊潭。这个公园四季的最大特色其实不在于花树,而在于一池子水。若是这池水出现在一个避世山村,也许是会被称为“海”吧!
冬天时,一大潭水都结了冰,冰上落一层雪,雪上近岸的地方,可以隐约看到一些枯干的树枝,就如一幅巨大的白色画卷,大部分的留白,点点枯叶,再配上潭外寂寥的人影,很像日本的某些艺术作品,禅意中满是人间萧索。

玉渊潭之冬
当时感觉工作很不顺,这种不顺在于,作为编辑只能执行很机械的指令,完全不能表达看法,也完全不能徜徉在自己喜爱的文化艺术领域。我也不是那种一定要怎样的人,只是觉得这不是我想要的,可是又觉得不应该好高骛远,应该像很多人宣扬的那样,先在自己的岗位上做出成绩来,再来想下一步。
成绩?哪有那么容易,一切都是机械的工作量而已。当时我的上级老田,是一位剔着光头,以及并未到中年的男人。他对工作中的一切也早已厌烦,做什么都不紧不慢的,而且会夹杂着不满的话语,都是些反着说的话,和他不熟就不容易听出来。他那个时候购置了房产,同事之间也会传他的生活,孩子,老婆……因为老田这副样子,我反而觉得他是个好上级,至少他是理解我的了。
可是这种工作就像一张网罩下来,老田逃不掉,我逃不掉,我的同事们也逃不掉。老田逃不掉在于每天想房子的事儿,不仅北京要买房,其他的二线城市也是可以买房的;同事的逃不掉可能是每天都享受着价格低廉的工作餐,早中晚三顿,有时候中午还会加一个蛋黄酥;我逃不掉在于还没想好下一步的去处,反正在家待着也很尴尬。和同事我也很少聊我的想法,他们觉得工作的稳定大于一切,当然还有工作餐,我唯一受到影响的,是无可就药的在一位同事的带动下喜欢上日剧,以及和另一位同事去吃一家免费送粥的香河肉饼,只是吃饭,也没法说更多话。
再有,就是偶尔去玉渊潭一个人哭。现在说起来好像都是小事儿,可是当时在那张大网下,没有挣脱出去,也就黏在上面,越是感觉黏在上面,日常的桎梏就越多。可是去了玉渊潭呢,面对着巨大的画卷,冬之收敛尽在眼前。一切都那样沉静,沉静到出现了美感,将一切不顺心吸走了,这一潭冻水不是那种算计得失的“伶俐女子”,而是一位没有固定性别的老者,一切尽在不言中。然后,便不禁想到,开春后,这冻水会活起来。
想要一个人哭?冬天,去玉渊潭吧。

“没有”
于一爽 | 作家,资深媒体人
在北京,没有地方可以一个人哭。

“奥体中心,地铁站附近”
李君棠 | 伦敦大学学院(UCL)比较文学硕士,单向空间编辑
这是一个伪问题。答案大概是,北京在几乎任何地方都可以一个人哭,因为没有路人会过问。
来到北京之前,我住在伦敦。伦敦人很喜欢拿自己与人之间的界限感开玩笑,在公共场合,不轻易进行眼神接触,不对陌生人突然微笑,甚至有笑话说老派伦敦人,因为在地铁车厢里不幸遇到熟悉的同事,不得不打招呼,而焦灼到满头大汗。他们管这个叫城市孤独(urban solitude),是他们要小心维护的精神文明。有一次,一位美国人发起活动,号召大家在地铁里戴上“和我聊天吧”的胸章,希望拉近乘客之间的距离,就有反对者制作了“尊重城市孤独”(Respect Urban Solitude)的胸章,人们看了,会心一笑,保持珍贵的沉默。

“和我聊天吧”胸章

反对“和我聊天吧”的人,制作的“尊重城市孤独”胸章
但伦敦也有为数众多的见义勇为者,或者好管闲事的人;如果在伦敦的公众场合大哭,总会有路人来问:你还好吗?
在北京的情况是相反的。找到闲谈的人,可比找安慰你痛哭的人容易得多。
我在北京第一次哭,是在奥体中心地铁站附近,一个公园的凉亭休憩处。坐在硬石凳上,广播突然轰隆隆地开始播放:《北京欢迎你》。我就在那儿一个人大哭起来。

北京地铁奥体中心站
在北京,你很容易学到宏大的概念,学到大局观,很快就会学会说“我家大门常打开”,觉得自己背后有一整个集体。就像你来到一个地方,就被赠送了一整片丰饶的大海,你是大海里的,并不是一根针,而是一滴水。大海的荣耀应该是有你一份的。
但是我要怎么把一滴水,从整片大海里区分出来呢,我这一滴水,又如何区隔于其他的水呢?就如同我无法把自己从北京的匆匆行人中区隔出来,我和你,心连心,我们都一样。所以,我并不需要写出,自己当时正在经历什么,我究竟为什么哭,在北京学到的第二件事,就是你的麻烦并不重要,并没有重要到那个程度,你的麻烦就是北京,你的良心也是北京,北京包括你的一切,你没得抱怨。
网络上流传中国人的四条哲学,以这四个理由,可以忍让、劝解任何事:“来都来了”“大过年的”“人都死了”“都不容易”。我们都学会了不去打扰那个在奥体中心痛哭的年轻人,因为我们知道,我们都不容易,我们都经历过那个,在《北京欢迎你》的歌声之下,意识到自己孤独一人的时刻。
在北京,任何时候你都是一个人哭。

“天安门”
Sam | 三联·松果 内容运营总监
我大概是世界上最爱哭的男生了。电影感人的瞬间,和家人的矛盾,工作上的挫折都足以让我哭一场。
2008 年,也就是奥运会举办那年,我决定到北京求学,那也是我人生首次进京。凌晨,拖着行李箱抵达火车站后,我决定先到天安门去看升旗。那个时间段的北京,好似一个巨大的空城,我知道有几千万人聚居在这里,却完全感受不到这个城市的边缘。
天安门似乎并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大,但是,当国旗升起的那一刻,我哭了!那一刻的我,似乎已经意识到,这个城市将承载我的梦想和最好的青年时代。

保罗·格雷厄姆(Paul Graham)曾游历了全世界各个城市,在那篇著名的《市井雄心》里他说,最终决定一座城市是否吸引我们的,是它是否满足我们对生活的雄心。野心高低决定着我们可以多大地忍受环境并追求自我可能性。你要是在一个城市过得很自在,有找到家的感觉,那么倾听它在诉说什么,也许这就是你的志向所在了。
是的,也许因为嫌故乡太小,也许因为我的梦想太大,我下意识的把自己推向一个巨大的城市,一头栽进自己的命运。
在北京的这十年里,我的确更爱哭了,我会在卫生间或者无人识的街头痛哭,怀疑这个城市是否真的有我的位置。但是,当我每次都要撑不下去的时候,我都会去天安门前看一看,一个人哭一会,那里能让我想起我第一次来到北京的那一瞬间。
我就这样怀抱着自己的“市井雄心”,在这个城市里一年年住了下来,试图生长出自己的枝蔓。我常常穿越几十公里,和朋友们聚会,我需要热闹的饭局,临时的陪伴,去抵抗这个巨大城市的冷漠,虚无和幻觉。
在北京的第一个十年就快这么过去了。北京的秋天又来了,这个季节没有让人抑郁的雾霾,天空澄澈高远,蓝得一望无际。
北京的秋天,郁达夫在《故都的秋》里这样描述过,“在南方每年到了秋天,总要想起陶然亭的芦花,钓鱼台的柳影,西山的虫唱,玉泉的夜月,潭柘寺的钟声。在北平即使不出门去罢,就是在皇城人海之中,租人家一椽破屋来住着,早晨起来,泡一碗浓茶、向院子一坐,你也能看得到很高很高的碧绿的天色,听得到青天下驯鸽的飞声。”

《故都的秋》
最近几年,我也有朋友相继离开,回到了属于他们自己的城市。我也靠举家之力在北京有了属于自己的房子。我也很少再去天安门“缅怀”自己来到北京的那个时刻。
现在,每一次回京降落前,我总爱朝窗外看去,然后一个人静静哭一会。当我看到整齐划一的四方城,明亮璀璨的灯火,那么绚丽迷离,像熠熠星空,闪烁着光芒,就觉得前方一定有光明在等着。

“圆明园嘛”
秦霜 | 热爱大自然的美学博士
不过
就算我怎样装作若无其事
我都没有办法不承认
我失去的东西实在太多
——关淑怡《三千年前》
圆明园嘛。对我来说,这大概是一个不需要思考的问题。在秋日的黄昏,西风或是残照里,大水法遗址日复一日地讲述一个关于衰败的故事。你安静地听,默默行走或是驻足,石头面露难色,地面衰草迷离。

你或许以为我要说的,是那个有着一段伤心过往的,历史书上的圆明园吧。不,不是的。遗址适合凭吊或怀古,但作为景点的遗址,是属于众人的。而当我们想要为无须克制的流泪去找到一个场所,我们则希望它,是尽可能私人的。这个时候就有人告诉我,圆明园其实很大,他要带我去的那个地方,哪怕是像黄金周这样的日子,也可以用人迹罕至这个词来形容。
他说的,是真正的圆明园。比长春园和绮春园的面积加起来还要大的一个极易被忽略的存在。作为一个从一栋楼前门进去,后门出来就找不到路的脑残级路痴,我怎么可能知道哪是哪儿。

圆明园全图,可以很明确的看到三个园:圆明园,长春园,绮春园
但也不用害怕。相比于带着怀古的目的去找长春园的大水法,无知和无目的意味着,一切都是随心而自在的。心有戚戚却走向“坦坦荡荡”,对着一片草地去想这是不是乾隆听雨作诗的“碧桐书院”,看到“天然图画”和“上下天光”却始终都无法在胸中勾勒那曾是怎样一幅盛景。
这些都不重要。是遗址了,是旧事了,分不清了,说不清了,就好像回到一切刚开始的样子,自然而野趣横生。
这便是我们想要找的那方,哭泣的绝佳地点了。几百年前的秋天就开始萧索的树木,如今还是自顾自地站着,似乎从未坐下来休息。冬天的时候路过一片野湖,冰面碎裂的形状像是来自某种远古的力与几何,冰下像是冻住一个落难的太阳。

圆明园破裂的冰面
似乎是在呓语了。因为走了那么远的路,竟丝毫不觉得累,岂非在做梦。转眼就到了福海。冻得瑟瑟发抖的你,才会把那天的晚霞看成是太阳烧剩的火吧。连最后一根烧得焦枯的木柴都不放过,生硬地在天幕上再皴上几笔。连最后一把灰烬都不放过。寒鸦飞过,大片寒鸦飞过。黑色的寒鸦是晚霞的灰烬。
听说那片乌鸦,飞了有几百年那么久。
如此美妙的瞬间,就那么发生,又转瞬即逝。你睁大了眼,手脚并用也撑不住太阳的离去。白昼像坠落一样死去。
岂非在做梦。
而当我们试图去为无须克制的流泪找到一个场所,我们其实是在寻找一个可以安放自我的空间。

除此之外,我们所要找寻的,更是时间。
是让现在的你流泪的,那逝去的时间。是你可以不被打扰地回味过去的,现在的时间。是从过去到现在,需要遗忘或是愈合的时间。
回忆中的人是抽象的,真实的空间收留了人,而人打开所有的时间。
圆明园恰恰是一个可以将时间折叠进空间的地方。这个时候,我想我们可以听一下关淑怡的《三千年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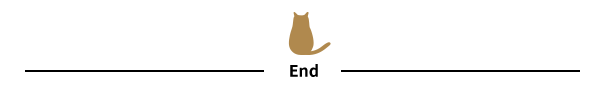
喜欢这一篇?单向街十一“地点”系列还在继续,敬请关注!
欢迎转发朋友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