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 读 书 开 始
尝 试 不 粗 糙 的 生 活
好书
「一起读经典」
计划仍在继续,在读了
《百年孤独》
《莎士比亚四大悲剧》
后,第三期,我们读的是《一九八四》和《美丽新世界》。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就是《美丽新世界》。这本书不仅是一个预言,也是一个寓言。在这个《巨婴国》都会被下架的时候,很幸运我们还可以看《一九八四》和《美丽新世界》。读过之后,也许会让你怀疑人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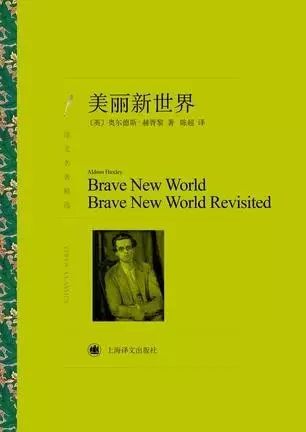
老实讲,《美丽新世界》的小说技巧并不高明,甚至有点粗糙,但是这本书仍然值得一读。因为赫胥黎通过小说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它不仅关乎未来的社会,也关乎我们每一个人生存的意义。
一个人生存的意义是什么呢?我们忙忙碌碌,辛苦一生,所求的是什么呢?
很多人会说,是幸福。
赫拉利在《未来简史》中就明确表示,当瘟疫、饥荒和战争已经被攻克之后,人类的目标,将会转向永生和幸福。
但是,幸福到底是什么东西?是满足感?是愉悦?是快乐?它还包括别的什么吗?
幸福说到底是一种感觉,随着科学的进步,我们越来越发现,这种感觉是可以控制的。实验室里,小白鼠会为了寻求快感,一次次的按下阀门,快乐到死。如果生化科学能够控制这一切,幸福还有意义吗?
所以有了第二个问题,幸福就够了吗?
赫胥黎通过《美丽新世界》设想了一个充满幸福的社会,但是我们经由作者的眼光去打量这个世界时,却觉得有点可怕。虽然人人都很幸福,但终其一生,人人都在“规定”的轨道上进行,幸福并不是追求而来,而是被喂食的。
被喂食是一件讨厌的事情,它违背了人类的自尊,在我们的概念里,一个人是有理性的,是能够做出选择的,是自由的。
《美丽新世界》所描绘的世界之所以可怕,就在于,在那个世界里,人人都以为自己是自由的,但其实,他们正像宠物一样被豢养。他们根本没有反抗的动机,统治和被统治者,两厢情悦,共谋共生。
不过,宠物的生活有什么不好呢?如果这样的生活可以让我们感到幸福,牺牲自由,有什么不可以吗?
这正是关键所在。
赫胥黎所持有的价值观是文艺复兴以来的人文主义传统,幸福并不是唯一,更重要的是一个人的自由。
在书中,主宰者和野人约翰有一段点名主旨的对话,主宰者说,“事实上,你要求的是不幸福的权利。”
约翰回答:
“我正是在要求不幸福的权利。还有变老、变丑、变得性无能的权利,患上梅毒和癌症的权利,吃不饱的权利,肮脏的权利,总是生活在对明天的忧虑中的权利,患上伤寒的权利,受各种难以言状的痛苦折磨的权利。”
说到底,就是一句话——“不自由,毋宁死。”
赫胥黎担心的不是有一个独裁者来限制我们的自由,而是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一起放弃了自由。就像书中的主宰者说,
“我们的信仰是幸福和稳定”。
为了实现幸福和稳定,人的内涵被缩小了。
在这个世界里,人从出生前就有出厂设置,出生后,还会有配套的教育和洗脑,以至于根本不需要思想警察,因为一方面,你想不到有另外的可能,另一方面,生活稳定,欲望被完全的满足,想买就买,想和谁做爱就和谁做爱,想怎么开心怎么来,没有什么好反抗的。当然会有无聊,可是无聊也被取消了,有一种叫做苏摩的药品,一吃就high了,一支不够,那么两支。
《美丽新世界》和《一九八四》都描绘了一个未来的极权社会,但是,奥威尔和赫胥黎选择了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在《一九八四》里,恐惧弥漫在国家的每一个角落,但在《美丽新世界》中,每个人心中反而充满了幸福和快乐。
就像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中所分析的那样:奥威尔害怕的是那些强行禁书的人,赫胥黎担心的是失去任何禁书的理由,因为再也没有人愿意读书;奥威尔害怕的是那些剥夺我们信息的人,赫胥黎担心的是人们在汪洋如海的信息中日益变得被动和自私;奥威尔害怕的是真理被隐瞒,赫胥黎担心的是真理被淹没在无聊烦琐的世事中;奥威尔害怕的是我们的文化成为受制文化,赫胥黎担心的是我们的文化成为充满感官刺激、欲望和无规则游戏的庸俗文化。
《一九八四》已经成为大家警惕的对象,但我们似乎正一步步走向《美丽新世界》。整个消费主义就是在尽力激发并满足我们的欲望,这是不是一种驯化的过程?人的价值是不是只剩下消费价值?
赫胥黎在《重返美丽新世界》这本书的最后提醒我们:
失去了自由,人就不能成为完整意义上的人,因此,自由是最高价值。或许现在威胁自由的力量实在太强大了,没有办法长久的抵抗下去,但不管怎样,我们的责任就是尽自己的能力进行抵抗。
不过,很多人会逃避自由。毕竟自由也意味着责任。如果真有一个选择摆在眼前,我想,很有可能大部分人会选择幸福的感觉而不是自由。而也许,并不会有这么一个选择,一切都是慢慢发生的。
- 不止读书-

魏小河
出品 微博 豆瓣 知乎
@魏小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