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 | 漠上烟
简书原创作者
散文专题推荐文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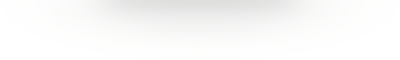
荒凉凄清的圩子里,除了三户十二口人,其余的人都搬去了远远的圩外。十二口人都是头顶一个字的家族。以婚姻的名义,我和这所离家几十里的圩子在余生里建立了一场扯不断理还乱的从属关系。
圩子四面壕沟深深,近乎被革命草吞噬。只留东西两处界埂供出入。想来,那俩界埂应该就是旧时用来架吊桥防外来侵略的地方吧?
圩子于我,是个与世隔绝的潦倒地。我在那里生活了四年,却从没踏足过其他两户。
没有书籍,没有报纸,没有朋友,手机网络都还没普及。所有的农闲,除了偶尔在屋子里看看电视,做做针线活,我大部分时间都晃悠在屋前屋后,灶上灶下。
后院的后院,是一片人去屋空的断壁残垣。成林的大叶柳们杵着十几米高的身姿,经年静默。只有风抽雨扫时,它们才会不约而同地发点儿啪啪声。像是为风雨鼓与呼,又像是在和风雨过招。齐腰的各类草植们在它们脚下没型没状地潦草苟生。
荒院深深,是可以诞生现代聊斋志异的绝佳场所。白天,我都尽量不一个人涉足,天一侧黑,更是不敢踏足半步。就连自己的后院,一到晚间,都胆虚虚得不敢久待。
第一年春天默默而来。某天,后院里飘来一阵浓郁的花香,那香,似熟非熟。循香举首,隔着矮矮的院墙,一树粉紫的泡桐花如一串串紫风铃,正在院门外迎风轻舞!原来,香味自它而来。
树阴似盖遮炎暑,花穗如烟胜紫鹃。
想起少时,应该只是八岁之前,也是在自家后门口,看到过一树泡桐花,是奶白色的。一树小喇叭样的花一串串簇拥在一起低垂着粉脸。
泡桐花可药用,据说也可食用,一直没吃过。倒是知道它的蒂部轻轻一挤,出来的汁液有丝丝的甜味。小时候顽皮地没少吮吸。孩子的审美里,它们单纯地美丽,好闻又好吃。因了美丽的花,泡桐,成为孩提时我最喜欢的树。
八岁之后,举家搬离到村部的新屋。此后,只见过泡桐,没见过泡桐花。成年泡桐空心,树材无有大用,在我们那乡间能活到花开的寥寥。
多少年后,当年的孩子已长大。被世俗之手推到这个人烟凄清的圩子里,沦为农妇。却居然在这里与一树泡桐为邻。这也是某种命定的天意吗?泡桐花,是天意下派来唤醒我少时的美好记忆,慰藉我,温暖我的吗?
泡桐花,是那个荒芜到凄凉的废院中最鹤立鸡群的风景。周遭都是无花的树,无序的草。唯有它的粉紫在十几米的半空高调地静默着。与风对语,与阳光雨露相亲,与东来西往的鸟儿打打招呼。

大多时候,它应该是独守内心,满腹寂寥的吧?它的香,它的心思,可有哪一株树,哪一棵草,哪一只过路的鸟儿懂得?
花事芜杂的季节,总是一夜后,泡桐树下就一地粉紫的缤纷落英。如一只只精雕粉琢的小喇叭,东横西陈。轻轻拈一朵于指间,依然余香袅袅,姣美到让人心生疼意。
终于真正透彻黛玉葬花的心态。很想也着一把花锄,把满地泡桐花隆重地掩埋,郑重等待来世再飞入枝头。而如许矫情,终归只是文字里的诗意,生活,哪得多少情可矫?
泡桐花落,旧貌已改。泡桐花下,尘事缤纷。
我常常独立在通往后院的那扇小门,一扇古老陈旧到变形的圆顶式木拱门下,看着它。看着它,像看我自己。我与它,殊途同归地寂寞着。
人挪活,树挪死。它注定挪不走。我,那时也不知自己能否挪走而活,还是终将老死于它的脚下。
一院子,一圩子的空气不够我呼吸,窒息感时时盘错体内。我不知这一树泡桐花,它是否也时时陷入不合于群的寂寥?
万千喇叭听无语,一片痴情诉向春。
春天总是稍纵即逝。在一轮轮相同的轮回里,流泻不同的风景。泡桐花,是那四年的春天里,我眼里唯一的亮点,我心底唯一的风景。
泡桐花,终归挪不走,我最终却挪开了脚步。关于那个圩子,关于圩子里我留下的印迹,都和泡桐花一起,构成一块可以生长的烙印,渗透进我每一寸肌肤。
十多年过去,我挪在城市里努力活着。泡桐花,却再也没回去看过它。圩子早已终成空空的废园。那所具百年以上历史的老宅孤零零地在凌风沐雨里摇摇欲倒,等待着某一日被开发的东风修颜整貌。
那株泡桐是否依然在后院安好?泡桐花花语是,永恒的守候。
不知道,它能否守候来花生里最好的春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