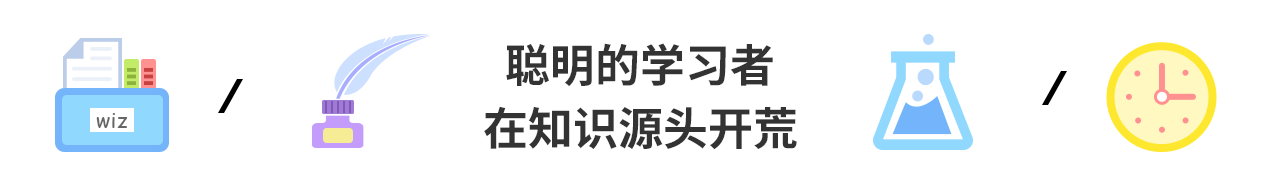
— Note170727003 —
如何写笔记?不是照抄,不是写阅读感想,更不是归纳总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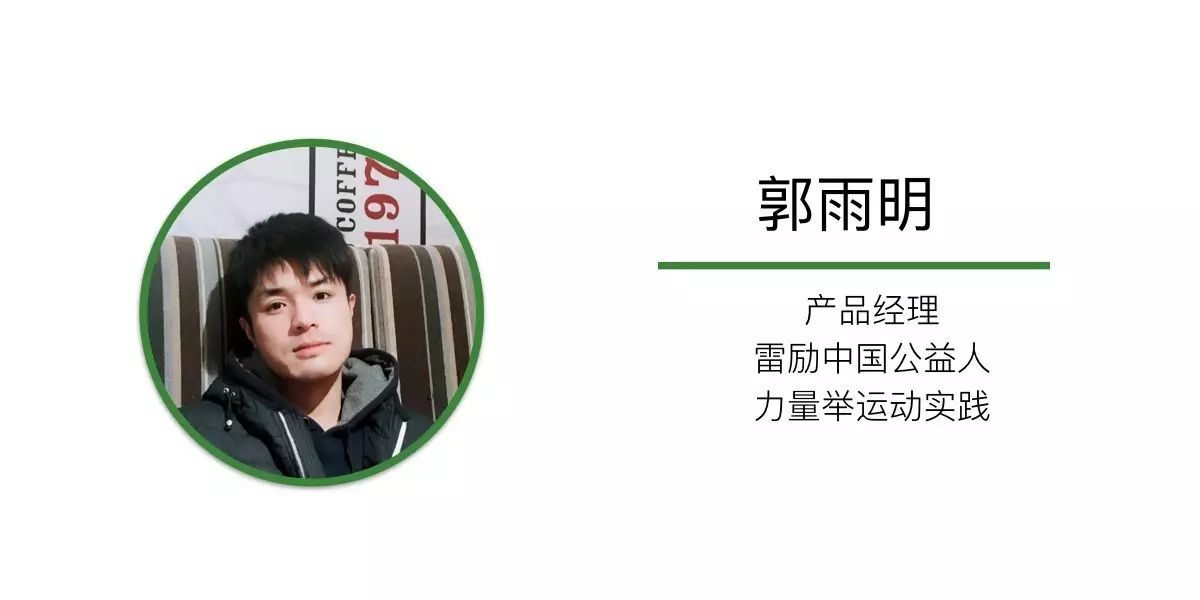
阳志平老师认知写作点评
这篇笔记的优点:
总结并串联课程要点, 用自己的话做解释;对知识点合理推论,发展出相应的写作技巧
。
写笔记时可能有两个极端:试图记录所有知识点;试图用自己的话解释所有知识点。学术界有一个概念叫信度效度,当你发挥过度,效度就可能出问题,认知科学总有限制性的结论,它会在某些情况下生效,某些情况下不生效。不要以认知科学的一个术语囊括一切,而是要明白这个术语是因什么原因诞生、对什么情况起作用。
雨明同学的笔记保持了很好的平衡,他针对核心要点进行了合理、适度的推论。比如文章中「为什么无论哪个时代,服装的主色都是那几种?黑白永远是百搭」、「这也是为什么人们喜欢分类排行,贴标签,减轻认知符合的方式」、「方差分析、统计检验都有此种倾向」这几句话都是课程中没有讲过的,是由作者在笔记中自然推理得出,恰到好处。另一个值得学习之处是作者将 「记忆生存效应」 和「基本范畴」这两个课程中没有直接关联到一起的概念放在一起进行对比学习。
作者对写作技巧的推论也是顺理成章的,如「借助于对于水果的联想表达对应的范畴,巧用范畴法评级的两端来产生新鲜文字联想」,「基本范畴层次中的词一定是要名词吗?有无其他高频的词属于其他类型,如动词」,「语义时空延伸,相似性」等,他从认知科学的结论再寻找到相应的例子、得出相应的写作技巧。这是很值得鼓励的学习方法。
Prologue
我一直以来都喜欢写作手册,尤其是某类文体的写作。知名报刊,比如经济学人、芝加哥、宾夕法尼亚都有自己的写作风格手册。我愿意花一生的时间去打磨写作技艺,像神话中的米洛,把牛犊抗在肩上前行,直至年月让它长成公牛。我现在研究认知和心理语言,写作风格不就是用言词传达人的内心吗?我像个猎人,听完久远的英雄传说,猛拍大腿起身,挎上弓箭走向绿森森的丛林。
最早我看到风格手册,还是个学生。在怀特的《心理学导论》课堂,他回忆自己的导师,像邪教徒,在学生面前,双手撑着讲台,全身前倾,声音沙哑地连说三遍 「删掉不必要的词」,如同说出一个阴谋。
现在,我对语言更加了解,再读怀特们的风格手册,多了些隐忧。怀特的有些写作建议说得太绝对,好像是在一个邪不胜正的世界,他们反对的词,没有存活的余地。他们自己坚持的写法,写成文字,往往打破了自己的坚持。同样还有乔治奥威尔,他取笑被动语态是「永远优先于主动语态被使用」。看,他们没法不用被动语态,即使在反对被动语态的宣言当中。语言是思维本身,被动语态在我们脑海中是占据了空间的,它唤起了我们的记忆,引导我们去观看。
怀特们对待规矩,像是神笔马良挥出的画卷,笔落形定,上古凤凰从纸上扯出,振翅高飞,羽毛的纹路不再有一丝变化。语言不是站在高台的君王写下的节目单,而是他的千万臣民,笔耕不辍也好,妙手偶得也好,说出的,写出的,汇聚成的活水。
怀特们怀念往昔优雅英文人皆可得,哀叹现在新词大行其道。不止是怀特们,每代人都会在追忆过往的时候,感慨世事在倒退。因为他们忽视了自己心理的变化,分不清自己的变化和围绕他们世界的变化。他们成长于电话发明前,成长于语言学和认知科学诞生之前,成长于信息技术重塑地球之前,他们已经老去。你不可能完全指望他们来指导自己写作。
不像暮年的君王,站在六根白玉石大柱子撑起的大殿里,对遥远的子民发出空谷回响的命令。我们会告诉你,为什么这样写?我们知道阅读时大脑在想什么,回溯记忆之潮的涨落,在思维的迷宫里探寻幽径。你的思维如同一面镜子,每种感觉,照在镜前,都会留下自己的影像,映入你眼中的言词,唤醒了这面镜子。
在信息汪洋泛舟的时代,连贯、清楚的文章就像你在荒漠里看见一串贝壳;书写的文字,是这个时代的硬通货。记住好的文字的样子,大家都渴望看到更美好的世界。
Chapter 1 Good Writing
我在沙滩上行走,低着头,数着脚下的石头,心中已有终点。右手边细细的海浪摩擦着沙粒,同那艘帆船一样,粘在岸边。我摘下帽子,迈进船舱,看见一抽着烟斗的人坐在里面。我看不出他的年纪,虽然头发已经花白,但肌肉依旧线条分明。他眼球里投射出星河的光辉,说,「我是个建筑师,周游世界,造出了你走过两千个星球也没有见过的城市。」我知道他就是我要找的人,「那请你带我去看一眼你造的城吧。」
城市与楼宇
九原城是建立在平原之上的大城,开阔的腹地,城墙随心所欲地环绕成圆形,十字纵横的两条大道穿过城市。市民从不需要记住街名门牌号,因为建筑的外墙,是不同颜色砖石排列出来的图画,人、野兽、刀剑、酒杯。旅人不用半天就会看出,图画代表着建筑里面发生的事情。每户人家的墙上,是家主的半身画像;法庭墙上砌出天平和稻穗;妓院墙上开出鲜红的玫瑰。传说九原城外的火山喷发过一次,漫天的尘埃掩盖了城市。后人挖掘的时候,那一刻的城市依然可见。
城市与街道
水镜城里,没有路标,路都是隧道。整个城市开凿在一座岩壁上,往腹地走,深入峡谷。第一次到水镜城的人,不需要担心迷路,所有路都是单行,行人走在隧道中,除了向前望去,上下左右是温暖坚硬的岩壁,留着铁铲和铜钻开凿过的痕迹。在城里漫游一天,眼睛望着前方,目之所及,就能到达。顺着隧道走,在转角处看见洞口摆出双手合十的天使石雕,在向前踏步时左边石壁雕刻出狩猎的图景,不小心走快了,眼中品拼不出完整的画卷,不过下一个路口,会有汩汩细流的水车等着你。
城市与剧院
海楼城是给艺术家兴建的城市。吟游诗人、水彩画家、歌剧演员、小说作家,在这个城市各个角落潜伏,繁盛。外来艺术家旅游到此,离开的时候口袋里装着下个作品的想法,或者索性就不离开了。纵情声音与颜色的游客,闻到街头空气中流淌的色彩,看到每五百米就有的露天舞台,每一千米就有的圆形剧场。在海楼城街头,只要是醒着的时候,就可以听到起伏的朗诵、高高低低的吟唱、花容失色的大笑、平静克制的告白,声音和声音举杯相碰,诗句和歌词唇交齿合。新奇的词汇土拨鼠一样地从海楼城各个角落蹦出。每个月人类学家、文化学者和字典编撰者来到这里,随身带着他们羊皮裹着的本子,在花坛、露天酒馆、长廊拱门,挥笔写下他们第一次听说的词语。
Chapter 2 A Window onto the World
为读者写作
写作就像是和读者一次交谈,引导他们去看
每年的蓝羽毛大赛,评选出当年最烂的章;官员、学者、律师往往是这个奖项的常客。今年,大赛组委会请来了平克,给获奖者点评。首先获奖的是:
第一部分会介绍「元话语」,以及一些主要的例子和标记词的展示。第二部分回顾了三个问题:偏重写自己的职业经历而非直入主题;过多使用缓和语气词语;过多的躲闪带来的缺点。第三部分解释了预先指出的动词的问题。
这段话初衷是给读者预览,结果适得其反。将目录打散之后的信息组织方式,超过了四个组块排列,读者过目就忘。元话语使用太多。比如标记词「第一」,漫不经心地用标记词,反而让读者不知所错,因为他们会花更多精力去理解标记词本身的意思,而非标记词所指向的要点。还有「部分」、「回顾」这类抽象的词,读者在现实世界中找不到物件来和这些词对应,消耗了语义能量。就像路标如果写得复杂,我们用在看懂路标上的时间,会超过选择的时间。
用「展示」、「表现出」,不如用「我们看见」。作者和读者就像伙伴,共同玩一个冒险游戏,看见更大世界。像谈话一样,作者引导读者的目光,让旅途更多起伏的波澜,更少无谓的曲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