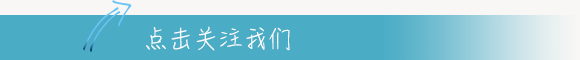
“一源多流”的民间传说及其改编作品,若评论文章中论及不同类型、不同时期的改编作品创作渊源,如果该评论文章为独立作品,未引用改编作品的内容,与各改编作品既不构成相同,也不构成实质性相似的,则不侵犯改编作品著作权人的署名权和保护作品完整权。
|
一审案号
|
(2016)桂02民初47号
|
|
二审案号
|
(2016)桂民终409号
|
|
案由
|
侵犯作品署名权、保护作品完整权纠纷
|
|
合议庭
|
周冕、张捷、覃岚
|
书记员
|
陈雪娇
|
当事人
|
上诉人(一审原告):邓奕
|
|
上诉人(一审原告):邓仪
|
|
上诉人(一审原告):邓绮秀
|
|
上诉人(一审原告):邓翊
|
|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柳州日报社
|
裁判日期
|
2017年2月24日
|
一审裁判结果
|
驳回邓奕、邓仪、邓琦秀、邓翊的诉讼请求
|
二审裁判结果
|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
|
涉案法条
|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
|
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16)桂民终409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邓奕。
上诉人(一审原告):邓仪
。
上诉人(一审原告):邓绮秀
。
上诉人(一审原告):邓翊
。
以上四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阳远德、潘毅,柳州市方正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柳州日报社,住所地XXXX
。
法定代表人:阳天,社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XX,广西华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航,广西华尚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上诉人邓奕、邓仪、邓绮秀、邓翊因与被上诉人柳州日报社侵犯作品署名权、保护作品完整权纠纷一案,不服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简称一审法院)于2016年10月28日作出的(2016)桂02民初47号民事判决(简称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12月2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1月18日进行证据交换,于同年1月19日依法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邓翊以及上诉人邓奕、邓仪、邓绮秀、邓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阳远德,被上诉人柳州日报社的委托诉讼代理人XX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邓奕、邓仪、邓绮秀、邓翊在一审诉称:其父邓昌伶(1973年病故)原系广西克强中学校长,根据民间传说于1953年创作了《刘三姐》剧本,这一智力成果是具有完整的独创性。柳州彩调剧根据该剧本完成了彩调剧《刘三姐》这一方案之初稿,相继又完成彩调剧《刘三姐》第三、五、八、九方案戏剧作品,这些戏剧作品都是根据邓昌伶同名剧本改编,已由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2005)桂民三终字第7号民事判决书认定。邓奕、邓仪、邓绮秀、邓翊作为继承人于2007年9月取得《刘三姐》彩调剧剧本著作权人资格。柳州日报社在没有实质性内容和证据的情况下,2016年1月17日在《柳州晚报》上刊登的《电影<刘三姐>与柳州作家肖甘牛》一文中公然宣称“彩调剧《刘三姐》又是根据民间故事《刘三姐》改编的,”同时叙说“这可能是较早的刘三姐文学作品”,不仅如此,还评论“这个民间故事不管是彩调剧《刘三姐》还是电影《刘三姐》都被吸收进去,没太大的改变。这是肖甘牛的贡献”等等,这严重侵犯邓奕、邓仪、邓绮秀、邓翊署名权、保护作品完整权。柳州日报社不仅歪曲事实,张冠李戴,而且不尊重客观事实,宣称彩调剧《刘三姐》是根据民间故事《刘三姐》改编而来,全归结于肖甘牛的“贡献”,这是一种侵权行为。早在2000年1月18日《柳州日报》对电影《刘三姐》署名重新规范,确认今后出版电影《刘三姐》光盘中注明“根据广西柳州同名彩调剧改编”。综上,柳州日报社的行为不仅诱导读者的思想理念,同时给社会造成不良影响,也给邓奕、邓仪、邓绮秀、邓翊带来极大的心灵创伤。柳州日报社侵犯了著作权和保护作品完整权,柳州日报社将“莫怀仁”称为“莫坏人”,歪曲和篡改了他人的作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十条、第四十七条第三、四、五款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二十条之规定,提起诉讼,请求:
1.确认柳州日报社侵犯了邓奕、邓仪、邓绮秀、邓翊作品署名权、保护作品完整权;2.判令柳州日报社至少2次在报刊上公开刊登侵权事宜,并公开赔礼道歉;3.判令柳州日报社支付精神损失费50000元;4.本案诉讼费均由柳州日报社承担。
柳州日报社在一审辩称:一、柳州日报社于2016年1月17日刊登作者肖杰明署名文章《电影与柳州作家肖甘牛》一文,1956年9月,肖甘牛与儿子肖丁三合作的民间故事《刘三姐》已在发行全国的《新观察》杂志发表,邓昌伶的彩调剧《刘三姐》吸收民间故事《刘三姐》的内容并非不可能。综上,邓奕、邓仪、邓绮秀、邓翊认为柳州日报社侵犯其署名权、保护作品完整权属于主观臆断,缺乏事实依据,理由不能成立。三、关于精神损害抚慰金。柳州日报社刊登《电影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邓昌伶系邓奕、邓仪、邓琦秀、邓翊的父亲,邓昌伶于1953年12月8日创作完成了《刘三姐》彩调剧剧本。邓昌伶于1973年因病去世。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2005)桂民三终字第7号民事判决书认定,民间文学中存在着刘三姐的传说,刘三姐的传说流传时间长、地域广,其传说的民间故事中已经存在刘三姐、刘二、财主、秀才、老渔翁等人物原型,并有刘三姐传歌、对歌、盘歌、拒绝豪绅托媒求婚、被老渔翁搭救、骑鲤鱼升天成仙等故事。邓昌伶以民间传说及民间故事为基础,在繁杂、散乱的传说素材中,精选出几个典型的故事情节,进行整理、加工、提炼,经过构思和布局,安排成按照一定时空顺序发展的、具有结构完整的戏剧作品,邓昌伶的彩调剧本《刘三姐》具有独创性,邓昌伶对其创作的《刘三姐》彩调剧剧本享有著作权。
2007年9月10日,邓奕、邓仪、邓琦秀、邓翊对邓昌伶《刘三姐》彩调剧剧本向广西壮族自治区版权局申请版权登记,广西壮族自治区版权局2007年9月10日颁布的《版权证书》记载,作品名称:《刘三姐》彩调剧剧本,作品类型:文字作品,作者:邓昌伶,著作权人:邓奕、邓仪、邓琦秀、邓翊,作品完成日期:1953年12月8日,作品登记日期:2007年9月10日,作品登记号:桂作登记:20-2007-A-167号。
2016年1月17日,柳州日报社在其出版的《柳州晚报》第16版《副刊•讲旧事》刊登了《电影〈刘三姐〉与柳州作家肖甘牛》一文,文上记载作者为肖杰明。邓奕、邓仪、邓琦秀、邓翊认为该文侵犯了其享有的《刘三姐》彩调剧剧本的署名权及保护作品完整权,并要求柳州日报社承担侵权责任,遂诉至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邓奕、邓仪、邓琦秀、邓翊是否享有保护邓昌伶《刘三姐》彩调剧剧本著作权中署名权及保护作品完整权的权利;二、柳州日报社是否侵犯邓昌伶《刘三姐》彩调剧剧本所享有的署名权及保护作品完整权;三、邓奕、邓仪、邓琦秀、邓翊要求柳州日报社至少2次在报刊上刊登侵权事实、公开赔礼道歉并赔偿5万元精神损失有无事实和法律依据。
关于邓奕、邓仪、邓琦秀、邓翊是否享有保护邓昌伶《刘三姐》彩调剧剧本著作权中署名权及保护作品完整权的权利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十五条规定,作者死亡后,其著作权中的署名权、修改权和保护作品完整权由作者的继承人或者受遗赠人保护。邓昌伶依法享有其于1953年12月创作完成的《刘三姐》彩调剧剧本的著作权,邓昌伶于1973年因病过世,邓奕、邓仪、邓琦秀、邓翊作为邓昌伶的继承人,享有依法保护邓昌伶《刘三姐》彩调剧剧本署名权及保护作品完整权的权利。
关于柳州日报社是否侵犯邓昌伶《刘三姐》彩调剧剧本所享有的署名权及保护作品完整权的问题。关于署名权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署名权,即表明作者身份,在作品上署名的权利”。使用他人的作品,应当指明作者姓名、作品名称。本案中,邓奕、邓仪、邓琦秀、邓翊认为,柳州日报社在其出版的《柳州晚报》第16版《副刊•讲旧事》刊登的《电影〈刘三姐〉与柳州作家肖甘牛》一文中写到“但电影《刘三姐》是根据柳州彩调剧《刘三姐》舞台剧本改编的,而彩调剧又是根据民间故事《刘三姐》改编的”、“这个民间故事不管是彩调剧《刘三姐》还是电影《刘三姐》都被吸收进去,没太大的改变。这是肖甘牛的贡献”,该文称彩调剧《刘三姐》是根据民间故事《刘三姐》改编的,将全部的贡献归功于肖甘牛,侵犯了邓昌伶的署名权。一审法院认为,庭审中,各方当事人均认可彩调剧《刘三姐》并非特指邓昌伶《刘三姐》彩调剧剧本,而柳州日报社刊登的《电影〈刘三姐〉与柳州作家肖甘牛》一文中,并未再现、引用或使用了邓昌伶《刘三姐》彩调剧剧本的内容,刘三姐的传说历史悠久、流传广泛,文中所提及的刘三姐故事系梗概民间传说刘三姐的内容,故柳州日报社未侵犯邓昌伶《刘三姐》彩调剧剧本的署名权。邓奕、邓仪、邓琦秀、邓翊主张柳州日报社侵犯邓昌伶《刘三姐》彩调剧剧本署名权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保护作品完整权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十条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保护作品完整权,即保护作品不受歪曲、篡改的权利”。本案中,邓奕、邓仪、邓琦秀、邓翊认为,柳州日报社在其出版的《柳州晚报》第16版《副刊•讲旧事》刊登肖杰明《电影〈刘三姐〉与柳州作家肖甘牛》文中写到“故事中的财主叫莫怀仁,由于心肠狠毒穷人叫他‘莫坏人’”,将“莫怀仁”称为“莫坏人”侵犯了邓昌伶《刘三姐》彩调剧剧本的保护作品完整权。一审法院认为,如前所述,柳州日报社刊登的《电影〈刘三姐〉与柳州作家肖甘牛》一文中,并未再现、引用或使用了邓昌伶《刘三姐》彩调剧剧本的内容,刘三姐的传说历史悠久、流传广泛,文中所提及的刘三姐故事系梗概民间传说刘三姐的内容,《电影〈刘三姐〉与柳州作家肖甘牛》作者肖杰明并未对作品进行了修改。且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2005)桂民三终字第7号民事判决书认定,邓昌伶《刘三姐》彩调剧剧本中“莫云”系反派角色,作为“莫云”的反派角色及其原型,在民间故事中已存在,并非邓昌伶的虚构和独创,故柳州日报社没有侵犯邓昌伶《刘三姐》彩调剧剧本的保护作品完整权。综上,邓奕、邓仪、邓琦秀、邓翊主张柳州日报社侵犯邓昌伶《刘三姐》彩调剧剧本保护作品完整权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关于邓奕、邓仪、邓琦秀、邓翊要求柳州日报社至少2次在报刊上刊登侵权事实、公开赔礼道歉并赔偿5万元精神损失有无事实和法律依据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鉴于邓奕、邓仪、邓琦秀、邓翊未能提交充分有效的证据证明柳州日报社有侵犯邓昌伶作品著作权的行为,故一审法院对邓奕、邓仪、邓琦秀、邓翊的该项诉请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邓奕、邓仪、邓琦秀、邓翊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邓奕、邓仪、邓琦秀、邓翊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050元(邓奕、邓仪、邓琦秀、邓翊已预交),由邓奕、邓仪、邓琦秀、邓翊负担。
邓奕、邓仪、邓琦秀、邓翊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本院:1、撤销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桂02民初47号民事判决书;2、判令支持上诉人在一审提出的诉讼请求;3、本案诉讼费均由被上诉人承担。其理由主要是:首先应当确认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2005)桂民三终字第7号民事判决认定,邓昌伶享有其1953年12月创作完成的《刘三姐》彩调剧剧本的著作权,彩调剧《刘三姐》第三、五、八、九方案系邓昌伶戏剧作品《刘三姐》的改编作品。其次,应当确认广西壮族自治区版权局2007年9月10日颁发给著作权继承人邓奕、邓仪、邓绮秀、邓翊的《刘三姐》彩调剧剧本《版权证书》(即作品登记证),编号为:20-2007-A-167号。《柳州日报》在其出版的《柳州晚报》第16版(副刊·讲旧事)里刊登的“电影《刘三姐》与柳州作家肖甘牛”一文中写到:“但电影《刘三姐》是根据柳州彩调剧《刘三姐》舞台剧本改编的,而彩调剧又是根据民间故事《刘三姐》改编的”,“这个民间故事不管是彩调剧《刘三姐》还是电影《刘三姐》都被吸收进去,没太大的改变。这是肖甘牛的贡献”。按其说法,肖甘牛的民间故事《刘三姐》(1956年发表在《新观察》期刊上),是柳州彩调剧《刘三姐》和电影《刘三姐》改编的源泉。依其逻辑推理,柳州彩调剧《刘三姐》(含一至九方案)是根据肖甘牛民间故事《刘三姐》改编的,而不是根据邓昌伶的彩调剧剧本改编的。这与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效判决书认定的事实相矛盾,全盘否决了邓昌伶彩调剧剧本《刘三姐》智力成果的独创性,侵犯了邓昌伶彩调剧剧本《刘三姐》的署名权。邓奕、邓仪、邓琦秀、邓翊在一审提交的证据7《彩调剧词典》记载,邓昌伶于1954年根据宜山民间传说创作四场彩调剧《刘三姐》,曾以桂剧形式演出,并将其创作的彩调《刘三姐》剧本交宜山专区文联审阅。由此可见,邓昌伶创作的《刘三姐》已于1954年公开发表,而肖甘牛在《新观察》杂志上发表的民间故事《刘三姐》是1956年,两者间隔两年多,是邓昌伶的剧本吸收了肖甘牛民间故事的内容,还是肖甘牛的《刘三姐》民间故事吸收了邓昌伶彩调剧本的内容?邓奕、邓仪、邓琦秀、邓翊在一审提交的证据7《广西之最》记载,邓昌伶1954年完成创作的彩调剧《刘三姐》剧本,人物如三姐、刘二、老渔翁、莫进财、莫怀仁、小牛、兰芬和三个秀才等都已定型。依据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2005)桂民三终字第7号民事判决书认定,“彩调剧《刘三姐》第三、五、八、九方案系邓昌伶戏剧作品《刘三姐》的改编作品”,“需在剧本前注明根据邓昌伶同名剧本改编”,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彩调剧《刘三姐》并非特指邓昌伶《刘三姐彩调剧剧本》”、“并未再现,引用或使用邓昌伶《刘三姐》彩调剧剧本的内容”、“文中所提及的刘三姐故事系梗概民间传说刘三姐的内容”错误。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应依法改判。
被上诉人柳州日报社仍然坚持一审的答辩意见,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恳请本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审判决。
根据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理由及被上诉人的答辩意见,本院归纳本案争议焦点如下:1、被上诉人柳州日报社在其出版的《柳州晚报》上刊登《电影〈刘三姐〉与柳州作家肖甘牛》一文是否侵犯了邓昌伶《刘三姐》彩调剧剧本的署名权及保护作品完整权;2、上诉人邓奕、邓仪、邓琦秀、邓翊请求判令被上诉人柳州日报社至少2次在报刊上刊登侵权事实、公开赔礼道歉并赔偿精神损失5万元人民币有无事实和法律依据。
上诉人邓奕、邓仪、邓琦秀、邓翊在二审中向本院提交了三份新证据:证据1系《中国戏曲志》,欲证明1954年邓昌伶编写的戏剧《刘三姐》后改为桂剧本,然后又改为彩调剧本,彩调剧《刘三姐》的原创作人是邓昌伶。证据2系《彩调剧词典》,欲证明1956年肖甘牛在《新观察》上发表的小说《民间故事刘三姐》是吸收了邓昌伶彩调剧《刘三姐》的精华。证据3系2000年1月18日《柳州日报》,欲证明长春电影制片厂1960年制作的电影《刘三姐》是根据柳州同名彩调剧改编,彩调剧《刘三姐》的作者是邓昌伶。被上诉人柳州日报社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如下:证据1及证据2的真实性均予以认可,但不能证明待证事实。证据3系复印件,无原件核对,不认可其真实性。本院对上述证据的认证意见如下:被上诉人对证据1、证据2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证据3虽然系复印件,但盖有柳州市图书馆地方文献资源部复制件印章,被上诉人对其真实性虽然有异议,但未能提供反驳证据,本院认可其真实性。但证据1、证据2、证据3均不是二审新证据,且与本案争议事实即被上诉人柳州日报社刊登《电影与柳州作家肖甘牛》的行为是否构成侵权无关联性,故本院不予采信。
被上诉人柳州日报社在二审期间没有向本院提交新证据。
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的基础上,本院补充查明以下事实:
2016年1月17日《柳州晚报》刊登的《电影〈刘三姐〉与柳州作家肖甘牛》一文被诉侵权的内容如下:
“1960年,由长春电影制片厂摄制的彩色故事片《刘三姐》在全国放映后,在国内引起轰动,刘三姐故事感人,歌曲广为传唱。1961年,电影《刘三姐》在国外公映,风靡东南亚,三姐山歌让东南亚观众陶醉,收到了最佳的艺术效果,这是过去没见过的现象。但电影《刘三姐》是根据柳州彩调剧《刘三姐》舞台剧本改编的,而彩调剧又是根据民间故事《刘三姐》改编的,提到民间故事《刘三姐》不得不提起柳州作家肖甘牛。
1956年9月发行全国的《新观察》杂志发表了柳州作家肖甘牛与儿子肖丁三合作的民间故事《刘三姐》,这是根据宜山县下枧村的传说整理成文的,虽有增删但基本上还是原汁原味的,这可能是较早的刘三姐文学作品了。故事中的刘三姐长得漂亮,唱山歌十分出色,名声远扬,远远近近的歌手都前来学歌、赛歌。刘三姐还用山歌为穷人说话和财主斗争。故事中的财主叫莫怀仁,由于心肠狠毒穷人叫他“莫坏人”,他见刘三姐敢于唱山歌骂他,于是请来三位秀才和三姐对歌,结果三位秀才被刘三姐唱得狼狈而逃……这个民间故事不管是彩调剧《刘三姐》还是电影《刘三姐》都被吸收进去,没太大的改变。这是肖甘牛的贡献”。
在二审庭审中,各方当事人确认,被诉侵权作品《电影〈刘三姐〉与柳州作家肖甘牛》与邓昌伶于1953年12月创作完成的《刘三姐》彩调剧剧本既不相同,也不构成实质性相似。虽然四上诉人的委托代理人主张《电影〈刘三姐〉与柳州作家肖甘牛》一文“故事中的财主叫莫怀仁,由于心肠狠毒穷人叫他莫坏人,他见刘三姐敢于唱山歌骂他,于是请来三位秀才和三姐对歌,结果三位秀才被刘三姐才唱得狼狈而逃”该内容引用了上述邓昌伶《刘三姐》彩调剧剧本,但并未能找到相应的出处。
本院认为,邓昌伶以民间传说及民间故事为基础于1953年12月8日创作完成了《刘三姐》彩调剧剧本,该事实不但有上诉人邓奕、邓仪、邓琦秀、邓翊在一审诉讼中提供的邓昌伶创作的《刘三姐》彩调剧剧本手稿证实,而且有生效的本院(2005)桂民三终字第7号民事判决书证实,
邓昌伶作为《刘三姐》彩调剧剧本作者,系《刘三姐》彩调剧剧本的著作权人
。邓昌伶于1973年因病过世,根据2013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之规定,作者死亡后,其著作权中的署名权、修改权和保护作品完整权由作者的继承人或者受遗赠人保护。上诉人邓奕、邓仪、邓琦秀、邓翊作为邓昌伶的继承人,享有依法保护邓昌伶《刘三姐》彩调剧剧本署名权及保护作品完整权的权利,对此各方当事人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刘三姐》彩调剧剧本署名权及保护作品完整权是著作权人邓昌伶享有的著作人身权,邓昌伶死亡后,由邓昌伶的继承人保护而并非由继承人享有。
一、关于被上诉人柳州日报社在其出版的《柳州晚报》上刊登《电影〈刘三姐〉与柳州作家肖甘牛》一文是否侵犯了邓昌伶《刘三姐》彩调剧剧本的署名权及保护作品完整权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署名权,即表明作者身份,在作品上署名的权利”。2013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十九条规定,“使用他人的作品,应当指明作者姓名、作品名称;但是,当事人另有约定或者由于作品使用方式的特性无法指明的除外。”本案被诉侵权作品《电影〈刘三姐〉与柳州作家肖甘牛》是文字作品,邓昌伶《刘三姐》彩调剧剧本是戏剧作品,两者表达方式截然不同,在二审庭审中,各方当事人亦确认,被诉侵权作品《电影〈刘三姐〉与柳州作家肖甘牛》与邓昌伶《刘三姐》彩调剧剧本既不相同,也不构成实质性相似。虽然四上诉人的委托代理人主张《电影〈刘三姐〉与柳州作家肖甘牛》一文“故事中的财主叫莫怀仁,由于心肠狠毒穷人叫他莫坏人,他见刘三姐敢于唱山歌骂他,于是请来三位秀才和三姐对歌,结果三位秀才被刘三姐唱得狼狈而逃”该内容引用了邓昌伶《刘三姐》彩调剧剧本,但并未能在邓昌伶《刘三姐》彩调剧剧本中找到相应的出处。因此,
被诉侵权作品《电影〈刘三姐〉与柳州作家肖甘牛》与邓昌伶《刘三姐》彩调剧剧本既不相同,也不构成实质性相似,也没有引用邓昌伶《刘三姐》彩调剧剧本的内容,即没有使用邓昌伶《刘三姐》彩调剧剧本,故被诉侵权作品《电影〈刘三姐〉与柳州作家肖甘牛》没有署名邓昌伶并不违反我国著作权法的规定
,被上诉人柳州日报社在其出版的《柳州晚报》上刊登《电影〈刘三姐〉与柳州作家肖甘牛》一文并没有侵犯邓昌伶《刘三姐》彩调剧剧本的署名权。上诉人邓奕、邓仪、邓琦秀、邓翊上诉称,被诉侵权作品中的内容“但电影《刘三姐》是根据柳州彩调剧《刘三姐》舞台剧本改编的,而彩调剧又是根据民间故事《刘三姐》改编的”,“这个民间故事不管是彩调剧《刘三姐》还是电影《刘三姐》都被吸收进去,没太大的改变。这是肖甘牛的贡献”侵犯了邓昌伶《刘三姐》彩调剧剧本的署名权,这是上诉人对我国著作权法规定的署名权的理解有误,其上诉理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十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保护作品完整权,即保护作品不受歪曲、篡改的权利”。如上所述,
被诉侵权作品《电影〈刘三姐〉与柳州作家肖甘牛》与邓昌伶《刘三姐》彩调剧剧本既不相同,也不构成实质性相似,也没有引用邓昌伶《刘三姐》彩调剧剧本的内容,即没有使用邓昌伶《刘三姐》彩调剧剧本,不可能侵犯邓昌伶《刘三姐》彩调剧剧本的保护作品完整权
。而且被诉侵权作品《电影〈刘三姐〉与柳州作家肖甘牛》的作者是肖杰明而不是被上诉人柳州日报社,根据被上诉人柳州日报社在二审庭审所述,柳州日报社对被诉侵权作品没有作内容或文字的修改,仅仅修改了标点符号,四上诉人在二审诉讼中也没有提交任何证据证明被上诉人柳州日报社对被诉侵权作品作了内容或文字性修改,故被上诉人柳州日报社在其出版的《柳州晚报》上刊登《电影〈刘三姐〉与柳州作家肖甘牛》一文并没有侵犯邓昌伶《刘三姐》彩调剧剧本的保护作品完整权。上诉人邓奕、邓仪、邓琦秀、邓翊相关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二、关于上诉人邓奕、邓仪、邓琦秀、邓翊请求判令被上诉人柳州日报社至少2次在报刊上刊登侵权事实、公开赔礼道歉并赔偿精神损失5万元人民币有无事实和法律依据问题。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法释〔2015〕5号)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如上所述,由于被上诉人柳州日报社在其出版的《柳州晚报》上刊登《电影〈刘三姐〉与柳州作家肖甘牛》一文并没有侵犯邓昌伶《刘三姐》彩调剧剧本的署名权及保护作品完整权,故上诉人邓奕、邓仪、邓琦秀、邓翊在一审所提出的各项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上诉人邓奕、邓仪、邓琦秀、邓翊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
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050元,由上诉人邓奕、邓仪、邓琦秀、邓翊负担(已预交)。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周 冕
审 判 员 张 捷
代理审判员 覃 岚
二〇一七年二月十四日
书 记 员 陈雪娇
附:电影《刘三姐》与柳州作家肖甘牛
作者:肖杰明
1960年,由长春电影制片厂摄制的彩色故事片《刘三姐》在全国放映后,在国内引起轰动,刘三姐故事感人,歌曲广为传唱。1961年,电影《刘三姐》在国外公映,风靡东南亚,三姐山歌让东南亚观众陶醉,收到了最佳的艺术效果,这是过去没见过的现象。但电影《刘三姐》是根据柳州彩调剧《刘三姐》舞台剧本改编的,而彩调剧又是根据民间故事《刘三姐》改编的,提到民间故事《刘三姐》不得不提起柳州作家肖甘牛。
1956年9月发行全国的《新观察》杂志发表了柳州作家肖甘牛与儿子肖丁三合作的民间故事《刘三姐》,这是根据宜山县下枧村的传说整理成文的,虽有增删但基本上还是原汁原味的,这可能是较早的刘三姐文学作品了。故事中的刘三姐长得漂亮,山歌十分出色,名声远扬,远远近近的歌手都前来学歌、赛歌。刘三姐还用山歌为穷人说话和财主斗争。故事中的财主叫莫怀仁,由于心肠狠毒穷人叫他“莫坏人”,他见刘三姐敢于唱山歌骂他,于是请来三位秀才和三姐对歌,结果三位秀才被刘三姐唱得狼狈而逃……这个民间故事不管是彩调剧《刘三姐》还是电影《刘三姐》都被吸收进去,没太大的改变。这是肖甘牛的贡献。
肖甘牛,原名肖钟棠,1905年出生于今永福县。解放后曾任广西区政协一、二、三届委员、中国作协会员、中国文艺家协会会员。1982年1月病逝。毕生致力于民间文学创作,先后整理、编著、创作少数民族民间故事、民间长诗、民间歌谣等民间文学作品集30余部。
受祖父影响,肖甘牛自幼爱上诗文。1927年后进入上海文学院读书,受鲁迅先生诗句“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儒子牛”影响,改名肖甘牛。毕业后先后在梧州高中、桂林高中任教。在梧州时曾兼任《梧州日报》文艺副刊编辑,他编写的《中国修辞学讲话》等著作由上海春光书店出版。又曾到广西大苗山和台湾高山族聚居地采风,收集创作素材。
1956年肖甘牛来柳州定居,辞去教师之职,专门从事民间文学创作。他带着妻子和两个正读小学的儿女到大苗山体验生活、收集素材,终于写出一批有影响力的作品。1957年肖甘牛写的《一幅壮锦》编入全国小学语文课本,在著名电影艺术家夏衍的鼓励下肖甘牛将《一幅壮锦》改编为电影剧本,后由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摄制成影片,获全国优秀剧本奖和卡罗维发利第12届国际电影节荣誉奖。这是柳州文艺工作者第一次在国外拿到大奖。
1981年,肖甘牛编写的民间故事《灯花》发表,之后被译成日本文字传到日本。惨遭生活不幸的日本妇女北岛岁枝读后被书中情节所感动,放弃了一家人自杀的念头顽强地活了下来,这消息见报后引起了轰动。之后这位日本妇女在日本几位作家陪同下带着儿女来到柳州拜访了肖甘牛,并观看了柳州地区歌舞团赶排的《灯花》歌舞剧,肖甘牛的作品成为外交之花,香飘国内外。
肖甘牛的作品为什么这么感人呢?我主观认为与他的创作思维是分不开的。大概在1961年前后,我与柳州当时的几位文学青年陪肖甘牛登鹅山游览,路上我们请教他关于写作的经验,他说创作不要被某些写作理论束缚住,要大胆创新……是的,只有创新文学作品才有生命力。
案例来源:知产宝网站(www.iphouse.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