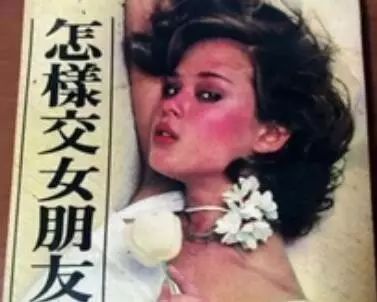本文分析了慕海姆戏剧节提名剧作所揭示的新戏剧现状,指出当代戏剧在挑选素材时越来越多地转向经典剧作,剧作家的创作日益抽象化,且更注重详述而非剧情。同时,新戏剧的形式特征包括:戏剧性场景减少,叙事形式成为主导,节奏处理更自由,对连续情节的依赖减弱,更加注重分析而非解释。然而,这种演变过程也有其益处,如音乐性和展示技艺的自由度增加。最后提到新戏剧与传统戏剧的对比以及其他类型的戏剧也存在。
新戏剧的益处包括音乐性和展示技艺的自由度增加;损失的是连续故事和情节引发的谜题,以及观众在想象中的参与。
虽然新戏剧有其独特之处,但其他类型的戏剧如叙事剧、气候危机寓言剧等也在不断发展。

《沉默》(The Silence),邵宾纳剧院,© Gianmarco Bresadola
每年五月,除了柏林戏剧节,德国另一重要戏剧节在慕海姆举行。与其他戏剧节不同的是,慕海姆戏剧节更关注剧作家,而不是作品。戏剧节颁发的奖项也是新戏剧领域最负盛名的奖项之一。下文转载自德国《午夜剧评网》。作者克里斯蒂安·拉考(Christian Rakow)与米歇尔·沃尔夫(Michael Wolf)分析了2024年慕海姆剧本奖提名剧作所揭示出的新戏剧现状:“
7部提名剧作勾勒出当代戏剧鲜明的美学特征,及其空缺之处。
”
1
个体消失了
对于许多人而言,或许是新冠疫情的爆发才让我们这个时代的特征显露无遗。当我们自问,在户外的公园或剧场中的感染风险有多高、戴或不戴口罩的差别有多大的时候,以及当我们开始钻研数据的时候。
在那时,我们明白了,个体的切身经历在不查看指数函数、曲线图和百分比的情况下,已不再具有说服力。科学无疑在很久以前就对这种现象进行了描述。社会学家施特芬·茂(Steffen Mau)将这类受数字和测量值控制的现代人称为
“度量的我们”(Das metrische Wir)
。这样的人不再是拥有独特个性的个体,也不再具备特殊且相互关联的内在特质。更确切地说,
他们被简化成了为系统和登记册提供数据的数值
。他们身上可被分离、概括和测量的特质才是值得注意的(字面意思)。
这些“度量的我们”早已成为当代戏剧写作的出发点。埃韦·本贝内克(Ewe Benbenek)在描写东欧劳工的恶劣工作条件时对发言者进行了极致的匿名化,称其为“A”“B”“C”“D”,这些发言者组成歌队携手登台。
有趣的不是人物本身,而是他们代表的话语立场
。虽然菲莉茜娅·策勒(Felicia Zeller)为她那个女性之家的人物取了名字,却也只是和本贝内克一样,将她们塑造成了集体经验的载体。每一个要点都预设了人物的社会普遍性。
西凡·本·伊沙伊(Sivan Ben Yishai)彻底放弃了对戏剧人物的命名,让台词自由地在页面上流动。她将庄园雇员塑造为高度典型的服务集体和核心论点的载体(支持交叉性理论),对易卜生及其“娜拉”发出质疑。即使是那些让主角们以伟大名字登场的剧目(例如托马斯·科克(Thomas Köck)作品中的俄狄浦斯),
它们所直接关注的依然是“系统”
,而系统中的主人公仅仅是在完成自己的角色功能罢了。

《沉默》(The Silence),邵宾纳剧院,© Gianmarco Bresadola
个体的服务已到期
。个体已成为集体中的人,以及社会库存中的案例。
消失的痕迹零星地出现在虚构自传性的剧本之中,比如福克·里希特(Falk Richter)那部以家庭为研究对象的剧目《沉默》(The Silence):本剧通过对个体经验无微不至的审视,以一种接近于归纳法的方式呈现出一代人的整体共性。在其余所有入围慕海姆的剧本中,话语的声音盖过了角色,总体的论断遮蔽了具体的情境。
剧作家的创作正日益抽象化
,而这种趋势是由埃尔弗里德·耶利内克(Elfriede Jelinek)(慕海姆奖的纪录保持者)等剧作家在几年前奠定的。
2
素材被发掘,而非被编造
当代戏剧在挑选素材时越来越多地转向了已被奉为经典的剧作。
近两年,这种趋势也在慕海姆戏剧节的提名作品中落地生根:西凡·本·伊沙伊解构了易卜生的“娜拉”, 托马斯·科克和罗兰·施梅芬尼(Roland Schimmelpfennig)则从古希腊的剧作中汲取养分。然而,这种基于重构的写作并不单纯是这些剧的众多特点之一,它本就是诗学创作的一部分。本·伊沙伊通过娜拉望向观众的目光说道:“你们大家都听过她的故事吗?/都读过这部剧了吗?/右侧点头/看过这部剧的演出吗?/左侧点头”。 托马斯·科克将对俄狄浦斯故事的理解与气候危机中人类的内疚感相结合:“所有人都知道这个秘密/从观众到专家到那些/演员们/但在那之后/大家仍在配合演出”。
在这些作品中,写作意味着“改编”、“调整”,且主要指向“批判”和“阐释”。
剧本要求观众具备一定的知识储备
。毕竟,尽管你在对原著一无所知的情况下仍有可能看懂这部新剧,但如果你从未读过易卜生或索福克勒斯的原作,难免会错过一些内容。这类政治上雄心勃勃的剧目有其矛盾之处:它们同时也传递了精英的精神。
这种“重构”或“二创”式的写作并不仅限于对经典作品进行新编。这两个词同样也适用于当代戏剧的其他趋势。例如由行动小组“纠察”(包括让·彼得斯/洛丽塔·拉克斯或卡勒·富尔)(Correctiv, Jean Peters/Lolita Lax oder Calle Fuhr)主导的调查剧场,以及汉斯-维尔纳·克罗辛格和雷吉纳·杜拉(Hans-Werner Kroesinger und Regine Dura)编导的文献剧,亦或是福克·里希特(Falk Richter)以他的参赛作品《沉默》(The Silence)展示的虚构性自传项目。
所有这些作品的共同点在于对原创性的背离。
在这些剧目中,主题、情节、剧构和人物并非被编造,而是被发掘。
这类当代戏剧不生产新事物,而是对已读过的、已经历过的事件作出回应。尽管想象力和创造力仍然是必需的,但它们更多地服务于对细节的打磨。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分析的野心,
旨在更新现存的一切、提出质疑,并使其与当代产生关联
。
3
汇报取代了表演
也许对于熟悉新戏剧的行家来说,这早已不言而喻,但我们仍需说明:
狭义的戏剧性在新戏剧中是不存在的
。即作为表演形式的戏剧性,意味着现场表演一个虚构的情节。某人扮演一个虚构的角色,并在我们眼前展示角色的行为,比如(桑德拉·赫勒(Sandra Hüller)饰演的)奥菲莉亚推开(拉尔斯·艾丁格(Lars Eidinger)饰演的)哈姆雷特。然而,在这些新剧本中,至少在慕海姆的新剧本中,这类戏剧性的、场景性的时刻极为少见。
在这些剧作中占据统治地位的是
叙事形式(epische Form)。角色,或者更准确地说是“话语的载体”(因为没有人真的期待他们成为行动者)在向我们汇报曾经发生的事件。演绎这些事件在很大程度上已成了一种窠臼。同样不合时宜的还有对白,以及角色之间的互动,甚至是他们的行为。回忆覆盖了此时此地应该做的事。
4
详述打败了剧情
如此开篇的剧本意欲何为?
A: A
B: A
C: A
而且后面还跟着27个“A”,之后场景才发生转变:
歌队:那么。
A: 那么么。
A: 不!那么
C: 那么 么!
您肯定已经知道了 ,之后还会有更多“那么”的变体。
埃韦·本贝内克的《果汁》(Juices)就是这样开篇的,以一个戏谑的场景,是的没错,这就是开头。情节层面上并没有发生太多事:“我们开始了,但还没真正开始。”然而,这无疑给了我们充足的想象空间:演员们将如何利用这些文字“大闹一场”,每个“A”会被赋予何种不同的声调,而每个“那么么”又将以何种滑稽的方式从他们的嘴里挤出。情节被无限推迟,
形式的奇观直接了当地喷涌而出
。
简而言之,新戏剧在这样的文段中形成了一个显著特征:整体情节已退居二线。
重要的是表达诗意,成为媒介,而非传递讯息
。修辞学将这种写作手法称为详述(Amplifikation):
话语在内容层面停滞不前,却用丰富的词汇不断装饰自身。每个时刻都被置于放大镜之下。
大多数慕海姆邀请的剧本都存在这种对“详述”的依赖性。剧作家们坚持如此,进行节奏化处理,并为报道中的每个要点赋予重音。然而,他们并没有推动一个更大的故事向前发展。即便有故事的发展,比如基于古希腊文本改编的剧作《拉伊俄斯》或《预言:俄狄浦斯》,也都是以分析型戏剧的模式(以刑侦剧的方式展开)进行的:将其视为一个众所周知的故事,截取片段并给出相应的评论。
这种详述型戏剧文本意味着剧情链条被暂停、中断,并分散在点状的个体视角中。随着故事脉络的消失,情节也随之消失,行为者之间必然展开的冲突也不存在了。
5
讲述已经完结
这种演变过程也有其益处,粗略而言,就是音乐性和秀(show)。当我们不再将全部精力投入到构思剧情的发展、不再试图打造一个由意图和后果构成的精密戏剧系统时,演员们便获得了自由,能够去表现我们称之为“行为性”(Performanz)的东西:对情境的演绎,展现此时此刻的技艺。
然而,损失也随之而来:我们不再能从戏剧文本中期待一个可复述的、包含起承转合的故事。相反,这些剧本所做的是叠加主张与说明。当我们这些观众回到家,试图向亲友复述故事时,往往只能借助某种混合物,或者串联起不连贯的片段。我们提及主题的聚集体,却无法讲清故事的脉络。
随之消失的还有由某个情节引发的谜题。想要得知后续的迫切心情(罗兰·巴特称这种功能为“解释学符码”)也不见了。现代性的文本不设置亟待解答的难题(谁杀死了哈姆雷特的父亲?儿子会成为复仇者吗?)。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它们是一览无遗的。它们讲述事实,却不讲述形成的过程。它们总是在出现时就已完结。在报道的形式中,
一切都让位于人物(即论点的载体)
。
在这里,我们只有在偶尔的情况下才能进入想象中的体验之旅。比如,在忒瑞西阿斯面对神谕时会发生什么(科克的《预言:俄狄浦斯》)?这是一个谜!当福克·里希特叙述的那个年少的自我遭到一名恐同男性的追击时,他会有怎样的遭遇?他逃脱了吗?获救了吗?在这些时刻,我们能够全神贯注地投入故事,猜测可能的后续,并进行热切的思考。
然而,这类能让观众在想象中参与剧情的锚钩非常稀少。新戏剧对这类连贯的情节持有深深的怀疑态度(福克·里希特的叙述者曾呼吁自己不要把剧本写得太像小说)。对事件的预想在很大程度上是不被希望的。
6
也存在其他的剧本
“新戏剧”(Die neue Dramatik)的说法在本文中一再出现,但此处介绍的当然不是唯一的诗学。这仅仅是慕海姆戏剧节多年来形成的一种鲜明的戏剧风格。根据慕海姆的传统,像卢茨·赫布纳&萨拉·内米茨(Lutz Hübner & Sarah Nemitz)和约翰·冯·杜费尔(John von Düffel)这样的叙事能手难以在戏剧节上有所斩获。近几年的大热剧作,费迪南德·冯·席拉赫(Ferdinand von Schirach)的法庭剧《恐怖》(Terror),也无缘入围慕海姆。社会喜剧女王诺拉·阿卜杜勒-马库苏德(Nora Abdel-Maksoud)2022年的参赛剧本《越野车》(Jeeps)在慕海姆表现平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