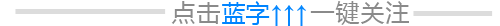

原刊于《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4年第6期,原标题《围绕朝鲜半岛的日清、日俄矛盾与甲午战争》,经《武汉大学学报》授权转载。
1894年,日本为实现其野心勃勃“经略大陆”的构想,悍然发动了甲午战争。而在某种意义上,甲午战争是中、日、朝、俄四国间内在矛盾的表面化。而东北亚诸国,围绕朝鲜以及中国东北地区的利益争夺则由来已久。日本以维护朝鲜独立之名,自日朝间“文书问题”起,就不断挑战中朝传统的宗藩关系;俄国自1860年攫取了乌苏里江以东的大片领土之后,在觊觎中国东北之余,其侵略眼光也瞄准了朝鲜半岛,并与日本在“桦太”等地直接展开争夺。日本担心在扩张之路上落后于人,加紧攫取朝鲜半岛的控制权,也因此更加激化了日清矛盾。东北亚诸国彼此忌惮,互相警惕,使得这一时期的东北亚局势错综复杂。各方势力的消长,彼此矛盾的演化,与“甲午战争”的爆发有着深刻的联系。
明治维新后的日朝矛盾,始于日朝间的“文书问题”。1868年底,一向负责对朝外交的对马藩“先问使”抵达朝鲜。在呈递“王政复古通知书”之前的“先问书契”中,一改“日本国对马州太守拾遗平某”的旧有称谓,而使用了“日本国左近卫少将对马守平朝臣义达”的名衔,并在其后的“王政复古通知书”中使用了新印。
对此,朝鲜方面反应强烈,称“不但岛主职号与前有异,句语中皇室奉敕等语,极为悖慢……岛主图署之自我铸给,今忽谓以铸印,亦为骇然”,表示拒绝接受日本的正式文书。对于朝鲜来说,日本单方面对旧有外交模式做出的调整,实为“三百年以来所无之举也。惟我两邦之率由旧章,永以为好者,为其诚信之不可渝,约条之不可违,则今日之事,谓之诚信乎,约条乎”。朝鲜对日本“无信无约”的指责背后,也隐含着对日本“称皇称敕”的警惕。就日本的立场而言,明治维新后的日本,无论在外交领域还是内政领域,绝对主义倾向下的主体一元化则是既定的改革方针。借由对“神户事件”与“堺事件”的处置,明治政府承诺对于以幕府将军名义缔结的条约,将以天皇的名义加以继承。这使得明治政府在戊辰战争之前,就迅速取得了西方各国对于明治政府作为外交主体资格的确认。“江户开城”之后,各国公使又相继在东京觐见天皇,呈递国书,并在协商之后撤销了“戊辰战争”以来的局外中立。天皇作为外交唯一主体的资格被各国所承认。而作为江户幕府时代的“大君外交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日朝“交邻”关系,则与明治政府力图迅速实现外交主体一元化的努力相违背。同时,以对马藩为中介进行的日朝外交,其封建性也与逐渐近代专制化的日本政体相违背。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一向专擅对朝交涉的对马藩,也不得不废弃原本朝鲜方面认可的印信,又在文书中强调“朝廷特褒旧勋,加爵进官左近卫少将,更命交际职,永传不朽,又赐证明印记”,表明了其外交权限来自于天皇的“授予”,实际上放弃了作为朝鲜“外臣”的身份。
日朝间的交往格局,在谨守旧传统与开拓新局面之间的冲突,其背后也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外交观念的冲突。这种冲突在19世纪的东北亚并不鲜见,而其结局也大多蚀刻着时代的烙印:强权与武力左右着国际格局的基本走向,巨舰与大炮决定了国家间的基本关系。谋求改变日朝旧有关系的日本自身,就是在“黑船”的威胁之下打开国门的,在需求突破日朝外交死结的同时,日本也不得不考虑来自其他列强的威胁,而最直接的威胁来自俄国。1860年中俄缔结的《北京条约》使得俄日之间形成隔日本海而对峙的局面,旋即俄国军舰就于次年占领了对马,对马藩对此无力解决,甚至提出放弃对马,要求幕府转封九州。直到幕府出面请求英国干涉,俄国的企图才未得逞。实际上,俄国的这一动作是对早在1859年英国测量对马海岸的回应,占领对马的俄国官员就曾向对马藩宣传英国对于对马的野心。而英国干涉俄国的占领行为也不过是出于防止俄国在远东壮大实力并为自己谋取利益,英国公使甚至称“对俄国军舰的非法行为提出抗议,迫令退出,如果俄国拒绝,英国就自己来占领该地”。这一事件作为“围绕着日本的严重国际关系的象征,其严重程度甚至使人预想到日本国土将遭到瓜分”。之后日俄在“桦太”问题上矛盾逐渐实质化,应对俄国威胁并在列强的东北亚利益争夺战中占据一席之地,成为左右明治政府外交政策决断的要因之一。
大久保利通在明治二年十一月给岩仓具视的信中说,“唐太(桦太)之事实为今日之大患,愚亦为此寝食难安”。在信中,大久保建议原任外务权大丞的黑田清隆专任兵部大丞,专职陆军事务。黑田任兵部大丞未及满月,大久保又向岩仓建议,让其担任开拓次官,负责“桦太”事务。黑田赴任之后,提出通过军事手段应对俄国在“桦太”问题上的“攻势”主张,认为“朝廷应为与鲁(俄国)一战谋划,可派遣留学生兼充间谍之任。谋划此战,人力与财力实为两大根本”。而在当时的日本,黑田所言谋划与俄一战所需的“人力与财力”的条件是根本不具备的。黑田也逐渐将其立场修正为“桦太放弃论”以保证北海道地区的优先开发。俄国在日本北方咄咄逼人的姿态,以及其在中国东北的扩张,使得日本对于俄国终会将其势力渗透至朝鲜半岛的可能表现出极大的担忧。早在明治二年十月,时任日本公务办理职(总领事)的法国人モンブラン(Charles Descantons de Montblanc)就曾向外务卿泽宣嘉提出警告说:“俄国人掠夺朝鲜之时,较之俄国的东方领地桦太,长崎将更加直接的与大陆毗连(既直接面对俄国势力),前述之情状至之之时,大日本国也将变为今日之桦太”。出于对预想中俄国势力南下的警惕,日本朝野内外“对露警戒论”一时间甚嚣尘上。柳原前光在其《朝鲜论稿》中称,“近年各国于彼地(朝鲜)窥探其国情者亦不在少数,如鲁西亚(俄国)者,其业已蚕食满洲东北,而势必鲸吞朝鲜”。明治三年五月,兵部省曾提出“创设大海军之议”,在计划的提案书中谈及俄国的南下意图,称“(俄国)于近年取得黑龙江沿岸满洲之地,已与我北海道及朝鲜国界相接,压逼皇国、中国及朝鲜之北境……若无法阻止其南下之欲,此诚为两大洲之大害”。明治八年四月,岩仓具视在《国事意见书》中也谈到了对于俄国南下吞并朝鲜的担心:“若俄国以其排山倒海之势吞并之,则我国首尾皆受俄国威胁,此于我国势之害大矣”。

在上述诸多围绕朝鲜的“对俄警戒”论调之外,尤为需要注意的是外务省在明治二年九月向太政官提交的“朝鲜外交报告书”。其中谈到,“即使无法令朝鲜成为皇朝(日本)之藩属,也应当保持其国脉永世不变。而今自鲁西亚(俄国)始,各强国皆视朝鲜为鱼肉。此时得以维持万国公法,行匡救扶绥之任者,舍皇朝之外岂有他国。此诚燃眉之急也。一旦置朝鲜之安危于度外,任由鲁(俄)狼等强国吞噬之,必为皇国永世之大害”。外务省的报告书中,对于朝鲜地位的预期,无论“皇朝之藩属”,还是“国脉永世不变”显然与朝鲜在当时东亚国际关系中的实际地位有极大的冲突。朝鲜与日本之间并无“藩属”关系,而“国脉永世不变”之说,考虑到朝鲜与清政府之间的实际情况,与其理解为外务省希望朝鲜不被其他强权染指,莫如说,在外务省的预想中,一个与清政府间并无“藩属”关系的、“独立”的朝鲜更符合日本的利益。
虽然在其后发生的“江华岛事件”之时,外务少辅森有礼曾强辩称,“朝鲜虽曰属国,地固不隶中国,以故中国曾无干预内政,其与外国干涉,亦听彼国自主不可相强等语。由是观之,朝鲜是一独立之国而贵国谓之属国者徒空名耳”,但事实上,同处于东亚政治文化之下的日本,对于中朝间的藩属关系是有充分认识的,外务省早在明治三年就曾提出解决朝鲜问题的“三策”,在放弃与朝鲜交往可能,撤退倭馆人员以及以军舰威逼朝鲜迫其开港开市之外,提出“先派遣使节前往支那,签订通信条约,之后,于归途前往朝鲜王京(以条约)迫之”的办法。希望首先取得与清政府对等的外交地位,并借由此取得对朝外交的地位优势,如果日本不是充分了解中朝关系,显然是不能提出这样的解决办法的。而事实上这也是日本在当时处理朝鲜外交问题的第一选择。对于中朝关系,木户孝允也在“江华岛事件”发生之后,提请岩仓具视处理朝鲜问题时加以考虑,称“朝鲜之与中国,现奉其正朔,虽于其互相交谊之亲密,患难之互相关切情况,未可明知,然而其有羁属关系则可必”。显然,日本要令朝鲜成为“皇朝之藩属”或者保持其“国脉永世不变”以应对预想中,由“鲁(俄)狼等强国吞噬之”的可能,与清政府之间关于朝鲜的摩擦就不可避免。实际上,在日本与朝鲜因“江华岛事件”一度走向战争边缘之前,日本方面就已经为可能的日朝,甚至是日中战争进行准备。1873年(明治六年),时任参议陆军大将的西乡隆盛,与外务卿副岛种臣及参议板垣退助商议,“派遣陆军中佐北村重賴、陆军大尉别府晋介为实地调查委员赴韩国;同时,又令外务省十等出仕池上四郎、武市正斡以及外务省權中錄彭城中平赴满洲,调查满韩地形、政治、兵备、财政、风俗”。彭城中平在中国东北游历调查之时,其调查内容涉及极广,其在《清国滞在见闻事件》中提及盛京将军“尽心于武事政治”,但同时,彭城中平也屡屡谈到,“政府高官多苦心于武备之事,至于兵卒则流于懒惰”。对于已经开港的牛庄,彭城中平对其进行了详细的了解,“清国的开港地牛庄,即奉天府管辖下的海城县没沟营之海口……称之为营口”,对于营口的守备,彭城中平也做了调查“此庙(老爷庙)以南大致二里稍偏西处,有兵营一座,常备兵五百人,共分十队,每队兵员五十人,队长一人。队长均为满人……其所持兵器大炮、小铳、枪、弓等,炮铳皆为西洋旧款。”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彭城中平在对营口及周边地理进行调查时特意提到“(营口)距金州城四百里,距金州城下辖小平岛四百九十里,自此岛至山东芝罘之渡船,顺风一日即达。冬日营口港冰封之后,此地渡船通信仍可为之。”在充分的武力调查与准备之下,日本以炮舰外交的手段强行打开朝鲜国门,就并不是一件令人意外的事情了。
“江华岛事件”之后,日本与朝鲜签订了《日朝修好条规》。其第一款称“朝鲜国自主之邦,保有与日本平等之权”。“自主之邦”的称谓,一方面是日本追求外交近代化的必然要求,也是《日朝修好条规》得以成立的根本基础;但同时,忽略朝鲜的实际外交地位,“创造”朝鲜“自主之邦”的假象,这也正是《日朝修好条规》的最大目的所在。而日本政府原本为解决“日朝国交”的“中断”而提出的“对朝三策”,最终还是通过“炮舰外交”,在中朝日三国对于朝鲜地位并未取得一致认识的前提之下,强行以条约的形式重建了“日朝国交”。以损害中朝关系为前提的“日朝国交”直接导致了日本政府与清政府在朝鲜问题上的激烈对立。“自主之邦”的表达如果成立的话,那么中朝之间原有的藩属关系则必然受到损害。这是清政府绝不愿意看到的。而几乎与此同时,日本从其自身实力的立场出发,与俄国达成了《桦太与千岛交换条约》,以放弃“桦太岛”的方式,达成了日俄关系暂时的协调。日俄关系的缓和,使得清政府成为了阻碍日本在朝鲜扩张势力的主要对手。而如何实现《日朝修好条规》,将朝鲜“独立之邦”具体化就成为了日本外交中极为重要的课题。时任朝鲜办理公使职的花房义质在与金宏集商谈仁川开港的具体事宜之时,曾向其强调“我政府保护朝鲜之意切,与朝鲜共富强之欲深”。所谓“独立之邦”,在“保护朝鲜”的“意切”之下,无异于一句谎言,而“独立之邦”的具体化,也无非是彻底摈弃清政府在朝的影响力,使朝鲜在日本的羽翼之下,成为日本间隔俄国的战略缓冲地带。这一点,在花房义质就与金宏集谈判事宜向外务卿井上馨提交的报告书中,有更直接的阐述。花房义质称“以我(日本)助其(朝鲜)全然独立至为重要”,而“倘若能够对其国政之枢轴,外交之方略加以干涉,其(朝鲜)定不能再持全然他国从属之局面”。花房义质的提议,可视为《日朝修好条规》签订之后日本对朝鲜的外交主要方针。这一方针简言之,即实现朝鲜的“去清亲日”。为此,日本一方面利用朝鲜遣使赴日的时机,极力展示日本近代化的成果,培养朝鲜政府中的亲日派;另一方面,日本政府也不断实化与深化《日朝修好条规》的各项约定,加紧釜山、仁川、元山等地的开港进程。朝鲜的开港,不单是日本出于扩张其在朝势力的考虑,同时也是阻止俄国向朝鲜扩张的手段。在极力促成朝鲜开港之余,日本方面也极力实现“使节驻扎京城”的政治目的,试图从朝鲜的中枢着手,对朝鲜政府施加影响。对此,花房义质在与金宏集的谈判中将“使节驻扎京城”称为“至要之事”,并威胁称,美国使节即将直接前往京城与朝鲜交涉,俄国也有这样的计划,并称“倘若日本公使得以驻在京城,则各国使臣抵达京城之后,日本亦可从中妥为周旋”。朝鲜在日本的逼迫之下,不得不同意日本“使节驻扎京城”。日本成为了第一个在朝鲜驻留官员、设置使馆的国家。花房义质常驻汉城后,积极开展活动,拜会朝鲜当政要人,宣传日朝接近的必要,在向朝鲜赠送武器的同时,又要求朝鲜聘请日方军事顾问,建立日式军队,并向日本派遣留学生。朝鲜方面也正式聘请堀本礼造担任军事教官,成立了“别技军”。然而,这只从装备到待遇都有别于传统军队的日式军队的存在,非但没有使日朝关系更加紧密,相反却成为导致朝鲜局势发生动荡的壬午军变的导火索。
日本在朝势力的扩张,如前所述,虽然有为应对预想中俄国势力势必南下侵入朝鲜半岛的局面出现而提前布局的考虑,但更多的则是试图颠覆中朝之间的传统关系,创造一个与日本“共富强”的、处于日本“保护”下的朝鲜。这一点,非但引起清政府的警惕与不满,在朝鲜国内也很难获得民意与舆论的支持。这样的背景之下,“壬午军变”的发生,作为朝鲜对于日本势力入侵的自我抵抗,则显得顺理成章。这一深具必然因素的偶然事件给了正在寻找机会回击日本扩张的清政府以机会。接到驻日公使黎庶昌关于花房义质已由日本陆海军护送返朝的报告之后,光绪八年六月二十四日(1882年8月7日),署理北洋大臣的张树声上奏称“日本现在派兵前往,其情尚难揣度。朝鲜久隶藩封,论朝廷自小之义,本应派兵前往保护。日本为中国有约之国,既在朝鲜受警亦应一并护持。庶师出有名兼可伐其阴谋”。其后的总理衙门《奏请派兵护持折》中称“日人夙谋专制,朝鲜朝臣阴附日人者不少。今使内乱蜂起而日兵猝至,彼或先以问罪之师代为除乱之事,附日之人又乘机左右之,使日本有功于朝鲜则中国字小之义有阙,日人愈得肆其簧鼓之谋”,如总理衙门所论,则张树声奏折中“阴谋”之所指亦不言自明。针对于此,清政府迅速派兵入朝,表现出极为明确的态度,其主旨就是“防范日本借机扩大对朝鲜半岛的控制权,而对朝鲜‘派兵保护’与对日本‘一并护持’,在宣示了宗主国形象之余,也有效地维护了清政府的在朝利益”。

壬午军变作为一次偶然事件,日本军方对此并无战备预案。虽然黑田清隆与副岛种臣倾向于对朝开战,但廷议最终并未支持开战论。也正因为日本政府对于动用武力准备不足,对于壬午军变的解决,日本的外交方针也不得不“一方面秉持政府当局的强硬态度,另一方面将和平解决作为基本方针”。花房义质携井上馨训令在重兵护持之下赴朝谈判,而其后签订的《济物浦条约》及其后的《续约》中,除捉拿凶徒的时限及赔款数额之外,日本基本上实现了预设的交涉目标。但即便如此,壬午军变对于日本来说,也仍是一次极大削弱其在朝影响力的事件。清政府借由迅速平定壬午军变,有力地对外宣示了其宗主国的地位,其后与朝鲜签订的《中朝商民水陆通商章程》更是将清政府对朝鲜的影响及控制提升到前所未有的局面。原本主动调整日朝关系的日本,其在朝鲜半岛获得的“先手”优势开始丧失。面对此种局面,日本也开始调整其对朝政策。这种调整,外务卿井上馨将其总结为“积极”与“消极”两策,在“内则养成实力为我之隐秘辅助;外则以各国确认其独立自主为要”与“若无法钳制清政府之干涉,则姑息其所为以保持日清两国及东洋之和平”之间,日本不得不根据时势做出对其自身有利的选择。与之前“以我(日本)助其(朝鲜)全然独立至为重要”的咄咄逼人相比,此时的日本也“不得不暂取前述之消极政策以为保持东洋和平之大局以为万全之策”。右大臣岩仓具视在此时提出通过“应与有约各国协议,达成朝鲜乃独立之共识”的手段应对中朝藩属关系的新局面。但事实上,在“壬午军变”之前,清政府主导的《朝美修好条约》未如《日朝修好条规》之例,对朝鲜“独立之邦”做出约定,而其后纷至沓来的西方诸国,也大多以《朝美修好条约》而非《日朝修好条规》为范本,与朝鲜签订了条约。“朝鲜独立”非但不是一个被公开承认的“共识”,在实际上,各国也大多从务实的角度出发,委任其驻华使节兼任驻朝使节。日本寄希望于创造一个“朝鲜独立之邦”被公认的局面,在其尝试参与朝美外交失败之时,就几乎已经注定不会出现了。
与西方列强不同,俄国正式踏足朝鲜半岛则显得姗姗来迟。直到1884年7月,其驻天津领事韦贝尔才经由穆麟德的暗中斡旋,赴朝签订了《朝俄修好通商条约》。但与大多数在朝鲜问题上持观望态度的西方国家不同,对于朝鲜来说,“其利益此时尚未遭到来自俄国的直接损害,朝俄之间也并无实际的大的冲突,此外,俄国不但是有助于朝鲜摆脱清政府,能够对清起到牵制作用的力量,同时将来其在牵制英、日势力方面的价值也不言自明”。《朝俄修好通商条约》的签订是朝鲜试图外交自主的努力,这种“自主”的努力,也从反面反映出清政府在“壬午军变”之后对朝控制和影响的不断加强。而这一点,也令日本如坐针毡。如果说“壬午军变”导致了日本“被动”地调整对朝政策,那么,“甲申政变”则显然是日本针对日、清势力在朝此消彼长的局面而主动做出的回应。日本以其武力为后盾试图策动朝鲜亲日派政变,却遭到了清政府同样的武力回击。虽然以西乡从道为首的军部势力主张对清采取强硬措施,但就实力与舆论而言,日本对清开战显然难取必胜把握。伊藤博文也坚持先处理对朝交涉,并认为“朝鲜问题既已告和平解决,在此基础之上,对清谈判也应当采取追求和平的方针”。“追求和平”这一方针也在伊藤博文和井上馨的坚持之下,成为了对清谈判的主导方针,在伊藤博文出发赴天津之前,井上馨以外务卿身份发出训令,强调“我政府向以日清两国和好为重……为将来计,善后之事宜当倾向于商弁解决”。三条实美也以太政大臣身份将天皇内谕“奉旨晓谕”各地方长官,称“与外国交涉之事,兹事体大,各国现在之情势及将来事态之发展仍需观察,为不误国家永远之大计,交涉一事,当取妥善之方向以全邻好之谊”。要其镇抚人心,防范“轻举”之事。伊藤博文赴清之后,中日双方在都做出一定让步的前提之下签订了《天津会议专条》,约定“将来朝鲜国若有变乱重大事件,中日两国或一国要派兵,应先互相行文知照,及其事定,仍即撤回,不再留防”。日本方面就此获得了所谓“共同保护朝鲜”的权利,但是,“当时的亲日的开化派被一扫之后,对于清国来说,以维持宗主权的行使为目的,在韩国驻扎本国军队已无必要……两军同时撤兵实际上也就意味着日本势力的相对减弱”。

如同当年日本利用英俄互相保持“克制”的时机插手朝鲜半岛一样,俄国也在此时确立了“利用日清冲突的有利时机,占有韩国某处港湾”(37)的方针。由于风传俄国利用《朝俄秘密协定》占据了永兴湾,同时作为对俄国占领阿富汗的回应,英国舰队于1885年4月占领了朝鲜巨文岛,试图将其作为封锁俄国太平洋舰队的基地。在巨文岛被英国占领之后,井上馨深感此事是“予俄国插手朝鲜以最大良机”,认为“日本近海就此成为争夺之焦点,东亚和平难保”。而清政府则利用解决“巨文岛事件”的契机,以朝鲜宗主国的身份直接与英国展开交涉,使英国“改变了以往对中朝宗属关系的暧昧态度,对之给予了公开的承认……围绕中朝宗属关系的国际形势开始变得对中国有利”。对于此,井上馨不得不以个人名义向李鸿章提出了“朝鲜办法八法”,希望能够在对朝事务上取得与清政府的协调。有日本学者认为“朝鲜办法八法”是“默认清帝国对朝鲜的宗主权,提议以清政府为主导,把朝鲜置于日清两国共同保护之下,以抵抗俄国的入侵”。而已经在朝鲜问题上获得优势的清政府拒绝了井上馨的提议。随着“甲申事变”与“巨文岛事件”的解决,日本对朝预想的“积极策”与“消极策”接连破产,日本在朝势力受到巨大打击,在其后十余年里,日本完全丧失了在朝鲜的“先手”和“主动”的地位,日本描画的“朝鲜独立之邦”的假象也无从成立。
甲午战争的爆发,是围绕朝鲜问题的中日矛盾激化到不可调和境地的产物。如前所诉,在甲申政变后的十年里,日本在朝鲜丧失了主动,日清矛盾朝着对清有利的方向发展。对于日本来说,发动战争几乎是扭转其被动局面的唯一手段。“防谷令事件”之后,天皇于1893年5月19日批准了《战时大本营条例》。条例的颁布,“具体地表明了军队预定不久将要进行战争”。而近十年的备战,也令日本政府对于甲午战争的结果有“乐观”的期待。相对于日本,清政府则对于战争的可能性预估不足,战备更无从谈起。在战争一触即发之际,俄国也对日本发动战争以改变朝鲜半岛状态的企图表现出极大的关切。中日正式宣战之前,驻东京俄国公使希特罗渥奉俄国政府训令正式向陆奥宗光提出问询,称“中国政府已请求俄国调解中日两国纠纷,俄国政府甚望两国早日和平解决,因此,若中国政府撤退其派驻朝鲜之军队,日本政府是否亦同意撤退其军队”,陆奥宗光称,撤军的条件为清政府同意由中日两国共同负责改革朝鲜内政,而如果清政府不愿承担改革朝鲜内政之责,则日本政府必以其独力施行之。6月30日,俄国又向日本发出正式照会,称“朝鲜政府已将内乱平定之意知照各国使节,并请各国使节协助请求中日两国共同撤兵,俄国政府劝告日本接受朝鲜之请求”。陆奥宗光接此照会后,立即赴伊藤博文官邸商议此事,并就拒不撤兵一事达成一致。其后,陆奥宗光电告驻俄公使西德二郎,称“本大臣与伊藤伯意见一致,日本绝不可接受露(俄)国之劝告”。事实上,在此之前,陆奥宗光已经接获报告,就俄国在西伯利亚的兵力配备而言,俄国不可能就日本在朝鲜的战争行动做出具体的激烈反应,而这也成为日本决然发动甲午战争的原因之一。

战争爆发之后,随着日本在军事上的不断胜利,列强对于日本动向的警惕也不断加深。大山岩率日本第二军于1895年1月在山东登陆之后,清政府战败几乎已成定局。此时,在针对清政府与朝鲜的宗属关系上和日本有同样利益的俄国,也并不希望胜利的一方有任何“破坏朝鲜领土完整的企图”,而战争的继续发展,对于俄国在远东地区,尤其是中国东北的利益必将有极大的损害。有鉴于此,在战前拒绝了清政府正式调停请求的俄国,此时也开始尝试了解日本停战的条件。1895年2月,俄国外交部就向日本方面提出,若日本发表宣言承认朝鲜在名义与事实上独立的话,俄国政府愿意劝告清政府派遣全权使节赴日谈判。2月24日,俄国驻日公使希特罗渥拜访陆奥宗光,称接获本国政府电报,“获悉日本希望清国能够派遣可以签署包括朝鲜独立、赔款、土地让与等条件,及将来两国关系条约之全权使节……倘若日本政府宣布在名义及事实上承认朝鲜之独立,我政府当劝说清国政府派遣包含前述条件之全权使节赴日”,表示俄国认可以“朝鲜独立”作为日中媾和的基础。确保朝鲜“独立”,这是俄国的既定方针,而对于日本从中国割地一项,俄国则希望日本能将割地的要求限定于台湾。早在1894年底,希特罗渥曾以私人身份暗示陆奥宗光,“俄国对于日本占领台湾一事并无任何异议”。在上述俄国政府正式提出以朝鲜“独立”作为“劝告”清政府派遣全权使节赴日媾和的条件之前,1895年2月14日,希特罗渥又一次以私人身份强调,“日本要求割让台湾,俄国对此毫无异议,若日本放弃岛国之地位向大陆扩张版图,则绝非上策”。面对朝鲜“独立”木已成舟的事实,“俄国利益”更加明确地指向了中国东北。日本通过战争获取在中国东北地区的“割地”是俄国决不能允许的。而在此之前,俄国政府在2月1日召开的第二次远东政策会议上也已做出决定:“第一,增强俄国在太平洋的舰队,使俄国在太平洋上的海军力量尽可能强于日本;第二,同英国及其他欧洲列强,主要是法国,达成协议,如果日本政府和中国缔结和约,所提出的的要求侵犯俄国利益时,则对日本共同施加压力”。在获悉日本提出议和条件中包括割占辽东半岛之一项之后,4月6日,俄国外交大臣罗拔诺夫上奏称,“日本所提和约条件,最引人注意的,无疑是他们完全占领旅顺口所在的半岛;此种占领,会经常威胁北京,甚至威胁要宣布独立的朝鲜;同时由我国利益来看,此种占领是最不惬意的事实”。在4月11日召开的关于远东外交政策的特别会议上,外交大臣罗拔诺夫又称“在任何情况下,不能指望日本的友谊。它不仅对中国战争,还要对俄国战争,以后会是对全欧洲。日本人在占领南满之后,绝不会止于此,无疑将向北推进殖民”,在此之外,维特也在会议上强调,“日本之所以进行战争是我们开始建筑西伯利亚铁道的后果。欧洲列强及日本大概都意识到不久的将来要瓜分中国,他们认为,在瓜分之时,由于西伯利亚铁道,我们的机会将大大增加。日本的敌对行动主要是针对我们的……假使我们现在让日本人进人满洲,要保护我们的领土及西伯利亚铁道,就需要数十万军队及大大增强我们的海军,因为我们迟早一定会与日本人发生冲突”。也正如维特的推测,日清矛盾的地位随着清政府的战败以及朝鲜的“独立”而逐渐让位于日俄矛盾。而对于日俄于将来可能发生冲突一事,早在甲午战争爆发之前的1890年,山县有朋在提出其著名的“我邦利益线之焦点实在朝鲜”之论时,就已经声称“西伯利亚铁路竣工之时,自露(俄)都出发,十数日即可饮马黑龙江。对吾人而言,西伯利亚铁路完成之时,既朝鲜多事之秋也”。俄日两帝国的相互警惕,也使得其后的日俄战争与其说是甲午战争的延续,莫如说甲午战争是日俄战争的序曲。而此时甲午战争尚未终结,暗流涌动之下,日俄双方皆已经蓄势待发。中国的东北地区,成为两国争逐的焦点。

但对于日本来说,俄国对于中国东北地区的关注并不是其考虑如何攫取甲午战争胜利果实的主要出发点,此时的日本,朝野内外“对于中国的割让唯欲其大,发扬帝国的光辉唯欲其多这一点,几乎是一致的”。军队之中,更是主张“辽东半岛是我国军队流血牺牲夺取来的……而且辽东半岛既控制朝鲜的侧背,又扼北京的咽喉,为国家前途久远之计,绝不可不归我领有”。一方面出于对国内舆论民情的回应,另一方面,中国东北,尤其是辽东半岛的战略价值也早为日本所觊觎。为此,日本决意占有辽东半岛。这一企图令日本与俄国的矛盾愈发凸显。在获悉日本正式提出割让奉天南部之后,俄国立刻向日本表达了强烈不满。在与俄国公使会面之后,林董外务次官向陆奥宗光报告称,“与露(俄)国公使面晤,该公使对日本政府要求(清政府)割让奉天省南部之事颇为不快,并声称就其个人意见而言,日本之要求必会伤害欧洲各国之感情,予欧洲各国干涉之口实”。在彼此协调之后,4月23日下午,俄、德、法三国公使又同时向日本政府正式表示对中日条约中割让辽东半岛一项表示异议的备忘录。俄国在备忘录中称“露(俄)国皇帝陛下之政府,查阅日本向清国提出之媾和条约,其要求中有辽东半岛割与日本所有之项,此件非但将使威慑清国之都成为常态,同时朝鲜之独立亦有名无实。上述之情形,将为远东永久和平之障碍。露(俄)国政府为向日本国皇帝陛下之政府再次重申其诚实与友谊之故,兹劝告日本政府明确放弃领有辽东半岛一事”。法国与德国也通过备忘录的形式表达了相同的对朝鲜“独立”以及远东和平的担忧。对于可能招致列强不满,甚至引发干涉的局面,日本政府在事先亦有预想,但如同陆奥宗光在同一日稍早时候给伊藤博文的电报中所称那样,“据青木(青木周藏,时任驻德公使)、西两公使电报获悉,来自欧洲各大国之强力干涉,已不可避免……此无非是倘若我政府最初向欧洲大国提出我之条件所必然招致之干涉延迟至今日而已。我政府既已成骑虎之势,无论如何危险,除维持如今之立场,示人以一步不让之姿外,别无他策”。对于日本来说,此时做出让步,放弃割地,甲午战争的主要“胜果”立时化为灰烬,果若如此,“即使我当局者为国家长久计忍受内心无限的痛苦,有决心承担将来的难局,但此变化一旦对外发表,将使我国陆海军人员如何激动,我国国民又将如何失望?即使能够减轻外来的危机,但从内部发生的变动又将如何抑制?实已处在内外两难之间,不知轻重何在”。24日,广岛大本营立刻就此事召开会议,会议商定三个方案,“其一:断然拒绝三国之劝告,此种情况之下,当有与三国以兵力决雌雄之觉悟……其二:撤却对于金州半岛(辽东半岛)之占领,将条约交由各国会议协商,此种情况之下,如何会议,于何地何时会议,仍需与三国公使谈判商定……其三:全然接受三国之劝告,将(还辽)视为我之恩惠,以确保中国政府对于其他条件完全施行”。伊藤博文等人虽较为倾向与第二套方案,但从外交实务角度出发,陆奥宗光认为,中日换约迫在眉睫,长期彷徨于和战之间徒增变数,各国出于各自立场,必于会议之间提出种种条件,这无异于招致欧洲各国新的干涉。鉴于此,日本方面将此时的外交方针确定为,“对于三国纵使最后不能不完全让步,但对于中国则一步不让”。4月29日,陆奥宗光又接到驻俄公使西德二郎的电报,电报中称,“近期与露(俄)国外交大臣曾长时间面谈……俄国之所以反对我于大陆的割地要求,根本在于,其认为一旦日本于辽东半岛获得优良军港,日本之势力发展必不限于该半岛之内,日本将来必会向朝鲜全国及满洲北部丰饶之地大举殖民。上述之地久之必成日本之屏藩。俄国之领土势必从海陆两方面受其威慑。由此,日本政府相信,对于俄国,“我国如无以武力一绝胜负的决心,单凭外交上的折冲是不起什么作用的”。同样觊觎中国东北的日俄两国,双方的意图均已摆在桌面之上,日俄矛盾已是不通过战争无法解决的了。而此时在军事力量上居于下风的日本,除了还辽一途,也别无他法。
日朝矛盾的产生,是宗藩体系与条约体系两种不同国际秩序碰撞的结果。虽然日本强行以条约的形式重建日朝国交,但是这一矛盾并未随着日本逼迫朝鲜签订空有“平等”之名的条约而宣告终结。相反,日本在朝鲜半岛表现出的咄咄逼人的态势,不但损害了朝鲜的利益,也颠覆了东北亚国家内部间近300年的和平局面。日本与清政府的矛盾不断激化,双方实力此消彼长,最终导致了甲午战争的爆发。在这一过程中,日本始终保持着对俄戒备、与俄争雄的意识,日本的大陆政策与俄国的远东政策遂产生直接冲突。日本对于朝鲜、进而对中国东北地区的野心,随着甲午战争的胜利而逐渐暴露出来。俄国在默认朝鲜“独立”之余,坚决要将日本阻挡在亚洲大陆之外。日俄双方争夺的焦点从朝鲜转移到中国东北,至此,继日朝、日清矛盾之后,日俄矛盾逐渐成为左右东北亚国际关系走向的主要基点。从这个意义上说,甲午战争与1904年的日俄战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东北亚地区,各国围绕着朝鲜以及中国东北所展开的争夺也令中、日、朝、俄诸国间的关系变动不居,彼此牵连,头绪万端。时至今日,东北亚地区国家间虽然经贸关系密切,人员往来频繁,但是仍然存在着军事对峙、领土纠纷等诸多棘手问题,而其中有的本来就是近代暨甲午战争以来遗留的问题。有鉴于此,在东北亚时局错综复杂的当下,重新梳理和审视这段历史,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无疑具有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对于建设稳定而协调的东北亚地区国际关系也不无裨益。
在长安建都乃千年之计,大汉繁荣至此开始
从公元前202年刘邦定都,到公元904年朱温挟持唐昭宗离开,期间虽然并未一直作为京城存在,但长安作为中国的政治文化经济中心,足有千年之久。而这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强盛的时期。
△点击图片进入文章

△点击图片,查看所有往期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