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绮贞有一首名曲叫《旅行的意义》,被很多知识分子奉为圭臬,据我研究,该曲目的中心思想是最后一句歌词:你离开我,就是旅行的意义。
也就是说,这个男的通过死命旅行,规避和女方发生肢体接触,然后达成分手的目的,在这个案例里,旅行变成了逃避性生活的手段,属于冷暴力的一种。
还有一首最近很火的网路歌曲,里面有一段歌词:我想要带你去浪漫的土耳其,然后一起去东京和巴黎,其实我特别喜欢迈阿密,和有黑人的洛杉矶,其实亲爱的你,不必太过惊奇。
这首歌的中心思想是带女友去洛杉矶看黑人,安抚女方不要害怕。其实我也不知道这个中心思想怎么解读,可能男方是个科比球迷。
说了这么多,我是想表达,不同人对于旅行的看法和目的各异,都有其道理和存在价值。而对我来说,旅行的意义是什么,我想具体展开探讨一下。
在日常生活中,我是一个严肃而无趣的人,过着自律单调的生活,虽然被视作美食大家,但实则每天吃沙拉、啖藜麦,我不爱笑,不喝酒的时候甚至都不爱说话。我热爱思考,认为自己的内心世界是远比real world有趣的东西,所以,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不喜欢旅游,而是把自己关在家里,看书、写文、健身、搞研究。有朋友劝我,作为一个写作者,除了读万卷书,还应该行万里路,我说那是普通人,我信奉爱因斯坦那一套,即使没有数据没有实践基础,自己也可以通过“思想实验”认识世界。爱因斯坦在专利局思考出了相对论,我也思考出了几篇旷世名著,并付梓刊行。
朋友反驳我,说爱因斯坦和牛顿的人生后三十年都在浪费自己的伟大智力,除了搞原子弹和搞臭莱布尼茨,他俩几乎一事无成。要是爱因斯坦和牛顿多报几个自由行,去去土耳其或者洛杉矶,藉此机会规避一下性生活,没准虫洞都被发明出来了。所以我应该汲取他俩的教训,为了我国严肃文学的未来,多搞旅游实践。
我听从了他的规劝,在过去数年里去了很多地方,发现朋友诚不我欺。有些认知,光靠在家搞思想实验还真搞不出来,试举几例:
一、
去年春节我去了越南芽庄,那的大海和越南菜并未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唯一铭记的是越南的通货问题。我在去越南前兑换货币时就发现,越南盾的面额大得惊人,随随便便兑了点就成了亿万富翁。我查了查资料,1985年越南盾和美元的汇率还是1比200,而后越南政府主动搞了一次货币改革,1年后这个汇率就变成了1比3700,而现在的汇率是1比22700.

这也就不到1美元
![]()
我很不解越南政府此举意欲何为,有人说是东南亚金融危机引起。但一来该危机始于1997年,比大贬值晚了整整一轮,二来越南并非东南亚的重要经济体,在80年代也没有搞市场经济,把锅扣在金融危机上并不妥。越南政府到底为何要在80年代末主动进行货币贬值?
唯一能和这个时间段联系起来的越南政事,是我国对越自卫反击战的全面胜利,可越南人把自己搞得通货膨胀、民不聊生,和战略战术也不大联系得起来。
在芽庄的一次出租车之行中,我洞悉了秘密所在。由于钞票面值巨大,越南的出租车计价器是无法显示车费的全部数位的,它会省掉3个0,比如在计价器上显示的是100,我实际应该支付100000(十万)盾。可我急着下车,一不小心就多算了一个0,付给了司机一百万盾,回到酒店我才觉得不对,心算了一下汇率,这可是275人民币,我才反应过来,我多给人家加了一个零,把车费打了个一百折。
这就是越南大搞通胀的秘密所在!越南政府知道未来中国人是越南旅游的最大消费群体,所以宁愿把自己搞得病入膏肓,也要让中国人掉点肉。他们通过货币贬值,间接导致我这种粗枝大叶的中国人算错数位,损失钱财,虽然这点钱不算什么,但是越共可是我国培训出来的,深谙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道理。就像当年搞胡志明小道,用牛车拉装备打美国人一样,现在的越南用出租车计价器打货币战争,意图搞垮我国实体经济,实在是苦心孤诣。
二、
去年圣诞我去了新西兰。大多数外国人对于新西兰的印象,停留在《魔戒》里壮阔的美景和毛利战舞,总的来说,这是一个神秘的国度。在去程之前我同样做了一番调研,新西兰是一个农业国,主要产业是农产品出口和加工,几乎没有工业,所以环境好得发指,可就这样它仍然跻身于全世界最发达国家的行列,其中的奥妙值得探究。
我住在奥克兰的朋友家中,在第一次去洗手间前朋友拦住我,神情恳切地告知厕所里有一只庞大的蜘蛛,当时那一幕让我似曾相识,就是想不起在哪见过。后来才回忆起是在水浒传里,武松去景阳冈前酒店小二也曾这样的真诚。我说虽然我有点怕大蜘蛛,但不能因蛛废尿,于是大义凛然地推开了洗手间大门。他们的洗手间里真的有一只长脚蜘蛛,腿完全张开比成年男子手掌还大,我战战兢兢地尿完,出去质问我朋友,为何这样懒惰,连只蜘蛛都懒得清理。朋友说你有所不知,新西兰环保好,各种昆虫和小动物无孔不入,他经常正专心致志的小便,突然一只螳螂挥舞着镰刀朝他扑来,吓得他好几次差点缩阳。后来这只大蜘蛛来了,成为他家厕所的顶级掠食者,一切昆虫和小动物灰飞烟灭。只要人和蜘蛛互相尊重,上厕所时也乐得清静。
“感情这只蜘蛛是你们养在厕所里的。”
“这就是新西兰人的理念,以夷制夷。”
之后在南岛自驾,我们开车穿梭在广袤无边的草原、田野和丘陵,蓝天白云、羊驼和薰衣草让旅途宛如漫画。但最让我感兴趣的是新西兰的农田,高度的自动化耕种使我没看见一个农民,我猜他们正在家里喝啤酒玩王者荣耀。而农田与农田之间存在着这样一种东西,见下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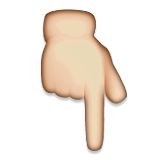 :
:

或者是栽种浓密的树群,其树大概有3层楼那么高。


我很是纳闷,如果只作分隔之用,那么一般的栅栏就足够了,为何要修建如此宏大的工程,搞得漫山遍野都是。我问我朋友,他说他也不知道,只知道这是新西兰政府的强制要求。
我想起了挪威的高压电线传说,说挪威的深山里架设着密密麻麻的高压线,而那里压根是无人区,没有用电需求。据传是山里生活着政府制造出来的巨人,高压电线是做隔离之用,免得巨人跑到城镇里去。
联想到我在新西兰农田里看到的火烈鸟尸体,这明显不是被汽车碰撞所致。

我回溯了一下新西兰的历史。这里曾经活跃着一种叫恐鸟的顶级掠食者,身高超过3米,它灭绝于19世纪,即是欧洲殖民者到达新西兰之后。欧洲人把恐鸟肉当做珍馐,大肆捕杀,导致曾经横行于新西兰的恐鸟在100年内消失于世。

两百年来,新西兰南岛一直流传着恐鸟并未绝种的传说,当然政府历来都是一口否认。
我想,这9米高的大栅栏一定就是用来防恐鸟的,同时也是在保护恐鸟,它们一旦和人类相遇,可能会互相把对方吓死。
政府选择保守这个秘密,一定是为了避免重蹈当年的覆辙,毕竟,除了欧洲殖民者,现在岛上还多了10%的史上最强掠食者:华人。有些事,还是让它成为大自然永远的秘密比较好。
怪不得新西兰的农民那么少,在城市之外,恐鸟才是真正的主人,一如200年以前的每一个日夜。
三、
通过旅游,我还治愈了自己的心魔。
众所周知,我总是为自己发际线日益增高而困扰,好好的一个肌肉帅气小伙,健身的时候总是不停照镜子,看看汗水有没有黏住头发,使得发际线暴露。一旦街上刮起大风,我更是狂怒不已,觉得这是生活在和我过不去。
正是通过去荷兰旅游,治愈了我的这个心魔。

2015年我去阿姆斯特丹休年假,主要是为了去买巧克力。众所周知,阿姆斯特丹有着全世界最好的巧克力,我当时的女朋友患有低血糖,所以巧克力就成了她的刚需,随身携带,类似于心脏病人随身携带速效救心丸。我去阿姆斯特丹就是专门去给她买巧克力的,没有别的想法。
我是跟我的朋友王睿一起去的,众所周知,他们这种搞金融的对未知事物总是抱有强烈的好奇心,所以我也被迫陪他去看了live show, 甚至逛了红灯区,但绝对只是逛逛,没进去。
当然阿姆斯特丹不是只有红灯区,我还去了梵高美术馆,去看他画的麦田、农民、皮靴、老妇,以及那些绚丽诡异的向日葵和星空(进去后才知道《星空》是在美国,大失所望)。一大早美术馆门口就排起了长队,经常有我国中年男性路过,看见排队就凑过来问我,怎么一大早就有live show了?这家店的主题是啥?
我说梵高。然后他们就摇摇头走了,脸上的神情写满了“我裤子都脱了你给我看这个”。这时我和王睿都很失望,心想怪不得我国资本市场不行,旅行消费映射出的本质是投资选择,简直不成体统,怪不得A股那么糟。
在阿姆斯特丹的最后一天,我去了阿姆斯特丹最古老的天主教教堂Oude Kerk,当时在出租车上,王睿跟白发苍苍的司机说去看Oude Kerk,司机当场就开始解皮带,被我摁住了,还差点报警。后来王睿反思了一下自己的发音,才明白是错怪了司机。司机应该是听成了Old cock.
之所以要去Old cock教堂,是因为这教堂坐落在阿姆斯特丹的红灯区,它700年前就建好了,而红灯区的形成也是在那个时候,因为这里靠近港口,水手们有这方面的刚需,就像我当时的女友需要巧克力。

Old cock的尖塔被低矮的民居和莺歌燕舞的玻璃橱窗环绕着,似乎是一个老去的巨人,沉默地注视着脚下的一切。教堂门口居然有两个袒胸露乳的女性雕像,一看就是性工作者。雕像双手叉腰,显得理直气壮,我问王睿,她那大义凛然的表情是啥意思?王睿分析,她应该是在和人还价,估计还是和一个中国人,你看她手上那像纸的东西,应该是发票。
进入教堂,弧形的木质拱顶就像帆船,一下就把我们的思绪拉回了大航海时代,我想起《白鲸记》里那段出海前的教堂祷告,疲惫的水手们需要神谕赋予自己勇气,来对抗对于深海和怪兽的恐惧。而此刻在教堂里祷告的人们同样神情倦怠,他们也才从战场上下来,刚做完激烈的对抗。
我来到一个深褐色樟木制成的告解室,这是天主教的传统项目:忏悔。你在告解室的这头,牧师在那头,你忏悔,牧师听。大多数时候牧师不会说话,但有的牧师风格比较激进,他不但会和你交流,还会diss你。
Old cock告解室的牧师就是这样的风格。他是个冷峻高大的中年男人,长得就像这座教堂本身。我一走进去,他就主动问我今天去嫖了哪国的性工作者,后悔的点在哪里?我说我没有去嫖啊,他说没有嫖来忏悔干嘛,这里99%的忏悔者都是嫖客,嫖完后利用贤者时间来忏悔,尤以你们中国人居多。很多中国人忏悔的是选的性工作者不够漂亮,自己还是不够沉稳,没有货比三家。他以为我也是来忏悔这个的。
我说不是!我没有嫖!而且就算嫖了,我这人的性格很绝,绝对不会后悔选错了,大不了去重嫖一次。
牧师对我的处世观交口称赞,不过他还是不信我没去嫖,他说那你来阿姆斯特丹干嘛?我说我是来买巧克力的。牧师让我滚,说在上帝面前撒谎是大恶,心不诚就不要来忏悔。
我说真的是买巧克力,并把女朋友的病历递给他看,他才相信了我。说请开始你的忏悔。
我说我没啥可忏悔的,我主要是来和你进行学术探讨。他问我探讨啥,我说探讨一下阿姆斯特丹。我一直想不明白,为什么这个天主教国家会有如此堕落的首都,为什么Old cock会坐落在红灯区的腹地?
牧师说,你知道堕天使吗?也就是撒旦。堕天使的身份是一个诱惑者,在伊甸园中他诱惑亚当夏娃吃下禁果,从而导致他们被上帝放逐。但是,上帝全知全能,他是知道堕天使的行为的,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是希望通过堕天使的诱惑去考验人类的信仰。
“所以没有堕天使,亚当夏娃就不会被放逐到人间,也就是说,上帝创造堕天使,其实是为了创造人世?”
“可以这么理解。”
“可这和阿姆斯特丹有什么关系?”
“红灯区的建成最初是为了水手的刚需,他们需要先堕落,再去对抗海里的恶魔。大航海时代结束后,来到阿姆斯特丹搞对抗的人不降反增,可见人们的心魔远比海怪更多。”
“原来人们来阿姆斯特丹是为了对抗心魔。”
“阿姆斯特丹就是欧洲的堕天使,它集中了整个欧洲的美,又集中了整个欧洲的堕落。白天的阿姆斯特丹是郁金香、阳光和湛蓝的天空,以及梵高、高更和毕加索,还有你女朋友需要的Puccini Bomboni巧克力。但入夜后就是堕落者的天堂,来自五湖四海的年轻人等不到太阳落山就开始抽大麻,然后去看live show, 最后找个橱窗女郎搞对抗。全欧洲找不到另外一个城市像阿姆斯特丹一样,把天使和恶魔结合得那么好,它就是欧洲的撒旦。”
“而按照您刚才的意思,撒旦是上帝默许存在的?”
“是的,阿姆斯特丹集中了整个欧洲的堕落。堕落的人来这里自我放逐,流连忘返。他们就像大航海时代的水手一样,没有家,没有归宿,没有灵魂。而红灯区的霓虹就是是堕落者的灯塔,指引他们穿过迷雾来到这里。上帝建造了阿姆斯特丹,让它像撒旦一样用美丽去吸引人类,再用堕落去测试他们的信仰。”
“就像上帝创造堕天使,是为了让他背负整个天堂的恶?”
“是的,但真正有信仰的人,比如我,就绝对不会被堕天使的禁果所吸引。上帝是看得见的。”牧师自豪地说,“年轻人,你有信仰吗?”
“有,我的信仰是自然科学。自然科学告诉我巧克力可以治疗低血糖,所以我来到了这里。”我亦骄傲地回答,“可据我所知,撒旦在世界末日被上帝投入了火狱,承受永恒的灼烧之苦。那阿姆斯特丹的结局会怎样?”
“那是审判日的事了,在审判日到来之前的最后一秒,阿姆斯特丹会继续歇斯底里地堕落。但是,只要你在最后一秒钟之前忏悔了,你仍然有希望获得救赎。我们为什么要在红灯区里建设教堂,就是相信那些堕落的人总有一天会来的。他们来这里忏悔,然后得到救赎,找到归宿,从而离开,并且永远不会再回到阿姆斯特丹。审判日里,阿姆斯特丹会遭天火之焚,但是被救赎的人已经不在。”
“我们中国曾经也有自己的阿姆斯特丹,坐落在广东的某地级市,但还没到世界末日就被政府取缔了,因为我们中国人只相信现世,不相信来生和末日。”我若有所思地自言自语,“如果我有一杯酒,此刻我会敬伟大的阿姆斯特丹。”
“也敬广东的某地级市。”牧师举起水杯回敬。
从告解室出来,我觉得自己把生活看穿了。我不再鄙夷周围的红灯区,也终于明白了为啥教堂门口要摆设性工作者的雕像。王睿问我都跟牧师忏悔啥了,我把牧师的话给他简单复述了一遍。我说阿姆斯特丹集中了整个天主教世界的堕落,实则是在测试人们的信仰。
王睿想了半天说明白了,原来上帝建造阿姆斯特丹是在搞钓鱼执法。
我说,也可以这么理解。
阿姆斯特丹之行让我收获匪浅,我不仅堪透了宗教和城市规划问题,还堪透了发际线问题。
我们都知道,很多男人成年后会脱发,是因为睾酮随着血液循环到达毛囊中的毛球细胞,而细胞中的5α-还原酶会和睾酮反应生成双氢睾酮,对细胞的代谢系统产生作用,导致毛发生长期缩短、提前进入休止期,还没发育成熟就掉了。
而带有“脱发基因”的人,头部某些部位毛囊细胞上的双氢睾酮受体活性过高,极易与双氢睾酮结合,前额就是这样的部位,所以发际线处最容易脱发。
所以,睾酮分泌多的人,会胡须浓密、腿毛旺盛,全身只有发际线处的毛发会稀疏,这种看似矛盾的现象就是因为发际线集中了全身所有的双氢睾酮受体。
就像阿姆斯特丹集中了整个欧洲的堕落。
所以发际线就是阿姆斯特丹,就是堕天使撒旦,就是广东某地级市。它是伟大的,是上帝的安排。发际线高的人内心纯洁高尚,因为所有的堕落都被他的发际线一己承担,虽万千人吾往矣。
想到这里我不禁热泪盈眶,我们的发际线就像萧峰一样,对着漫山遍野的双氢睾酮怒吼,你们一起上吧,我萧某何惧。
从那以后,我再也不为自己的发际线高而纠结,也打消了去植发的念头, I’m the chosen one.业已得到了救赎。
当然同时女朋友也没了,我在阿姆斯特丹忘了给她买巧克力,回中国她就跟我分了,她一口咬定我是在阿姆斯特丹搞对抗,把巧克力给忘了。
以上就是我在阿姆斯特丹的旅行收获:战胜了心魔以及丢掉了对象,算是扯了个平,这就是生活。
四、
前文里提到过爱因斯坦是我的偶像,我曾经致力于模仿他的思维方式和科研方法-思想实验。那么本文就以我去爱因斯坦故居的旅行作为结束吧。
2012年,我去了瑞士,此行是奔着爱因斯坦去的,110年前,他在伯尔尼专利局当一名专利鉴定员,业余时间研究物理学。这和我有点像,只不过我的主业是金融,业余时间搞搞文学创作,当然我还没得诺贝尔奖,所以爱因斯坦是我偶像,而我不是他偶像。
步出苏黎世机场---我去到过的最混乱的机场,堪比《仙剑奇侠传》里的迷宫,我直奔火车站而去,火车站对面就是著名的班霍夫大街,和纽约的第五大道齐名,被称为世上最富有的街道,满眼望去全是银行,据说马桶都是黄金做的。可我无暇一顾,因为在我看来伯尔尼的克拉姆大街47号是一个更富裕的地方,一个世纪前爱因斯坦在这里发明了质能公式,这个式子能让一公斤的鹅卵石变得比全世界的黄金加起来都有价值。
我在火车上还没来得及睡着就到了伯尔尼。果然没让我失望,澄净的阿勒河、一碧如洗的蓝天和远处白雪皑皑的阿尔卑斯山交融在一起。城市雅致静谧,像一个老派绅士。阳光穿过满城的喷泉,将方砖路面辉映得波光粼粼。我来到了克拉姆大街,这条被歌德称颂为伯尔尼最美丽的街道,从头走到尾也没有看见爱因斯坦故居,倒回去才发现是走过了。门脸实在是不起眼,德文的EINSTEIN-HAUS竟然被我无视,还有上方那毛毛虫一般的手写体:E=mc^2.


这不起眼的宅子里唯一的工作人员是一名老太太,她叫伊娜。脸上的皱纹看起来让我觉得她是爱因斯坦的同龄人。她友好地为我打开大门,示意我可以拍照。我却在进屋的一瞬感到一种强烈的窒息感,就像穿越了时空之门,来到了理论物理学那最美好的年代。整间屋里只有我一名游客,安静得吓人。事实上,爱因斯坦终其一生都是在这样的静谧中度过,无论是他的生活还是他的心灵。不过在1905年的伯尔尼,这间略显寒酸迫仄的小屋里却是暗流涌动,整座经典物理学的大厦在这里被爱因斯坦用钢笔一点一点敲成了碎块,那年他26岁,正是我当时的年龄。
室内的墙上挂满了爱因斯坦和爱人在不同时期的照片,鲜花摆满每个角落,给古朴的单色调家具平添了几分亮色。这一切都是如此地简单和具有美感。事实上,爱因斯坦与众不同的天赋就在于他直觉里对简洁的美的敏锐和追求,他说,“我想知道上帝是如何创造这个世界的。对这个或那个现象、这个或那个元素的能谱我并不感兴趣。我想知道的是他的思想,其他的都只是细节问题。” 他评价一个理论美不美的标准是原理上的简单性。他毕生的最大成就“广义相对论”用几何语言写就,将时间和空间统一在一起,这种极简主义的形式充满了令人叹为观止的数学美感。人们惊叹于爱因斯坦在没有任何理论实验的支撑下,用纸笔就创造出不可思议的理论。而事实上,思想实验在他的大脑里无时无刻不在进行。比如狭义相对论的创立就源于他关于“人和光线赛跑会看见什么”这一设想的不倦钻研。而广义相对论将引力创造性地解读为空间的弯曲,更是来自他在专利局上班时的突发奇想:要是自己从椅子上跌落,在那一瞬间自己是没有重量的。
这一切使得爱因斯坦的生活充满了画面感---他本来就长得像从童话故事里走出来的人物。我想象着他在专利局日复一日鉴定着各种民间科学家荒诞不经的小发明的间隙,如何偷偷摸摸从抽屉里拿出自己的稿纸,像小学生作弊似的看上一眼,然后合上抽屉开始漫长的思考。----他称之为在和上帝交流。对爱因斯坦来说,专利局就是他的“世俗修道院”,“一个离他最近的地球上的天堂”。在这天堂里只有他和上帝,彼此交换着宇宙最深刻的秘密。
事实上,爱因斯坦没有获得自己最渴求的秘密。他人生的最后30年苦苦追寻着统一场论这一终极理论,试图将所有的物理定律统一在同一个公式里。但这一次他失败了,甚至被人讽刺说,哪怕1925年后爱因斯坦改行去钓鱼,也不会对物理学有丝毫损失。不仅仅是统一场论的难产,和量子力学哥本哈根学派的争论也以爱因斯坦的失败而告终。他去世前跟美国医院的护士说了一句德语,这成为了爱因斯坦最后的秘密。也许他是在说“上帝终究还是不会掷骰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