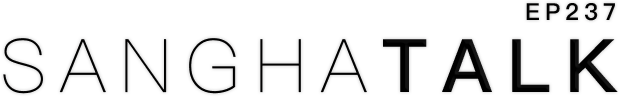
|
DEC. 14
2017|
日居月诸,照临下土;
日居月诸,东方自出。
正 文
当太阳满含慈心缓缓普临大地的那一刻,暖风扬起的一丝慰藉浸满全身。路与路总是要交织在一起,人与人总是要有这般或那般的因缘。在孤立无援之时,那脚下的路,那千丝万缕的因缘,总能留下如海般沉静的抚慰。
曾也唱叹过山川青空、蝉鸣鸟语的悠静,缘真愿亦实。踏步于原始森林,茂密翠林,屹之耸之,附和清脆鸟语,嬉唱喳喳,卸下等待。江流河湖的那边,我寻觅已久的钟鼓之音,早已在等待。

如海浪般涛涛涌动的心,填补在这一条条非黑即白的长旋街道。阴晴不定的天气,似乎总在昭示着人世无常,“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一场圆环般的缘分,附之特殊的征兆,离却不失悲情,合则与聚相欣。《楞严经》里“我今示汝兜罗绵手,汝眼见时,心分别否?”深刻阐释着佛陀那双教化众生的手,佛陀的手,菩萨的手,师父的手,那是怎样累生的修行?心手相连,犹如力量的重生,告之谛理,示之非相,亦着,亦不着。
又一次与师重逢,虽近一年未谋面,但一切恍如昨日。
一年,师经历了些什么?古语有云“士别三日刮目相看”,月色仍旧,长空忽放慈音,不变中的无常,竟回忆起往昔感人的对话。这场从西南跨向东南的漫漫长路,我的手机铃声不时总会响起。

“你们到了没?到了我接你们。”
“哦,师父,还没到呢。”
“嗯,好,路上照顾好自己。”
“嗯!放心吧师父!”
心喻慈海,无微不至,直至安全抵达。
都言高山难攀,原来也不过尔尔,雾气缭绕,云翻云涌的青空,荡漾在来时路上的点点滴滴。清一色的灰白棕褐墙,古色古香,或有儿童嬉戏打闹于朱红古阶梯,邻里间的饭后余谈,那些挂满笑容的齐声礼敬,仿佛已成一番独特的风景。家家户户门立相对,好似要一直以这番姿态绵延下去。偶立一方眺望,此地的清净之韵无需刻意显露,仅是门内那幅低眉舜目、面如满月的观音圣像就如此引人眼球,传递着何为善之源。

“这片村子叫观音阁村,家家户户笃信佛教,邻里往来犹其和睦。”
侧耳倾听着师父的介绍,思维着“信、愿、行”的真谛,驻足于东华山之簏的佛音,怕是已绵延数千年了。祈伸开慈愿的手,盼接引……
一颗慈心能融化僵硬的冷漠,拨开乌云,照亮心房的不只是太阳,还有那双抽取覆盖真相的布的手。我怕自己唐突,更怕打扰这惯常的纯净,所以谨言慎行,但师父那至始至终的慈悲终于让我感动地有些“造次”。

“都给你们安排好了,有什么需要的尽管说。”
话语虽然简单明了,却柔成一片清水,沁人心扉。正当吃完晚餐,偶然间和几位这里的居士闲聊。
“师父特别慈悲,那时候他一个人来到这里,日子可苦了,什么都是一个人,但他都毫无怨言,待每位居士及其和蔼,几乎是无微不至…”
“我们有这个师父在这里真是我们的福气!”
师父得有多大坚韧的力量,才能从苦难挣脱后寻求另一份不知名的解脱,忍人所不能忍,行人所不能行,他完全可以在条件更好的寺院弘法利生,却偏偏选择了这里,不惊不怖不畏,穿行浑噩的幽梦。那份广大的慈心所化的我相、人相、众生相令人泪眼朦胧。

师徒之缘,该是如斯,师若水,徒似茶。茶需要合适的水,它可能是稍温的,又可能是滚烫的,上善若水,利万物而不争。而茶之奉献就在那供奉给众人的醇香之中,芳香四溢,而终“化作春泥更护花”。水轻触于茶身,如如不动,一支嫩芽忽之浸润在水的柔怀中荡漾徘徊,似屈似伸,蜷缩的身体不再彳亍,清水倾洒,悄无声息地带走了它所有的固执与疑惑,从而不惊、不怖、不惧、不畏,光明体性油然而生。
茶透禅心,归兮将至,拈一支清香,在净如琉璃的呼唤中默默祈祷,旋回婉转,卷入长空,寂静寥寥。
问:归去当如何?
答:澈月常随之。

我在看不见空气的烟尘中四处流浪,遥看残垣断壁,与月作伴的路,似乎遥不可及。
师父缓缓拿起茶杯,茶具之形若月捧怀,诠释法身,或青或白,或紫砂或琉璃:“八万四千,总有一段专属于你的征途。
”
|愿 吉 祥|
SANGHATALK 2017
抠鼻屎也是表法?
当我脱了这身衣服还剩下什么?
·
那些令人尴尬又搞笑的法名
·
· 一位当代学佛大师的自白 ·
|
找不二
|
投投稿
|
字太小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