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
杜拉斯诞辰110周年。
杜拉斯一生
共创作出50多部小说、剧本。
其中,她
最负盛名的作品《情人》,
写于她70岁时,讲述了一个贫穷的十五岁法国少女和二十七岁中国富少的故事。
而这个故事,颇具自传色彩:杜拉斯年少时生活在西贡等地,她在这片热带土地上确实邂逅过一位中国情人。
这部轰动文坛的小说,在改编为电影《情人》后,同样轰动影界。
然而,杜拉斯,这位爱情故事的拥有者,
却对电影的改编并不满意。
在电影拍摄时,杜拉斯时刻在和导演
雅克·阿诺相爱相杀,
她甚至
天天都在批评拍摄脚本是“垃圾”。
杜拉斯的许多作品都曾被改编为电影,随着时间流逝,杜拉斯公开表达对这些影片的不满:
“我之所以产生了拍电影的念头,是
因为那些根据我的小说拍成的电影,简直让我无法忍受
。”
于是,在写作生涯中杜拉斯中途有10年的停歇,不再写书。1965年之后,她
转身
专注于另一件事——拍电影
。
她尝试了所有的调子
:传统叙事型的,颂歌式的,实验电影,创造性的纪录片,哲学对话式的,喜剧电影,甚至还拍过没有画面的电影,只有声音、文本和黑色,黑色。
显然,杜拉斯的电影是小众的,总有人试图评判作为一个电影人的杜拉斯是“成功”还是“失败”的。
然而,杜拉斯总会给出一个“杜拉斯式”的回答:
“失败就等于选择的自由。”
在她的戏剧被评论炮轰,在观众看她的电影《大西洋人》后说想要“掐死电影人玛格丽特·杜拉斯”时,杜拉斯说:
“我很偏激,但这使我快乐,应该偏激”。
杜拉斯,不仅是文学史上的超级偶像,
也是一位出色但被低估才华的导演。

杜拉斯在片场
中信出版最近的
新书《迷途:杜拉斯谈电影》
首次汇集了杜拉斯以《印度之歌》为代表的
14部电影手记、访谈录及3篇随笔
。此前,
这些文稿和访谈录难以获取,也从未发表和出版。
《迷途:杜拉斯谈电影》
点击书封,一键下单
《迷途:杜拉斯谈电影》
[法] 玛格丽特·杜拉斯 著
[法] 弗朗索瓦·博维耶/[法] 塞尔日·玛热尔 编
袁筱一/袁丝雨 译
中信大方×雅众文化 2024年5月
——您为什么要拍电影?
——我喜欢电影,很喜欢。
杜拉斯一如既往用破碎、绝望但炽热的语言,展现了在电影拍摄的当时当刻,对世界、电影和写作的艺术思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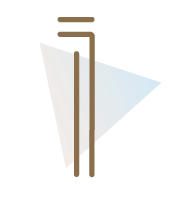
作为法国电影“左岸派”代表,杜拉斯将“反传统”体现得淋漓尽致。“左岸派”特点是将有逻辑性的线性叙事打破,转变为了错综复杂的心理时间—
—这注定了杜拉斯的电影不可能成为大众、商业的电影。
杜拉斯的
《印度之歌》
是其作为导演最为声名显赫的一部。这一部明显受到阿伦·雷乃和阿兰·罗布-格里耶的《去年在马里昂巴德》的影响,是一部阴森甚至有些激进的影片,完美体现了她对电影传统的颠覆。
影片以梦幻般的镜头展开,同时,
还有杜拉斯对电影声音的颠覆
——在她的电影中,
对白被配乐取代
,演员们在对话时只是互相凝视
,或者辅以大量的旁白。消失的声音成为一种幽灵般的存在,它同时存在于过去和现在时态中,衍生一种孤独。

《印度之歌》剧照
《大西洋人》中,
更是大胆地用了大量的黑色镜头,杜拉斯认为影片中的黑色是“倾听之所”
,这确实在当时(甚至在现在也会)让不少观众震惊,“直到电影结束,人们依然坐在位子上”。
杜拉斯希望自己的电影被更多人接受,但是她依然也很清楚自己的观众定位:
我没有大众观众。
大众是一种社会组织,甚至是一种阶级组织,他们是在被美化的和虚假的情境下被培养出来的群体,例如工人、学生和读者。谁是好人?谁会死?谁会杀人?谁会去爱?它是否有一个好的结局?诸如此类。但是对电影真正的观点,超越这些次要情节的观点,会晚一些才产生。而对我来说,这段时间才是真正重要的。
当我在拍摄一部电影时,我会陷入一种激情带来的精神危机中,我并不考虑观众。
在电影剪辑的过程中亦是如此,但那时我并没有将观众视作某种阶级现象,我将他们看作独立的个体。
 《大西洋人》剧照
《大西洋人》剧照

客观记录与文学呓语
《迷途:杜拉斯谈电影》中收有杜拉斯的拍摄手记和访谈。在此之前,这些手记散落在各个档案馆和基金会资料中,难以搜集和获取。
这些文章,大部分是杜拉斯在拍摄电影时的想法,这些本应该是客观冷静的记录内容,在她的笔下,
出乎意料地展现为一些梦幻般的呓语
。她几乎用尽所有可以表达的途径和体裁,
以相当具有文学性的方式记录下来
,用一些细细碎碎的语言呈现当时的心理:
一切,凝固。没有什么比死亡更凝固了。
布景化为石头。一切停滞在动作的瞬间。
庞贝。
你在空间里、剧院里失去的东西,将在混乱中追回,将在成堆的杂物中、在嘈杂的声音中萦回。《印度之歌》正诞生于这种混杂。
仿佛没有陈设布景。仿佛一切都未经策划。
没有界线。
自人群中行动,自满溢中行动。
这些像散文又像诗的语言,只是出现在她的戏剧布景笔记当中,她将一些冰冷的记录性文字切碎、打乱,又用自己独特的语言韵律组合起来。
如果那时流行MBTI,杜拉斯大概率是ISFP,
热情、容易共情,极富想象力
,并能将她的内心以令人赞叹的方式呈现出来。她常常有一些新奇的句式,“大使馆是一艘进了水的船”“我们相信,我们不再相信任何东西”,甚至电影名字“她在威尼斯时的名字在荒凉的加尔各答”,这些陌生化的排列,让人感觉身体某处的破裂,再一次对杜拉斯而感喟。
在文字中,常常能感受到杜拉斯语言的爆发力,她那样绝望、痛苦而撕裂的爱。是的,她仿佛不能爱就会死,像一位战士,常常寻找勇气,寻找战场,只有疯狂地攫取爱才能活下去。
(插播一条:杜拉斯是白羊座。)

杜拉斯肖像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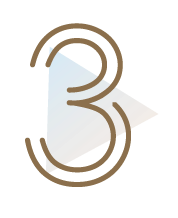
杜拉斯与电影
作为写作者,杜拉斯认为电影:“它永远无法取代文本。然而它仍然试图去替代文本。唯有文本才是图像的无限载体,电影对此心知肚明。”
她也说过:“
我拍电影是为了消磨时间。
如果我有魄力什么事也不干,那么我就会不干任何事。正是因为我没有勇气无所事事,我才选择拍电影。这就是唯一的原因。以上是我对我的事业所能做出的最真实的评价。”
可别认为杜拉斯是高屋建瓴,
她常常也为现实的电影投资而感到发愁
:
“那时的巴黎热得可怕,八月份,那是八月份。
我为了钱的事格外发愁
。即使在工作中,也依旧忧心此事:该怎么挨过这个冬天,靠什么过活?我恨那些不给我钱的人。
从1969年开始,我就在无偿拍电影,没有一分钱报酬
。我马上就会谈起这部电影,请别不耐烦,且让我倾吐我的窘迫,倒尽这些无谓的苦水。我恨金钱。”
杜拉斯讨厌别人改编她的电影,对这些改编作品,她往往都不满意
。有人问她,是否有对她的作品改编留下了好的回忆,她答:《广岛之恋》,阿伦·雷乃非常好。杜拉斯如此挑剔、毒舌,但对雷乃和与其合作的电影是例外,那是她相当愉快的回忆。
由于杜拉斯所导演的电影,大部分都是由自己的作品改编,有记者问她,是否会改编经典作品,杜拉斯答,“对于经典作品,我们可以试着做实验电影,但不能做成商业电影。我最恐怖的记忆之一就是《危险的关系》的电影。放映完之后,我简直想吐。”杜拉斯就是如此,聪明、偏执、毒舌。
杜拉斯一如既往的热情,也体现在电影拍摄中,她被迫一次次与电影分别,被迫一次次割舍:
在《印度之歌》的拍摄后,我感觉自己要死了。我不知道自己那时染上了什么病。我不知道工作结束之后发生了什么,那种黑暗中的崩溃。我不知道是什么造成了这种恐慌。
我想这是因为被迫与电影分离,不是吗?就像被迫与恋人、与爱情分离一样
。
我无法从《毁灭,她说。》中走出来。我以为拍完电影我能走出来,可我发现我没能做到。这对我来说还是第一次。我几乎什么也没写,而且也读不了书。
她对电影有着恋物般的情感。有人问杜拉斯,为什么要拍电影?
杜拉斯简单而热烈地回答——我喜欢电影,很喜欢。
她在《卡车》手记里夹带私货地写道:“她所注视着的世界令我目眩神迷——那是电影。”

杜拉斯在片场
今年是杜拉斯诞辰110周年。110年以后的今天,我们再次看到她的电影时,还是会感到震撼。
1995年,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杜拉斯写下:“我想一切都结束了。我的生命结束了。我什么都不是了。我已变得面目全非。我正在崩溃。快来吧。我不再有一张嘴,不再有一张脸。”
她一生有爱,有写作,有电影
,她是电影界最精明、最安静的激进分子之一,那些战后法国最创新、最感性、最大胆的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