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月
17
日,我写了一篇文章《
服务你的人和修理你的人
》,后台很多人猜测我在影射一场最近热议的集体督导。其实并不是。这场督导我没看,对专业范畴内的交流细节,没资格也不应该议论。
但今天要说的跟这场督导有关。
这场督导之所以在行业内部引发争议,因为有参与者公然通过自媒体,把求助者的信息曝光,并发动全网批判。
这是唯一引发我强烈不适的点
。和督导过程无关。后台说我在含沙射影的,我不妨明言:我不会在公开场合评论一场受保护的工作。而我也无法忍受,这些受到保护的信息可以被街谈巷议,导致一个人被围攻,遭到职业生涯的重挫。
哪怕他在所有「旁观者」眼中,都应该受到惩罚,这种处置仍然冲破了过去的行业底线。
刚看到这件事,震惊之余,我第一时间向督导的主办方求证。我的想法是,如果泄密者及时受到惩处,公开道歉,还可以亡羊补牢。但主办方也办不到,只能发一篇防君子不防小人的声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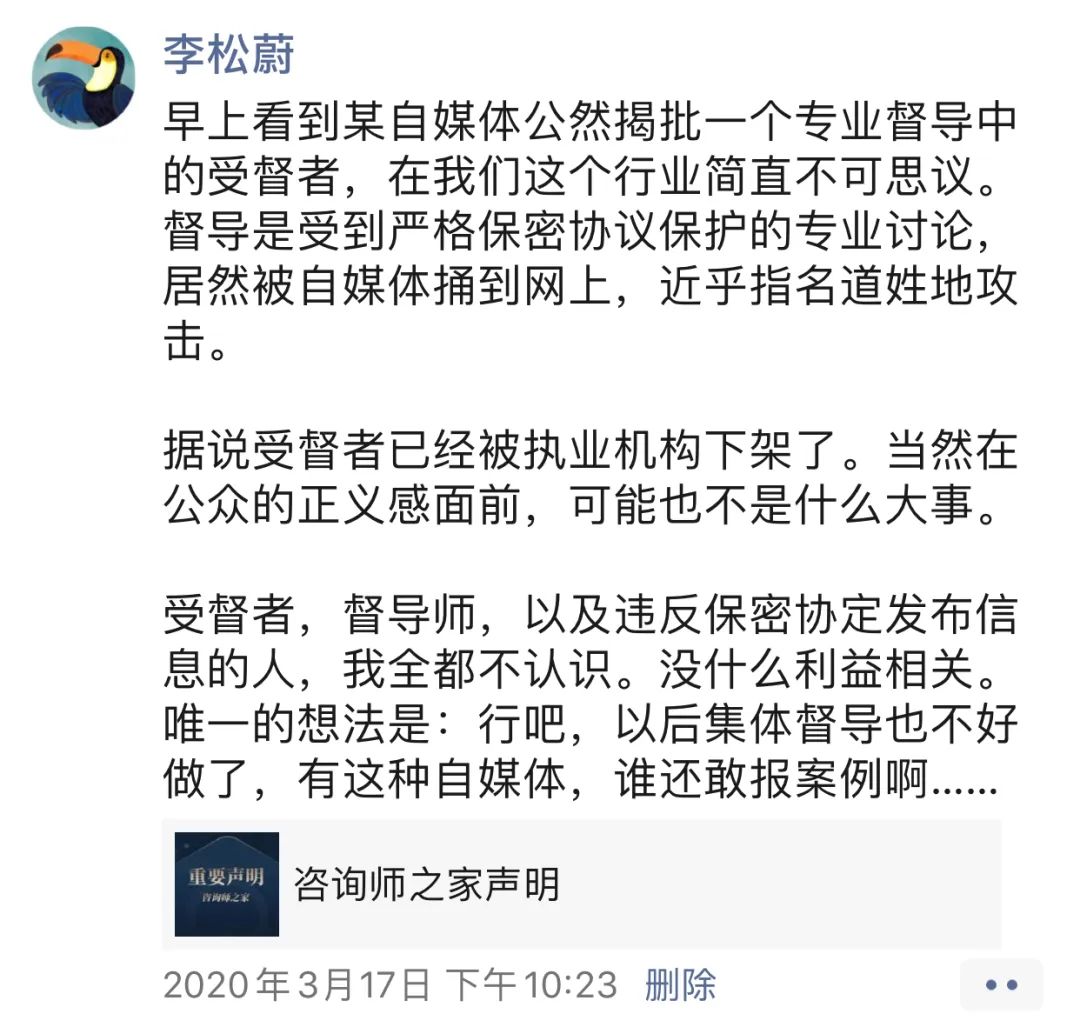
现在我的情绪也平复了。熟悉我的人知道,我平复的方法就是认怂,告诉自己「你喜不喜欢都只能接受」。事实明摆着,有一个人突破保密,就代表信任已经消失了。哪怕其他人还坚持保密,只要其中一个人保留突破的可能,保密就形同虚设。
当然,一对一的工作还是安全的。独立设置下的咨询、督导,只要咨询师或督导师本人承诺保密,这个承诺就有效。这里讨论的是集体的(特别是网络的)工作,包括但不限于网络集体督导、教学用的案例、咨询示教、团体。个体求助者的信息被暴露在多人包括平台面前,等于就是不设防的。
爆料的这家自媒体,后来发了一篇文章解释,最后反将了一军:反正有这么多人看,泄密是免不了的嘛,那是集体工作设置的「结构性风险」。
听听,结构性风险,学习了。
好,现在我承认这个风险了,我要向前走。
2020
年
3
月
17
日,
我把这一天视为集体性的专业工作失去保密设置保护的起点。
我问自己:保密设置的意义是什么?
保密代表了承诺。
我向你承诺这段关系是安全的,你才敢在这里呈现各种想在这里求助的信息。你相信它们不会对你产生边界之外的影响。
心理咨询的求助者,谈论的并不是什么重大机密,但哪怕只是花边小事,仍然需要有承诺的保障,才能畅所欲言。有个创业的朋友,请我给他推荐咨询师,他说最初级的就可以,不用别的,就一条,「嘴要严」。因为创业过程中有很多话,跟投资人不能讲,跟员工不能讲,跟亲人朋友也不能讲。憋得难受,「想找个安全的地方吐吐槽」。
这个承诺,在过去的专业服务中,是被默认的。
默认的意思,就是我们不用说,大家都这样相信。因为相信,才敢在专业设置中暴露自己的弱点。就拿接受督导的人来说,他可能水平很差,犯了很多错,
但他可以不暴露啊
。不暴露永远比暴露安全。除非他相信这段关系是有边界的,才会把这些问题拿出来求助。早知道有可能影响自己丢工作,完全可以藏拙,不让人看出来——就算被推到台前,也可以说些冠冕堂皇的话,这有什么难的。
承诺,会鼓励求助者暴露出有「问题」的信息
(这句话是泛指,我并不知道暴露了什么)。也多少是因为有承诺的存在,问题才有被处理的机会。
这是保密曾经的意义。
如果有需要突破保密的情形,这些例外是需要事先约定清楚的。心理咨询的伦理,严格限定了保密的突破。这是相当敏感的一个议题。比如在咨询中提到重大的人身伤害的风险,咨询师必须突破保密,启动预警。虽然是必须的,但它也是双刃剑。所以需要特别精准的设置:
谁,在达到什么条件的时候,才可以突破保密?
标准越严格越好。
这是中国心理学会的伦理条目:
3.2 心理师应清楚地了解保密原则的应用有其限度,下列情况为保密原则的例外:
(1)心理师发现寻求专业服务者有伤害自身或伤害他人的严重危险;
(2)未成年人等不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受到性侵犯或虐待;
中国心理学会临床与咨询心理学工作伦理守则(第二版)
几种条件,都可以抠字眼,很死板。稍微主观一点的句子,就是「
心理师发现……伤害自身或他人的严重风险
」,这个标准看似掌握在咨询师的手里:什么级别的伤害?多严重才够得上是「严重风险」?但实际操作的时候,有一套约定俗成的评估细则。也就是说,只有在极少主观判断参与的情况下触发条件,保密例外才可以启动。
只要把这些提前约定好,承诺就还是有效的。
但这次的督导事件,暴露了一个新的风气:有人主张把「个人主观判断」作为一个新标准。
意思是,只要有人判断,求助者有可能对别人造成「伤害」,这种情况下就可以突破保密。
3月17号发生的,就是这种情形——
求助者被认定为能力不足,有可能伤害他的来访者。所以,突破保密协定是为了苍生福祉。
写到这里,我仔细想了想。大概我真正震惊的,还不是这一次泄密事件本身,而是这种思维的方式。
过去,因为网上的人多眼杂,偶尔发生专业讨论的外泄,还可以看成一种「事故」,可以通过技术手段防止。而这次的事件和讨论,让我更理解了当下一部分人的心态。我意识到,
突破
保密在这些人看来就是正确,正常,而且符合正义的
。
不知道是不是我的信息选择偏差,但我确实在事后各种渠道的讨论中看到,为数不少的人主张「干嘛要替他保密?这种人以后不知道要害多少人」。
我没办法说谁是对的。他们有强烈的正义感。也许在他们看来,保密是迂腐,是纵容邪恶。一方很难说服另一方。所以我想,我必须做好准备:
如果一部分人就是不认可保密,我能够做什么?
我想,以后我能做的,就是告知。
在集体的,尤其是网络场合,提醒每个参与的人:
你说的每一句话都可能被外传。这里没有承诺,请不要默认这里的每个人都会为你保密。
这话是不是有点吓人?但只能这样。
在我看来,「我认为不会对别人造成伤害的信息,我都会保密」这种话,约等于是「我不会保密」。说得直白点,意思不就是我想保密才保密吗,解释权掌握在我手里:
我相信,大多数人都认为,显而易见,多半,万一……
这些词太玄妙了,谁也摸不透。「万一他以后害人」,怎么才是害人呢?把人逼死才算害人吗,还是让对方哭了就算害人,还是咨询了几十次没效果就算害人?随地吐痰算不算害人?捡到五块钱不上交算不算呢?……
这么说下去像是抬杠了,我打算就此打住。这不是为了说服任何人,只是帮我再次认清这样的现实:
在一个多人参与的设置中,哪怕有一个人相信,自己有道德义务清除那些(他认为的)败类,这个设置就约等于无法提供任何保护性的承诺。
我们必须学会适应,没有承诺的设置。
——这叫什么来着?「结构性的风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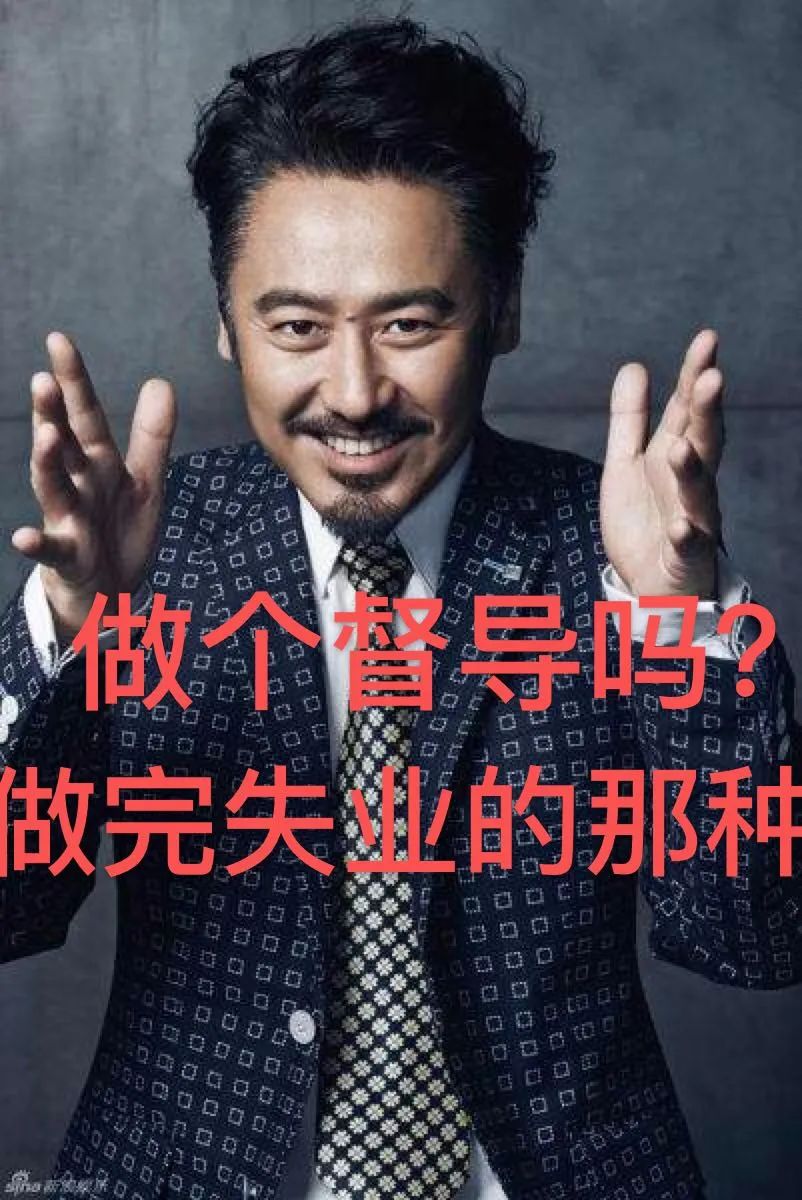
我已经能适应很多事了。我适应了在社交网站要谨慎发言,在自己的朋友圈要谨慎发言,现在我又接受,有他人在场的督导场合,也要谨慎发言。
这也没什么大不了的,适者生存。
写到这里,我又觉得增加了一点力量。我问自己:在集体的设置下,还有可能达成以前那样的保密承诺吗?我现在的想法是,还可以试一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