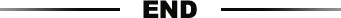一
2017年,我面临就业大关。没考上研究生,家里人的意思很明朗,女孩子,读的又是师范专业,做老师最合适不过。
我的老家是浙江省一座二线城市,基础教育行业比较发达。当老师绕不过去的就是考编制,因为错过了16年年底第一批优秀毕业生直招考试,我只能等三、四月份陆陆续续发布的春招信息。
在这读研无望又降为无业游民的挫折旋涡里,秀秀成了拯救我衰弱神经的唯一稻草。
她当时四处托人在各种教师招聘群里发布代课消息:找小学语文代课教师,两周,薪资丰厚。我恰巧看到了,欣喜若狂,迅速加她微信。几番下来就摸清了门道,秀秀只比我大两岁,在Y区直属的实验小学当了两年语文代课老师,因为Y区四月份有教师编制招聘考试,她想借这半个月时间参加某考编培训机构的考前培训班,临时抱抱佛脚,“考了两次了,这次怎样都得全力以赴。”
照理,Y区我也势在必行。但我没有那么强的危机意识,只是觉着从没教过小学生吧,趁机会试试水也不错。于是很爽快地应承下来。工资每天100元,两周10天1000元,包吃住。
学校位于Y区J镇西南角,周遭的建筑还保留着上世纪90年代城乡结合部的标准风格,白墙黑瓦的低矮平房像哨兵似的顺次整齐排开,这样,倒显得这所小学资本雄厚。
一幢暗黄、红褐双色夹杂的主教学楼拔地而起。春天,主楼两旁柏树郁郁葱葱,守卫着一面顶天立地、迎风招展的五星红旗。校牌和主楼颜色辉映,棕褐色大理石上刻有暗黄楷体校名,两侧是工厂常用的防盗拉锁门,门两侧都有一个保安亭,正面看去,整个校区以红旗为分割线左右对称,有种庄严而压抑的秩序感。
我拿着简历去分管教学的副校长那儿报道,副校长面相宽厚,脸上有风尘仆仆后的疲态。他略微瞟了几眼简历后,目光直直地盯着我,嘴唇微微翕动着。他连续用了三个“不管怎样……你都不能……”句式:“不管怎样,你都不能体罚或变相体罚学生;不管怎样,你都不能用‘神经病’、‘十三点’这样带有侮辱性的词语谩骂学生;不管怎样,你都不能用棍子打学生。”
我愕然,差点没举起右手对天发誓:“校长您放心,不管怎样,我都不会做出此等伤天害理之事。”
从校长办公室出来,我就拖着行李箱直奔四年级语文组办公室。行李箱的轱辘与瓷砖地摩擦发出尖锐的噪音,我嘴上不断说着抱歉,但办公室里的新同事似乎并未注意到我的到来,大家心照不宣地忙着手头的事儿。进门第一个女老师正在高声呵斥一个瑟瑟发抖的小女孩——于是我第一见识到真正的河东狮吼,从旁边经过,我感到耳膜像开了鼓风机似的呼呼作响——你这个猪头,别和我说话,你们班没用了,去死好了!!!
吼完,她顺手把一本作业本扔在小女孩的脸上,“啪”、“啪”,本子弹到地上甩开办公区几米远。女孩子肩膀不停地耸动着,呆站了一会儿,终于在她大喊一句“滚”之后,灰溜溜地捡起本子,像得了残疾似的踉跄着往后退。退出办公室之后,我见她用手抹了把眼泪,小老鼠似的撒腿跑远了。
学文科的到底生性敏感,且总带有某种探案的癖好。经过一上午的细心观察和旁敲侧击,我很顺利地就获取了这间办公室的核心信息。除了80后倪姐和本年级教学组长、90年出生的晴雪外,其他五个90后女孩同我和秀秀一样,都是没编制的代课老师。
她们在这所小学已经至少代了两年课,“没办法,不是应届生,现在很多区考编对往届生要求里都有‘在公办学校有两年及以上工作经历’这么一条。”而在这半个月里,这五个姑娘的主要任务,不是教育教学工作,而是全身心回归高三题海战术,为Y区考编做最后冲刺。
二.
我从我的室友郑敏那儿知道了更多内幕。
郑敏比我大三岁,从浙江省某直属师范院校化学专业毕业后,被父母要求回家考编。奈何科学老师本就僧多粥少,第一年没考进,第二三年哐当哐当就混过去了,现在25岁,依旧是没名没分的代课老师。但郑敏在说起这段“黑历史”时倒是宠辱不惊,“习惯了,就这样过呗。”她把一朵裹着银箔的蓝色妖姬往鼻尖凑了凑,不无骄傲地对我说:“怎么样,挺美吧,我男朋友情人节时送的。”
郑敏的样貌实在乏善可陈,代课老师的工资待遇也差,一个月只有2000出头,一年加上补贴,顶多3万。社会婚配讲究门当户对,我便以单身狗求指教的名义问她,如何钓到一个帅气多金的男朋友。
“哈哈哈哈哈”,她把手里的视频一关,做大姐大的姿势告诉我:“现代社会教师地位多高啊,即便是小学老师都很抢手,我男朋友是做水产生意的,有钱,但文化水平不高,所以我们就看上眼了呗。”
“可代课老师毕竟没有正式老师有身份,你做了三年,不会觉得憋屈吗?”
“憋屈?”她瞥了我一眼,声音陡然提高了八度:“有什么好憋屈的?我今年就结婚了,都不想考编制了,做代课老师多轻松啊,8点下班,4点下班,包吃包住,我又是副课老师,压根不用担什么责任心。”
她突然凑到我面前,压低声音对我耳语:“告诉你个秘密,这所小学有一半以上是代课老师,靠关系就能进来,你以为他们是什么正儿八经的师范专业毕业的吗?屁!”她吞了口口水,继续说:“像我们这样算是专业的了,很多都是二本三本专科毕业生,还教主课呢,谁管啊,没人管!”
“可工资这么低,也难养活自己吧。”
“你傻啊,他们都有副业,炒股票啊,做微商啊,搞代购啊,有些人家里本来就挺有钱,开着保时捷路虎做做代课老师,纯粹为了打发时间。”郑敏像教育弱智小孩儿似的教育我。
我再见到秀秀,是在代课第一周的周六。早上7点左右,Y区职教中心已经涌动着按捺不住的骚乱和恐慌。那日,从早上9点到11点半,下午1点半到4点,短短5小时里要完成本市最大一次教师考编报名工作。
8点左右,职教中心已经人山人海。幼儿园老师在第一楼报名,小学二楼,初中三楼。从二楼往下看,下面密密麻麻里三层外三层,像是一条即将暴毙的贪食蛇。
对很多往届生来讲,这次考编不啻是打翻身仗的良机,因为Y区报名限制少,只要有相关专业的教师资格证,不管本科专业是否对口,都能报名。但奇葩的是,Y区从13年开始,笔试就不再考教育学心理学等学科相关理论,而是完全随机的公务员试题和公共基础知识,这也意味着,在降低专业性门槛,为非师范生增加更多鲤鱼跃龙门机会的同时,也让师范生直升教师的通道变得更加逼仄。
“生死一念间,全凭运气。”秀秀右手拎着装有豆浆和油条的肯德基袋子,左手抱着一叠报名材料,语气里满是哀怨。我宽慰她说面试总看实力,秀秀噗嗤一声笑了:“怎么这么傻,笔试考运气,面试看人脉。况且现在某些培训机构做得那么出色,非师范专业学生集训两礼拜,早就和师范生不相上下了。”
同样的话,从郑敏爸爸嘴里说出来,则更为赤裸裸、血淋淋。
第二周周日晚上,我搭郑敏家的顺风车回校。郑敏爸爸操一口本地口音,脖子上挂着一条很显身份的金项链,一副财大气粗的模样。我屁股没坐热,他就把我家庭底细全打听清楚了。
“Y区水很深的,我去年参加一个饭局。听说凡是进面试的都找了关系。但是面试也要淘汰一半的人啊,所以你猜怎么着……”他卖了个关子,然后自顾自地说:“就是比背景谁厚咯。一个找的是教育局局长,一个只是某某小学的校长,你说招谁?傻子都知道。”
“就像打牌一样的咯。A吃K,K吃Q,一级一级吃下去。”他怕我没听懂,又打了个比方。
“看我们敏敏,考了这么多次连面试都进不了。这一回可得菩萨保佑啊,只要笔试过了,面试我一定找最硬的后台,多少钱无所谓哈哈哈哈哈。”郑敏爸爸的笑声里透着囊中取物的自信。
一下子听到那么多“背景资料”,尽管心里早有准备,但对于涉世未深的小姑娘来说,人情世故关系门户这些东西赤条条地摆在台面上,到底还是有些触目惊心。为了显示诚意,我交换了自己三月份在H区考编又惨遭淘汰这段屈辱经历。
没想到郑敏爸爸听完后不但没有感同身受,反而放开嗓门教训我:“你脑子坏掉了啊,居然没拉关系。现在谁考编不托人啊!多好的机会!”郑敏悄悄拉了拉她爸爸的袖子,他知道说过了,便默不作声了。
下车后,我去后备箱取行李,间隙听到郑敏爸爸压低声音对郑敏说:“敏敏,你找个借口,下礼拜别让她坐我家车了。一看就是家里没钱的。”
但也不是所有人像郑敏那样生来命好,在备考期间还能准点下班、约会、刷视频、睡美容觉。到了晚上11点,主教部分办公室依旧灯火通明。那些白天教书育人、没有社会背景的临时教师像灰姑娘般在夜晚悄然完成了身份转换。不过,送上新衣服、水晶鞋和南瓜马车的善良老婆婆只存在虚构的童话故事里,现实凛冽只能靠赤身肉搏——不停刷令人作呕的试题、背空洞无物的理论、写永远都考不到的教案,一遍一遍在空无一人的教室模拟上课……
她们不眠不休地将智慧和体力消耗在这场对职业生涯毫无帮助的“交谊舞会”上,只为了获得一张能担保一生无虞的“国家结婚证”。
四年级语文组办公室里,最拼命的要数那位河东狮吼的女老师梅倩,和秀秀口中脾气最好的于娟。梅倩在同事面前判若两人,和气内敛,语气轻柔,她一边喝急支糖浆,一边勤勉应付着三本均厚20厘米、红色封皮的公务员考试试题。她最近咽喉炎犯得厉害,“都是吼学生吼出来的。”
于娟避开锋芒,选择了同时间考试的X区。她本科学贸易,为了这次考试已经连续七天接近凌晨2点才回寝室睡觉,这让她白天上课很没精神,经常发火,但她还是觉得时间不够用,“要是能在办公室打地铺就好了”。
“为什么非做老师不可呢?我们难道没有其他出路了吗?”我间或也会发神经似的问这种冒天下之大不韪的问题。
“不然呢,不然像我们这样的普通女孩还能做什么?没钱没颜能当网红吗?”“还是踩着高跟鞋去做销售,做私企老板的贴身秘书?公务员系统更难进!”“那你呢,你又为什么来代课呢?”
在并不犀利的左右夹击下,我无言以对。
三.
小君在我上班的第一天清早,送了我一个粉色蝴蝶结和自己剪的红色窗花。她生得瘦弱,比巴掌还小的脸上不自觉地淌两行清涕,马上又被她重重地吸了回去。
“老师送给你”她说完一溜烟跑了。
第二节课下课,两个女孩子拥着小君来我办公室。小君泪眼婆娑,她伸出两只手,十只手指上长满了山丘似的冻疮,手背上有几个破了,血带着脓水源源不断地淌出来。我的心像针扎般的疼。梅倩说:“用酒精擦擦得了!”我小时候受过伤,对酒精消毒带来的疼痛感至今仍心有余悸。
实在不忍心,我跑到三楼语文组借了棉签和云南白药创口贴,小心翼翼地帮小君擦去脓水,处理完伤口,把自己的手套给了她。她把手套叠好揣进上衣口袋,低眉顺眼地说了声“谢谢老师”,又问我讨了几个创口贴,“我多贴几个,这样老师的手套就不会弄脏了。”
这所学校一共1557个学生,全是外来打工子女的孩子,无一例外。他们衣服破破烂烂,脸庞黝黑,个头矮小,身上带着酸土豆的味道。他们的父母忠心耿耿甘做这座城市渗出血汗的螺丝钉,城市提供给他们的子女看似平等的基础教育,却压根没有给予同等价值的尊重和经得住检验的灵魂工程师。
我后来才知道,学校还有一个孪生姐姐——南校区,那里读书的全是本地学生。南校区比北校区大一倍,建筑是模仿迪士尼乐园的,外墙五颜六色,充满童真童趣。孩子们长得白净体面,脸上挂着自信天真的笑容,“每个人都有才艺”。
北校区是16年暑假刚刚翻新的,为了不和南校区相差太远,每个教室都装上了新的投影仪和电子白板。但教师缺口依旧难以弥合。自从国家统一实行机构编制总量控制后,Y区大部分中小学只能根据国家统一要求维持在2012年底的编制基数,然而随着二胎政策、学校扩建、外来户口不断迁入等因素影响下,教师编制早已供不应求,成了大多数毕业生眼中的香饽饽。
学校只好不断找代课老师来填补空缺。教育部规定非在编合同教师上岗必须具备相应学历、教师资格证等岗位资格条件,录用前还要经过试讲、能力测试等环节考核。但纸上明文规定的“公开”、“平等”、“竞争”、“择优”在人情社会中不过是一个电话和一句“麻烦你”,多方角逐的博弈最终塌陷成一个讳莫如深的制度黑洞。
孩子成了最无辜的受害者。疏于管教的家长,走马灯式的老师,整体下滑的教学质量,使得北校区孩子在学科素养、兴趣创造、行为规范上都和南校区差了一大截,而且这将是一场病入膏肓的恶疾,即便用政策做手术刀,也终难以直达病灶。
我和秀秀同报考小学语文,志愿表里可以填三个平行志愿,她没填代课学校。我问她原因,她说即便考进了也会被分配到北校区,北校区实在太烂了,“那是一潭死水,沉下去就沉下去了,没人愿意呆那儿,但怎么说呢,它也确实是只靠关系就能做代课老师的学校了啊。”
说这话时,她眼中有一种深不见底的沧桑。
倒像极了学校出门那条小河,河水常年接纳排放出来的生活污水,河道阻塞,早已污浊不堪,臭气熏天。可依然有人日日不厌其烦地在埠头钓鱼,桥头柱子上还贴着“保护母亲河”这样的文明标语。
有人像那污水渐渐变成死水的一部分,有人妄图从死水里榨取最后一丁点儿好处,还有人拼了命地想摆脱这令人绝望的死水,即便很清楚岸上的空气里也尽是伤人肺腑的PM2.5和粉尘颗粒。
在每天放学送走孩子后,我就去河边玩打水漂。旋转的石头和腐朽的水面摩擦后会激起一圈一圈的涟漪,偶尔也会扑腾出不小的水花,尽管很快又复归平静。
我教孩子们礼貌待人,他们很快学会了进办公室先敲门喊报告;我告诉他们解决问题的办法在于独立思考,一周之后他们来我这儿告状的次数明显少了,连最调皮的阿杰都会说“老师,我有个问题,我想请你这样帮助我”;我一遍又一遍地在课上强调语文学习最重要的是形成阅读和写作能力,后来他们主动要求以后的班队课都用来看课外书;我教他们练书法、读古诗、背成语,他们每次下课就跑来办公室给我展示他们骄傲的学习成果,还自发在班里搞起了竞赛小组……
他们在我离开的前一天,三三两两地给我送临别礼,绿植盆栽、剪纸、许愿瓶、封面破旧的名著,甚至还有孩提时代的相册,挽留我说“老师你能不能多留一个星期”,我却找借口拒绝了他们加qq好友、微信好友的请求,在他们问我要手机号码时顾左右而言他,把礼物都留在了办公室,最后连和他们道别的勇气都没有。
我是偷偷摸摸离开的。办公室只剩下倪姐和晴霜两人,其余五个上午都回家复习了。郑敏周五下午没课,没打招呼,走了。去时又开始下雨了,淅沥淅沥地,远处孩子们嘹亮稚气的朗读声穿雨入耳,哇啦哇啦,他们还小,读书总喜欢用尽力气吼出来。
醉中赠符载
唐·窦庠
白社会中尝共醉,青云路上未相逢。
时人莫小池中水,浅处无妨有卧龙。
是我昨天教给他们的古诗。
责编:糖糖
本文版权归属有故事的人,转载请与后台联系
阅读更多故事,请关注有故事的人,ID:ifengsto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