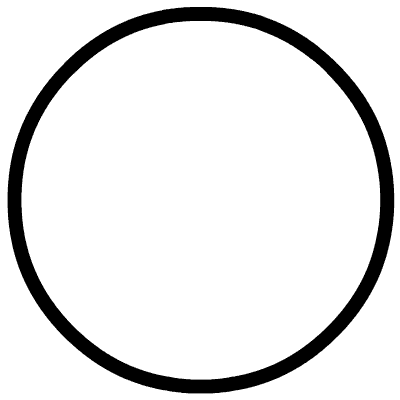有些读者可能辨认出这个情节的概要。这是日本著名导演黑泽明(Akira Kurosawa)改编自作家芥川龙之介的小说《莽丛中》和《罗生门》的代表作《罗生门》(Rashômon 1950)。它带给观众的独特观赏体验是:屏幕上的思考不是通过结构严密的论证也不是通过深奥艰涩的语言而是通过精巧的故事讲述、引人入胜的形象和新颖别致的电影艺术进行哲学思辨。

(电影《罗生门》海报)
接着轮到武士的妻子作证。在她讲述的故事中,她被多襄丸强奸,但此人离开的时候并没有杀死她的丈夫。遭到强暴之后,她解开了绑住丈夫的绳子,然后就昏过去了,醒来后发现丈夫死在她旁边,他是自杀的。
黑泽明电影核心的哲学奥秘已经非常清晰:如果我们并不真正知道发生了什么,却要讲述发生的故事时,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如果我们对周围世界的任何描述都是世界的自我呈现,每个人的描述都和其他人完全不同,谁也不知道到底哪个描述是真相,该怎么办呢?
更加引人入胜的地方是,死了的武弘借女巫之口说出自己的故事:那强盗完事后,又花言巧语引诱女人随他去,做他的妻子,那女人同意了,条件竟然是要求强盗杀了丈夫。闻听此言连强盗都大惊失色,他突然选择站在丈夫一边。这个女人设法逃走,强盗放了武士就离开了。武士自己选择自杀。
黑泽明的人物看到了同一个世界,但是因为道德和认知的理由,他们对看到的东西所做的描述是那些世界本身,这使得人们根本不可能认识世界的真面目。电影的终极信息是我们根本就没有办法“说出真相”。
接下来是另外一个版本:樵夫的叙述。他目睹了案情的全过程,但是没有向法庭讲述。审讯之后,他在罗生门下讲述了故事:在强盗多襄丸强暴过武士的妻子后,请求原谅,还请求女人跟他走,他愿意金盆洗手,改恶从善,用劳动来养活她。但她不为所动,拾起匕首,跑近丈夫,割断捆绑他的绳索,希望丈夫与强盗决斗。武士金泽武弘与强盗多襄丸笨拙地决斗,最后被杀。

这是最新的版本,但我们也不能说它是真实的。如果有更多的人涉案,我们可能听到更多版本,而且每个版本都与从前的不同。从哲学上看,这没有什么新鲜之处:从弗里德里希·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的“权力意志”术语对真理的解构到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的“真理是制造出来的而非发现的”概念,再到我们时代的一切都是“社会建构”的结果,我们已经习惯于这样一个世界,它似乎免除了认识真理在何处的必要性。这个信息虽然在人类层次上或许令人担忧,但黑泽明的电影加入了西方哲学中早已存在的对话。
但是,你可能感到纳闷,电影制片人加入哲学对话时要做什么呢?按照常常被边缘化但影响越来越大的思想线索,黑泽明恰恰做了任何一个好电影制片人应该做的事:向观众提出挑战,通过电影手段追求哲学目标,使人们超越他们在屏幕上看到的东西,参与人生活更大问题的探索。从法国后现代主义哲学家吉尔·德勒兹(Gilles Deleuze)到哈佛大学哲学教授斯坦利·卡维尔(Stanley Cavell)再到斯蒂芬·马尔霍尔(Stephen Mulhall)和罗伯特·辛那布林克(Robert Sinnerbrink)都提出过电影能成为哲学的论证。事实上,电影不仅以一种附属性的角色成为哲学---如在课堂上提供哲学问题的“说明”,而且本身都是哲学,它有自己的手段,有一种无法简化为传统哲学方法的方式。显然,不是所有电影都有显著的哲学色彩,但某些电影的确如此,这就够了。正如马尔霍尔在《论电影》(2001)所说,“这样的电影不是哲学的原材料,不是装饰的来源;它们是哲学练习,是行动哲学---电影就是一种哲学思辨。”
哲学家如果没有论证,他就什么也不是了,电影是哲学的“大胆主题”也一直遭到适当地批判。电影不可能是哲学,其主要攻击路线是这样的,因为它与总是依靠论证的哲学不同,是通过形象、情感等发挥作用的。换句话说,电影导演不能成为哲学家,因为他们并没有达到对哲学的深刻理解,即可归结为提出论证和驳斥反论证的过程。但是,若按照这个定义,很多哲学家也称不上是哲学家: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或狄奥根尼(Diogenes)将被排除在哲学家的队伍之外,孔子和尼采也将被剔除在外。
无论电影是否满足专业性的哲学定义,它的确能给我们带来像伟大而永恒的哲学著作带来的那种影响,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它让我们惊醒,动摇长久以来保持的观念,赋予心智新的生命,为我们开启看待自我和周围世界的新方式。大导演安德烈·塔可夫斯基(Andrei Tarkovsky)、英格玛·伯格曼(Ingmar Bergman)和黑泽明等的电影作品中纯洁的凝视、发人深省的视觉和入木三分见解完全能够与伟大哲学家相媲美。
不过,考虑到哲学家对理性的不健康的痴迷,电影导演能够教导他们意识到人性的本质,这一点或许更为重要:比如人的善变、复杂、和不可理喻以及行为方式上的一塌糊涂等。我们受到理性的驱动,但同时我们也受到情感和激情的驱动。我们使用论证思维,但同时我们也运用神话般的想象力。为了自身的利益,哲学或许应该给出更加慷慨的定义,在与其他领域的关系上或许应该更加谦卑一些。比如,哲学能够从电影中学到很多有用的东西---人性的温暖、社会的紧迫感以及直接诉诸内心的言说方式---这些东西在哲学文本中都是非常缺乏的。
黑泽明的《罗生门》恰恰就做到了这一点。这部电影不仅栩栩如生地展现了真理是制造出来的观点,而且用哲学自身无法做到的方式将此观点戏剧化和不断强化。我们依靠电影人物的叙述、表演、拍摄风格、场面调度(mise-en-scène)等等真切地体会到无法抓住真相的真实感受是什么。相互冲突的故事用倒叙的方式讲述出来,这提出了一些关键议题,如真理与记忆和遗忘的关系,真理与回想和错误记忆的关系等。记忆和重新讲述是没完没了的,就像无情的倾盆大雨:世界上的一切---现实、真理、和我们自己---好像都变成了流动的液体;记忆的背景是残垣断壁之地,是沦为废墟的寺庙。如果需要的话,它会提醒我们上帝已死或者至少是沉默无言的。在法庭上,我们根本看不见法官的面孔,只有那些被带进来的当事人给出矛盾重重的作证:他们向我们诉说,我们成了法官,我们必须接受一切;接着是直接刺向太阳的袭击,这造成萦绕周围迟迟不肯离去的一种茫然无措和无所适从的感受。所有这些都只能加剧我们见证的那种压倒一切的感受---我们讲真话的能力已经终结---这是无以复加的巨大悲剧。行脚僧的哀叹让人久久不能忘怀:
战争、地震、狂风、大火、饥荒、瘟疫。年复一年,除了灾难似乎没有别的东西。每天晚上都有强盗来袭击我们。我已经看到太多的人被杀掉就像被踩死一只蚂蚁那样,但是我从来没有听说过像这样的可怕故事。是的,太可怕了。这次我或许最终丧失对人类灵魂的信心。它比强盗、瘟疫、饥荒、火灾或者战争更为可怕。
当然,所有这些都“只是电影而已”。而且,把玩真理是人们编造出来的观念一直有很多的乐趣,一切都能无休止地建构和解构,太有意思了。但是,承担后果的时间可能比我们预料的要早得多。当政府鼓动我们接受谎言时,鬼扯什么那不是谎言而是“另类事实”,我们就知道参照系不再是罗蒂或尼采而是奥威尔的《1984》(1949)。那不是我们读过的小说,而是我们即将生活其中的世界。
至少,我们应该看到它已经向我们走来。毕竟,《罗生门》给了我们太多的警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