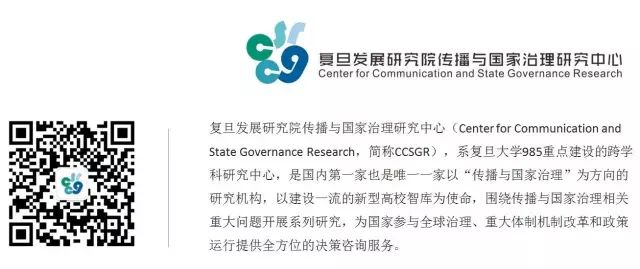欢迎点击上方订阅本公众号。
欢迎点击上方订阅本公众号。
导读
本文为CCSGR研究员、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朱春阳的《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经验坐标、发展机遇与路径创新》一文摘要,获取全文请参阅刊发杂志。
本文认为,以“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的提出为标志,我国以行政力量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媒介融合行动进入第二阶段,长期处于行业边缘地带的县级媒体终于有机会进入政策关注的焦点区域,获得政策扶持的发展机遇。本文在既有经验坐标基础上讨论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的路径创新,探讨了融合如何引导群众、融合如何服务群众,以及融合发展模式等问题,剖析了县级融媒体中心作为新型主流媒体建设的一部分需要解决的诸多关键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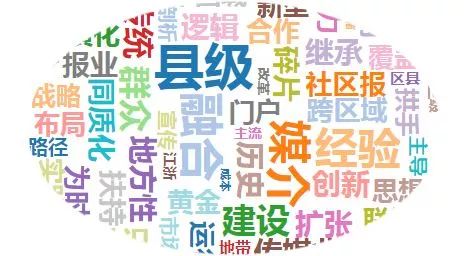
2018年8月21日至22日的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扎实抓好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更好引导群众、服务群众。”
这是中国县级媒体首次在国家级会议上被最高国家领导人关注。中宣部部长黄坤明此前也强调,打通继承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最后一公里”,要大力推进媒体融合发展,创新建设县级融媒体中心。这使得改革开放以来一度淡出传媒行业视野的县级媒体再次成为行业关注的焦点。
媒介融合的重心已经由第一阶段强调以人民日报社等大型传媒集团为代表的“中央厨房”模式的探索开始转向第二个阶段:以县级融媒体中心为建设主体的新一轮媒介融合行动的关注焦点。
至此,媒介融合发展的版图不仅涵盖了大型传媒集团,也关注到了地方性的中小传媒集团。和大集团的大融合相比,县级媒体的融媒体中心该如何建设才能实现“引导群众、服务群众”的目标?既有媒介融合发展的经验如何在县级层面实现有效的“创新-扩散”?如果要准确回应上述问题,则需要寻找到县级媒体发展的经验坐标与历史方位,厘清县级媒体发展可以借力的资源清单,才能从中有效率地抓到通往未来创新道路的机遇。

县级媒体在中国最初的发展道路基本上复制了中央、省、市三级的媒体管理体制和资源配置方式,作为县域空间大众传播资源的垄断者而深嵌于区县行政体系,跨区域的资源整合也因此基本上是无法实现的。新时期以来,这一县域媒体生存方式表现出行政与市场的混合模式,因同质化程度高、缺乏竞争而导致资源配置效率甚是低下,因而并不是一种经济型的办媒体方案。因此,我们看到,改革开放后的历次媒体结构调整,县级媒体都是裁撤的重点区域,这样既方便了管理,又降低了县级行政的运行成本。但2003年的区县报的裁减似乎有矫枉过正了,因为采取了一刀切的办法,大量的区县的报纸被取消刊号能够有刊号公开出版发行的县报全国只剩下50余家。这些县报大多数是依托“经济百强县”的富足社会资源而生存下来,多集中于江浙、广东等地。从之后近20年中国传媒业的演化情况来看,这一政策导致中国大众媒体的发展严重脱离县区、社区空间,更多集中于大众化覆盖层面进行同质化竞争。其实,
伴随着中国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区县媒体对新社区群体的黏合功能将会有助于社会共识的达成,降低碎片化的社会关系导致的摩擦和冲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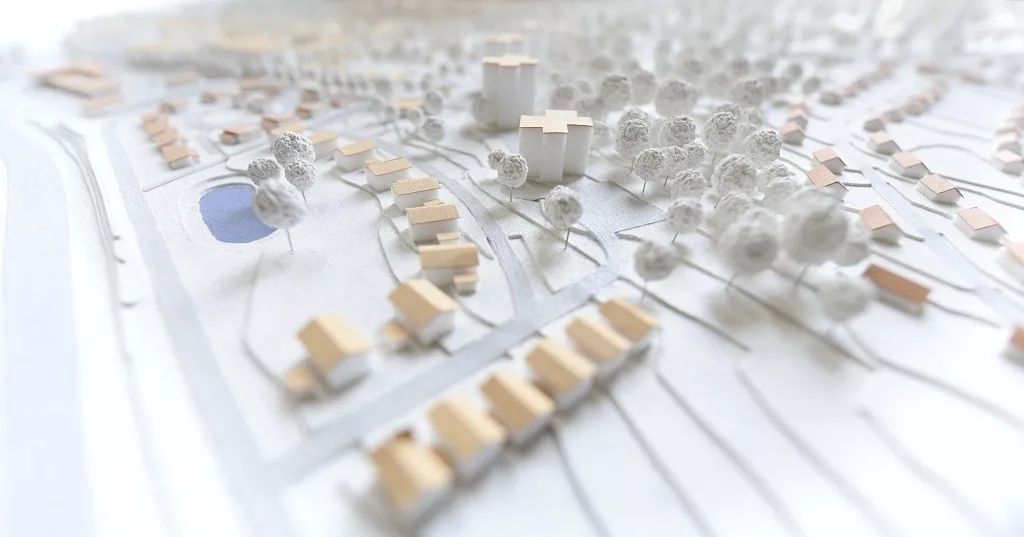
在互联网和中国传统媒体的竞争过程中,互联网如入无人之境,究其主要原因在于,传统媒体缺乏能够依托社区和目标用户形成强黏度的依存关系,互联网进入的社区空间原本是传统媒体结构布局的空白点,或者说,传统媒体拱手把自己联系民众的生命线送给了互联网,从而架空了自己与区域社会关联的通道。
在这个时候出现了两个现象。一个是都市报在遭遇到政策与制度的创新瓶颈后开始转向地铁报或社区报,但遗憾的是,为时已晚。依托智能手机而快速扩张的移动互联网出现了以后,对人们移动空间的时间和注意力的占有居于优势地位,由都市报操作经验扩张而来的地铁报的黄金期的含金量急剧下降,对广告客户的吸引力也因此降低,正逐步退出市场。而另一个现象是杭州日报报业集团旗下的“19楼”。它通过专刊渠道和用户基础构建起了全方位覆盖的网络生活社区并得以迅速扩张,不仅覆盖了整个浙江省而且向上海、江苏、安徽、河南进一步渗透,号称要成为区域网络生活的入城口和门户,成为传统媒体进军网络社区的标志性创新平台。

从上述中国以区县媒体为代表的区域媒体在整个政策体系演化过程中的遭遇来看,时至今日,大中小共生的传媒业融合发展格局基本已经成为共识,而县级媒体的独特价值和地位也在这过程中终于被认识到了。区县媒体以融媒体中心的新面孔成为新一轮政策扶持的对象,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机遇期。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2017年,绝大部分地市级广电都陷入了经营不善、负产出甚至负资产的状况。这一定程度上说明,县级融媒体中心的大范围兴起也正是被当做区县电视台走出当前困境的破局之举。
可以预见,县级融媒体中心作为行政力量主导的新一轮媒介融合的标志性工程,其获得的政策扶持资源也将远远超过之前广电行业的自救力度。
但我们要看到,非常遗憾的是,因为新媒体技术的快速兴起,中国县级媒体已经错过了依托传统传播形态操作经验的扩散而获得快速发展的历史机遇。
同时,从既有媒介融合探索经验来看,“报业新媒体的发展经历了电子版、网站、手机报、阅读器、iPad版、微博、微信、客户端、短视频等各种形式,在赢利模式上均未取得成功。何况,运作新媒体的成本却非常高昂,这成为报业不能承受之重”。对于遍地开花的县级融媒体中心来说,高成本的媒介融合建设经验一旦在县级媒体平台被复制将会带来巨大的财政压力,也将成为一场灾难。因此,
进入媒介融合发展的第二阶段,既不能简单照搬既有社区媒体的操作经验,也不能复制之前大型传媒集团融合发展的实践经验,县级融媒体中心的建设需要在社区媒体和媒介融合的双重经验坐标下寻找新的方向,或许才能抓住政策转向带来的发展机遇。

基于自上而下的和自下而上的县级融媒体中心探索经验的综合考量,参考国外社区报的融合发展经验与媒介融合在中国的特殊规定性,以及商业网站融合发展的经验示范,我们认为,在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过程中,路径创新经验的坐标系大致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一)如何“引导群众”:移动传播优先,抵达本地社会变动的第一现场
媒介融合是传统媒体走进新媒体空间,主动参与社会讨论并引导舆论的过程。传统媒体内容的生产一传播流程基本上是按照“黄金24小时”的节奏运转,这和互联网以秒为单位的信息发布时效形成强烈反差,而身在现场的网民的“随手拍”行动也会倒逼传统媒体加快传播节奏,以便跟得上时代演化的节奏,跨越“数字鸿沟”。在“全世界在观看”的场景下,“引导群众”,就需要在事件发生的第一时刻抵达现场,并在第一时间把真相传播出去,不给谣言、流言和谎言留出滋生危险的空间。就媒介融合的发展现实来看,移动传播优先,而非传统出版和播出优先,是检验真假媒介融合的第一块试金石,也是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需要首先完成的技术转换。就目前来说,两微一端、抖音等新的传播技术平台在县级融媒体中心的建设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这为官方媒体声音直达社会舆论第一现场提供了技术上的可能。

但我们也要看到第一阶段媒介融合过程中存在的显著问题。之前中央、省、市三级媒体系统也大多在技术上实现了移动传播优先的可能但却很难在社会舆论第一现场实现有效沟通,尤其是危机时刻常常游离于舆论发生的第一现场,回避诱发舆情的核心问题。因此,
我们也把能否抵达社会冲突第一现场进行有效沟通作为判别是传统主流媒体还是新型主流媒体的第一准则。
按照既有的行政话语逻辑,政务机构主动走进网络空间,是对网络群众工作路线的实践,即做到从群众来,到群众中去。
(二)如何“服务群众”:创新始于用户,而非生产者
当我们在谈论媒介融合的时候,我们在谈论什么?对之前的媒介融合实践经验的考察发现,媒介平台常常占据了我们讨论媒介融合的第一落点。这和在互联网空间获得巨大成就的BAT的逻辑基本上是背道而驰的,在BAT的行动逻辑链条中,传播平台是对用户需求反应的结果,而非起点。当我们把媒介融合的讨论聚焦于传者端的技术更迭,而不是用户端的需求变革,很可能是倒置了媒介融合的逻辑。无论是传播学的研究还是营销学的研究都已经明确无误地指出,受众(或者说是用户),而非传播者(或者说生产者,才是主导传播和营销演变趋势的力量。但这一理念落脚到媒介融合的时候却还是常常回到了传统意义上的以生产者为中心、以传播者为中心,传统理念的惯性思维作用之强大由此可见一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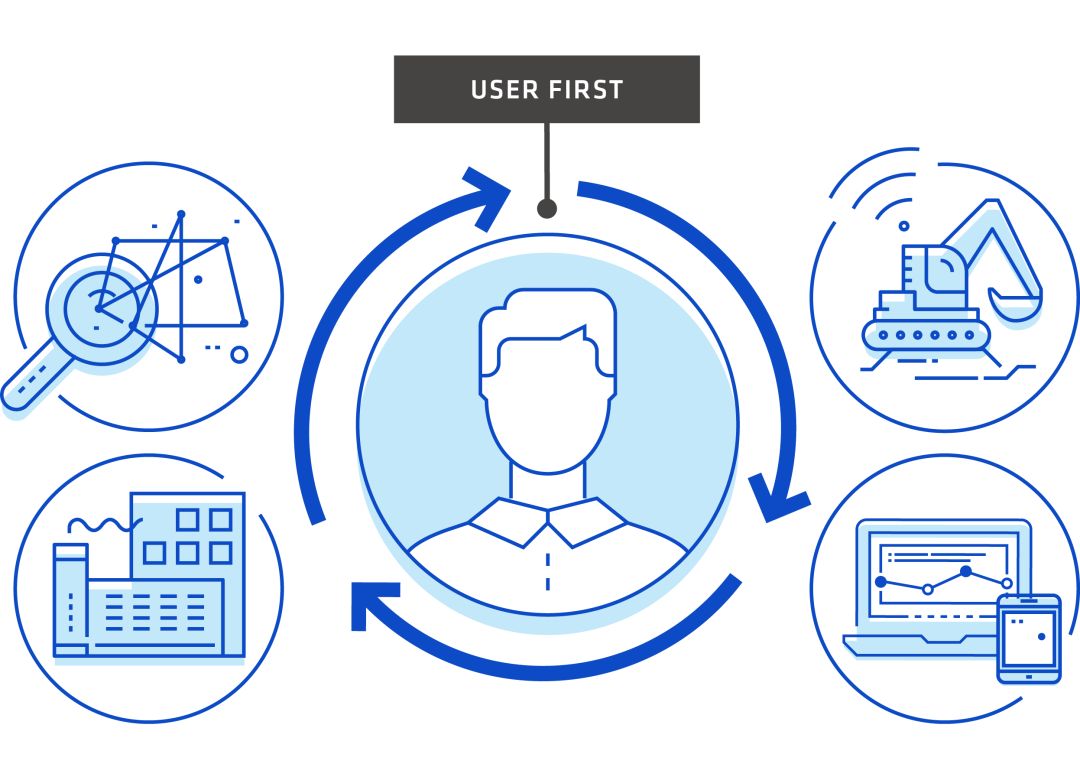
那么,如何在融合中“服务群众”呢?根据以往社区媒体的成功经验,通常是强调新闻立足本地,而非放眼世界。
县级融媒体中心的主要任务是对本地社会变动的关注,在它的上一级有覆盖面更为广泛的融合平台提供范围更加宽广的新闻信息。
在美国,研究者通常把大报上的新闻称作“降落伞新闻”,他们高高在上,读者只是地面上一个个类似蚂蚁的点。社区媒体要做的,就是弥补这种个体被淹没的失落感,走出去和居民交流,了解并报道这些对大报来说没有价值、不值得报道的每一个街区的动态。这种突出个人存在与价值的社区新闻,被称为“冰箱新闻”社区居民将报纸剪下来,孩子的、家人的、亲友的,贴在自家的冰箱上,那是与他们贴得最近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人文关怀。因此,关注本地、关注小人物、以小切口来考察社会大问题是提高县级融媒体中心服务效率的基本坐标。因此,
县级融媒体中心平台的操作经验不仅包括社区报经验,还要把地方资讯门户网站作为自身融合创新的另外一个坐标,为当地人提供生活成长的一站式服务,最终成为世界了解本地的首选视窗。

(三)成长方式:嵌入大平台,形成广泛联结
参照腾讯融合发展战略的变革,我们可以看到,以2011年为分水岭,之前的腾讯战略强调以封闭垄断为价值主导的丛林法则,而之后的战略则强调以开放、合作、共赢为价值主导的天空法则,合作、开放也因此成为互联网经济的精神内核。不仅互联网的未来趋势如此,高效率、低成本的海外地方媒体在传统上的运营经验也是如出一辙,这就决定了县级融媒体中心的未来也必将在这一框架内运行。因此,
嵌入大平台,形成广泛的社会联结是未来县级融媒体中心发展壮大、获得资源与养分的主要方向。
从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的现有规划方案来看,报业系统主导的建设方案表现出了非常强的资源整合、平台联结特征。广电系统主导的县级融媒体中心则表现出较弱的整合性。按照现有地方媒体布局,县报的分布较为有限,而广播电视在县区层面是媒体资源的标准配置。从全国范围来看,在县级融媒体中心的建设过程中,县级广播电视台应该是主体。因此,依托广电平台为主体的融合路径应该是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的主要方向。而且,发达国家广电系统的发展模式都是以广播网为单位,美国历史上曾经出现的三大广播网构成了美国广电行业的主体。基于此,
未来广电系统主量的融合发展则需要强化区域整合力度,唯有此,才能避免县级融媒体中心的建设陷入到碎片化的尴尬境地。
此外,在报业系统和广电系统之外力量主导的县级融媒体中心的布局也有一些,其碎片化程度更高,也需要以上述理念去予以整合。
(图片来自网络)
复旦发展研究院传播与国家治理研究中心 研究员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 教授
本篇文章发表于《新闻界》2018年第9期
。
本文由作者授权发布,未经许可,请勿转载(个人转载不在版权限制之内)。如公开出版机构需转载使用,请联系刊发杂志及作者本人获得授权。
朱春阳.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经验坐标、发展机遇与路径创新[J].新闻界,2018(09):21-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