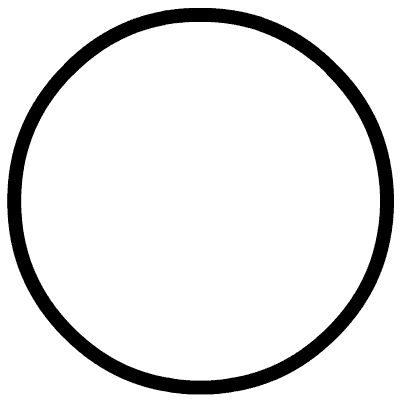
点击上方关注我们


康 德 与 外 星 人
文 | 彼得·桑迪 Peter Szendy
译 | Nowhereman
译自
Kant chez les extraterrestres:Philosofictions cosmopolitiques
Les Éditions de Minuit, 2011
POURQUOI PAS ?
LA PHILOSOFICTION DU TOUT-AUTRE
从他最早的著作之一(写于1755年的《自然通史》和《天体论》,当时他只有21岁)到他最后的著作之一(《实用人类学》,发表于 1798 年,即他去世前六年),康德虽然没有把外星人当作他哲学的一个主题,但还是经常把其他星球上的居民纳入了他的思考,并邀请他们进入他的论述。
在《天体论》的第三部分,他指出:“我认为,没有必要肯定所有星球都一定有人居住,尽管否认所有星球甚至大部分星球都有人居住是荒谬的。”这是一种“猜想”(康德的用词);哲学家既不断言也不否认,而是问道:为什么除了地球之外,其他地方不应该有智慧或合乎理性的生命?
这个问题也是丰特奈尔(Fontenelle)著名的《关于世界多元性的谈话》(Entretiens sur la pluralité des mondes)(1686年初版,比康德的《天体论》早了近60年)的基本基调。正是一种表现为“为什么不呢”的热忱,使丰特奈尔的叙述者在面对略带怀疑的对话者侯爵夫人时提出了一种普遍的宇宙解决方案:
“从表面上看,月球上有人居住,那为什么金星上就不能有人居住呢?”侯爵夫人打断了我的话“但你打算在所有的行星上都安置居民吗?”“当然,”我回答道,“为什么不呢?”
那为什么不呢?
我们需要明确这一点:在这种否定式的提问形式中,突出的是虚构的空间,它不仅决定了《关于世界多元性的谈话》等文本优美且俏皮的基调,也在形式上困扰着最严谨的哲学著作,正如我们在《判断力批判》和康德的其他著作中所看到的那样。这个空间就是我所说的哲学小说(philosofiction)的要素(就像我们所说的科幻小说一样)。
《火星人玩转地球》
在康德生前亲自撰写并出版的最后一部著作《实用人类学》中,外星生命这一哲学问题又引人注目地出现了。该书第二部分是“人类学特征”,即“从外在的人认识内在的人的方法”,先后论述了“人”、“性别”、“民族”和“种族”的特征,最后是“物种的特征”。他说,如果我们的经验无法触及人类物种,无法了解人类物种的特性,即人类物种与其他物种的区别,那我们又如何了解人类物种的特性呢?康德在谈到“合理的陆生生物”时,宣布它们不可能被定性,注定是不确定或不确定的:
“我们无法指出它们的任何特征,因为我们对非地球上的合理存在物没有任何知识,这使我们无法指出它们的属性,从而无法在一般合理存在物中指出地球生物的特征。因此,指明人类物种特性的问题似乎是绝对无法解决的,因为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通过经验对这两个合理生物的物种进行比较,而后者并没有为我们提供这样做的可能性。”
地球人是无法比较的,因为他们没有关于外星生命的经验或可能的知识。然而,同样是这些地球人,在康德的带领下,当他们想把自己当作有理智的人时,就会不停地诉诸于一个比较词,无论这个词多么难以表述。
当然,在缺乏比较特征的情况下(康德的人类学似乎不情愿地放弃了比较特征),康德似乎首先选择了从本质上来定义“物种的特征”。也就是说,在不离开地球的情况下,通过下定决心留在地球上,并且一起留在地球上的必要性来定义“物种的特征”:
“所有时代和所有民族的经验都表明,人类的特性如下:作为一个整体(人类整体),人类是由一群相继或共存的人组成的,这些人不能不和平共处,但又不能不不断地给对方造成麻烦;因此,这些人感到,由于相互制约,他们天生就注定要组成这样一个联盟,该联盟不断受到不团结的威胁,但又作为一个整体不断进步,以建立一个世界公民社会。”
这些世界公民,即我们这些宇宙公民,仍将是地球人,注定要分享地球。也正是在地球上,我们必须解决这样一个问题:人类这个物种,除了是一群注定要彼此共存的地球人之外,不可能有任何其他特征,“无论他们是被视为一个好的种族还是一个坏的种族”。
尽管康德似乎已经得出结论,即我们地球人应该以地球人的方式来评判,但他还是觉得很难。我们几乎可以说,他无法完全放弃同地外生命的比较,尽管他刚刚说过这是不可能的。当他把人类说成是一个“种族”时,在结构上就不得不把它与另一个甚至是未知的物种联系起来:“人类物种”,他写道,“如果我们把它看作是一个合理的地球生物物种,那么与其他星球的生物相比,它也可以被称为一个种族[......]”。它回来了,不顾一切地回来了:外星人回来了,而且还会再回来。
在康德的《实用人类学》中,这些其他世界的居民再次出现。他们的最后一次出现是在康德对“我们这个物种的道德面貌”的思考中。康德写道(这几乎是最后一句话):
“每一个谨慎的人都认为有必要隐藏自己的大部分想法,这本身就足以说明,在我们这个种族中,每个人都认为最好保持警惕,不要让别人看到自己的全部,而这恰恰已经暴露了我们这个物种怀有对彼此的恶意的倾向。在其他星球上,可能也有一些理智的生物,他们只能大声地思考,也就是说,无论在社会上还是在独自一人的时候,他们都不能有自己不会立即表达的想法。这会使这些智慧生物对待彼此的行为与我们人类的有何不同呢?”
在康德遗著的最后几页中,这位哲学家似乎不能不提到地球人中唯一名副其实的宇宙人:宇宙的居民。因此,如果我们从某种角度来看待人类,那他们旧注定会不断地回归。
《铁血战士》
康德真的相信外星人吗?他相信外星人的方式是否与今天那些声称亲眼目睹外星人的人一样?
康德到处记录了他的信念。在他的著作中,我们还发现了一些段落,随便读一读,都像是今天科幻小说的开端,比如《判断力批判》中的这一段:
“如果一个人在他看来是无人居住的国家里发现了一个画在沙地上的几何图形,比如一个规则的六边形,[......]他不会认为沙子、周围的海、风或他所知道的动物的脚印,或任何其他缺乏理智的原因,会是产生这种形状的可能性的基础。”(第64节)
读到这一段,我们可能会想到奈特·沙马兰(Night Shyamalan)的电影《迹象》(Signs, 2002),其中外星人的到来首先是由美国一个人烟稀少的省份(宾夕法尼亚州巴克斯郡)的农田中描绘出的巨大几何图形所宣告的。正如康德面对在沙漠中画出的假想的规则六边形时断言“自然界中没有任何原因可以包涵这样一个结果的因果关系”,换句话说,它是“只有理性才能给出的概念”的结果,沙马兰的主人公也不断地逐一否定他们发现的在玉米种植园中大规模绘制的不可能的图画的可能的自然原因:格雷厄姆·赫斯牧师(梅尔·吉布森饰)的孩子在凌晨被狗叫声惊醒,他们立即认为是“上帝干的”,而他们的父亲却拒绝相信;然而,在与当地警方代表通话时,他自己却说“这不可能是人为的,太完美了”。犯罪行为的假设也被排除了。而当电视从世界各地播出地球表面到处都有类似的在玉米地里雕刻的巨型标志的图像时,对外星人的怀疑就变得令人头疼了。
但是,除了康德与当代科幻小说之间的这种肤浅的类比之外,除了哲学家本人公开或不公开的观点之外,等待我们的是一个更为激进的问题:我们与其说是在试图找出康德在内心深处可能相信外星生命的存在,不如说是在试图确定某种“为什么不?”。我们将试图确定某种“为什么不?”的必要性,这是哲学无法回避的哲学小说/虚构维度,如果哲学想要判断和思考判断,就必须暴露在这一维度之下。或者更确切地说:此后它必须面对我们称之为观点的东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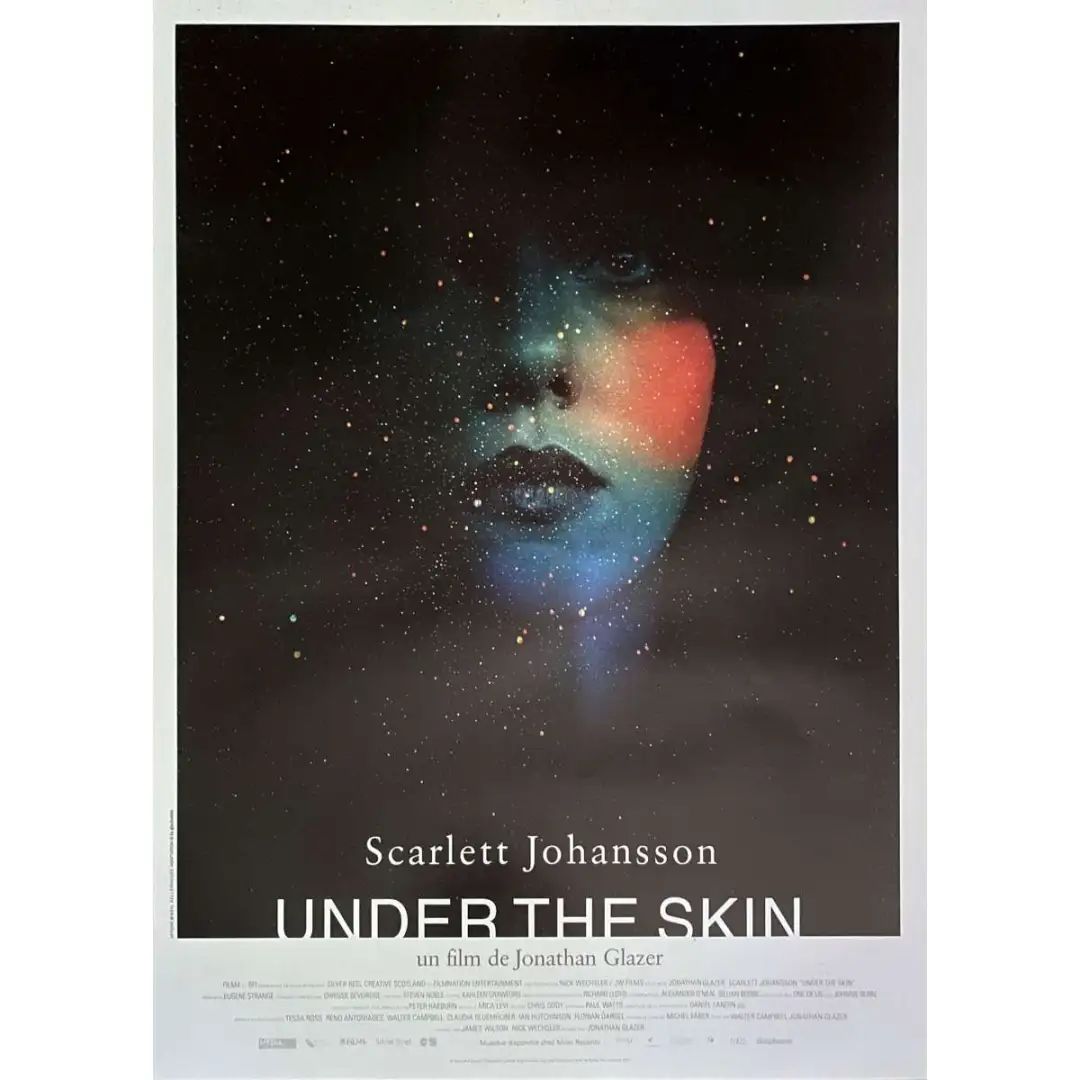
丰特奈尔的《关于世界多元性的谈话》中的叙述者明确宣布,“地球和月球之间将有商业往来”,他还对仍然感到难以置信的侯爵夫人断言,“总有一天,我们将走到月球那么远的地方”。
至于康德,在《天体论》的结论中,他以一种更加谨慎的揣测性方式,设想了未来的星际旅行时代,即使不是这样,那他至少也是设想了死后在其他世界逗留的可能性:
“那么,不朽的灵魂在其未来的无限期(坟墓本身并没有打断它,而只是改变了它的未来)中,是否应始终依附于宇宙空间中的这一点,即我们的地球?[......]谁知道呢,难道有一天它不需要近距离了解这些遥远的宇宙球体吗[......]?也许行星系中的某些天体仍在为此而形成,以便在我们停留于地球的时间结束后,有其他天体为我们准备新的居住地。”
谁知道呢?
为什么不呢?
无论是在我们的有生之年,还是在坟墓里,星际探索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惊喜?我们在那里会遇到什么样的生命形式,我们可以将最终成为可比物种的人类与之相比吗?
如果说在关键转折点之后的著作中,康德避免(并非毫无困难地)对不同世界的居民进行自由的比较性推测,那么在这篇所谓的早期或前批判的文章中,他开始了对地外生命和思想模式进行分类的理性尝试:
“[......]木星居民的身体必须由更轻、更流动的材料构成,这样,太阳在这个距离上所产生的微弱激励才能像在较低区域一样有力地推动这台机器。而且,为了把一切都归结为一个统一的概念,我想说的是,形成不同星球的居民的物质必须是一种离太阳越远就越轻、越细的物质......这些外星居民从外部印象中获得的概念的活力,以及组合这些概念的能力,最后还有在实际运用中的灵活性,总之,他们的整个完美程度都受制于某种规则,根据这种规则,这些生物总是按照他们的居住地与太阳的距离之比变得更加优秀和完美......从水星到土星,甚至更远(因为还有其他行星)的行星中,精神世界和物质世界的完美程度,都是按照它们与太阳的距离的比例,在一个精确的程度序列中增长和推进的。”(《天体论》)
在这种自由而无拘无束的民族宇宙学推测中,康德似乎并不过分关注对其哲学中固有的小说/虚构维度的批判性规范。尽管他在《天体论》第三部分的开头提出了警告,但占上风的却是他自己所说的“想象的自由”。正如结尾处半信半疑地指出的那样,这种愉悦似乎是审美性的:
“用这样的表述来自娱自乐是允许的,也是应该的[......]事实上,当一个人满脑子都是这种思考时[......],在宁静的夜晚看到满天繁星会带来一种只有高尚的灵魂才能体验到的愉悦。在大自然的普遍寂静中,在感官的休憩中,不朽精神的隐秘知识力量说出了一种无名的语言,给出了尚未孵化的概念,这些概念可以被感受到,但无法被描述。”
这几句话为《天体论》画上了句号,让人联想起《判断力批判》中的段落,我们稍后会再谈到。但最重要的是,这种推测仿佛——是的,仿佛——人类进步的地理和时间视角被投射到宇宙中,并扩展到了宇宙空间。因为,在康德的宇宙生命尺度中,地球人和他的地球处于中间,处于中间点或中点。这个点当然不再是牛顿时代之前和哥白尼时代之前的古代宇宙论体系中的中心点,但仍然保留了它的某些特征:
“如果居住在木星或土星上的最高等级的合理生物的形象引起了他的嫉妒,使他因认识到自己的卑微而感到羞耻,那么,对低等生物的思考又能使他感到满意和安抚,因为那些在金星和水星上的低等生物,它们远远低于人性的完美。多么令人钦佩的景象啊!一方面,我们看到的是有思想的生物,与他们相比,格陵兰人或霍屯督人简直就是牛顿;另一方面,其他人却把地球居民视为猿猴。”
这里重要的不是地心人类学和地心地理学的简单扩展或宇宙论放大。从这个意义上说,外星小说/虚构并不完全等同于孟德斯鸠的《波斯人信札》,也不等同于任何其他借助异国情调的虚构:在虚构外景的掩盖下,更好地讲述发生在我们国内的事情。因为《天体论》的哲学虚构——正如我们将看到的那样,它在康德晚年的著作中以弱化的形式存在——似乎必然要超越可能的经验:不仅仅是面向他者,而是面向全然迥异的他者。
《星河战队》
尽管康德不断提到牛顿体系,尽管他肯定了远离太阳的行星上的生命的优越性,但这种人类-地球中心主义仍在暗中继续支配着康德的宇宙论论述;在有必要脱离地球的时候,却不顾一切地赋予地球及其居民以特权,而这种特权早已出现在丰特奈尔的著作中了。事实上,在《关于世界多元性的谈话》中,欧洲的种族中心主义也延伸到了宇宙的维度,决定了人们对其他星球居民的特征进行推测时所采纳的逻辑。因此,侯爵夫人可以这样评价离太阳更近的金星人:
“他们像格拉纳达的摩尔人,一个被太阳灼伤的小黑人,充满灵性和火焰,总是在恋爱、作诗、爱音乐,每天都在发明盛宴、舞蹈和比赛。”
叙述者补充道:
“请允许我告诉您,夫人,您不太了解火星的居民。就冷酷和愚蠢而言,我们格拉纳达的摩尔人不会比拉彭人和格陵兰人好多少。那么水星上的居民呢?他们离太阳的距离是我们的两倍。他们一定是疯了,因为他们活泼可爱。我相信他们没有记忆力,就像大多数黑人一样,他们从不思考任何事情,他们只是一时冲动。”
与康德的《天体论》一样,太阳系在这里也是地球人的民族地理和种族特征的一面镜子。以至于在这些充满宇宙色彩且往往滑稽可笑的哲学小说/虚构中(人们不禁要嘲笑这种令人咋舌的恒星种族主义),我们似乎正在目睹一场双重运动:一方面,正如我们刚才所读到的,外星生物无论多么古怪,一旦与地球人类学没有任何联系,那他们就无法被形象化或虚构化;但另一方面,正如我们所瞥见的,而且我们将立即再次验证的,地球人只有通过脱离他们的地球土壤和基座,将自己(至少在想象中)转移到全然迥异的他者的视角,才能将自己视为宇宙中的合理物种或种族。
相关推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