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饶佳荣
如果你置身第十届“中国中古史青年学者联谊会”的现场,或许会觉得有点奇怪:一群即将迈入不惑之年的学者都感叹“老了”,纷纷表示这是自己“退休”前的一次“告别演出”。在这次会议上,80后和85后被看成“两代人”,80后大都扮演的是分场讨论主持人的角色,即使有论文发表,在联谊会上大概也是最后一次了,而会议期望关照的是即将获得博士学位或刚刚进入科研岗位的学界“新锐”。也就是说,这里的“青年学者”基本上是30岁上下的初出茅庐之辈。在某种程度上,第十届中古史青年学者联谊会就有了更新换代的意义。
十周年毕竟是一个特殊的段落,用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孙正军的话说,“这是一个时代的结束,也是一个时代的开始。”为此,这届联谊会专门设置了十周年纪念座谈,武汉大学历史学院胡鸿主持。下文对联谊会的介绍主要就来自这场座谈。中国中古史青年学者联谊会创办于2007年,在与会者眼里,这不止是一年一度的学术会议,更是一个沟通学术、交流思想、论文会友的重要平台。与众多学术会议相比,联谊会确有其不同寻常之处。首先,与会者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学术群体,朝气蓬勃,锐气十足。其次,除了第一届是中国大陆和日本两方构成的青年学者研讨会,从第二届开始,都是由中国大陆、中国台湾和日本三方选定的优秀青年学者参会,比例基本相当,间或也有美国、韩国的学者参与。由于采取了三方互评的机制,对任何一方来说,联谊会上都是“他者的在场”;每届联谊会都是三方协商讨论的结果,因此也是“自治体的联合”(徐冲语)。第三,联谊会非常突出的一点是,会议用作讨论的时间比较充裕,这次围绕一篇论文展开的专场长达50分钟(发表15分钟,从会议情况看大都是12分钟上下;评议15分钟,一般6分钟左右;剩余时间综合讨论),有几届还设置了双评议人,为的是真正达到切磋、研讨的效果,发表人要接受与会者方方面面的“轮番轰炸”,视作一场答辩亦未尝不可。第四,据联谊会“资深”成员介绍,与会者都会把他们当时自认为重要或最新的代表作提交给大会主办方(比如魏斌的“安世高传记的形成史”、徐冲的“历史书写”、孙正军的“想象的南朝史”、游逸飞的“汉初楚国无郡论”等),评议人也会不留情面地“围而攻之”,在唇枪舌剑的批评往复中,渐渐形成了联谊会严谨、创新的会风。第五,与会者提交论文自不在话下,评议人也要把评论意见撰写成文,自第二届开始,评议还装订成册。这样做,一方面是为了便于中、日学者交流,另一方面也使评议人严肃对待,在学术竞技场交锋之意油然而生。值得一提的是,联谊会于2010年创办了会刊,却不是会议论文集,而是在联谊会团队基础上的专业刊物,构筑会议之外的互动平台,目前已出至第五卷。

胡鸿主持座谈(本文图片由焦天然拍摄,特此致谢)
8月26—27日,第十届中古史青年学者联谊会暨“国家、区域与社会”人文学术论坛在北京大学李兆基人文学苑1号楼召开。按照联谊会的惯例,没有冗长的领导致辞和资深学者的主题报告,只有专场报告与综合讨论。这次会议共设置了7个专场,15位学者发表(中国大陆7位,中国台湾4位,日本4位)。论文集有393页,评议集有47页。从发表论文主题看,制度史、政治史与历史书写构成了本次会议的“重头戏”;从时段上看,魏晋南北朝史占据了“半壁江山”,秦汉史4篇,以唐史为中心议题的论文2篇。会议名录上有40多位学者,一半左右是在读博士生和刚刚毕业的博士。东京大学大学院人文社会系研究科博士生付晨晨担任现场口译。整个会议议程十分紧凑,评议和讨论相当热烈。
限于篇幅,本文选取其中几场略作介绍。需要说明的是,此处选取的发表和评议并不意味着某种价值判断,尽可能兼顾三方,但无论怎么选择都难逃“偏颇”之议。其实,本文的出发点,是从一个侧面介绍中古史青年学者的研究动态,尤其关注联谊会的办会机制和会议的“研讨”环节,所以并不是一个“客观”、“全面”的报道,敬请与会者、读者鉴谅。
“农战”体制与“君—臣—民”结构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孙闻博第一个作报告,题目是《商鞅“农战”体制的确立与帝国兴衰——以“君—臣—民”政治结构的变动为中心》。这是一篇长达39页的鸿文,篇幅长,处理的议题也大。文章共分八节,这里把每节的标题抄录下来,或有助于读者了解其梗概:一、商鞅“农战”体制的肇创与“君—民”联结;二、《商君书》所见秦民群体划分与“农战之民”的出现;三、“士大夫”、“官人百吏”考辨——兼论秦对“臣—民”关系的制约;四、惠文王以降“农战”体制的调适及“资人臣”、“徕民”问题;五、吕不韦、《吕氏春秋》与“农战”体制的波动;六、“事皆决于法”、“外抚四夷”:始皇前后期政治的两次转向;七、始皇事业的继续:二世“更始”诏书与“用法益刻深”;八、以“术”辅“法”:二世后期的政治特征与帝国覆亡。

孙闻博(面对镜头者),其左为小野响
台湾中兴大学游逸飞担任评议人,在他看来,这篇论文“超越了秦汉/军事”的研究范畴,“从整体政治社会结构的角度,重新梳理秦帝国的兴衰,企图提出有别于前人的新解释,气魄不可谓不弘大,在碎片化历史学的当下,尤其难得”。不过“此文的整体框架有些过于复杂”,很容易导致误读。游逸飞认为,从“战国模式”到“帝国模式”这一概念最适合用来解释帝国兴衰,但作者未能充分发挥。他建议作者从“农战”体制、“君—臣—民”结构等方面入手,探究“从战国到帝国”这一历史脉络的内涵。孙闻博在回应时表示,自己这篇论文的关键词并不是“帝国兴衰”,而在于探讨“农战”体制与“君—臣—民”政治结构的关系。

游逸飞
接着,北大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陈侃理就论文中对秦二世政治思想的分期提出疑问。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叶炜认为这篇论文是“一个很宏观的思考”,他向作者提了几个问题:一是“战国模式”、“帝国模式”的具体内容,以及这两个模式之间的关系;二是“战国模式”向“帝国模式”的转变,与梁云《战国时代的东西差别》所说的社会结构的转变,这两者是怎样的关系;三是如何把握“战国模式”、“帝国模式”与“战时模式”、“和平时期的模式”之间的关系。

叶炜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仇鹿鸣也围绕两个模式提出了疑问:“战国模式”与“帝国模式”真正的区分在哪里?所谓“帝国模式”是指秦统一六国以后把秦国原来的体制推广到东方六国,还是杂糅了六国的传统后形成了一种新的模式?他还向作者提出一个问题:秦始皇前后期政治转向(前期注重守成,后期继续开边)的动力来自何处?是秦统一之后的历史惯性推动的,还是秦国奖励农战的社会结构决定的?
汉光武帝与儒教性图谶
儒教国教化是日本秦汉史学者非常关注的一个主题,西嶋定生和板野长八堪为代表,两人对儒教国教化定型的时间存在分歧。西嶋氏定在王莽时期,板野氏定在东汉光武帝时期。东京大学大学院人文社会系研究科博士生三浦雄城的论文《论光武帝与儒教性图谶——基于新莽末期图谶情况的分析》,就是在这一学术脉络下,企图解决两位前辈的分歧,把儒教国教化最终完成的时间确定下来。为此,论文分三节(“儒教性图谶的形成时期”、“光武帝即位期的谶”、“光武帝治世期的谶”)作了细致的考索,最后得出结论,“新莽末东汉初期的谶与天文占的联系很强,与儒教的关系还未普遍化。很可能是在光武帝即位后,谶与儒教关系才开始巩固。”文章还揭示了光武帝本人在这个过程中的作用:“从即位到晚年封禅的这些年,光武帝才明确通过具有儒教色彩的图谶彰显自己的正统性。”

三浦雄城(左),右为胡川安
山东大学《文史哲》编辑部孙齐对论文的精义作了清晰的梳理,他指出,由于谶纬文献难以断代,以往的研究基本上是放在较长时段中来处理,而本文尝试从具体时段入手,作精细的分析。孙齐在评议稿中自称“对于本论题素无研究”,“只能勉强提出一些外行的无关宏旨的边缘问题供作者参考”,他主要提了三点:一是围绕论文一个注释展开的,孙齐核查了《后汉书》和《华阳国志》关于公孙述的相关记载,质疑作者一个论述的可靠性;第二,就“向天称臣”问题提出不同意见;第三,涉及文章提出的核心概念“儒教性图谶”。孙齐认为光武帝时代使用的主要是《河图》《洛书》一系的谶纬,很难说是“与孔子、经书结合的东西”。“这样的话,光武帝的‘谶纬革命’和王莽的‘符命革命’,其实都是依托上古圣王,其间在意识形态上是否存在结构性的断裂,是值得考虑的。”结合陈侃理、索安等人的研究,孙齐指出,与其说光武帝运用的是“谶纬”,不如说主要看中的是预言其上台的“谶”;至于由儒家之“经”与“谶”结合而成的“纬”,似乎是光武帝之后的东汉儒生追求的结果。因此,“‘儒教性谶纬’能否被认为是光武帝时期成立的,及其在历史进程中是一种主动性的力量还是一种被动性的力量,应当是今后值得进一步深研的课题。”

孙齐
台湾政治大学历史系博士候选人吴承翰指出了孙齐评议稿脚注的一处疏误:《论东汉“儒教国教化”的形成》作者是渡边义浩,而不是渡边信一郎。这显然是评议人的无心之失。连这样细微的疏漏也不放过,正说明与会者的严肃认真。另外,他还向发表人和评议人请教:如果厘清了儒教国教化成立的时间,这个问题可以衍生出什么理论上的意涵?
私人阅读与目录学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吕博是做唐史出身,这次提交的论文叫《与阮孝绪的知识世界》,探讨了南朝齐梁时代的学术风气与精神世界。这篇论文是在胡宝国先生《知识至上的南朝学风》的启发下,围绕《广弘明集》所存《七录序》,从私人阅读的角度,对阮孝绪的“阅读领域”和“知识轮廓”作了比较细致的梳理,希冀通过考察阮孝绪的精神历程,展示齐梁之际社会精神风貌的变化。

吕博(右),左为永田拓治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东亚系博士候选人黄旨彦担任评议人。《七录》将兵书、子书合并,她在评议稿中并不满意作者的解释,提出两个疑问:“其一,为何阮孝绪的前一代人王俭(王俭比阮孝绪大三十岁左右)在其书目《七志》中,将子书与兵书分列为诸子志及军书志?王俭的时代兵书的数量只可能比阮孝绪的时代少,武术南弱北强及南朝人诫兵的态度也不大可能丕变,为何却采取不同的作法?其次,如何解释将子书及兵书拢总归入乙部的荀勖并非出身于诫兵的时代?荀勖出身曹魏时代我们可能很难同意曹魏诫兵。因此笔者认为将南朝诫兵的文化特征作为阮孝绪合并子书与兵书的理由,尚须进一步商榷。”黄旨彦认为,作者在处理《佛法录》与《仙道录》的出现及排序问题时,其呈现方式“可能会造成读者的误解”。在她看来,阮孝绪自身说出佛道的先后是依据他精神所宗排序,这没有问题,但不能因此忽略南朝知识体系的发展。到了南朝,佛、道发展相对成熟,在士人的精神世界里占了重要的一席之地,又有陶弘景整齐道教的努力在前,因此作为一部目录学著作,不可能忽略这样的知识背景。黄旨彦还建议作者将《七录》置于目录学本身的脉络,“深化其中为书籍分类的讨论,并进一步探讨以国家力量介入集书的意义”。

黄旨彦
孙齐认为,这是一篇“非常有野心的”文章,企图通过阮孝绪一人揭示南朝知识界的变迁,他觉得作者对阮孝绪的观察颇有启发性。接着,孙齐就文章的一些细节提出质疑,以利于论述的完善。
中国社科院历史所陈志远出语婉转,却抛出了一个很有“杀伤力”的疑问:《七录》能否看作阮孝绪个人阅读史的总结?他举了两个例子,一是在阮孝绪家藏谶书,惧祸烧掉,这样恐怕也不会写进目录;二是阮孝绪在《七录序》末尾说朋友刘杳在这方面也有积累,并有底稿,后来送给了阮孝绪,也就是说《七录》里面应该包含了刘杳的目录。这样看来,阮孝绪的私人阅读与最终成形的《七录》之间是有间隙的。至于南朝的无兵文化,陈志远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七录》其实辑录的是前代书籍信息,《隋书·经籍志》著录兵书的主体继承《七录》,梁朝三帝也均有兵书著作。不重武事,只是梁朝的士人。他建议从目录学史的角度解释子书与兵书的合并,刘歆《七略》,《兵书略》不入诸子,因为刘歆主张诸子出于王官的解释架构,而兵书是任宏访求,自成体系。汉隋之际,出现了从“七”到“四”的趋势,所以不少类别的书目会合并在一起。目录的变迁反映的是整个社会知识结构的变化,而不一定带有阮孝绪很强烈的个人色彩。
吕博在回应时表示,综合讨论环节涉及佛教、道教、音韵学等很多问题,《七录》包括五十五个门类,而自己知识寡少,难以对每个门类有非常准确的把握,当继续努力,以臻完善。

陈志远
唐代宦游官人与地方社会
对唐代宦游文化的关注和研究是台湾唐史学界的一个特色。甘怀真《唐代官人的宦游生活——以经济生活为中心》、胡云薇《千里宦游成底事,每年风景是他乡——试论唐代的宦游与家庭》、郑雅如《“中央化”之后——唐代范阳卢氏大房宝素系的居住形态与迁移》是其显例。这次联谊会上,台湾大学历史系博士候选人黄庭硕继承了这一“传统”,他提交的论文名为《唐代宦游官人与地方:以颜真卿为例》,考察颜鲁公如何接触、融入地方既存的知识体系与文化社群,并尝试分析地方文化精英之构成。借用评议人陈志远的话,“本文侧重观察宦游官员与地方社会的互动关系”,“作者将地方视为一个意义系统,分为物与人。所谓物,是指宦游地方的文史知识、物质资产;所谓人,是指地方的人际网络”。作者将地方文化精英归结为两大类,即“地方型”文化精英和“外来型”文化精英,地方知识随宦游者的迁徙而传播,“造就出一个以京城为集结点的全国性知识网络”。

黄庭硕(中),左为吴承翰,右为蔡宗宪
专攻六朝佛教史的陈志远在评议中主要指出有两个问题:一是图经、地志的性质。图经、地志在全国范围内通行,很难说是一种地方文史知识,而且,宦游者的寻访、修复,“固然有助于为地方史迹扬名,更大程度上还是确认、修正全国范围内共享的既有知识”。二是湖州的特殊性。论文标题为“唐代宦游官人与地方”,而且没有指涉具体时段,是初唐、中唐还是晚唐?至于地方,唐代疆域辽阔,是北方、南方还是江南?文中最能支持作者论述的只有湖州一地,但湖州本身相当特殊,它是在安史之乱后随着经济重心南移、南方文化崛起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而且湖州与江南其他地方可能也不太一样。陈志远建议,相比于对人员的分析,更值得关注的是交往方式的变化,例如联句诗的产生与诗歌格律化的关系,诗僧参与联句所反映的僧俗关系的变化等等。
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李丹婕指出,就这个论题而言,白居易或许是一个更合适的例子,白一生多次在地方宦游,诗文书写中夹杂着来自京城与不同地区的闻见信息和生命经验,这些信息与经验又在新的见闻、不断回忆和一再书写中反复交织,形成不少有趣的对照,值得仔细挖掘。作者承认,这篇论文是在学习报告的基础上修订而成的,而有关白居易的材料相当多,要做个通盘梳理比较困难,时间和精力都不够。接着,李丹婕就“local”和“place”的概念提出疑问。这篇文章试图从“place”的立场来讨论“地方”,不过,不少引述材料所表现出来的“地方”其实是“local”的意义。比如文章提到浙东节度使鲍防在大历年间组织的联唱集团,这个诗人群写过两组相映成趣的诗,分别是《忆长安》和《状江南》,两组文本的主题、风格差异显著,而又形成特别微妙的对照,这里的江南,是带着深厚长安记忆或情结的人所见的“地方”,而非纯然客观自在的地方,这是应该仔细辨析的。厦门大学历史学系林昌丈指出文中所引一则材料的两处细节讹误,涉及历史文献和历史地理。

李丹婕
仇鹿鸣指出,魏晋与唐在史料构成上有不少差别,今人看到的魏晋是以正史为中心建构的,而唐代,尤其是中唐以后,由于文集的保存,凭借这些材料,可以看到更丰富的层面,而不会完全以正史为骨架来理解唐代社会。不过,颜真卿在宦游途中留下的与地方精英唱和的作品,是否真正构成一种“地方性”?因为唐代官员大都有过长安宦游的经验,他们在地方做官时也常常想起长安,如果只讨论“地方”,在某种程度上说是不充分的。仇鹿鸣建议作者围绕颜真卿的生平,探察他在长安和地方的经历,那么就要关注哪些“行为实践”是按照地方官的惯例操作的,哪些是有意为之。比如说编地志,到底是一种职务行为,而有的官员确实产生了地方认同,觉得要保存地方文化,就会投入很多精力,这两种情况显然是有差别的。

仇鹿鸣
陈侃理就这篇文章的写法谈了“一点感想”:标题中出现“以XX为例”,这种写法相当常见,但这种处理方式可能有一个适用的背景,那就是我们对那个大的问题缺乏了解,在这种情况下选取一个个案,尽可能通过个案把大问题讲清楚。这篇文章读下来,感觉它提供了很多细节,这些细节很有趣,但最后的结论有点平淡,好像没有提供太多突破既有认识的东西,这就使个案研究的价值似乎没有被凸显出来。如果能对唐代宦游官人与地方社会的关系做一个梳理,然后检查颜真卿这个个案能够提供以往大家不知道的东西,把这部分拿出来大书特书,这样的话读者更容易发现文章的亮点。

陈侃理
官制文本的史学分析
四川大学历史学院的黄桢今年7月刚在北大取得博士学位。他说自己做过第六届联谊会的会务,到了第十届终于有机会发表,感到很高兴。黄桢提交的《官制撰述在汉末的兴起》是他博士论文第一章的一部分。他在这篇论文里想讨论三个方面的问题:汉代晚期为什么会集中出现一批以官制为主要内容的专著?书写官制这种风气是怎样兴起的?这些现在被视作史料的文献,古人是出于什么目的编纂的,有什么功用?黄桢指出,以往大多数官制研究止于“史料分析”,未能充分把握官制文本的史学意义。在他看来,一方面,官僚制度的撰述是因“书写”而成立的,而“书写”是一种主观行为,如果关注撰述的开展过程,审视制度条文背后的意图和理念,有助于更为准确地理解官制文献;另一方面,这些著述的作者往往是行政运转和制度建设的参与者,考虑到当时的政治生态,这正是职官制度生发、演进的土壤。从这个意义上,考察官制撰述也有助于加深对制度史的认识。

黄桢(中),左为章名未,右为徐冲
日本鹿儿岛大学法文学部福永善隆担任评议人,他认为这是一篇相当细致的论文,其中第三节从小学书籍考察制度书写尤为精彩,显然他也赞同作者的观点——“小学书籍完全可以成为思想史的素材”。不过,福永也提醒作者关注政治层面的背景,“如果只专注在学术层面的问题的话,将会忽略其他重要的影响因素”。他还指出,官职撰述与律令和故事编纂、法典化的发展过程相同,如能参考法制史的相关研究成果,对官制撰在东汉末期兴起这个问题也许会有更深入的理解。

福永善隆
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周文俊认为这是一篇很有启发的论文,读了之后对制度文本的生成过程有了新的认识。接着,他对论文中“撰述”和“书写”两个概念的混用提出疑问,建议行文时稍作说明;他还提到,经学家为了解释经典中的制度,而辅以当时制度作为说明,这是否可以视为一种“制度书写”?
黄桢的论文认为,汉制书写有一个现实作用,可以为官员入朝提供指南。武汉大学历史学院薛梦潇就此提出疑问:胡广《汉官解诂》主要是对汉官职掌的解释,如果在仪节方面并未提供详细的说明,那么它的现实作用到底有几分?这里涉及《汉官解诂》的写作目的和阅读对象问题。

周文俊

薛梦潇
游逸飞认为,这是一篇拓荒性的文章,只要“历史书写”和制度史研究继续热门下去,它的引用率会很高。他结合自己的研究,指出这篇论文中引用到的湖北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秩律》,是荆州一个地方小吏的随葬品。为什么一个地方小吏一辈子没有进入中央,也几乎不会碰到那些官吏,却要抄录中央官制的细部内容?此外论文指出汉代学者在叙述当时官制的渊源时,存在从秦到周、“回向三代”的变迁,游逸飞认为论文对这段历史的叙述过于顺畅,在汉承秦制的脉络下将汉官上溯到秦官没有问题,但要将汉官进一步上溯到可能并无关系的周官,难道一点困难都没有产生吗?如果有,古人是如何解决的?另外,游逸飞还提出:官制的书写会不会反过来影响到制度的实践,从而引发官制改革?如果存在这种情况,魏晋以后根据周礼进行的官制改革,其远因是不是都可以追溯到东汉?
孙闻博表示他自己感兴趣的是卫宏的《汉旧仪》,该书问世时代较早,他问道:这部书在官制撰述史上处于怎样的位置?与汉末官制撰述的风气有何联系?另外,他向作者提供了一些材料,以便论文进一步修订完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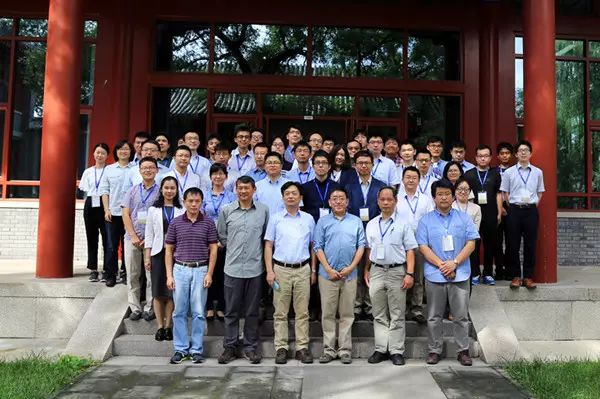
合影
限于时间和精力,对第十届联谊会的发表、评议和讨论只能作如上简单的介绍。与会者不难注意到,这次青年学者所提交的论文都有相当宏阔的视野,与前贤对话的雄心,并制定了下一步研究的计划。比如,周文俊报告的题目为《官职序列与品位结构:魏晋官品位序探微》,了解中国中古制度史研究的读者,一眼便知这是与阎步克先生“对话”的论作。日本立命馆大学文学部博士生小野响在《成汉政权初探——成汉革命与巴蜀人士》一文末尾表示:“笔者今后想做的是,进一步整理成与汉的国家制度,从而明确此类流民政权赖以存在的巴蜀地区有何地域特性,以及其在五胡十六国时代中处于怎样的位置。”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生章名未《制度书写中的“游戏”——从彩选到》受到了与会者高度赞扬,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徐冲就说,“我十多年前在北大读书的时候,阎步克老师就经常唠叨《西汉会要·班序》从哪来的,我自己也困惑很久了,想不到这次名未的论文近乎完美地解决了这一问题。”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叶炜在会议最后的发言是一个很好的总结,他说:“两天会议下来,有点儿暴饮暴食的感觉,一时半会儿不可能充分吸收。但这次联谊会报告的论文都很有特点,虽然在评论时有各种批评,包括研究方法、论证的过程、结论的表述,可能还存在不足之处。但不可否认的是,他们表现出对学术研究的真诚,对课题的投入,以及对自己研究的自信。这些就是他们带给学界的活力。”的确,就总体而言,中古史青年学者表现出一股赶超前贤的勇气和劲头,代表了新生力量茁壮成长的态势。
·END·

本文首发于《澎湃新闻·私家历史》,欢迎点击下载“澎湃新闻”app订阅。点击左下方“阅读原文”访问《上海书评》主页(shrb.thepaper.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