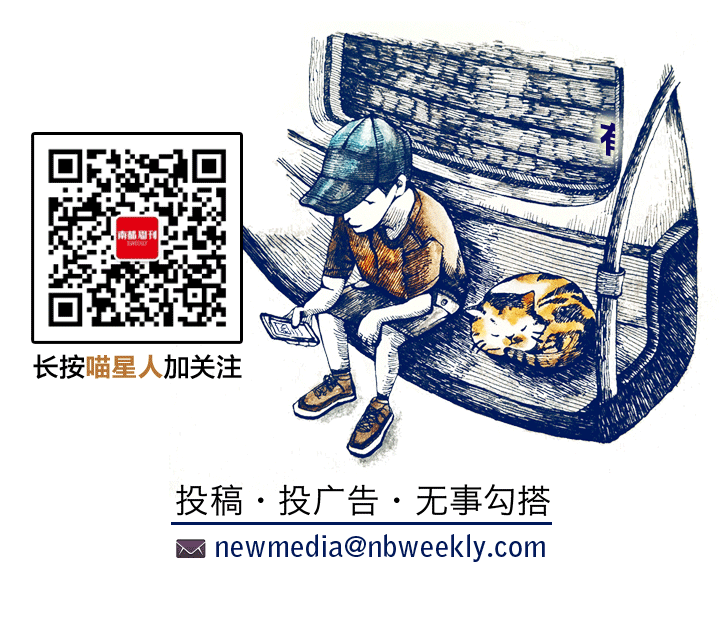封 面
《平原上的摩西》得到了文学圈的认可,双雪涛也成为了文坛上被频频讨论的人。他的作品里频频出现的父亲、拖拉机厂、艳粉街等等高频词汇,成为很多人试图解构和还原他生活的原点。
文|许智博 摄影|孙海 卢慧明
而立之前的分岔点
决定了双雪涛命运轨道改变的分岔点是2012年7月的一个晚上。在5个月之前,他拿到了台北关于资助作家创作台北题材长篇小说计划的项目入选通知。
这是他的处女作《翅鬼》在2010年台湾的一次文学奖上拔得头筹之后,宝岛上又一次对他投递过来的带着某种殷切希望的树枝,但对于大陆文学圈来说,这些奖项和写作计划,甚至是远流出版社为他出的小说单行本,都不足以吸引到资深文学编辑们的眼球。
但对于银行职员双雪涛来说,这个通知却仿佛一道催促他结束分裂生活的号角:两年前那次台北领奖之行回来后,上班的日子并未有任何改变:贴汇票、做表报、整理档案,活干完了就在电脑上看下载的电子书,领导来了便切换回EXCEL界面。不过他下班的生活变了,戒了讨好领导和同事的喝酒和应酬,回到家里,一边不断在烟灰缸里按灭快要燃尽的中南海,一边在电脑上凭直觉敲着一本回忆学生时代的小说《聋哑时代》。他把这部12万字的作品寄给了文学期刊《收获》,编辑打来了电话表示关注,但并没有发表。
接到通知后,他开始琢磨这辈子自己到底应该做什么,是不是应该担负起写作的责任,跟一眼可以望到几十年之后的银行职员生涯做一个决裂。这个炎热的晚上,纠结了小半年的双雪涛又像少年时代一样失眠了,他仿佛听见远处有另外一个自己,说:操,辞职吧。又觉得在天上不知道是什么神佛,说:辞职吧,没事儿,我挺你。
一夜未睡。天亮之前,选择的答案已经明晰,那天早上,眼睛肿胀但又内心澎湃的双雪涛,在外人看来,仿佛是以醉酒的状态,在上班时间之后冲进领导办公室,提出辞职。「我觉得领导仿佛闻到了我的酒气,但我真的一点儿也没喝。」
经历过经济衰败的辽沈大地,大多数尚未从计划经济时代思维方式里完全走出来、又对稳定生活有着极度需求的老百姓,对孩子最大的盼望就是能当公务员、进事业编、考进国企,为此甚至不惜找各种拐弯抹角的关系、拿出家里的所有的积蓄去「砸」。
所以在这家自成立小二十年来从未有过职工主动辞职的政策性银行里,双雪涛为了写小说而辞职成为了一个大新闻,不仅让领导第一次有了劝下属员工重新考虑一下离职请求的机会,也让负责人事工作的同事们第一次有了摸索办理辞职手续流程的尝试。
同事们的反应分成了三类,有人会带着恶意地劝他说「你先别着急回家写小说,你先去医院看看脑子是不是有病,是不是精神出了问题」;也有人是真的带着善意劝他不要舍弃已经到手的安稳;还有一类同样对体制内生活心有不甘的同事,则觉得双雪涛像是替他们疯了一把。
辞职手续办了一个月,办利索之后,双雪涛的《翅鬼》在大陆出版,出版社在沈阳为他举办了一场新书发布会,不少曾经的同事专程去排队买书为他捧场。沈阳当地一家都市报还对他进行了简单的采访,当记者文绉绉问他「放弃稳定的生活回归到追求梦想的道路上来,不会觉得冒险吗?」时,他回答说:「写作是我能够做好的事情之一,虽然收入不是很稳定,但是我希望不要辜负这一份可能。」
「现在再看,觉得自己的当时的回答有一种装B的感觉。」他说。「其实也是给自己打气吧,我是一个懦弱的人,干了一件疯癫的事儿。」
但那一刻,29岁的他就是那么想的,他觉得自己应该和自己喜欢的偶像之一村上春树一样。1978年4月1日下午一点半左右,29岁的爵士俱乐部老板村上春树决定写一篇小说,于是每晚在餐桌上挥笔不止,然后有了《且听风吟》的得奖和出版,两年后,村上春树为了专心创作,果断将酒吧转手,变成了专职作家。
「他说当时的心境就是别一起整两件事,想把好事儿都占了的心态,不适合写小说。我觉得大概是有道理的,人是很难成为A同时也成为B的,或者说,庸俗的人写小说总是差点意思。」他说,「我为了证明自己不是庸俗的人,就断了一把后路,人生第一次有点鲁莽。」
「当然,现在想起来有点后怕,这事儿干得太虎了。」他说,「万一沉了呢?」
穿越平庸的苦难
在这个「出名要趁早」的成功学年代,在而立前后敢于颠覆生活、取得成功的作家往往会被简单归于「大器晚成」的一类佳话,苦难也往往有被粉饰为美谈的倾向。假如苦难的内容只是物质上的窘迫,而非人命关天或千古奇冤,那么很多亲历者或许自己都不好意思认为自己承受过苦难。
作为东北重工业区的工人家庭的后代,1983年出生的双雪涛坦言:「我这三十几年一直活在经济的恐慌和压力之下。」
考察双雪涛童年时代的成长过程,恐怕很多出身普通的80后会有极深的代入感:小时候父母上班,扔给他几本连环画,把他在平房里锁上一天;上小学时要想方设法上重点小学,后来即便父母下岗,又逢「市场化」的教育改革,家里也要拼命勒紧裤腰带将他送到市里最好的初中、高中,面对功利的老师,在压抑的环境里枯燥地学习,高考后按照父母的实际考虑填上一个容易找到工作的法律专业,大学毕业后幸运地在银行得到了一个安稳的铁饭碗,算是用知识改变了命运,稍稍爬升了一个社会层级。
经济条件的窘迫确实一直贯穿于他的成长,1990年代初,父亲从拖拉机厂下岗后,家从沈阳市中心被迫搬到了当时还是沈阳城乡结合部的艳粉街,「艳粉街」的前身是浑河北岸的「艳粉屯」。在沈阳本地的东北口音里,「艳」字的读音为「胭」,还多少暗示着这个地区曾经为清代亲王府种植胭脂原料的历史,但后来无论是伪满洲国时期到解放前的砖窑厂,还是解放后地图上下左右到处带着「工」字的街道,都代表着这里的实地景象与名字意象之间的名不副实。
在双雪涛的记忆里,这个由2000多户平房像蚊香一样一圈圈盘起来的棚户区治安混乱,「刑满释放人员、诈骗犯、妓女、残障人士,还有一些想涌入城市又失败退回来的农民都聚在那一片」。与市里同学家的有线电视能收到几十个台不同,在这里,「电视只有两个台,中央一和中央二」。家里没有电话,不能约同学玩的双雪涛,会在艳粉街后面的煤场和庄稼地里没有目标地漫步,然后再沿着铁路的铁轨寻找回家的方向。
艳粉街的平房年岁太久,在土地每年一冻一化的循环中地基逐渐下陷,所以密集的房子之间或泥泞或冻硬的路面总是比门槛高一截,要是下大雪积雪,双雪涛的父亲就要先从窗户拎着铁锹跳出去,将门前的雪铲了才能开门。在这些平房里长出来的孩子们一般都野,王兵在《铁西区》里拍到他们无所事事杀时间的状态只是生活的一面,匮乏让他们奉行丛林法则,双雪涛的零花钱总是被大孩子们抢去,即便是女孩也一样彪悍,双雪涛有次冬天斗胆打架将邻居一个女孩的头发薅掉一撮,这个常年被家暴的女孩就在当晚偷偷卸掉了他家房子的门,把一家人在半夜生生冻醒。次日双雪涛找她道歉,她扇了他几嘴巴才把门还回去。
就是在这样的冬天里,父亲每天要花差不多40分钟,骑车送他去市里最好的小学、初中去上学,如果遇到大雪,路程便会耗去他们两个小时的时间。有次父亲踏着车,感觉自行车死活蹬不动,问儿子怎么回事,低头一看,原来是后座双雪涛冻僵的脚别进了车轮的辐条里,父子二人赶紧往医院跑。
在他离开艳粉街之前的16岁,还是有一件事情让他感受到了某种冲击:一个在艳粉街摆修车摊的中年师傅,居然是当年某起轰动辽沈的抢劫杀人案的从犯之一。这个系列案件的几个主犯们作恶多年,杀了不少人,抢劫上百万元,这个修车师傅的分工就给他们准备绳索、踩点、放哨。这个人平时为人低调,还会给孩子做冰尜(东北人在冰上玩的类似陀螺的玩具,用鞭子抽打而转动),在艳粉街那些不愿意、或者说没有能力供孩子读书的父母们当中,他却愿意花钱供女儿读书、出国,成为一个格格不入的传奇。
那时的双雪涛压抑着心里的叛逆,努力做着符合父母期望的那种好学生,从小学到高中,情绪随着是否有老师欣赏他或是否有同学能接纳他而产生起伏,在孤独和快乐的交替中,穿越过了这种平庸的苦难。
只不过,他在成年自后,没有像一些好面子的东北人那样,将这段微不足道又难以启齿的回忆选择性忘记。

王小波
——那是我想成为的人啊
除了超人的叙述天赋和想象力,从小到大没有间断过的阅读习惯也是那股将双雪涛推向写小说的动力之一。
「有时我会经常为了阅读而写作,一旦被阅读击中,就有写的欲望。」
喜爱阅读无疑是父亲给他的馈赠。父亲曾是知识青年,下乡时酷爱读书,「什么书都看」,「带字儿的就是好」,后来回城做了工人,依然视读书为极大的消遣和乐趣。在上学的路上,父亲一边在前面骑着车为他挡着风,一边会把武侠小说里的故事复述给他听。那时上小学的双雪涛已经开始看各种作文选,但却发现父亲从书里看来的故事远非作文选里的文字可比。
可惜父亲的武侠小说总是不全,「《碧血剑》缺结尾,《笑傲江湖》少开头」。对故事的好奇心,驱使双雪涛求着父亲给他办了张区图书馆的图书卡,到了小学六年级,「金庸的所有小说,古龙的代表作,福尔摩斯探案集,基督山伯爵,傲慢与偏见,巴黎圣母院,如此等等,大概都看了一些,所写作文也去过去大不相同。」
那时的双雪涛已经开始将零花钱省下来买《读者》,在家里的老房子被拆迁之后、去艳粉街租房子住之前的短暂时光里,双雪涛一家三口搬到父亲的工厂,住在车间里。「就是在那生铁桌台上,我第一次读到《我与地坛》,《读者》上的节选。」他后来写文字回忆说,「过去所有读过的东西都消失了,只剩下这一篇东西,文字之美,之深邃,之博远,把我从机器的轰鸣声之裹挟而去,立在那荒废的园子里,看一个老人在园里里呼唤她的儿子。」
写作的启蒙来源于双雪涛的小学班主任,她同时兼任语文和数学两科教学,却更醉心诗词,每天自习课时她都把宋词抄在黑板上,谁背得快谁就可以出去玩耍。双雪涛背得好,老师便青眼有加,开始定期审阅他的日记,于是少年写起日记便更加卖力。
初中不再有赏识他写作方式的语文老师,双雪涛便「升级」到市图书馆疯狂看书。到了高中,新的语文老师给他的作文格外好评,再次点燃了少年心里的火苗,为了可以写得更好,双雪涛更加疯狂地咀嚼、吸收着现当代作家的精华作品,被余华这样的先锋派作家们的文字深深影响。他写作文时经常「嫌作文本的格子框人,就写在八开的大白纸上,蝇头小字,密密麻麻」。高中毕业前,他写了一篇《复仇》,「写一个孩子跋山涉水为父报仇,寻找的过程大概写了近两千字,结尾却没有,老师也给我了很好的分数,装作这是一篇作文。」
虽然父亲将他带入了阅读之门,但却觉得靠文字吃饭是一件荒唐的事情。「我爸说,当作家,那不都精神病吗?生活在自己世界里,吃也吃不香,喝也喝不下。可不能当精神病,还得当正常人啊。」当自己成为了这个家庭未来的希望,心里自然就会形成某种负担。高考填志愿时,双雪涛放弃了中文系,而是选择了吉林大学的法律系。
大学四年,双雪涛几乎只字未写,学校图书馆管理方式陈旧,无法自由挑书,所以他胡乱看书之余,也将不少的时间交给了魔兽争霸和长春麻将。直到看到王小波,他想,「那是我想成为的人啊」。
上班之后,阅读变成了工作时的副业,做完一颗八小时的螺丝钉之后,他偶尔开始写写影评。直到工作三年后,一个朋友看到《南方周末》上的一个台湾文学奖的征稿启事,奖金不少,问他要不要试试。他算了算,六十万新台币大约相当于十五万人民币,足够在沈阳交房子的首付了。
于是,他花二十五天写出了处女作《翅鬼》,虚构了一个封闭的雪国和一群长着翅膀在井下做工的奴隶,写他们想飞的「历史寓言故事」。这篇后来被大陆出版社划归进玄幻小说的作品,被台湾的评委们视为严肃的佳作,一下摘得了头名。
描述父辈的跌宕起伏
还有猝不及防
辞职,开弓没有回头箭。
双雪涛没有怠惰,经过短暂的准备后,在2012年入冬时,开始创作那个拿到资助的小说。他像村上春树一样将写作变成打卡模式,每天到自己的新房子里「上班」,在前任房主留下来的一张铁桌子上写作。房子空空荡荡,供暖的管道堵塞了,冻手冻脚,他就不停地喝热水。文思堵塞的时候,便下楼去看路边的老头们下棋。
三个月后,第二部作品《天吾手记》诞生,双雪涛用这部十几万字的小说,向自己当时特别喜欢的村上春树做了一次致敬,但它和《翅鬼》一样,并没有奠定双雪涛的写作风格。
就在这个当口,《收获》的编辑建议他将之前写好的《聋哑时代》里个别的章节改成中篇试试,于是他便抽出了《安娜》和《我的朋友安德烈》。这种尝试让他上瘾,在随后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他连续写了十几个中短篇小说。
在这些作品里,后来被很多人称赞的短篇小说《大师》,则奠定了双雪涛目前的写作风格:他将日常的东北话纯熟地放进了小说的叙述里,短句、对话你来我往,却绝对没有抖包袱式的低俗,字里行间夹杂着一种经历过困苦的人特有的自嘲和黑色幽默,以及残酷和决绝。
在这之前,双雪涛也尝试过不少成名的先锋派作家的行文风格,却像练刀者使剑一样,虽然招式像那么回事,但自己总觉得不顺手。写完《大师》,他觉得,嗯,现在像样了。「就像每个人走路都有自己的频率和平衡感,找到了,就不别扭了。」
《大师》能成为双雪涛找到感觉的作品,变成他的LUCKY BOOK,既像掌管灵感的神在背后偷偷捅了他一下,似乎又像是来自父亲的庇佑:小说那个棋艺超群的下岗工人的原型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来源于他的父亲。父亲除了看书就是嗜棋,即便炒菜,也常常一手颠勺一手棋谱,在双雪涛的眼里,父亲为了磨练棋艺付出与收获不成比例,但「这种技艺却只能在特定的属于他的场域才能释放,让人得到精神上的满足」。
写这篇小说时,双雪涛也刚为人父亲。辞职之后,犹如一个人在汪洋大海里游泳,写作从一件牛逼的事情变成了打发时间的东西,压力山大与光明前景交替闪烁,「想起尿不湿的价格,实在不容易入睡。未来就像一条幽暗的隧道,时有微光闪过,但是看不清隧道那头是啥东西。我整三十岁,感到恐惧。」
他磨砺着写作的技艺、但却不确定这技艺能否给自己带来尊严的时候,就会想到父亲痴迷在路边摊下棋。「当时他已去世,我无限地怀念他,希望和他聊聊,希望他能告诉我,是不是值得。当时已无法做到,只能写个东西,装作他在和我交谈」。
经过两年的沉淀,双雪涛又产生了讲新故事的冲动。2014年,他花了一年的时间,创作、修改,反反复复改了七八稿,终于完成了让更多人赞誉的《平原上的摩西》——一部中篇小说,三万多字。
这部小说的创作初衷,双雪涛只是想写「一个跨度比较大的,多角度叙述的」的作品,「反映一点东北人的思想、特有的行为习惯」。
正如他之前凭着对少年时学校的记忆写了《聋哑时代》,这一次他又想写大工厂:「东北人下岗时,东北三省上百万人下岗,而且都是青壮劳力,是很可怕的。那时抢五块钱就把人弄死了,这些人找不到地方挣钱,出了很大问题,但这段历史被遮蔽掉了,很多人不写。我想,那就我来吧。」
于是,一个交织着大案、下岗、棚户区底层生活、两代人爱恨的画卷,被他用书面语写成地道的东北话,用七八个角色的视角,虚虚实实地描绘、还原出来。
初稿出来之后,他总觉得有很多漏洞,最后导致了用写一部长篇小说该用的时间写了一部中篇小说。正是这种严谨的态度,让那些被千禧年之后搭建在棚户区和旧工厂上面的住宅楼盘、商超、写字楼所掩盖起来的辛酸困苦、粗糙暴戾,再次栩栩如生。父辈一代生命体验的「跌宕起伏和猝不及防」,勤勤恳恳却被 时代裹挟、玩弄于股掌之间变成一个失败者的忍受或抗争,历历在目。
在双雪涛的视角里,自己与上一代人的情感纽带关系简单而朴实:「父母其实也明白没有能力左右我的命运,他们把我培养成了一个跟他们不一样的人,就达到目的了。普通家庭的矛盾一般是生存问题,大家都是一个目标,想着怎么把日子过好,把书念好。我们之间不存在其他形而上的问题。」
不要离开地面
也不能陷入泥潭
《平原上的摩西》很快就得到了文学圈的认可,双雪涛也成为了文坛上被频频讨论的人。他的作品里频频出现的父亲、拖拉机厂、艳粉街等等高频词汇,成为很多人试图解构和还原他生活的原点。
「其实这涉及到‘真实’的概念,我们怎么看待这个世界,就怎么看待自己的写作。这些被反复提及的词汇,肯定是我印象比较深的东西,我看中的东西。」双雪涛说,「换句话说,它们也是我愿意反复虚构的东西,我虚构了一个艳粉街,艳粉街早已经不存在,我的印象也已经模糊。小说永远代替不了历史,我的小说是个人的精神史,而不是生活的历史。」
初入文学圈,每隔一段时间,他都找小时候一起长大的朋友见面。「我有恐惧,害怕离开生活。现在圈子不一样了,他们当律师、在银行、干什么的都有,但我要是有一段时间不见他们就觉得自己状态不对,心虚。」
从《翅鬼》到《平原上的摩西》,再到后来创作的《光明堂》、《北方化为乌有》和刚刚在期刊上发表的《飞行家》,双雪涛的小说里还有着另外一种隐性的意向:它可能是一对翅膀、一个一直想南下的女人、或者是一个飞向天空的热气球。这些「设定」在小说里总是有意无意出现,令人想起贾樟柯的电影里那些「乱入」的符号化道具。
双雪涛想要借此表达自己对自由的向往:「这是一个永恒的文学主题,包法利夫人的主题也是一样的,挣脱所有的束缚,我内心是个自由主义者,对我来说自由是一件特别牛逼的事儿,但世界上没有真正的自由,是个巨大的悖论。」
在2015年3月《平原上的摩西》发表之前,双雪涛辞职3年的写作生活变化很小,闭门写作、每天看着儿子的枯燥生活几乎将他逼到崩溃。
在作品得到关注之后,有前辈作家邀请他到北京读书进修,他欣然应允——「因为住宿舍很便宜」。
有时双雪涛觉得自己是一个分裂的人,因为「作为东北人有一种牢固的集体观念,很多生活的观念」,但「我又是一个叛徒」,因为他觉得自己并不只是为东北人写作。
双雪涛喜欢北京这种乱糟糟的活力,在北京,他遇到了无数东北人说他的小说唤醒了他们的记忆,也有来自湖北黄冈的电影人情绪激动扑腾跪下,说《聋哑时代》让他重温了一遍自己的少年时代。
「所以地域性只是简化人的一种方式,总体来说人是相通的。」他说,「我的小说其实在东北的杂志上发表的很少,发表最多的反而在上海。」
在北京,双雪涛卖出了几部小说的影视版权,交了不少新的朋友,找到了可以踢球的球队,也多了许多需要应酬的琐事。但固定不变的,是半个月乘坐高铁回到沈阳一次,看望家人,这种双城生活,至少要维持到他读完书再做打算。
他有时在作品的自序里自黑:「每天有无数必须回复的微信,几乎每月都要准备一个讲稿。之前经常蓬头垢面,胡子拉碴,挽着裤腿东走西走,今年这些情况渐少,因为有些场合要登台,有时候在镜子里一看,把自己收拾得干干净净,一时无法相认。才终于明白,之前对自己有些误解,以为自己是个老实人,其实不然,对虚名之在意,为目的之手段,一直从未放松。」
比如去广州录制「一席」的讲演,遇到飞机延误,凌晨才落地,被出租车拉到酒店眯了两个小时不到,便撑起自己杀奔录节目的剧场,一上台,看着下面的观众,「眼睛里都是重儿影。」只能咬着牙,用东北话把故事讲完。
渐渐的,跳出东北的双雪涛发现他对沈阳的感情有些微妙的变化,很多看法变得跟以前不同,有时在沈阳呆得时间长了就会觉得不自在。这种变化同样悄悄体现在这两年的新作里,故事的时空背景像他的生活一样,经常是现实的北京与曾经的沈阳穿插出现,有些新鲜的东西,正在刺激着他潜意识地进行某种新的尝试和改变。
他喜欢北京这种「恰当的自由」。
「哪哪看着都乱糟糟的,有钱人和打工仔挤在一个地铁,有很多问题,但同样有活力。一个作家坐在家里煞有介事的生活是危险的,没有真实的生活、朋友、世界,为了写而活,会有问题。」他说,「不要离开地面,但也不能陷入泥潭。」
「我喜欢被人尊重,也喜欢有自由的经济条件,分寸在于绝大部分时间你在思考什么事情——是思考如何把自己的活儿干好、还是想着让更多的人知道自己,最后还是看你是不是对写作上心。」双雪涛直率地说,「人都贪心,想干很多事情,但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一个作家得知道带给你所有东西的那个‘一’是什么,就是一把枯燥的椅子,还是硬的。」
文章选自《南都周刊》2017年第11期▼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