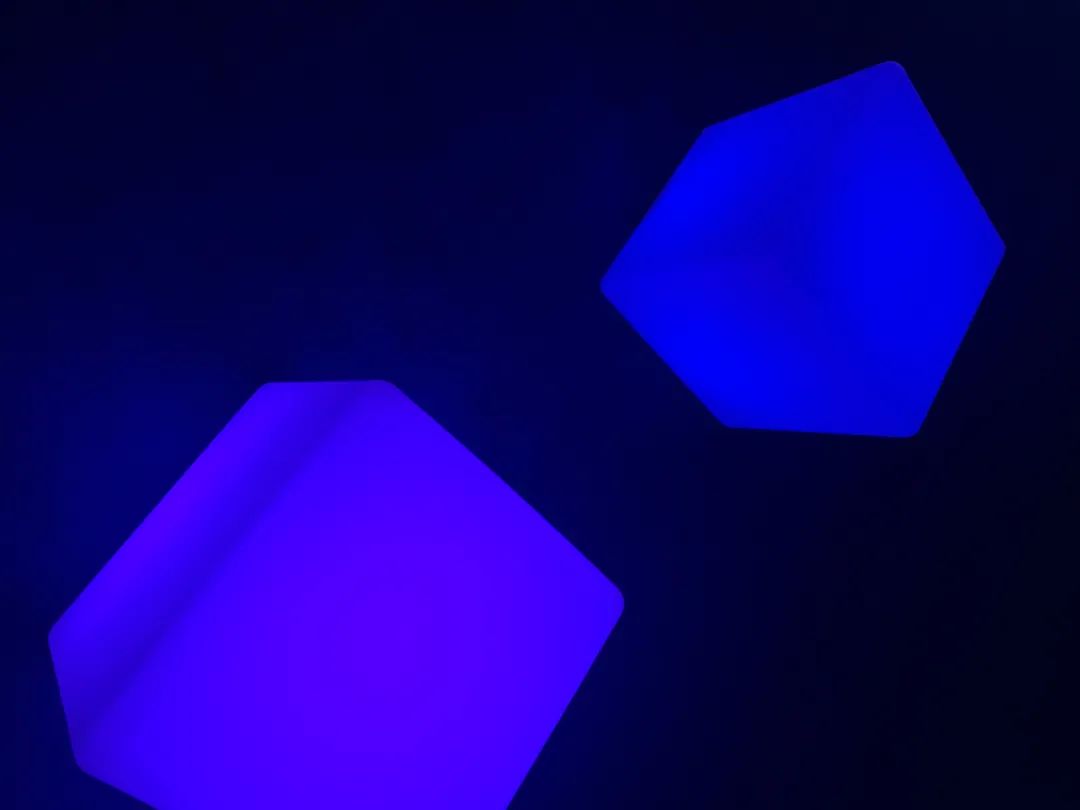
塔林
五座塔都是佛教祖师的塔,至于是谁的祖师,哪家的祖师,并不重要,知道是祖师就够了,只要纳头便拜就对了。所谓“礼多人不怪”,那“头多磕也没人怪”。还特地花钱请了导游讲解祖师爷们的事迹,当谈到塔的层数的时候,导游老郭附体般——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十三层……这十三层啊,代表着佛教修行的阶位,一层一层往上修,修到最高的佛祖就是第十三层……
诸师面面相觑,又暗自庆幸,无用的知识又增加了一些。
听完祖师爷们的故事,一定要爬爬后面的山,“走过他来时的路”,也想象着祖师爷们在禅凳上坐的上火的时候,爬爬山,登登高,呼吸一下新鲜空气,时不时的吼上两嗓子,回去一定可以坐一支好香。风和日丽,近处的松柏青翠欲滴;春意盎然,远处的山花开得正在兴头。一路不断感慨,由于没有文化,只能不断说美!好美!真是美!有文化的师父们时而言“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时而说“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时而感叹“桃花一簇开无主,可爱深红爱浅红?”,时而欢呼“梦回人远许多愁,只在梨花风雨处”。这许多的风雅附庸完,总觉得不够尽兴,似乎缺少点什么,以致心中的情绪表达的不够透彻、完全。
到一崖边,崖极陡峭,崖边一棵硕大的山桃树甚是活泼,崖上的老松扣抓在崖缝中,看那远处群山蔓延,稳坐于碧空之下,一师感慨道:“如此壮丽之景,不知塔中的祖师当年是否也曾见闻啊!”“自然也曾见闻,想是比今日更妙上几分。”“不知行状如斯,见此景作何言语?”“定是直透本地风光,作崖上狮子吼吧!”“祖师作何言语某不知,临着此景,若不假思索,且胸臆直达,非扶栏国骂不可也,须深吸气,一气到底,方可透彻、完全、淋漓尽致也!”
北海
花开正艳,与道长相约共游北海,原本僧有数人,道有数人,到北海,仅两人,因缘常常就是如此,不必管它。在人群之中,两人并步同行,道长头戴黑色庄子巾,脚蹬双梁云勾鞋,一身青色道袍,甚是飒爽英姿;法师头戴灰色瓜皮帽,脚穿六洞罗汉鞋,一袭暗黄色大褂也别有一番味道。来往人群中,不时迎来频频的观望。成年人们想多看几眼这奇怪的组合,但又不好意思,只能偶尔用眼角瞥上几眼,或等两人走过才敢直勾勾的望着,想必心里在琢磨:“cosplay?傻帽?”。这点倒不如孩童,迎面看到这一对“活宝”便瞪大眼珠子一动不动的看着,撞上目光也不躲闪,还是就这么盯着,估计心里在想:“这是哪里来的怪叔叔?”还会奔跑着告诉小伙伴,像发现了什么惊天秘密似的。
两人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四面八方看这俩人,不时的从人群中模模糊糊传出一两个“和尚”、“道士”的单词。忽然间想到之前一位法师遇到有人对他大喊“和尚,和尚,光头和尚”时他的应对,便笑了起来,道长问为何发笑,我告诉他那位法师的应对方式,他也哈哈大笑。问:是如何应对?答:那法师两眼一瞪,喝到:“和尚是你爹!”如此炸裂的方式,想来是难以普遍适用和推广的。仅此一提,谨慎模仿!
在这暖风习习的北海,一僧一道给众人贡献了一道别致的风景,于日复一日的岁月中或给予谈资或带来启示。佛经有言,在法灭时代,一人因发疯而穿上了修道人的服装,他走在路上被人看见,即有无量功德。因为在无人修行的世界里,让人们看到了一个修行者的形象,哪怕是疯子的无意之举,也会在人们的心里种下一个种子。如同暗夜里的烛火,即使不能带来长足的温暖,也能给予光明和希望。
有偈曰:
大道同一天,虎溪老衲仙。
青鸾舞方丈,黄鹤鸣须山。
连翘消众厄,海棠除毒缠。
共情因缘世,山岗牧云烟。
798
诸师结伴去看艺术展,艺术街区不常去,倒不是因为不适合,而是本就觉得自身的存在就是最大的艺术了,除了博物馆里玻璃橱窗里的“老古董”,还有什么能像这种生活方式一般活泼泼、灵动动的保存到现在?站在艺术街区,那一身服装,走起路来就是一种最直接的表达,佛教术语叫“表法”,用艺术的话来说,应当是属于行为艺术吧?甭管什么艺术,都是在表达,用着各种各样的方式。院里师父们贴玻璃的一张张纸,被煞有介事的贴上了名称、艺术家、价格。贴标签的法师很认真的说:“不要笑,请认真点,我很严肃的,我是在极其严肃的……开玩笑!”
走到一现代艺术的展览馆,表达的意思是看懂了,对时代的反思。各种被特意挑选、组合、分离的零零散散的零零碎碎。眼见一扫把和簸箕,刚想感慨——艺术的表达竟可以如此出乎意料。一大爷过来:“麻烦让一下!”说着便把这两件“艺术品”拿到旁边用了起来。
逛了大半天,累的坐在路边的长凳上,一师说:“艺术真实迷人的东西,你看表达的方式多样、有趣,每一种都能给人带来不一样的感受。”一师回:“最有趣的还是人,没有人的分别和执着,这一切都不会存在,我就喜欢人。”说着眼盯着三三两两的路人。
一阵风吹起,风携带来食物的味道,几人刷的同时站起:“走!去下一个艺术中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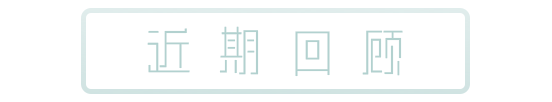
横竖纵身一试
透网之鳞
有情心地自光明
在“信”的加持下
不信如来
“悉达多”的心思
心无挂碍,无有恐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