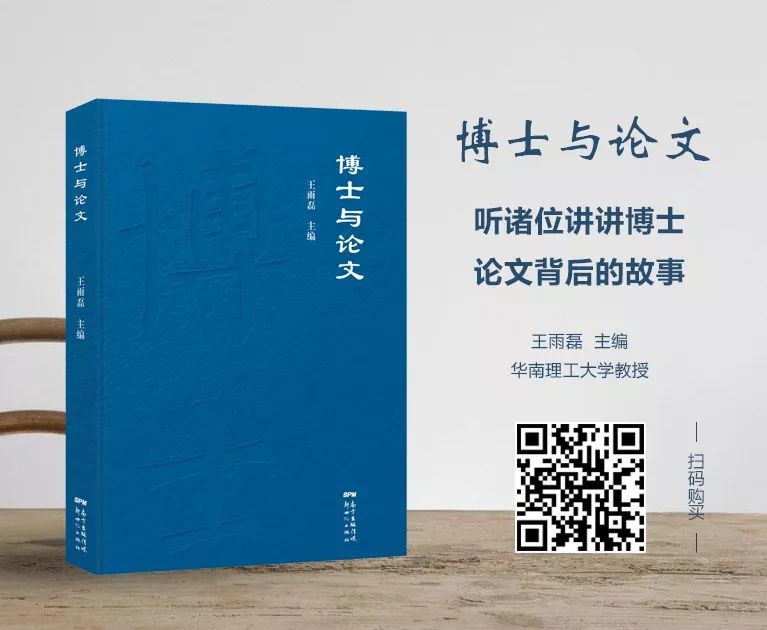【石头引】
2020马上来了,时间还真是快呀!这个专栏也马上要进入“80期”高龄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前段时间指导我们研究生班的同学们办了一期博学论坛的
“
碰碰
会”
,请了一些朋友来分享研究心得与历程,现场反响挺好。一直有读友在催《博士与论文》的新书见面会,元旦后我准备做一个新活动,请一些学者来当面讲一讲自己的博士论文经历,有兴趣的读友可以来现场。本期嘉宾我们邀请到季程远博士,让我们听听他的分享!
【作者简介】
季程远,
江苏张家港人,现为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比较政治系助理教授,北京大学政治学博士,哈佛大学访问学者(2016-2017)。发表论文见于Political Research Quarterly、《政治学研究》、《中国行政管理》、《社会》等刊物。研究兴趣集中于基于抽样调查的政治文化研究和基于文本大数据的政治传播研究。
【写在前面】
感谢耿曙老师的引荐、石头君的首肯与包容(确实拖延很久),让我有机会对我的博士论文和学术旅途有一些总结。
我时常想,从苏州大学开始,浙大、北大,再到哈佛访学,我的学术旅途无比幸运,以“中国公共管理与政治学研究方法暑期培训班”为代表的培训班、“万卷方法”的大量研究方法译作、北京大学中国国情研究中心的经历,是沿途最重要的站点,它们的出现于我而言是充满偶然性的。
但是,与首富们津津乐道于生财有道而忽略改革开放的春风不同,我的学术旅途,要感激中国政治学实证研究整体性地快速发展,登上这样的列车,让偶然成为可能。
一、博士论文选题:
中国现实与西方理论
我的博士论文题目是《中国社会何以稳定:
基于公众获得感的解释》,Puzzle在于中国现代化进程导致了高度的不平等,西方的理论推演表明中国应当崩溃甚至民主化,而中国事实上维持了整体性的社会稳定。
中国的现实对于西方理论提出了挑战,如何解释这种理论与现实的冲突,就是我的论文的出发点。
显然,解释的路径有很多,也的确有很多的论文和著作。
大众心理层面的既有理论认为,客观不平等引发公众的相对剥夺感,相对剥夺感积聚无法化解,使得公众质疑社会整体的公平性,最终引发对现有体制的不满和反叛,酿成政治不稳定。
我的解释来自于对相对剥夺感的重新挖掘,因为这一路径容易忽略相对剥夺感的时间维度。
中国的快速现代化产出了不平等,以及对比他人的相对剥夺感,也产出了时间比较维度的获得,两相权衡,使得大众的相对剥夺感维持在一个可控的水平,最终成为社会稳定的大众心理基础。
这一研究问题和解释视角是我在2017年7月中旬的一天突然萌发的,距离导师王浦劬老师到波士顿还有1周,距离我结束哈佛访学还有1个月,距离我博士毕业还有1年,可以说,对于一个准毕业生而言,博士论文选题的确定已经非常迫切了。
论文选题在当时是灵光一现,但站在今天回望,的确不是一蹴而就、自然而然地出现在脑海中的,最终是自己长期研究关注的一个走向。
首先是中国家庭金融调查公布基尼系数后的一次大讨论,其次是在北京大学中国国情研究中心作为研究助理对接的第一个大型调查,再次是谢宇老师在北大国发院的一次报告,最后是纪录片《将改革进行到底》让我了解到获得感这一词汇。
容我慢慢道来,一些观察与体悟也在其中。
(图中右一为导师王浦劬教授,中间为政治学“五老”中的赵宝煦教授)
基尼系数是测量不平等的一个关键指标,在国际上,基尼系数高于0.4就已经超过警戒水平。
中国官方公布2000年基尼系数为0.412,此后停止发布,第三方也鲜有令人信服的数字。
惊雷来自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高起点的各方面配置使得其结果具有重要价值。
2012年底,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根据第一轮调查的测算,举行发布会,指出中国家庭收入的基尼系数在2010年已经高达0.61,这可能超出了最乐观专家的预期,在国际上,基尼系数超过0.6的国家大多处于动乱之中。
为此,各方专家学者展开了激烈的讨论,以至于国家统计局在1个月后发布了2003年至2012年全国居民收入的官方版基尼系数。
这与当下二胎政策后出生人口到底是多少的争论有些相似,显然,基尼系数、出生人口数不是简单的数字,背后是事关国计民生的宏观判断,所以专家学者的争论才如此重要。
这种大规模的抠具体细节的争论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也让我意识到不平等与政治稳定之间的关联。
2014年9月进入北京大学后,我即进入了北京大学中国国情研究中心,一方面是严洁老师的邀请,更重要的是我对这一中心的向往。
这种向往来自于我的第一次学术会议经历。
2013年12月,我还在浙大读研期间,参加了复旦大学举办的全国政治学博士生学术论坛。
这一经历于我而言是无比重要的,首先第一次参会就拿到了二等奖,坚定了我走学术这条不归路的信念;
其次,我见识了高水平学术的模样,当时主旨演讲的阵容、评议的阵容都很强大,包括唐世平老师、耿曙老师、陈慧荣老师、包刚升老师、李辉老师等,参会的博士生水平也都很高,有很多现在已经在各大高校任教,包括我现在交大的两位同事;
最后,两位北大博士王衡和臧雷振师兄的汇报使用了同一份数据,即北京大学中国国情研究中心执行的2008年亚洲民主动态调查数据,我是第一次知道有政治学相关变量如此丰富的调查,第一次了解到北京大学中国国情研究中心。
因为当时在浙大读研的自己已经深感数据为王的道理,参会的论文虽然获奖了,也尽量使用基于宿舍为总体的抽样调查数据,但靠一个学生自己去设计问卷、执行调查显然没有任何性价比。
这让我萌发了考入北大的念头,最后梦想成真得感谢王衡师兄的考博指导。
因而来到北大并没有特别多的犹豫,我就成为了中心的研究助理。
北京大学中国国情研究中心在90年代沈明明老师接手后,密歇根大学抽样调查的流程随即搬到了这里。
中心的研究助理通常会独立对接至少一个大型社会调查项目,从与外方专家沟通、问卷设计、抽样设计到调查执行、数据库建立和清理、调查报告撰写都属于研究助理的工作,因而如果在中心有1到2个大型调查的研究助理经历,其所学会远远超出看几本教科书学得的知识。
我作为研究助理接手的第一个项目就是“2014年不平等与分配公正调查”,当时数据录入工作已经完成,我的工作是数据库的建立和清理,以及执行报告、codebook等的制作,当然一切在严洁老师的指挥下。
后知后觉的我并不知道这项调查实际上大有来头,2004年和2009年已经有过两波调查,2014年为第三波调查,这一调查的前两波的负责人是哈佛大学社会学系Martin Whyte教授,他的著作Myth of the Social Volcano: Perceptionsof Inequality and Distributive Injustice in Contemporary China即基于调查完成,也从微观视角讨论了中国的大众为何容忍不平等这一问题。
2009年的研究助理是孟天广老师,他的博士论文是我的重点模仿对象,分配政治也大概与这一项目有密切关系。
对于当时的我而言,一遍又一遍地清理数据库中几百个变量的过程,让我迅速对问卷熟悉了起来,也很自然地去揣摩设计者一组问题的测量概念究竟是什么。
这份问卷涉及了大量与不平等和公平正义相关的测量,成为我博士论文中使用的关键数据。
2015年5月下旬,北大国发院召开了“中国的不平等:
来自前沿微观数据的证据”的专题会议,请来了谢宇、李实、甘犁等大人物,印象最深的还是谢宇老师的发言。
谢宇老师展示了基于CFPS、CHIP、CGSS、CLDS等调查数据测算的中国收入基尼系数的变化图(来源于2014年PNAS上的论文),结果是2012年之前中国收入基尼系数一路上扬。
同时,他并谈到收入基尼系数还不计算房产,如果考虑这一因素,基尼系数可能更高。
但引人思考的不是基尼系数的计算,而是他讨论了为什么这么高的基尼系数,中国依然稳定的问题。
的确,中国的基尼系数无论官方还是学术测算的结果都很高,都超过了警戒线,但就个人生活中的体验而言,完全没有那种社会不稳、行将崩溃的感觉。
那么显然,单纯讨论基尼系数有多高就没有考虑中国的语境。
谢宇教授分享了发表于《社会》的文章的一些思考(后来看过文献才意识到),包括民众可能低估不平等的程度(个体生活于集体之中,集体之中的不平等程度更小),以及中国文化中更强调机会公平的因素,总而言之,就是中国社会不平等的问题本身在当今中国不太可能造成政治和社会的不稳定。
这打开了我的视野,不平等很重要,不平等的程度很高,但中国依然可以不那么当一回事,是有一些解释的,而且是一些可操作、可验证的解释。
获得感出现在官方话语体系中可以追溯到2015年2月的中央深改会议,但出现在我的视野中是2017年7月的纪录片《将改革进行到底》。
在国外期间,国内的很多资源是不大好用的,但是哔哩哔哩无广告、高分辨率纪录片的特性进入了我的生活,每两周的纪录片播放榜单是重要关注对象。
《将改革进行到底》是当时双周榜单的一员,最后一集的题目是《人民的获得感》。
获得感的确是一个好词,我迅速意识到这个词在不平等与社会稳定关系中可以扮演关键的角色,因为获得感天然就强调时间比较的维度,而相对剥夺天然就更关注与他人比较的维度,两者是同一个概念的两个维度。
中国的不平等程度的确很高,也必然引发大众的相对剥夺感,但相对剥夺感加入时间比较维度后,就复杂了,因为相对剥夺感就会同时受到客观不平等负面影响,和高速经济发展、社会保护制度建立等因素带来的正面影响。
我迅速找到不平等与分配公正调查数据,试着跑了数据后,我发现基本结果与设想一致,博士论文的选题由此确定下来。
实际上,这是我博士论文的第三个选题,第一个政府创新可持续性的研究计划因为数据不可及而只具备开题报告意义,第二个腐败议题因为敏感性而搁置,导师王老师对于这一选题也迅速表示肯定并提出了很多建议,这让我在波士顿见到他的时候没有那么忐忑。
后面王老师对于论文一些章节逐字逐句的修改大概与他对选题的肯定密不可分。
回望这一选题,能够从一个西方理论与中国实践冲突的puzzle出发,当是国内政治学博士选题的不错视角,理论和实践价值兼顾。
我领会到这一点还是经历了太长的时间。
同时,在这些经历中,中国社会科学的快速发展是重要的背景,围绕学术问题的争鸣、留美博士或美国教授回国并将一些前沿研究方法和方式带回国内、中外学者更加频繁交流、更多的博士生讨论平台等等因素让诸多偶然成为了可能,帮助我形成博士论文的选题。
我的博士论文指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战略和持续的再分配改革,从整体上塑造了有利于政治稳定的大众政治心理。
具体机制上,得益于经济发展的普惠性收益和再分配改革的特定性收益,公众对比个人不同时点状态产生的纵向获得感得到了持续稳步的改善,平抑了公众对比他人而产生的横向剥夺感,塑造强化了机会公平偏好,抑制了结果公平偏好,进一步促进了公众社会公平感的提高,形成对既有再分配体系公平性、特别是机会公平性的承认,汇成广泛的社会稳定共识,使得大众诉诸非制度政治参与渠道的可能性下降,最终促进了政治稳定。
在论证过程中,实际是构建了一个新的变量(纵向获得感),并将之与既有理论中涉及的变量(客观不平等、相对剥夺感、社会公平感、公平偏好、社会稳定等)进行再关联,力图修正理论,使得既有理论能够兼容中国的语境。
每一个关联我都尝试通过定量研究的办法予以建立,差分模型、匹配、固定效应模型、文本主题模型等方法都应用到了论文中去。
个人的研究方法学习固然重要,但中国内地定量研究方法的普及浪潮却扮演了更加关键的角色。
我2008年进入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行政管理专业就读,当时这一专业并不开设任何的研究方法课程。
转变来自于两方面的影响。
首先是苏大有浓厚的学生课题氛围,从莙政学者、国家级省级创新性实验计划到学校自行设立的重大、重点、一般课题,让学生有机会有一个由头看看学术的模样,与其他学科的同学有所交流(学习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学习科研论文的写作,学习一些研究方法。
其次是我的学术启蒙老师张晨老师。
张晨老师是2008级行政管理班的班主任,他在7603的办公室带领同学们办读书会、指导学生课题、做国家社科青年项目。
最重要的一件事是,他连续参加了2008年和2009年“中国公共管理与政治学研究方法暑期培训班”,第二次甚至进行了录像,虽然回来只给我们放映了一次,但是spss、回归分析这些新鲜事,却通过他的推崇,进入了我的视野。
“中国公共管理与政治学研究方法暑期培训班”是我所知的国内较早(也许是最早)的大规模的政治学(甚或公共管理)研究方法培训班。
在此之前,量化研究方法在国内政治学界是非常小众的存在,零星的美国等地毕业的教师及其学生才可能有一定认知和掌握。
培训班发起人是杜克大学政治学系牛铭实老师,据培训班网站介绍,“牛老师在香港中文大学担任讲座教授期间(2004-06),和中国的政治学、国际关系和公共管理学界开始比较频繁的交流,牛老师有感于中国政治学缺乏严谨的方法学训练,因此自2006年起,他每年暑期联络一批海内外有经验的教师举办研讨班,培训国内高校政治学师生的研究方法”。
培训班历年承办高校包括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大学、吉林大学等政治学顶尖高校,历年的课程内容主要是定量定性研究方法、问卷设计、抽样理论、博弈论等等。
从培训班网站的历年合影看,诸多政治学、公共管理专业的老师都曾经是培训班的学员。
在当时国内顶尖高校都缺少师资开设研究方法课程的大背景下,这一培训班可谓功德无量。
如果2006年是起点,中国政治学经历的变革仅有10几个年头。
我是很典型的培训班的受益者,作为一个苏大的学生,我通过一种很间接的方式了解到了这一潮流,并自此认定这是更令人信服的研究方式。
虽然了解到这一潮流,但人人去上培训班是不现实的,重庆大学出版社的“万卷方法”丛书为像我这样的学生打开了一扇窗。
万卷方法丛书的策划人是社长助理雷少波,他曾在采访中谈到了导师张诗亚的箴言,“社科学术研究的万人敌就是方法,方法先进则成果先进,方法严谨则学术严谨”,在对比了国外赫赫有名的SAGE、台湾地区出版的方法书之后,策划了这一丛书,通过大规模翻译(采用台湾地区书籍)和请国内有经验者原创的办法,经过多年的努力,将万卷方法丛书建设成为我国第一套(最大一套)系统介绍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大型学术工具书。
在了解到这一潮流后,我借阅了苏大(后来是浙大)图书馆万卷方法的多本图书,也为了早日看到新出版的图书给图书馆荐书。
几本台湾学者的书让我入了门,包括吴明隆、邱皓政等,因为他们的书往往非常非常详细,甚至厚达500多页,操作的每一个步骤及其解读,这在英文翻译书籍中是很少见的。
通过这样的一系列契机,因为做学生课题、本科毕业论文的需要,我艰难自学(用中学),逐步摸索掌握了一些现在看来很浅薄的方法。
不过蹒跚学步,只能说自己足够幸运。
随后,我保送研究生进入浙江大学,师从郎友兴老师。
郎老师也参加过2009年的中国公共管理与政治学研究方法暑期培训班,当时是浙江大学社会调查研究中心的主任,因而他提出资助我去参加2012年的培训班。
这样我才从自学进入到科班学习。
值得一提的是,浙江大学社会调查研究中心与洪永泰老师也有长期合作关系,我因此受益颇多。
培训班的学习是速成式的,对于我这种方法使用者而言,量化研究方法学习的关键是对授课教师代码的理解,包括代码的运行、结果的解读等,我使用的软件也转为stata。
所以我自己成为老师后也逼迫自己分享课程的代码,因为这可能是价值最大的材料。
在尝到培训班甜头后我又自费参加了2013、2014年香港科技大学社会学大咖吴晓刚老师发起、在上海大学举办的“应用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研修班”,这一培训班的好处是根据学习基础将课程分为基础课程和专题课程,2013年和2014年的专题课程均由郭申阳老师主讲。
郭申阳老师是北卡教堂山分校(后为华盛顿大学)教授,专精于研究方法,他将他在美国开设的事件史分析、多层分析、倾向值匹配的课程直接搬到国内。
他的讲授深度、教授技巧等都让学生受益匪浅。
我也因此正式接触到因果推断这一方法论革命,因为他颠覆性地告诉我们,之前学的回归分析不大有用了。
经过三次培训班的学习,我终于摸到了一些门道,让我逐渐领会了方法学习的一些要领,首先是learning by doing,听老师讲过是远远不够的,需要自己本身有强烈的使用需求。
其次是李连江老师提出的“使用者”的学习之道,一个方法什么时候用(面板数据还是截面数据、因变量是连续型还是类别型),如何用(代码操作)以及结果解读。
最后,是自学的能力。
听老师介绍当然是学习新方法的可靠路径,但很多细节需要事后自行搜索补充。
在方法学习中,也终归需要进入到自己知道新方法在哪及自主扩充工具箱的境界,善于使用7*24小时的搜索引擎服务,不把疑问弄清楚不罢休的精神都至关重要,有时候一行代码就是一下午。
到了最后一步,实际上也就不需要参加培训班了,文本大数据、机器学习、主题模型等分析技术就是自学完成的。
现在已经进入付费知识时代,我们获取知识更加方便了,培训班的选择面更大了,网络上也有众多的课程不仅性价比高,而且可以反复听,只是需要擦亮眼睛进行选择。
进入北大后严洁老师的授课全程干货,哈佛访学时哈佛政府系的贝叶斯、文本大数据课程和MIT的因果推断课程也都受益匪浅。
另一个关键性的学习对象是你的合作者。
我确定到哈佛访学后,师姐邵梓捷就告诉我可以去旁听美国政治学年会,既然都到了美国,到费城的距离就大大缩短了。
2016年的APSA首次组织了一个中国研究的全天mini-conference(一般为panel,5人发言结束就地解散),水平都非常高,一天下来,就密集见识了最高水平的研究。他们使用相似的统计语言进行研究,使用相似的漂亮图表汇报结果,甚至使用相似的ppt模版(哈哈,实际为beamer),研究设计则各有千秋,但都追求casuality。
之后自己也参加了第二年的美国中西部政治学年会,这些机会让我认识了刘含章、蒋俊彦等博士,我的job talk文章是与含章合作的,第一篇ssci则是与俊彦合作发表的。
在合作撰写过程中,诸如LaTex、ggplot2等技术就自然学会了。
当然,更重要的是,理论思维能力、精益求精的态度在沟通中提高了。
美国的博士训练还是非常扎实可靠的。
有了研究方法工具箱的储备,博士生活就不会过的那么痛苦。
我虽然博士论文选题确定较晚(2017年7月),但确定了也就不那么急切了,在确定了研究的框架后,就是一步一步把获得感与相关变量的关联建立起来而已。
在研究方法的学习过程中,启蒙老师可遇不可求,更加规范前沿的集中式研究方法培训班和高质量研究方法丛书的出现,为中国政治学实证研究的发展开辟了多元学习道路,而与合作者的相遇让的学术旅途有了更多可能性。
我自己主要学习的是定量研究方法,曾经也觉得技术上是一种优势,但是看过周雪光等等老师的作品,以及经历长期的实际数据处理后,现在是师兄孟天广老师提的方法论多元主义的支持者。
研究方法服务于研究问题,高质量的研究不会因为研究方法被埋没,他们本质上是相似的,就是为一个puzzle提供了可信的、逻辑自洽的解释。
对于博士生而言,研究方法、无论是定性、定量都可以多加学习。
我对我研究方法课上的同学讲,它们都是一种可能性,如果没有一定的积累,实际上我们并没有依据去判断好坏优劣。
我不想做太多的总结,我的个人经历中有成功有失败之处,虽然本文更多分享了我认为的成功经验,包括名校名导、名家讲座、高质量学术会议、培训班学习、海外合作者等,但只是一家之言。
最重要的是,我登上的是中国政治学实证研究快速发展的列车。
但是,对于一个土博士而言,在走向国际化的路上,我们的学科还面临太多困难。
对于当下各大名校追求国际发表的潮流,土博士的国际化之路(马亮老师语)还需快人一步。
关注《学术与社会》,在后台回复关键词“
石头
”,可以获取公号的所有文章。
《
博士论文背后的故事
》摘选
久等了!《博士论文》专栏正式集结出版!
【78】李怀印:我的求学经历与治史心得
【79】蔡文轩 | 壮年听雨客舟中:我的台湾求学历程
《
读研指引
》摘选
【1】
怎样读研,才能不虚度未来三年?
【2】
致研一新生:这学期,一定要上好seminar!
【3】
再致研究生:毕业前,先掌握这五项基本素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