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罗新教授
(李永生 图)
6月19日上午,罗新与鲁西奇两位教授的对谈在武汉大学珞珈山庄第六会议室举行。罗新现为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鲁西奇现为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对谈活动由武大历史学院魏斌教授主持。这次活动主题为“发现弱者的历史”,来自武大、华中师大等校的众多老师和学生到场聆听,并参与讨论,气氛热烈。兹根据录音整理对谈部分精彩内容,以飨读者。
整理︱饶佳荣
魏斌:罗老师长期研究草原部族强势者的历史,为什么开始关注弱者的历史?
罗新:我过去的工作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根据墓志理解北朝社会或南朝社会,根据这点理解再去读老师们和同代学者的一些重要研究,从这个角度去掌握一点知识;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做所谓草原历史的研究,草原历史研究跟草原历史一样,很薄弱,将来一定会有学者做得非常好,比我想象要好得多。我现在主要回到从墓志看北朝社会的研究。
我们知道北朝墓志都是以前有钱人、有权的人留下来的,都是当时的上层社会,下层社会的人没有墓志。但是呢,在读墓志的过程中,也能看到社会的差异,或者是一些受迫害的受侮辱的,被推到边缘去的,可以看到很多这样的人。这个思路我过去很早就有了,我大概在做北方民族社会的时候就尽量避开帝王将相啊、征服者啊,就尽量避开跟这些人过度接触,担心跟他们接触太深,产生对他们的崇拜。
另外,我的性格,别人说我是一个老是跟人家唱对台戏的人,有点桀骜不驯,不容易当一个顺民。这个性格对我的学术研究也是有意义的。第一,在学术思潮上不愿意跟着主流,第二,在研究对象上我不愿选择大家都崇拜的人,你们喜欢孝文帝,你们喜欢冯太后,你们喜欢研究他们,我就不大乐意,或者我会研究他们的另外一面。我想的是我们不能只看到这一面,还可以看到另外一面,一些人在历史上好像总是站在台面上,在比较热闹的地方或是被歌颂的地方,另外一些人处在被挤压被打压、作出重大牺牲,同时又被历史埋没被遗忘的状态。所以我更愿意看到被压迫这一面,因为这一面往往被历史遮蔽了。当我看到这一面,我就忘不了这一面。
最近在我生活中影响很大的一件事:有一天,我看完电影,散场的时候都十一点、快十二点了,我从电影院走回家,看到路边有个老太太,也许有八十岁了,也许年轻一点,她摆着一堆东西在街头卖,但这个点了,街上几乎没有什么人了,我走过去了,但我心里觉得很不舒服,又走回来,问她:你是不是在卖东西?这么晚了,又没有人。她说:白天不能卖啊,只能晚上卖。我们家没有别人,只有我一人。我觉得她没有必要撒谎,我显然只是问问她,不是想买什么东西。不知道为什么,这个事对我影响很大,很久老想着这个老太太。我想生活中这样的人很多的,人类相当部分是这样的人,而他们在传统历史学里是不被关注的,这些人不会进入历史学家的写作当中,或者说不会成为历史素材,根本不会被记录。可是他们是我们生活当中的人。
这种情绪这种思路纠缠我很久了。从去年开始,这个思路逐渐清晰,前年在这里参加青年学者联谊会的时候,我讲过“走出民族主义史学”,当然我那时候还是针对民族主义史学,还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是我们不能只是走出,走到哪儿去呢,这是一个问题。当时能够设想到的办法,就是回到个体。用个人来against,不叫对抗,不是抵抗,反正就是在这个背景上,我们还是承认国家主义、民族主义这一套话语是主体、是主流、是主导,但是不能只有这个,还得有一些在这个背景下的别的话题,比如个人,比如边缘。去年杨奎松先生出版了一本《“边缘人”纪事》,那里面讲到1949年之后一批很普通的人,甚至一些很糟糕的人的经历,即使用我们今天的道德标准,宽容的态度来看,这些人都不值得来往。同性恋者、小流氓、小偷,这种人当然你不跟他们来往,但他写了一群这样的人。我是非常感动地读了他那本书。这些人也是历史学家应该关注的。

《“边缘人”纪事》
大概从这些思路出发吧,来来回回的,这几年很幸运,尤其常碰到鲁老师。我很吃惊啊,万人之中不知道谁的想法跟你一样的,我很意外地发现鲁老师的想法基本上跟我一样,当然他比我思考得深一些,关注的具体问题也不一样,但是我觉得在情感和理论的层面上是有共同的关怀的。而且我相信,吾道不孤,不只有我们几个人,事实上只要有机会出去谈,不管是不是同龄的人,都有同样的思路,都有同样的想法。这几年别的工作做不下去了,因为过去的思路断掉了,甚至被否定了,做过的都是半成品。我不到五十岁,或刚过五十岁的时候,这种内心的煎熬就很严重了,老想做点什么不一样的。我现在还处在摸索的阶段,尝试去做一个实验性的工作。
这学期我在民族史的课上,跟同学讨论、交流。我当时刚看完这本书,跟大家介绍一下我的思路。大家知道,Charles Mann写了两本书,都很通俗易懂,一本是《1491》,一本是《1493》。1492年哥伦布发现了美洲,这个作者就以1492为断限,把1492之前看作一部历史,之后是一部历史。他不是一个学院派的历史学家,但是他读了很多专业的书,对他影响最大的是提出“哥伦布大交换”概念的Crosby,大概Crosby跟他私交也很好,还专门为《1493》写了推荐语。《1491》我读了之后,感觉不是很强烈,但我读完《1493》,特别读到第九章,觉得很棒。第九章题目叫作“逃亡者森林”,写的是欧洲人对美洲殖民,美洲因此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特别是殖民的高峰时期,17世纪到18世纪中期,整个美洲的变化非常大。第九章举了好多事例,搜罗了好多材料,专门讲我们刚才说的边缘人:逃亡的奴隶,反抗者,不服从国家秩序的人。他专门写了这些人,比如逃亡的奴隶建立了自己的国家,抵抗了很久,有的抵抗了长达五十年、八十年,有的还部分获得了成功,使得某个地区的历史面貌跟过去大不一样。当然有些反抗失败了,但他们反抗的时间很长。这是我们过去讲历史、写历史都不容易触及的话题。过去我们的历史观就是国家主义史观。简单地说,叫民族主义,其实就是国家主义,不是以哪个民族,而是以国家结构为中心,以它为唯一的衡量标准来谈历史,来结构我们的历史,来重新叙述过去的历史。像这样反国家的,很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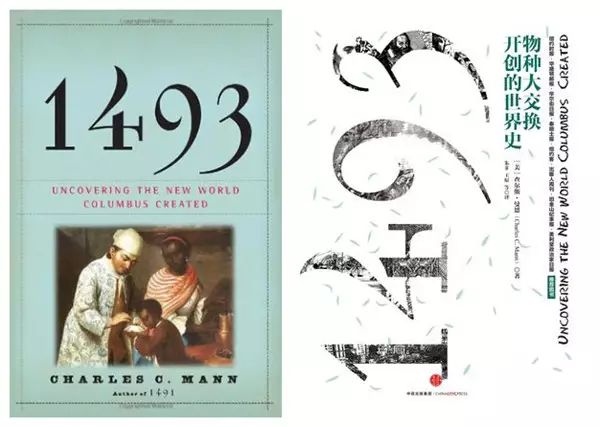
《1493》
再举一个例子,就是James Scott《不被统治的艺术》,中文译本叫作《逃避统治的艺术》。我读Scott的东西,也是很感动。他有一个特点,他把东南亚高地,zomia,这样一个地区的很多人群,描述成主动逃避国家、逃避大型的社会政治构造,而这种叙述很不符合我们过去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从部落到国家那一套。他说不一定所有的人都愿意走这条路,当然有的地方显示走了这条路,但是有的地方的人主动逃避走这条路。我过去写《王化与山险》讨论中古蛮人,鲁老师也有一篇文章讨论这个时期的蛮人,我们都涉及这个话题,但是在理论上没有给它总结。我们当时意识到了,这种人不愿意加入到一个更大的政治组织——显然加入到更大的政治组织没什么好处。我们现在歌颂秦始皇统一六国,其实那是很大的灾难。原来是在一个小国家之内服役就很费劲了,但是秦统一之后一下子从安徽从江苏跑到渔阳服役,那不起义才怪呢,日子没法过呀。我们过去大概意识不到这种历史叙述,或者说没有深刻意识到它所带来的灾难和痛苦,因为都在讨论统一啊、国家发展啊这些看似更大的问题,就把那个话题搁下了。像这样的思路在我内心纠纠缠缠来了好久。如何把这些想法落实到我的具体研究,这就变成我最大的难题。
我想人文学的研究不在于具体课题本身,而在于即使对你说的这个故事兴趣不大的人,读了之后也会有启发。这就超越了个案,更有价值。我是说,在走出国家主义史学,或者说,在国家史观的笼罩之下,可以做出一些新的工作。大概很多人已经走出国家史观了,而我们知道,传统史学还有一个英雄史观。很多学者已经走出英雄史观了,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由于进入现代历史学之后,问题史学成为主导,作为个体的人在历史学中似乎变得不重要了,在这种情况下,英雄史观在悄悄地起作用。所以我觉得今天还存在一个任务,如果回到个人的话,同时要非常警惕英雄史观。我们所说的个人,其实并不平等,身体状况、个人能力,等等,都是有差异的。但是这些差异是不是可以放大为历史,好像变成对历史发生作用的差异,这是很危险的,不能简单地就想到这一点,好像有些人就是对历史影响大,另一些人对历史影响小,我们内心也不容易怀疑我们的直觉,但是我总觉得我们面临着真正把英雄史观从脑子里去掉的任务,必须把这个问题解决。我们总是讲帝王将相,总是讲成功者,现在真的应该看到那些英雄是被塑造出来的,所有的英雄都是被塑造出来的,都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历史原因被造出来的,上到皇帝,下到普通英雄,都一样。我相信有一些强势的力量,但不相信有一些强势的个人。大概强势的个人都是各种原因造出来的,在读历史、想历史和写历史的时候,怎么把英雄史观真正抛弃掉、清理掉,这是一个很大的任务。我认为国家史观、英雄史观还是目前主导的史观,所以怎么把这个去掉,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同时,我还在探讨一种历史叙述的方式,就是怎么写历史的问题。现在我在写作上自由度很高了,但是怎么用好这个自由,怎样写出一个好玩的,有意思的,也是历史的东西,是我时刻琢磨的。毕竟我希望我所尊敬的同行看了之后说,你写的东西也还可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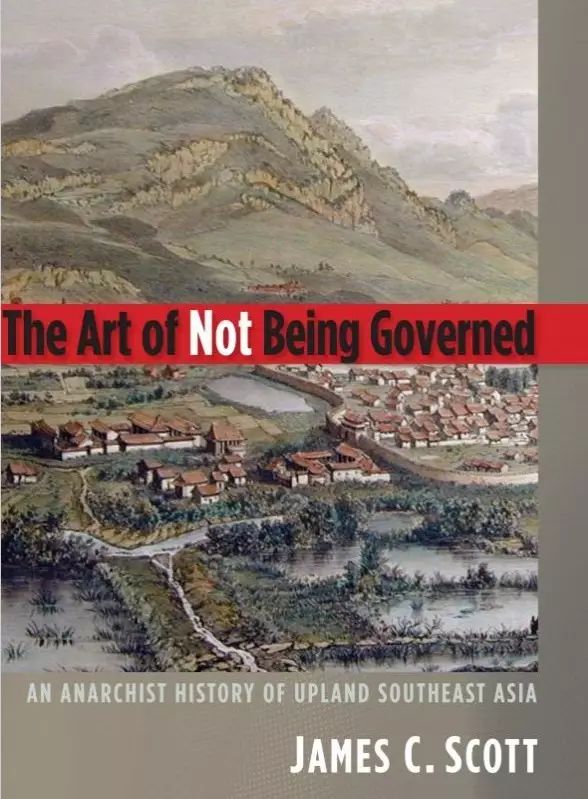
《逃避统治的艺术》
魏斌:您定义的弱者,是像斯科特这样明确的一个阶层的人群呢,还是观察人群的一个角度啊?其实强弱之分是可以转换的,每个人既是强者,也都是弱者。像孝文帝,他是一个强者,但早年冯太后在世的时候,他就是个弱者。您怎么定义弱者?
罗新:对。这是个很有意思的问题。过去我们说边缘人的时候,也有这个问题,谁是边缘人呢?我是这样想的,人和人之间,人群和人群之间,因为社会现实而造成的强弱高低之别。就他个人而言,作为个人的孝文帝,和作为皇帝的孝文帝,是两个人。这两个人有边缘,有弱者。他失去了母亲,失去了自己的儿子,他谁都不能相信,甚至跟皇后说话都拿着一把刀,这样一个人,你能说他是强者吗?他已经吓得要死了,这个人是弱者。代表着国家的时候,他是强者。在他本人面前,他所代表的体制是一个强大得多的强者。冯太后也一样,她固然有一个时刻强大得不得了,但她有一个国家。跟国家相比,所有的官员、帝王都是弱者。这确实是相对而言的,就像我们搞出一个弱势群体,当然这是体制化的弱势群体。
鲁西奇:据我理解,这个弱者是相对于民族、国家,甚至大众而言的。对每个人来说,面对的是远比自己强大的社会和文化的权力。所有人都可以是弱者,或者说所有人都有弱势的一面,但这一面经常被掩盖起来。我想即使是君王,面对国家,就像罗老师刚才举的孝文帝,作为个人,即使是皇帝,他所面对的制度,那个所谓的文化传统,他也可能是弱者。如果这样来理解,把弱者的历史,理解成个体的人的历史,会更清楚一些。我们说弱者的时候,容易引发歧义。
魏斌:我们这个话题的意义,在于发现在国家面前,作为个体的人弱的那一面。我们就是要去发现这样的历史。
罗新:这就像戴上新的滤镜,我们专门找其中的这一面。在个人生活中也有跟他(她)个人意志相冲突的地方,我们看,跟个人意志相冲突的时候,他(她)个人是什么反应。这种反应有时候构成了塑造历史的力量之一,虽然不一定是主导的力量。而这一面往往是被忽略的。过去一般强调历史是理性的,所以就讨论所谓的历史大势,历史的另外一面就不讨论了。而历史的丰富性就表现在个人意志跟周边环境有冲突的地方(当然也有协调的地方),在发生冲突的地方他怎么反应,这是历史当中非常有意思的。对于个人能力非常强,权势非常高,地位非常重要的那些人来说,他(她)的反应是一方面,而对于普通人,小到小萝卜头、街上的一个乞丐,他(她)也有个人意志发生冲突的时候,他(她)的反应也应该纳入视野。我是想说,应该具备一种敏感,学会一种寻找,老是发现这种例子,讨论这种例子,使他们成为历史观察的一个对象,成为历史描述的一个对象。
归根结底说实话,我是觉得到了一定年龄,学历史的人,——用唐(长孺)先生的话,“勤著述,终无补”,对不对?但我们还是想有所补的,这个“补”在哪里呢?也许最终还是跟唐先生所说的那样“无补”,但我们希望有所补,因为不甘心嘛。“补”在哪里呢?那就围绕我自己的工作做一点事情,如果只是去歌功颂德,去顺应国家发展大势,那实在跟很多历史学家的初心是不相一致的。如何讲出不同的历史,就是对现实有所回应,满足自己内心的一点点需要。

鲁西奇教授
(李永生 图)
魏斌:在我们心目中,罗老师是做统治者的历史的,他是出于良心发现,来关注弱者的历史。(众笑)鲁老师,您长期做基层社会的研究,您是从弱者群体出来的(众笑),您怎么看弱者的历史?
鲁西奇:今天,我们每个人时常感到自己在这个社会上有一种孤弱无力的感觉。在国家,在制度,在强大的文化权力面前,甚至在大众面前,自己非常非常渺小,一点事情都做不来。而且,这种不断弥漫开来的、逐渐强化的孤立和无助,在这个全球化和所谓网络的时代,越来越强烈。它反过来让我去想,在这样一个世界里作为个体的人的觉醒和对个体的局限性的认知。以前投身革命,投身国家,那是有意识和无意识的自我泯灭。后来,才想到自己的存在。反过来说,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很多人喜欢,它很有市场啊。为什么很多人拥护它?其实它提供了一个逃避自己、克服自我觉醒的工具。如果有一个“国家”给我们安排所有的一切,多好啊。我从年轻的时候一直期盼过这种日子。结果发现不可靠,找不到。
这些年我对华南的研究接触得比较多,我在思考我们所说的作为个体的人的历史,或者弱者的历史,它并不是大众的历史。其实作为整体的大众不是弱者,不管它是否有组织,大众在本质上跟民族、国家是分不开的。无论怎样意义上的大众、民众或者乌合之众,都不孤独,不孤立,都不突显“个体”,他们甚至“抹杀”个体。各种集体主义的表达和组织,实际上跟“国家”是吻合的。所谓立足于民众的,从地方社会出发的,自下而上看待国家的,这些研究本质上还是国家的历史。它是中华帝国史的地方社会版或民众版,甚至是地方精英版。
我大概从2013年开始涉及滨海地域的历史,其实我是有意识地想去看,跟山区蛮人一样,在国家直接控制之后,这群人是怎样生存的。这两年我又有一点困惑,当我们把他们当作人群、群体的时候,又赋予了他们力量,甚至赋予了他们反抗的力量。但是在历史过程中,他们没有感受到。就像山里的那些蛮人,他们一个个很孤立,只有被裹进某种组织,不管它是政治的还是社会的,他们才感受到他们是那群人的一部分。在我们的研究尺度里头,罗老师做的宫女的故事,胡鸿讨论过的各种群体的问题,我们要把握怎样的研究对象呢?这是一个我不知道的东西。在墓志里头,以及其他材料,我们可以看到个体的人;但在更多的历史文献里面,我们看到的是一群人,他们由若干个人组成。但是这个群体是不是文献制造出来的呢?
胡鸿让我接着罗老师的话来讲怎么做。我觉得如果我们来揭示弱者的历史的话,第一个可能要说清楚他们为什么是弱者。在国家、制度和文化的力量面前,他(她)如何成为弱者。传统制度史的研究,政治经济与社会的结构主义的分析,和作为权力的文化史的考察,这些研究从很多方面告诉我们,作为个体也好,作为群体也好,他们所面对的力量非常强大,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她)一定弱。他(她)的弱,是指他(她)的个人权力和意志被剥夺了。所以我想有一个东西可以做,就是制度如何控制个人的行为,如何侵夺个人意志和群体意志,如果研究这个东西,材料应该是许可的。我这学期上的课是乡里制度的研究,我的入手点就是想看乡里制度确定以后,本来不需要缴税纳赋的人,如何被迫给国家劳动。那些散布于农舍田间的农户,他们被纳入王朝国家控制体系,成为编户齐民。我把这个过程,称作“从人到民”的过程。我相信,我们同样可以去关注那些读书人,又是如何从“人”变成“臣”的过程。在国家制度与机器面前,民、臣都是孤立的个体,他们主动或被动地进入王朝国家体系,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是孤立无助的。
第二个,罗老师说这些人在历史的过程中是有自己的能动反应的。面对国家体制,我们的选择大约有两种,一种是从,一种是不从。迄今为止华南研究揭示了不同区域不同层次的人群进入国家的方式和过程,他们最终成了这个国家、民族和文化的基础。在我看来,这是华南研究这些年来做的一个最大的贡献。那么另外一个选择,大概有三种方式,抗拒是一种,逃亡是一种,自主选择、主动死亡是一种,这个概念是从弗洛姆那里来的。不同人群有不同的抵抗方式。那些已经进入国家体制的人,被纳入王朝国家的人,我们不去看他们进入国家的过程,而关注他们脱离国家的过程,他们有不同的方式脱离国家。他们会成为浮浪人、成为逃户、成为亡人,这说明他们之前有一个进入国家的过程。我们说到斯科特的研究,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

现场
(李永生 图)
魏斌:也就是说,他们原先都有一个积极融入体制的过程,那么他们脱离国家之后的走向是什么?成为荫户,成为附属民,成为部曲,成为另一种体制下的人。
罗新:但我觉得价值不在于反抗是否成功。也许不成功才是我们史学关怀所在。主要要看他们为什么会有这个选择。当然也要看到,对他们个人来说,这种选择是失败的。或者从外界观察来看,他们还是被抓走了。但是,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因为这揭示了所谓国家是什么,有助于打破我们对国家一味的崇拜,我们看到国家并没有那么美好,这对于人的理性认知是很有意义的。
鲁西奇:我想意义可能还不止于此。弗洛姆说人类历史起源于最初的不从,所谓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没有听上帝仁慈的安排,做了上帝不许可的行为,才有了人类的历史。他从这个角度来讲人类的起源。他还讲了很多其他例子,总之不从导致革命、导致改良,那么我们可以说“从”创造现实,“不从”带来变革。你说的荫户的例子,恰恰说明他们要逃离国家直接控制的编户系统,与此相配合的,这样一套新的体制出来了。随着逸出体制的人越来越多,而且是富有力量的那一部分,这就导致了旧有体制的彻底崩解。这是革命啊。
罗新:历史就是这么塑造的。
魏斌:他们逃离了国家体制,而进入私人控制的一套体制。
罗新:这可能是新的国家体制的雏形,至少是新的国家体制的选项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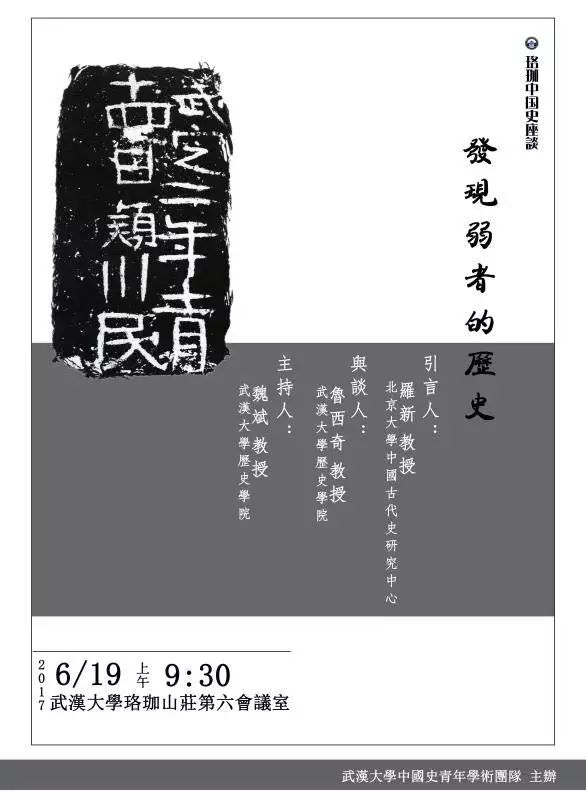
·END·

本文首发于《澎湃新闻·私家历史》,欢迎点击下载“澎湃新闻”app订阅。点击左下方“阅读原文”访问《上海书评》主页(shrb.thepaper.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