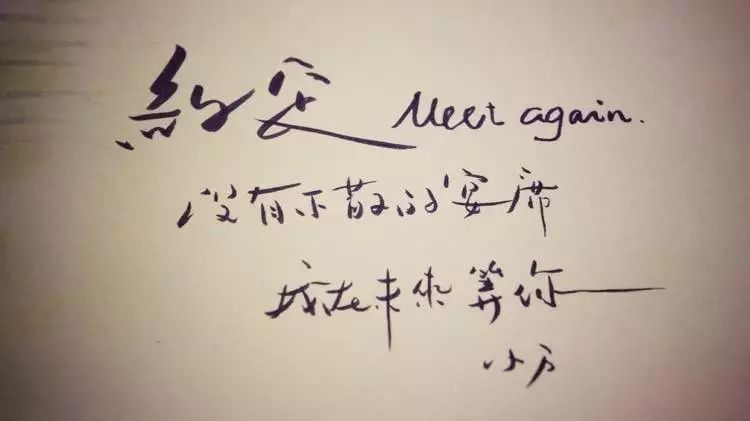作者|
沟口雄三
(1932-2010)
日本汉学家、中国思想史学家,1958年毕业于东京大学文学部中国文学科。1967年名古屋大学大学院人文科学研究科硕士毕业。历任埼玉大学教养学部助教授、教授,一桥大学社会学部教授,东京大学文学部教授、东京大学名誉教授,大东文化大学教授。
明末的君主观
早在黄宗羲的君主批判论之前,在明末被称作东林党的反宦官的政治集团中,就已经有了下列观点。
天下大矣,人主不能自理,分而寄之一相,相臣者,君所与共天下者也(徐如珂《徐念阳公集》卷三)。
惟夫国之有是,出于群心之自然,而成于群喙之同。然则人主不得操……廷臣不得操,而天下匹夫匹妇操之。匹夫匹妇之所是,主与臣不得矫之以为非;匹夫匹妇之所非,主与臣不得矫之以为是(缪昌期《从野堂存稿》卷二)。
天为民立君,士为民事君(陈龙正《几亭外书》卷一)。
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奈何以我病百姓?夫为君之道无他,因天地自然之利而为民开导撙节之……凡以安定之使无失所,而后天立君之意终矣。岂其使一人肆于民上而剥天下以自奉哉(吕坤《呻吟语》卷五)?
天下人各有欲也,岂独人主?……而人主独能外天下以成其欲乎(钱谦益《牧斋初学集》卷八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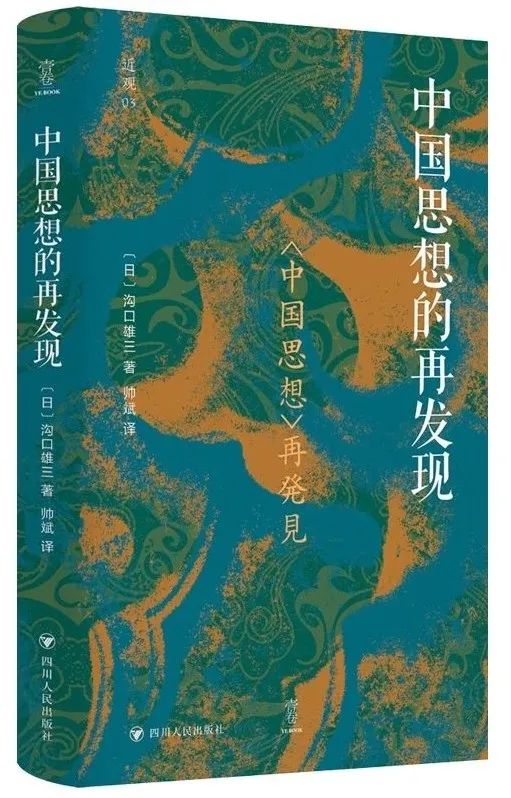
这些观点与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中的君主论有以下共同点。第一,单凭君主一人,即使是有德的君主,也不足以统治天下,在政治上应由君主和官僚分工合作。第二,政治应顺从“匹夫匹妇”等天下万民之舆论而运作。第三,政治应以满足民之生存(自私自利)为根本。
可以说,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是将明末东林党人之间零碎出现的这些新思想整合在一起而完成的。
新的君主观
那么上述三点在哪些方面可以说是有新意的呢?
首先就第一点来说,虽然说宋代以后,由天谴式天观向天理式天观转化,将皇帝的有德性作为政治中心的这一点仍没有变化。对于天谴式天观来说,将皇帝的修德看作防止灾异的核心,而在天理式天观之下,也仍以皇帝自己实现天理为政治的核心。这里流传下来的是认为有德的皇帝才能施仁政这种自古以来的德治主义。
与之相对,明朝末期出现的上述第一点的思想,可以看作是一种皇帝机关说。其最重要的一点是皇帝与官僚如何合理分工,如何建立一种有效吸取民意的行政系统。
而第二点的尊重舆论,在明朝末期也经常被称为“公论”。在这个公论的背后,是地主制发展的社会大变化。明代将征税的行政制度设立到了乡村的每一个角落,各丁各户(丁是指成年男子)都是征税的对象,也就是说这是依据一君万民体制的原理,认为万民皆平等,皆为皇帝的子民,这种税收制度被称为里甲制。然而明朝末期时,地主制已变得非常普遍,在乡村中有了地主与佃农的分化倾向,贫富差距扩大的趋向。
以被称为乡绅,有着做官经验的地主为中心的阶层,开始扩大其对经济的控制力。与此同时,官僚的制约力相对减弱,以地主阶层为中心的地方统治势力的力量开始变得强大起来。这也就是上述提到的“公论”。它不是以往的那种认为皇帝的仁政从上到下施与一君万民体制下的万民,而是更加重视官僚阶层如何采纳这种公论,这也是它与第一点的关联之处。
第三点的“满足民之生存”则是与明朝末期主张民之所有欲,生存欲相关。如黄宗羲就曾指出,“先王之时……田出于王以授民,故谓之‘王土’。后世之田为民所买,是民土而非王土也”(《破邪论》)。这一“民土”的主张,与土地私有权的主张相通。也就是说,相对于皇帝对民众施以仁慈就好的传统德治主义的政治观,这时已经开始要求制定满足民之私有权的具体政治策略了。
这三点主张,也反映了当时政治结构上的对立。
这是一种中央与地方的对立,前者要求强化皇帝的一君万民之中央统治,后者依靠乡村地主制的发展,实行重视乡绅阶层意见的地方自治统治。
到了明朝成熟期的万历年间,由于地主制的兴起,导致里甲制出现问题等,使得政府不能顺利征税。再加上当时日本的丰臣秀吉出兵朝鲜与北方女真部落的入侵等的外在压力,及因此带来的财政支出,出现了国库屡告空虚的局面。
对此,明神宗与首辅张居正(1525—1582年)采取强化中央集权以谋求充分税收的方针。张居正死后,神宗又不顾群臣反对,依靠宦官,直接派遣宦官去下面征税强夺。例如,他设立了所谓“矿税”这一新税种,宦官们甚至冲入有些富裕家庭的宅院中,谎称发现矿石而掠夺其家产。对此从正面加以批判揭露的,是东林党人,他们以乡绅地主阶层的舆论为背景,对抗中央权力,谋求重视乡村的政策。
民的自私自利与皇帝的大私
黄宗羲对于皇帝大私的批判,正是基于上述时代的趋势。但这种批判,在他脑中是有例可循的。
明神宗十分溺爱宠妃之子朱常洵,多次想要立常洵为太子,都因遭到百官的反对而未能成功,于是他竟想寄予常洵4万顷封地了事。虽说当时中国的全部耕地面积约700万余顷,但要将接近0.6%的土地赐予一介皇子,还是遭到了大臣们的强烈反对,最终将封地面积减至2万顷了事。那2万顷封地具体就是指被称为王府的王族的庄田。因为王族以各种手段压制庄田内百姓的权益,因此王族并不受此地老百姓欢迎。其实在明太祖时期,对这种扩大王府或皇帝私有地等朝廷私有土地是有严格限制的。随着王朝到了末期,这种皇帝庄园、王府,或是勋戚的庄田等一代代不断扩大,其中最极端的便是常洵之例。
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田制篇》中主张将包括官田在内的全部耕地分配给老百姓。据他所说,官田占了全部耕地的三分之一以上,皇帝庄园或王府也是官田的一部分。
他是否有针对常洵之例虽不得而知,但至少可以看出他对不断扩大的皇帝庄园与王府是持批判态度的。他对于皇帝的大私压制民之自私自利的批判,可以看出当时朝廷的私产对民土扩展的阻碍。将朝廷的私有财产称为“大私”,一方面,也可以从中看出对民之私有财产这一权利意识的增强。
清代的变迁
但在进入清朝之后,这种对皇帝的批判便见不到了。虽然《明夷待访录》被后人视为清代之作,但黄宗羲的笔锋是探求明朝之所以灭亡的原因,而并不以清朝为对象。
明朝末期那种批判皇帝的思想之所以销声匿迹,一方面是由于清朝的武力镇压,但最根本的原因是清朝不同于明朝,它承认地主阶层的权益从而确立了自己的政权。清政府将江南一地的很多明朝皇帝庄园与王府分给老百姓。除了在北方保有八旗军的屯田,并没有额外增加朝廷的私有地。
雍正帝时期施行的地丁银制更是将丁税并入地税而形成税收的一体化,这实际上是废止了丁税。丁税是中国古代以来就有的一种徭役,是指成年男子必须上缴的人头税。废止了人头税,也就意味着放弃了一直持续到明朝的一君万民原理,也就是天下民众都由皇帝控制这一原理。而取而代之的土地税一体化,则不管地主雇佣几个佃农,只按地主所有土地来征税,意味着清朝承认地主的土地私有权及在私有土地上对农民的控制权。
也就是说,清朝实际上是一种承认地主的乡村控制权的皇帝地主联合政权,在这一点上,与由宋到明的王朝是有决定性的区别的。
清朝之后君主批判的思想便销声匿迹了。这可以认为是因为作为明朝末期舆论先锋的乡绅阶层与同样是地主出身与其有诸多共鸣的官僚阶层,对清朝政府的政策,基本上是满意的。
反过来说,明朝末期兴盛的君主批判思想中可以看出,当时的地主阶层对一君万民体制已抱有强烈的不满之情。明朝人心尽失的原因,是一味强化一君万民体制,实行了与时代趋势完全相反的基本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