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媒体与传播学系副教授孟冰纯做客引擎,
分享她对于版权问题、中国媒介及社会生态以及底层发声的研究和思考,提出了不能
泛化、简单化及去历史化地理解
传播学研究的中国视角,强调了将版权视为“第二次圈地运动”的批判路径,并分析了在全球化时代中国媒介生态中精英与大众、城市与乡村之间复杂的权力关系矩阵。
采访丨张宇杰
孟冰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媒体与传播学系副教授、副系主任,LSE-复旦全球媒介与传播双学位硕士项目主任。1997年毕业于南京大学,获得汉语言文学学士学位,2000年获得比较文学硕士学位,2006年获得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大众传播博士学位。主要研究领域为全球化时代的中国媒介、版权法与传播、传播政治经济学与信息产业、女权主义媒介文化研究。新书
The Politics of Chinese Media: Consensus and Contestation
已于今年出版。

引擎:您本科、硕士都在南京大学读文学,那为什么博士期间会有比较大的转向,选择去美国读传播学呢?
孟冰纯:我其实最开始申请去美国读博士的时候是申请比较文学,因为我在南大硕士念的就是比较文学,所以比较顺理成章。但是到美国念了一年以后,觉得有点沮丧。美国比较文学的博士要读大量的理论,而且那个时候兴盛的是各种“后学”——后现代、后殖民,后结构。他们的那些批评、那些理论,你刚开始接触的时候还是挺兴奋的,因为它批判的角度能打破你之前很多的认知,打破你之前想当然的觉得普适性的东西,给你一些智识上的刺激和挑战。但是,整天浸淫在这类言说方式里面,就变成了一种完全是在象牙塔里面的思想和文字游戏,失去了现实指涉。我还记得我在比较文学系第一次做课堂报告是讲后殖民理论家霍米巴巴。这个人的文风非常晦涩,因为他要在写作风格上也贯彻自己的后殖民立场。他有一个重要概念是混杂(hybridity),用来批判基于殖民主义的话语和知识建构。所以他在自己的写作当中也有意破坏在他看来被白人殖民者净化过的语言风格。我当时就觉得,如果知识分子要承当社会批判的责任,写出来的东西却没几个人看得懂,那还谈什么公共性呢?传播学呢既跟这些文化研究理论相关,又比较接地气一点、比较关注现实一点,因为传播学研究会更注重经验材料。而且传播学有社会学的维度,我们的研究里有人的活动,人的主观能动性。
引擎: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将自己的研究兴趣聚焦在传播政治经济学以及版权研究?
孟冰纯:主要是受宾州州立几个老师的影响比较大吧。因为美国的博士生课程比较多,不像英国这边一进来就做研究,当时博士生第一年有两门必修的基础课,其中一门课的老师是斯坦福毕业的,除了媒介研究的学位还有心理学副学位,完全是美国最主流的传播学研究,就是效果研究、定量,完全实证主义;还有一门课完全不同,任课老师叫RonaldBettig,是UIUC(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毕业的,因为UIUC的传播学从传统上政治经济学就是很强的。虽然这是一门基础理论课,但里面着重介绍了传播政治经济学。Ron 前几年因为意外去世,我也没能回美国跟他告别,很遗憾。他是我的批判理论启蒙老师,我很感激他。
讲实话,传播政治经济学在美国的传播学研究里处在比较边缘的地位。美国大量的传播学研究都是实证主义,而政治经济学经常被批评:一方面,文化研究批评它是经济决定论,以及完全不考虑受众的主观能动性;另一方面,从政治和意识形态角度,马克思主义在美国的传播学界已经被认为是过时的了,所以政治经济学会被政治上的右翼批评为阴谋论。比如传播政治经济学肯定会讲到的赫尔曼和乔姆斯基的《制造共识》,那是很早写的,讲美国关于国际事务的报道与美国的外交政策导向以及资本财团的政治经济利益之间的关系,这一类的研究在学界会被批评为经济决定论和阴谋论。
而关于版权研究,首先我受我的老师Ron Bettig影响很大。他的第一本书也是根据他的博士论文写的,就叫
Copyrighting Culture
。所以我对版权问题的兴趣,包括对于把知识产品和创造性的内容商品化、私有化,以及版权和民间产业发展之间的关系的兴趣,其实也是从这里来的。我博士期间还有另外一门人文地理学的课程,讲资本主义的发展对于环境和自然的公共资源的商品化,比如说水资源、社区森林,所以这其实跟我后来对版权的兴趣有一种平行关系。杜克大学法学院的James Boyle写过一篇很有名的批评版权的文章,题目叫做The Second Enclosure Movement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Public Domain,所谓
第二次圈地运动
。
就是说,资本主义的商业化、商品化的逻辑是不断扩张的,第一次完成工业化的积累的时候,它要建立在对于自然资源的私有化、对于自然的掠夺性积累的基础上。
而版权就是在完成工业革命以后,由于信息产业或者说知识产业的发展需要下一轮增长动因,资本主义就把对自然资源的私有化转向对于知识、信息、符号、文化产品的私有化、商品化,然后让这些产品都以商品的逻辑进行流通,把它们从公共领域当中剥离出来。
引擎:在互联网上,普通用户也可以通过UGC(用户生产内容)参与到内容生产的过程中。但比起机构化的组织,他们的权利似乎很难受到相关法规的保护,比如前段时间频繁发生的自媒体“洗稿”事件。您觉得版权是否能保护个体创作者的权利呢?
孟冰纯:其实版权从来就不是为了保护个人创作者的权利的。版权一直与知识文化产品商品化和市场化的流通方式难以分开,即使在前网络时代,版权所有者其实都是复制和发行产品的人,就比如说一个歌手要发行唱片的时候,唱片的版权并不是你的,而是唱片公司的;一个作者,你跟出版社签约的时候,其实是在转让版权。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就不可能指望版权去保护每一个个体创作者的权利。但是反过来,
从商业利益、媒体产业公司的角度来说,当它们要宣传版权保护的时候,都会把创作者的权利放在最前面,运用“饥饿的艺术家”这一套叙事来包装对于商业利益的保护。
所以其实我觉得UGC被挪用,可能更加暴露了版权这个东西本身最初的逻辑、它的导向、它要保护的是什么,它从来就不是为了保护个人创作。
引擎:目前,传播学界的非华人学者也开始越来越多地关注中国研究这一领域,这些非华人学者对于中国语境下的传播学研究有没有提供一些新的视角或者不同的理解方式?
孟冰纯:其实在海外高校,很多学科对于中国的研究最早就是由非华人学者发起的。所谓区域研究(area study)的兴起,本来就跟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乃至冷战时期的政治需要分不开。包括东亚研究(早年美国精英院校东亚系最有名的汉学家都不是华人)、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尤其是比较政治。反倒可能是这些年随着华人学者慢慢能够在海外的学校就职,才开始了海外华人学者对于这些领域的研究。而传播学不一样,可能真的刚开始研究中国的确实就是华人学者,因为传播学这个学科它是不讲区域研究的;而像政治学、人类学以及东亚研究本身就是区域研究,像做政治学或者人类学的学者,他们都会很明确地说明他们的研究特长是在哪些地区的,不会特别泛泛而谈,当然可能除了做政治哲学政治理论的。
之所以会有这些差别,是因为传播学刚开始是实证主义当道的,而且有很多东西是从社会心理学借鉴来的,觉得文化、政治、历史这些语境不重要,觉得用实证主义的方法可以得出非常普世性、普泛性的结论,而不用在意研究者自身的立足点,也不去追究研究者的问题意识本身是受到哪些因素影响的。而且因为传播学这个学科本身是非常美国中心的,它也觉得不需要关注其它国家。
而关于学术研究的视角,我觉得学术观点和学术视角与学者的身份认同不是一个简单的对应关系。我遇到过跟我立场接近的非华人学者,也遇到过跟我立场相左的华人学者。这都不能简单一概而论。
作为传播学研究的中国视角到底是什么意思?我觉得这是一个需要problematize的,而不是想当然,觉得讲点中国的事情就叫做中国视角。
我在我的书里想强调的一点就是,
谈中国当下的媒介政治,必须放在中国特定的历史语境当中,尤其是以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轨迹作为历史的参照点。
这个历史的参照点不仅能帮助我们理解当下,比如很多明明是政治上非常落后的意识形态,比如消费主义,比如市场原教旨主义,比如父权资本主义,这些从我的立场来看是非常“反动”的思想意识,因为裹上了“自由”的外衣站在专制政权的对立面,因为它们是社会主义时期被压制的东西,现在就摇身一变成了解放人性的,带有赋权色彩的观念。
但我书里提历史语境还想说的是,
历史不仅仅是从哪里来的问题,还有到哪里去的问题。
不同版本的历史叙述不仅仅包含对过去的理解,这种理解是一个意识形态斗争的场域;更塑造着对未来的想象,这个想象更是高度政治化,充满斗争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书的副标题强调contestation。
我在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有四百五十多年历史的图书馆里看到这样一句话,很有哲理。他们在介绍这个图书馆的时候说:这里收藏的一切并不是尘封的过去,历史是被我们放在身后的,对未来的记忆。所以,我理解的中国视角绕不开对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评估。但就像我刚才说的,这不是和身份认同简单对等的,肯定会有很多人对中国视角有完全不同的理解。
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我确实也一直很清醒地意识到我作为中国人的身份,就是说,
我可能更能看到在表面的universalism这种普世价值和普泛性背后,看到传播学主流研究的西方中心论跟白人中心主义。我作为一个在西方高校任教的有色人种女性,必然有身份错位带给我的敏感性,让我想要去质疑这一套话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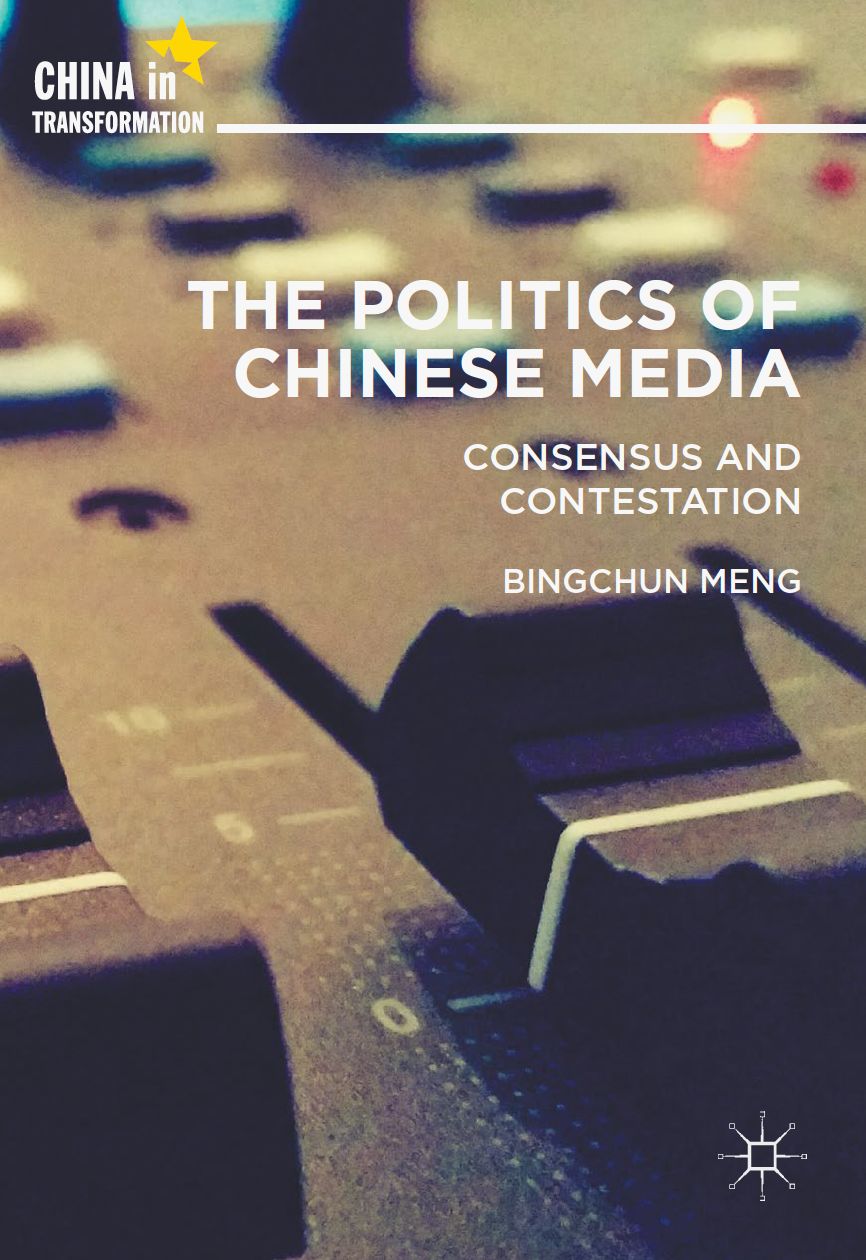
引擎:在您的新书
The Politics of Chinese Media: Consensus and Contestation
的导言部分,您提到了当前中国媒介生态中复杂的权力矩阵,包括国际和国内、党的喉舌与市场化媒体、精英和草根之间的权力关系,并认为这些权力关系被简单化为了审查制度和言论自由的二元对立。那么,哪些重要议题由于这种简单化的二元对立而被忽视了?
孟冰纯:从大的方面来说,首先我的书在开头就强调一种历史化的分析和理解,因为我觉得
如果一谈到中国媒体就简单化为审查制度和言论自由的二元对立的话,这是一种完全去历史化的、非历史化的理解
。
比如说现在对于中国新闻媒体最占主导的考察方式,都是以西方自由民主的模式作为历史终点、作为地平线上的目标,然后以它为标杆衡量中国现在离西方模式有多远。但我觉得对于中国媒体的考察是需要放在中国特定历史语境下的,包括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以及中国的政党和政权在作为革命党的时候所作出的一系列的承诺:因为中国共产党在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或建设社会主义的时候,本来就没有承诺要建立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它承诺的是媒体的人民性,是这个政权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使命。所以我觉得在中国的语境下,不应该用福山所说的历史终结、意识形态终结来作为西方自由主义民主的标杆,进而衡量中国离这个标杆有多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