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7月5日,伊朗导演阿巴斯·基阿鲁斯达米于巴黎去世,只给世界留下了一部未竟之作《杭州之恋》。

这位既会写诗、也爱绘画和摄影的导演,被视为世界影坛上标志性的“东方”导演。

阿巴斯·基阿罗斯塔米善于从平凡的事件中揭示人类最深的情感。他从不写冗长的诗歌,但是却始终充满了拥有独特观察之眼的诗人对于世界特有的专注凝视和细致观察。
他的那些简短、迅疾、跳跃但目光细致的诗句,让我们重新审视身边的事物和景象。
如今,阿巴斯·基亚罗斯塔米已经离开我们一年的时间,让我们在他的诗歌和摄影作品中,向这位大师致敬。

当我口袋里没有什么
我有诗歌。
当我冰箱里没有什么
我有诗歌。
当我心中没有什么
我就什么也没有。
如今,阿巴斯已经离开我们一年的时间,但是从他的诗句中,我们还能看到一个深邃而又充满哲学意味的世界,和他的诗作背后古老的波斯诗歌传统。
如今,由著名诗人、翻译家黄灿然先生精心编译的阿巴斯诗集《一只狼在放哨》在中国大陆首次面世,是迄今为止最全的阿巴斯诗集中译本,几乎囊括了阿巴斯全部优秀诗作。在这本书中,阿巴斯用他对于世界特有的专注和凝视,带领我们看透日常世界的诗意本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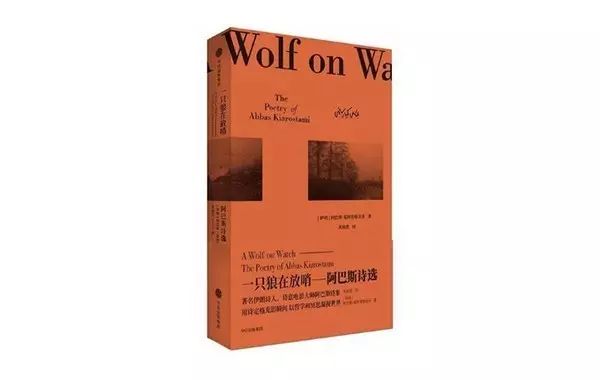
阿巴斯从小就受诗歌的熏陶。
“我家里的小说,一本本都近于完好无损,因为我读了它们之后便把它们放在一边,但我书架上的诗集缝线都散了。我不断重读它们。”
他能够背诵伊朗诗人迈赫迪·哈米迪·设拉子的大部分诗。后来在伦敦,有朋友介绍他认识病榻上的老诗人。他当着哈米迪·设拉子一首接一首背诵他的诗,让诗人感动得老泪纵横。
伊朗本身就是一个诗歌国度,诚如阿巴斯所说:“在那里我们装饰诗人的坟墓,在那里有些电视频道只播放诗歌朗诵。每当我祖母要抱怨或表达她对某样东西的爱,她就用诗歌。”
诗歌并非只是关于人生和世界的,它还能改变我们对人生和世界的看法。“在悄悄绝望的时刻,感到无可安慰,我便使自己脱离野心的激流,伸出去拿一本诗集,并立即意识到我们周遭耗之不尽的丰富性,感到能够沉浸在这样一个世界中的人生是有尊严的人生。于是我感到宽慰。”
也因此,诗歌起到了重新定义人生的作用:“一首诗,每次阅读都会因为你的心境和人生阶段的不同而显得不一样。它随着你成长和变化,也许甚至在你内心成长和变化。这就是为什么我童年读的诗,会在今天给我带来不同的体验。一首昨天觉得有教益的诗,明天可能就会觉得乏味。又或者,也许用对生命的新看法和新理解来读,我会兴奋于发现我以前忽略的东西。在任何特定情况下,在任何特定时期,我们都在以新的方式与诗歌发生关系。”

在他那本访谈录精选Lessons with Kiarostami (中译名《樱桃的滋味:阿巴斯谈电影》) 中,他有很多地方谈到诗歌和诗歌的重要性,以及诗歌对电影和其他艺术的重要性。
“在伊朗,相对质朴的民众都怀有一种表达起来很有诗意的人生哲学。一旦拍起电影来,这就是一个宝藏,可以弥补我们在技术方面的不足”。他认为“诗歌是一切艺术的基础”,并说“真正的诗歌提升我们,使我们感到崇高。它推翻并帮助我们逃避习惯性的、熟视无睹的、机械性的例常程序,而这是通往发现和突破的第一步。它揭示一个在其他情况下被掩盖的、人眼看不见的世界。它超越现实,深入一个真实的王国,使我们可以飞上一千英尺的高处俯瞰世界。”
如果我们以为写诗只是他拍电影之余顺便玩玩的小消遣,那不但会误解他的诗,还可能会误解他的电影,因为他与诗歌的关系还远远不止于读诗和写诗。
他还一直在编选和改写古波斯诗歌,在2006 年至2011 年,他终于把这方面的成果公诸于世,相继出版了古波斯大诗人哈菲兹、萨迪、鲁米和现代诗人尼玛(1895-1960)的诗集,此外还有两本古今波斯诗人作品的“截句”。在晚年做出如此大手笔的举措,是因为阿巴斯太知道它们的价值了,不管是对他自己而言还是对读者而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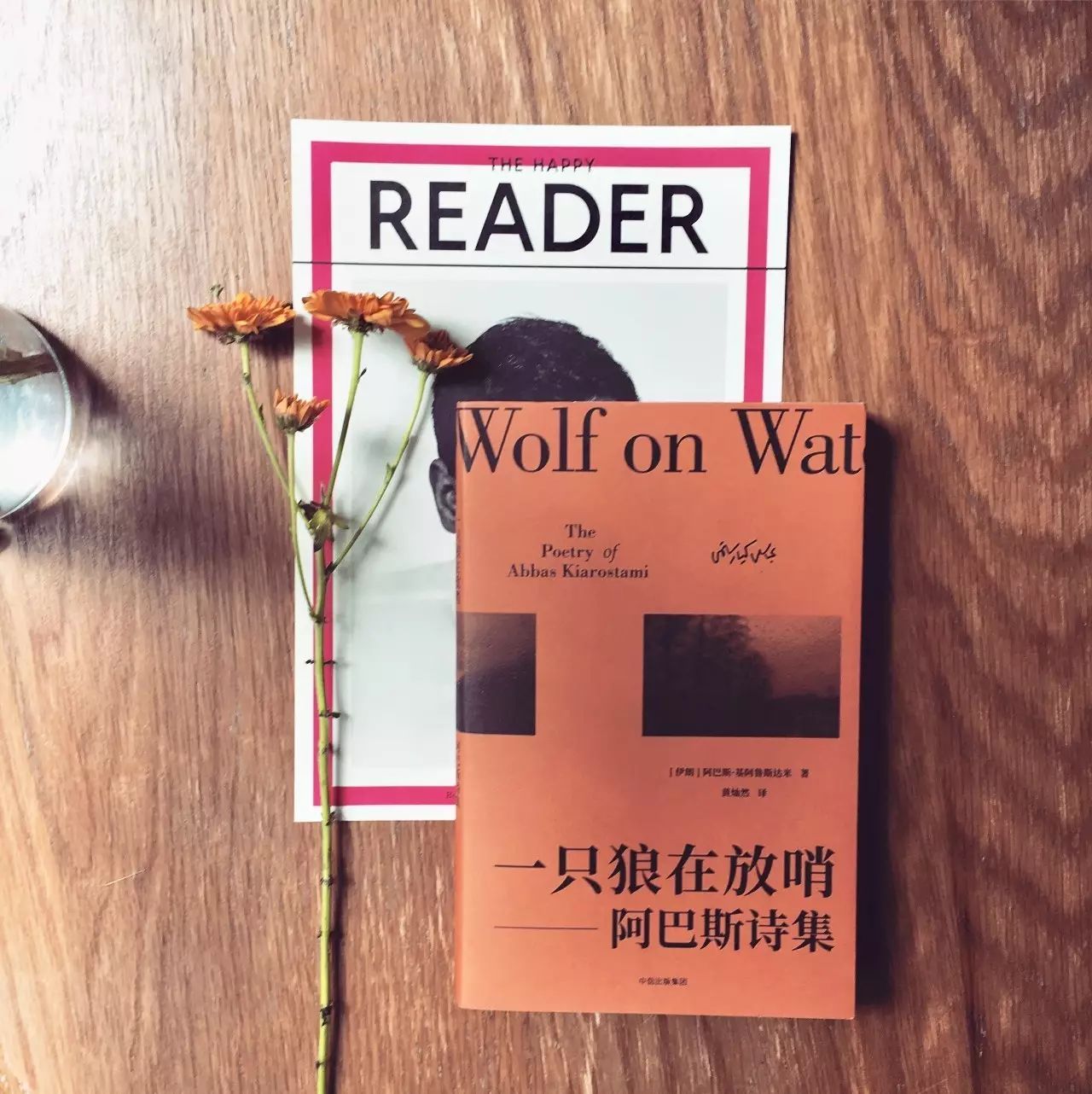
在他的访谈录中,有一段话谈到诗与电影的关系:
我的心灵就像一个实验室或炼油厂,理念就如原油。仿佛有一个滤器,过滤四面八方各式各样的建议。一个意象浮现心头,最终变得如此纠缠不休,使我不得安宁,直到我做点儿什么来摆脱它,直到它以某种方式被纳入一个计划。正是在这里,诗歌向我证明它对我如此方便和有用。我头脑中一些意象是很简单的,例如有人用一次性杯子喝葡萄酒、一座废弃的屋子里的一盒湿火柴、摆在我后院的一张破凳子。另一些则更复杂,例如一匹白驹在雾中出现,又消失到雾里去;一座被白雪覆盖的墓园,而白雪只在三个墓碑上融化;一百名士兵在月光之夜走进他们的兵营;一只蚱蜢又跳又蹲;苍蝇围着一头骡打转,而那头骡正从一个村子走往另一个村子;一阵秋风把叶子吹进我的屋子;一个双手黑兮兮的孩子坐着,被数百枚鲜核桃围绕。把这些意象拍成电影,要耗费多少时间?找到一个题材,把这些意象纳入一部电影,有多么困难?这就是为什么写诗如此值得。当我费心写一首诗,我想创造一个意象的愿望在仅仅四行诗中就得到满足。词语组合在一起,就变成意象。我的诗就像不需要花钱去拍的电影。仿佛我已找到一种每天制作有价值的东西的方法。在拍完一部电影与拍下一部电影之间,我往往有一两年空档,但这些日子很少有一个小时被浪费,因为我总是要做些有用的事情。

虽然阿巴斯的诗并不难懂,但是他在谈到诗的难懂时,却说得非常的合理和公正:“我们理解一首音乐吗?我们理解一幅抽象画吗?我们都有自己对事物的理解,有我们自己的门槛,过了那个门槛,理解便模糊了,迷惑便发生了。”他还认为,诗歌是一种“心灵状态”,因此,“对来自某一文化的诗歌的理解,意味着对所有一切诗歌的理解。”
诗歌无所不在,“只需睁开你的眼睛。”他表示,如果有什么事情引起他的兴趣,而他决定把它拍成电影,那么别人便也有可能觉得它是重要的。诗也是如此。“好诗总是诚实和敏感的。”这使我想起叶芝的一段话:“如果我们理解自己的心灵,理解那些努力要通过我们的心灵来把自己表达出来的事物,我们就能够打动别人,不是因为我们理解别人或考虑别人,而是因为一切生命都是同根的。”
阿巴斯的诗,主要是描写大自然的。“正是我们这个世界的政治危机帮助我欣赏大自然之美,那是一个全然不同和健康得多的王国。”他谈诗时,主要是谈诗歌对他的影响,而难得谈自己的诗。这是少有的一段:“传统诗歌根植于文字的节奏和音乐。我的诗更注重意象,更容易从一种语言转换到另一种语言而不失去其意义。它们是普遍性的。我看见诗歌。我不一定要读它。”

除了写大自然之外,阿巴斯还写爱情,写当地风土人情,写游子归家,写孤独,尤其是晚年的孤独。这些,都是阿巴斯的私人世界和内心世界,如果结合他的访谈来读,以及结合他的电影,就组成了一个里里外外、多姿多彩的阿巴斯的世界。而对我来说,阿巴斯永远是一个诗人。我不仅通过翻译他来理解这位诗人,而且还将通过继续翻译他编选和改写的古波斯诗歌,来进一步加深理解原本就对我青年时代产生过影响的古波斯诗歌。

古波斯诗歌,主要是以两行诗组建的,有些本身就是两行诗,例如鲁达基的两行诗;有些是四行诗,例如伽亚谟著名的“鲁拜体”;有些是以两行做对句,构成十二对以下的诗,例如哈菲兹的一些抒情诗;有些是以两行做对句,构成十二对以上的诗,例如鲁米的一些诗;有些是以两行诗做对句,构成长诗,例如菲尔多西和贾米的长诗。所以,阿巴斯以俳句或近似俳句的格式写诗,并非仅仅是采用或效仿一种外来形式,而是与本土传统紧密结合起来的。在我看来,阿巴斯的诗是独树一帜的。
这是因为正儿八经的诗人,他们可能也会写点儿俳句,因为俳句已经像十四行诗一样,每个诗人都不能不写点儿。但是诗人写俳句,往往是增加或扩大自己的作诗形式而已。他们如果有什么好东西要写,也会竭尽全力,把它苦心经营成一首正规合格的现代诗。俳句往往成为一种次要形式,用于写次要作品。要么,他们依然用现代诗对好句子的要求来写俳句,造成用力过猛。
因此,我们几乎看不到有哪位现代诗人是以写俳句闻名的。像特朗斯特罗姆晚年写俳句,恰恰证明他宝刀已老,再也无力经营庞大复杂的结构了,于是顺手推舟,把一个或两三个原本可以发展成一首严密现代诗的句子记下来,变成俳句。换句话说,写俳句应该是一生的事业,像日本俳句诗人那样,才会有真正成就。而阿巴斯碰巧成了这样一位诗人。你说他“拾到宝”也无不可。
译者,2017 年5 月14 日,洞背村
- 不止读书-

魏小河出品 微博 豆瓣 知乎 @魏小河
不止好物
点击下面的标题查看详情
▼
1.非常美的笔记本,很少有本子会让我这么喜欢→这可能是我见过最美的本子
2.夏天到了,非常实用的果汁机,让自己瘦下来→嗯哼,人是可以瘦的。
3.一款护眼、好用又好看的台灯→台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