虹膜:老杜,非常高兴你愿意接受我们《虹膜》杂接收我们《虹膜》杂志的采访,我本人就是你的超级粉丝。
杜可风:谢谢。
虹膜:我想从回顾你的电影生涯开始这个采访,首先想问下,最早的时候,你为何会选择由香港到台湾工作?因为你一开始是在香港居住。
杜可风:因为那个时候台湾比较便宜,然后,我没什么钱(大笑)。

杜可风
虹膜:生活成本比较低。
杜可风:对,另外我当时还有一个女朋友想去那边学功夫。然后就在那边开始发展了。接着就开始做一些影像作品,纪录片啊,摄影助理之类。后来杨德昌、张艾嘉找我去做第一部长片。那个时候香港和台湾年轻人的关系很紧密,创作方面来往交流得比较多。偶尔还会有一些大陆的人来交往。所以大家就互相认识了。
虹膜:你去台湾的时候也正好是「台湾新电影」蓬勃发展起来的时候,现在回过头来看「台湾新电影」,有何感触?
杜可风:就像我刚才提到的,当时三地的交流比较多,大家交换意见,互相鼓励,对中国电影来说,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过程。所以会有非常新鲜的口味、风格的电影出现。然后那个时候,怎么说,创作方面比较自由一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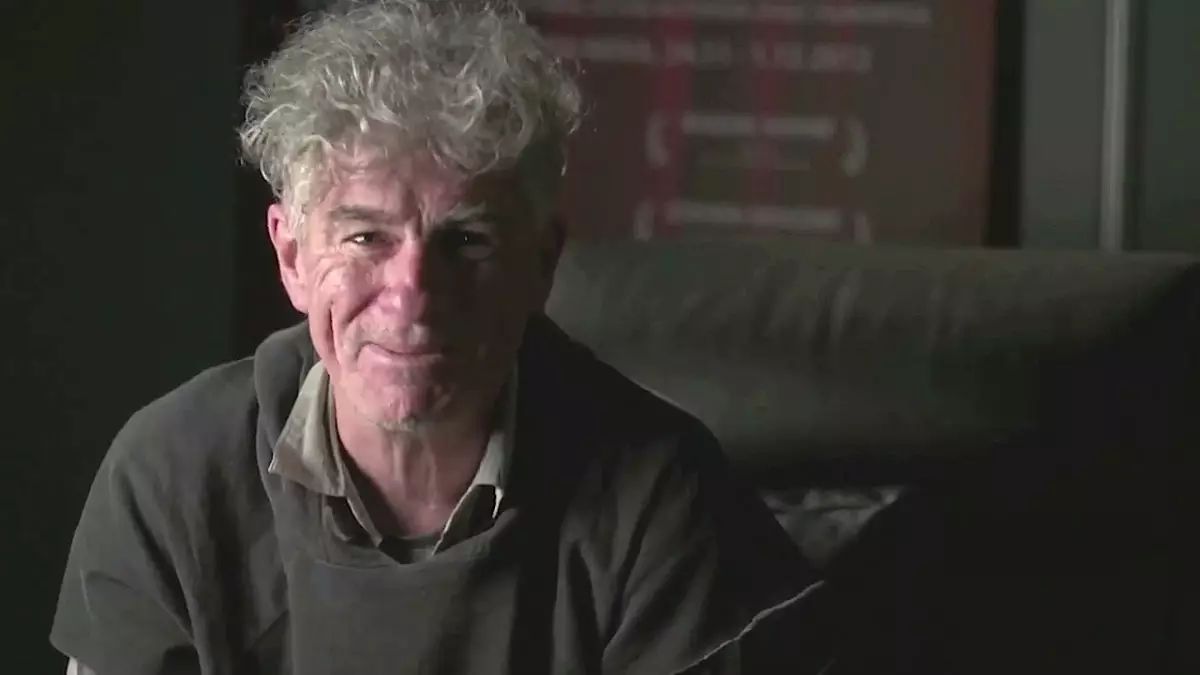
虹膜:自由是表现在?商业和艺术两个方面都比较自由么?
杜可风:是的。金钱方面的来源也比较多。第一,不需要那么多钱,第二,有一些有理想的投资渠道。包括了「中央电影公司」。年轻人也都想做一些创意性的东西。
虹膜:那能谈一些与杨德昌的合作么?关于《海滩的一天》这部电影,你们的合作能简单谈下么?

《海滩的一天》
杜可风:重点是他敢请我去做。我没有拍过长片。35毫米的摄影机我都没碰过。灯光我也不懂,我没有打过灯。所以这对我真的变成很大的一件事情。刚好张艾嘉也很支持,没有他们两个的支持,我是不可能去拍这部电影。甚至于很多人罢工,他们觉得怎么可能找一个外国人来拍中国电影。
反正对我的参与有很多的意见。这也有道理啦,我没什么经验,公司有很多摄影师可用,为什么要用我?奇怪的是,我后来得了最佳摄影(笑)。

虹膜:金马奖最佳摄影?
杜可风:金马奖最佳摄影。我觉得好奇怪啊,我怎么可能是最好的摄影师,这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疑问,所以我就到法国去念摄影了。
虹膜:正式地去研究。
杜可风:对。因为我觉得法国那边会提供很多的经验,艺术创作的机会。但后来我反而觉得法国那边太封闭了。接着又有人请我回香港,这样我所谓的电影生涯就开始了。

虹膜:当时杨德昌为什么会请你?你们在拍摄之前就认识了?
杜可风:我想他是要捣蛋(笑)。他的脾气是这样的。他要刺激别人,重点是他要做点与众不同的东西,让别人注意到他。还有一个原因,我刚才也说过了,大家都认识。艺术界,不管是舞蹈啊还是……
虹膜:剧场。
杜可风:剧场。兰陵剧场我也是创办人之一。所以很多方面的来往特别频繁。

杨德昌
虹膜:你们在拍摄的时候会针对具体的一些摄影问题讨论么?
杜可风:有啊。我们没有太多的经验,当然要谈很多的东西,很多东西都是靠谈出来的。用一些理论性的东西,那个时候我理论特别多(笑)。所以会有很多想法,但没有手法,所以工作进度不是特别快。现在完全不是这样了,现在不需要谈太多东西(笑),都是会直接做。

虹膜:那个年代还是挺理想主义的。
杜可风:对。
虹膜:后来你又回到了香港工作,奇怪的是,你回去后香港的商业电影就非常快地兴盛起来了,但你却没有怎么拍商业电影,拍摄的大部分还是艺术电影。
杜可风:现在也是。很多人以为我是很赚钱的摄影师,其实不是。
虹膜:那当时拍摄艺术电影是有意的选择么?
杜可风:没有,都是一样嘛,都是先互相认识再合作。我到现在也是这样,我拍了快一百部电影,大部分合作对象都是先是朋友才成为合作对象,包括在外国也是,加斯·范·桑特等等,我都是先认识他们,然后,噢,我们合作一部电影吧。不是什么一个公司请我去拍。

虹膜:不是合约聘用的关系。
杜可风:对,对。完全是朋友关系,只不过是拍电影的朋友,所以我们一起拍电影。
虹膜:接下去一个问题可能有点敏感,能谈下《2046》之后为什么没有再与王家卫合作了么?是没有合作的灵感了么?
杜可风:没有,我没有那么多的时间了啊(笑)。与王家卫合作,一部电影需要四、五年,那我现在是一年五部电影。这五部电影不一定每部都是杰作,但以我的脾气,我的个性,我对年轻人的期待,我觉得是要多拍。今年我就拍了五、六部,到年底前起码我还有两、三部要拍。

《2046》(2004)
虹膜:但好像在九十年代,王家卫的工作时间也没有拉那么长吧。
杜可风:有!只有《重庆森林》很短,才一个月。《东邪西毒》好几年呢。
虹膜:两年吧。但《春光乍泄》不长吧,就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拍了几个月。
杜可风:没有,没有,整整一年半!阿根廷拍完了还要回到台湾拍,还有其他事情一大堆。

《春光乍泄》(1997)
虹膜:你也曾经谈到,王家卫、张叔平和你,三个人在一起在艺术创作方面互相会有很大的刺激。
杜可风:主要是大家都对自己有要求,都有一个方向,这个方向组合起来会变成一种力量。另外一方面,我们的生活环境其实很不一样,经验也不一样,他有我没有,我有他没有,所以对艺术创作是一种帮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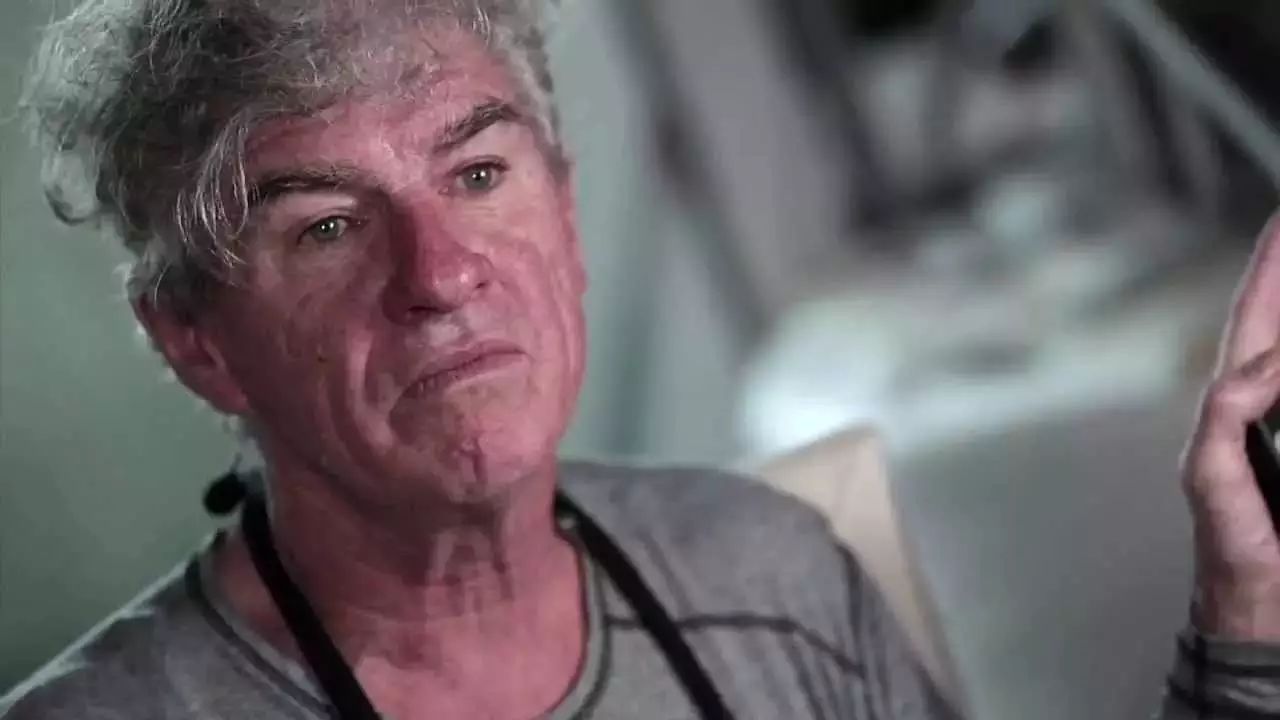
虹膜:《阿飞正传》是你们的第一部,那也是在拍摄之前就认识了么?
杜可风:那个时候我认识的是张叔平。在这之前我拍摄的所有电影只有一部不是张叔平做美术。所以,是因为张叔平,才认识的王家卫。

《阿飞正传》(1990)
虹膜:与王家卫一起合作的时候比较多的会使用手持摄影,这是有什么设想?
杜可风:快(笑)!现在也是,我宁愿用手持,而且很直接嘛,你不用告诉别人怎么做。与演员的来往是一种舞蹈,很近,很亲切,又快,也自由。演员在拍摄的时候什么地方都可以去,没有限制。
虹膜:作为摄影师,你觉得摄影师与导演,与演员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杜可风:最好是我自己全部做(大笑)。
虹膜:演员也是你自己么?
杜可风:也可以,没问题(笑)。我到现在导了四部电影,摄影师都是我自己,没有请其他摄影师。三人之间的关系就是要直接,要信任,相信对方。有时候还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比方说我在美国,有时候是一个三百人的工作团队,全部都听我的,要问我各种问题。所以信任很重要。

虹膜:我查了下履历,你好像从来没有跟欧洲导演合作过,这是偶然么?
杜可风:欧洲的话,我自己导过一部波兰的电影。广告,音乐录影带拍了很多。最近我跟爱尔兰导演马克·卡曾斯(Mark Cousins)合作了个新片。
虹膜:噢,爱尔兰还有一个尼尔·乔丹(Neil Jordan),你们好像合作过。
杜可风:对,对。
虹膜:接下去想问你下你自己执导的那部作品,1999年拍摄的《三条人》,这部电影部分的场景是有音乐,但我感觉即便没有音乐的部分也非常像MV。
杜可风:对。

《三条人》(1999)
虹膜:是怎么设计这种风格的?当时是在什么样的条件下拍摄这部电影的?
杜可风:人家给我钱就拍了呗(笑)。其实我每一次都这样的,不是自己去幻想要做一个导演,都是有人问我要不要做?其实拍摄了这么多电影,已经对电影的每个职位都很熟,导演不过是多了个帽子。
虹膜:影片的三个主角都不是香港人,有什么设想么?
杜可风:因为我在讲我自己的一个故事,我也不是香港人(笑),表面上不是。当时我是想,我离开祖国有四十多年了,我已经做了四十多年的外国人,所以影片要讲述的东西对我来说是非常亲切熟悉的一种经验,这么拍是一个很自然的手法与选择。

《三条人》(1999)
虹膜:那这部电影有没有包含你对香港的某种看法?
杜可风:有啊,全部都是啊。英国人在香港发生过的事情,我都经历过。
虹膜:接下去想问下好莱坞的情况,你在好莱坞也工作过,怎么看那个环境?
杜可风:无聊(笑)。太多的规则,他们对电影的看法,他们的手法,都太保守。你要说技术方面,那当然是全世界最好的。因为它拍那么多电影,因为它有那么多广告,因为它有那么多的钱。
我在那边有时候会拍一些广告,接触到些新鲜的手法,但大部分的电影对我来说真的没什么内容,而且他们的电影都太暴力了!我是非常反对用枪来解决问题的,可以说是极端的反对。我没有兴趣去支持这种制度。

虹膜:不过你在好莱坞合作过的一些导演,像是加斯·范·桑特、贾木许,都算是比较另类的。
杜可风:那种没问题。因为也是先是朋友,刚才说过了。他们有新鲜的手法,对社会有一种要求或者有特定的看法。
虹膜:我很喜欢你与加斯·范·桑特合作的《迷幻公园》,感觉镜头与男孩的关系就像你一直说的「与生活做爱」的关系,当时有什么特别的设计和想法么?
杜可风:有,有。其实没有什么剧本啦,就是二十多页而已,所以基本上是一种很自由的创作过程。小孩子也没什么经验,都不是演员,加斯是故意这么操作的。很多东西都是我们即兴创作的。我们放手让他们去做,很多对白都是他们自己说出来的。所以这种东西是很大的自由。

《迷幻公园》(2007)
虹膜:那与贾木许一起拍《控制的极限》也是类似这样一种很即兴的工作方式么?
杜可风:是,不过吉姆比较慢。因为他是乡下人,跟大卫·林奇一样的人。他们那个环境,那种生活就是这样,节奏特别慢。但对我来说有些……因为我不慢(笑)。我刚拍完了一部新片,二十天就拍完了。所以与他合作,要慢下来,用他的思考方法,对我来说是比较大的挑战。

《控制的极限》(2009)
虹膜:那沙马兰(M. Night Shyamalan)是不是又不太一样?
杜可风:非常不一样,完全不一样。
虹膜:他比较主流了吧?
杜可风:非常主流。从剧本到拍摄方法,每一样东西都是要讨论过的,讨论过的、确定好的每一样东西都是不能动的,非常非常严格。
虹膜:那与他合作是不是有点……
杜可风:很好啊。

沙马兰
虹膜:你觉得这样也可以是吧。
杜可风:对我来说这完全不是属于我的东西。刚才我也说过,现场有三四百个人,不包括演员。那我就要观察,因为我没有做过这样的东西。沙马兰的要求特别严格,手法特别细腻,出来的不是我喜欢的电影,那我觉得如果我可以做这样一部电影的话,接收这个挑战,我就什么电影都可以做了。
就好比是拉塞尔·克罗演的《怒海争锋》(Master and Commander),沙马兰是Master,我是Commander,第二重要的角色。而且有一点,沙马兰也是美国人噢,他也不喜欢我这个人,他们都不喜欢我,不喜欢我的电影,都觉得我是神经病。所以,如果可以过这一关的话,以后拍什么电影都没有问题了。这样的话,对我来说,就是对自己的一种探讨,一种试验,一种要求。

《怒海争锋》(2003)
虹膜:那你跟日本电影圈合作又是怎样一种情况?你跟清水崇他们都合作过。
杜可风:我都演过两部日本电影。
虹膜:他们跟好莱坞有何不同?
杜可风:很奇怪,你会以为他们特别严格,但其实他们特别混乱(笑),工作起来很混乱。他们分工分得特别清楚,每一个部门都只能搞自己部门的东西。好比灯光搞灯光的,摄影和美术互相不说话,在创作方面互相之间完全不来往,特别奇怪。
其实我真的拍了不少日本电影,这个月还有一部我拍的日本电影要上片。那对我来说,这样可不行,我认为一定要互相来往。所以当时工作的节奏也很慢,因为你会觉得这个东西不对劲。要不然你只能让步。因此也搞得有点不开心,但这种不开心是创作方面的。

清水崇
虹膜:想再问个技术性的问题,你还拍过一部泰国电影《无形海浪》(Invisible Waves),这部电影的光线设计非常诡异,特别特别的暗,有什么特别的考虑么?
杜可风:没有,因为导演彭力·云旦拿域安喜欢黑色幽默,他对社会也有很特别的看法,他喜欢捣蛋,喜欢刺激人。另外影片的故事,人的心态也都是非常黑暗的。
虹膜:你与大陆第五代导演像张艺谋、陈凯歌都合作过,这十几年来他们的创作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你怎么看这种变化?
杜可风:我都不看,真的,我是不看电影的电影人。
虹膜:那你与他们这些年还有交流么?
杜可风:没有,基本上没有了。真的,我不是故意不看他们的电影,我什么电影都不愿意看(笑)。基本上,我都看书啊,聊天,喝酒。另外我自己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拍电影,所以没有太多时间去看电影。

这样的话会比较单纯一点,不会去模仿其他人,不会受到其他人的影响。这也是一种选择。再说,有时候我待的地方都没有电影可看,偶然只能看看DVD。除非是朋友请我去,我会去看。
虹膜:那如果他们再找你合作……
杜可风:可以谈啊,为什么不。
虹膜:三十年来,你与中港台的电影人都合作过,能不能谈下大家工作方式的异同?
杜可风:最大的差别是剧本。国内的电影人,在创作的时候,通常都会先有一本书或者其他什么东西,然后再把它转化成剧本。其实这一点跟好莱坞有点像。他们会对文学语言,对叙事结构,对历史,有一种尊重。这里面当然也有审查的原因,有一些东西是不能谈的。

虹膜:香港电影界创作的时候好像很少改编文学作品。
杜可风:对,因为……怎么说呢,我不能说香港没有文学创作,但是香港的文学创作是比较孤独的。写作在香港是一种很孤独的生活方式,政府不支持,大部分的人关注的是钱嘛,不是生活,不是历史。而台湾有自己的历史包袱,所以他们的创作会比较偏向于某种特定类型的作品。
虹膜:你最有一部新作《香港三部曲》要在多伦多影展公映了,能不能谈下为什么要拍摄这部电影?
杜可风:因为我对香港有一些想法。不过我的想法跟别人的想法不一样,所以我要他们来告诉我,香港社会是什么样子。影片有第三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访问年轻人,最小的是五岁,最大的是十八岁,让他们来告诉我他们自己的故事。然后我根据他们的故事再来创造一个故事,这两个故事是相类似,但不相同。

《香港三部曲》(2015)
其实是他们在创作这部电影,只不过它的结构,它的内涵,它的空间都是我创造的,但故事的源头在他们身上。他们说出来的一些幻想,关于家庭的观念都是他们自己的。比如有一个小孩讲,他被耶稣基督控制了一切,「谢谢基督」,这样的东西我想不出来,是他给我的。
第二阶段就是访问大学生。第三个阶段是访问老年人。其实这么做的出发点、重点是,我凭什么说香港?虽然我对香港很熟,但我还是一个外国人。并且这么做还有一个好处,不需要写对白,只有旁白。

《香港三部曲》(2015)
虹膜:这是剧情片还是纪录片?
杜可风:不知道(笑)。没有人可以告诉到底是什么。在多伦多它被称为剧情片,接下来的釜山被称为纪录片,而在丹麦的一个影展,他们还在讨论,这到底是剧情片还是纪录片。其实我自己觉得两个都不是。
香港的话,是9月18日公映,因为是一个很特殊的电影,我们最开始不知道怎么发行。因为正常的电影院不太可能会放的,所以我们考虑后决定用特别的方法。我们决定每个礼拜放五场到八场,网上的订票现在已经卖光了。我想是他们都很好奇吧,他们自己的故事,经过我的所谓的手法的处理,会变成什么结果。
虹膜:想问一些艺术创作方面的问题,你在多次的访谈中都强调,对你来说拍电影最重要的是空间。那这次在震旦博物馆与画家张恩利合作,你觉得电影空间和绘画空间有何不同?
杜可风:当然是不一样的。不过这一次的合作(编注:杜可风与张恩利最近在震旦博物馆联合举办了名为「画影之间:张恩利×杜可风」的展览),过程其实是像电影一样的,有了博物馆展览的这个空间,才有了我们的合作。
我们之前其实沟通的不多,是到了这个空间后,我们才有火化,才有你现在所看到的东西。当然我也有所准备,但对我来说整个过程和拍电影差不多,都是有了空间后才有一切。

「画影之间:张恩利×杜可风」
虹膜:我看有一些场景,你自己也在里面演。
杜可风:对啊,也是因为我看到这个空间有意思,所以走进去了。
虹膜:你在好莱坞、日本都工作过,与中港台的电影人都合作过,你觉得东西方电影人对空间的把握思考有何不同么?
杜可风:这要去图书馆查几万本书才能回答啊(笑)。其实说到底这个跟社会、文化是同样性质的问题。西方是基督教,一直有一个比较在里面。电影创作也是这样,先有这个,再有那个,结果是这样子。
大部分都是三个阶段,疑问,冲突,结果。东方当然是因为有佛教,有道教的影响,所以是一个循环的系统,故事、风格以及真正意义是慢慢地被呈现出来的。我觉得创作的方式跟文化传统完全是联系在一块的。

后记:采访杜可风是一次很特别的经验。因为我本人不是专业记者,采访的经验不是很丰富,所以在采访的过程中一遇到自己感兴趣的话题常常会忍不住打断老杜,幸好老杜不是那种喜欢长篇大论的说客,所以话题最后总能适时的回到预先设定的轨道。这次采访最深的感触有两点。
一是老杜确实是纯感性的性情中人,有着很朴直的艺术家人格,整个采访过程持续不过半个小时,他却喝掉了两瓶龙舌兰、一听啤酒,要知道这可是大早上。
二是在言谈中,我能很明确的感觉到老杜非常怀念八十年代港台电影工作人紧密交流无间的那种气氛。那也是百年华语电影最有创造力的时代。遗憾的是,很多话题,由于时间限制没法展开,只能触及到面的广度,无法触及到点的深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