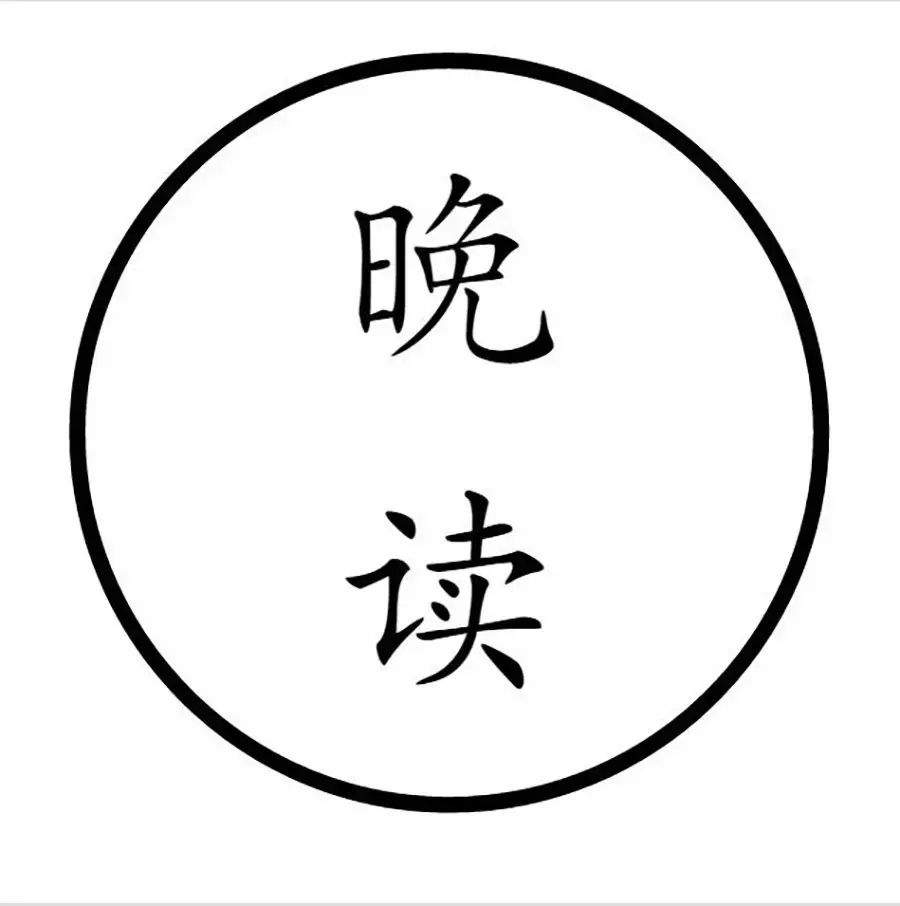前一段时间,“瑞士卷事件”冲上热搜,引发热议。起因是一位博主和丈夫对于如何分食瑞士卷起了争执:博主买来一盒8个瑞士卷,丈夫和两个孩子每人吃了两个,博主想吃时却被丈夫指责称“妈妈不应该抢孩子的零食”。这一事件在网络上引发了一波声讨,许多网友向自己的男性伴侣提出“瑞士卷拷问”,即“你认为应该如何分配瑞士卷?”仿佛这种分配就是爱的分配。更进一步地,在这场关于瑞士卷的家庭风波意外掀起全网讨论后,也引发更深一层的反思:为何女性普遍有着“低配得感”,把自己的需求放在家人之后仿佛理所当然?
“瑞士卷事件”折射出当下女性群体中,对情感关系和自我意识的认知分野。一部分女性依然深受浪漫爱观念的影响,更习惯于在爱情领域中强调自身掌控,试图制定情感规则并要求男性遵守以证明爱意;另一部分则提倡女性独身与自我价值,摆脱情感依附。这场关于瑞士卷的争论,其实更像是一次关于女性个体角色的时代拷问。
这种女性意识的分裂,在大众文化中尤为凸显,尤其体现在观众对影视剧的不同偏好。近年来,出现了“大女主叙事”热潮,对比从前以“爱情至上”为主的叙事,显现出了主流观众口味的转变。从观众对《如懿传》中“恶毒女配”魏嬿婉的推崇,和对女主角如懿的嘲讽来看,受欢迎的女性叙事的脚本似乎正在转变——传统上隐忍谦让,具有“利他”属性的女性主人公不再受人尊重,反而被视作“客体化女性”的附庸,而那些狠辣“利己”的女性角色则被推崇为主动表达欲望、追求自我实现的女性主体。这种转变折射出网络讨论中,持有不同性别价值观的女性群体在声量上的变化。尽管现实中仍有大量女性欣赏如懿这样细腻隐忍的角色,在先锋与传统的意识形态争论中,女性群体的分裂无形中正在加剧。这种分裂在文艺作品展现得淋漓尽致。
以上能够被总结为“控诉”和“宣判”两种女性视角的叙事,它们的女性受众群体截然不同且相互不理解。尽管它们代表着不同的挣扎路径,但都暗示女性处于无奈、被迫的边缘境地,用互联网上比较流行的惆怅情怀进行总结,即“逃离是刻进女性身体的史诗”。然而,在它们之外,还存在着一种更具兼容性和生命力的女性叙事,即“奔向”叙事,它强调强健的想象力,值得期待和构建的边缘,以及女性自主成长过程。
本文结合《他和她的她》《玫瑰的故事》《山花烂漫时》《我本是高山》《半熟男女》《一路朝阳》《某种物质》《好东西》等十几部影视剧文本展开,这些影视剧文本都极具当下性,也得以让我们看到大众流行文化当中女性叙事的转变趋势。

“女性叙事”与“女性主义叙事”都可能以“大女主”类型片展现出来,但两者在表现方式上存在差异。“女性叙事”侧重于展示女性的生活和经验,它并不一定带有强烈的社会批判意图,更多的是展现在特定社会结构中女性经验的复杂性。而“女性主义叙事”则带有明确的社会批判性,强调性别不公,倡导女性的觉醒和解放。当前流行的大女主叙事方式大致可以分为两种:一种偏向女性叙事,是败者视角下的“控诉”,比如《他和她的她》中被性侵的女主角;另一种则偏向女性主义叙事,是采取胜者姿态的“宣判”,比如《延禧攻略》中绝对自洽的复仇宫女魏璎珞。
《他和她的她》剧照。
“控诉”叙事通常聚焦于女性的苦难,尤其是以受害者的视角来展现。这种叙事方式不仅能使处于困境中的女性感受到某种联结——“原来不是我一个人在经历这些”,同时也能激发其他群体的共情。通过个体苦难的描绘,文艺影视作品能够以更直观的方式揭示父权制下女性的困境,较之抽象的理论,具有更强的情感冲击力。
然而,当控诉叙事过度依赖“诉苦”而缺乏自我反思时,往往会失去应有的共鸣。如《我本是高山》便因其单纯的苦情叙事而未能获得积极评价。另一方面,这种叙事也很可能受主创和观众意识的影响,失去批判性,甚至在不知不觉中被收编,成为封建陈规的无意识传承者。例如,《如懿传》原本试图塑造一位敢爱敢恨的女性,她以极端情感化的方式实现对封建父权制的厌弃,然而,最终,呈现的却是一个缺乏才华,却充满道德优越感的父权制附庸。

《我本是高山》剧照。
“宣判”叙事通常表现为女性主体性的胜利,往往带有较为乐观的基调。此类叙事以“胜利者”的姿态呈现,主要出现在古装剧和都市爱情剧中。在古装剧中,女主角通常通过宫斗或宅斗的形式展现其主体性。她们或是至亲惨遭不幸,以复仇为目标实现自我成长,或是在封建父权的压迫下,爱慕高位者却遭受伤害,最终看清男权秩序下的爱情神话,从而开始重构自我。另一方面,都市爱情剧则常常陷于爱情本位框架中,并因追求“爽”而虚浮失真,逃避了女性的真实困境。
《玫瑰的故事》剧照。
毫无疑问,“宣判”叙事能够赋予观众强烈的自我赋权感,但当前的流行趋势更倾向于讲述个人的传奇故事,而忽视了性别结构的不平等。例如,《玫瑰的故事》虽然通过黄亦玫展现了积极的女本位视角,但在胜利者的姿态下,却掩盖了女性在生育劳动和其他现实困境中的艰难处境。更为重要的问题是,这类偶像剧常常迎合观众对“强者”的崇拜,模糊了自强女性的个体心理与对女性群体苛刻的社会规范之间的界限,最终生产出理想化的强大女性形象,这在现实女性的无力感面前更显荒谬。
《再见爱人4》剧照。
理论上,这两种叙事方式并非相互排斥,而能够在同一部剧集中交替出现,它们分别呈现了不同女性处境下的情感表达和身份认同。但是,这种视角差异实际上时常引发观众之间的分歧。以情感综艺《再见爱人4》为例,嘉宾麦琳的行为模式在互联网上引发了广泛讨论。很多人讨厌她的地方在于,作为家庭主妇,麦琳频繁抱怨自己的付出没有得到丈夫的认可,却又拒绝接受对方所有的爱意表达。在某种程度上,她的讨厌源于其“怨妇”叙事过于平庸,与观众习惯的胜者姿态的精英化“大女主”叙事产生了冲突。此时,观众对“宣判”叙事中强者逻辑的偏好,盖过了对使用“控诉”叙事的普通家庭主妇困境的理解和关怀。麦琳的叙事困境,实际上揭示了女性主义叙事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如何在表达苦难、揭示社会结构问题和追求自我解放、自强奋斗之间找到平衡。这也许正是当今流行文化中女性叙事的空白所在。
相比于“宣判”叙事,“控诉”叙事在当下似乎更不受欢迎,结合“娜拉出走”的母题,我们能够更清晰地呈现问题的脉络。在易卜生的《玩偶之家》中,娜拉成功逃离了笼罩着夫权的家庭,这种独立和自我解放的魄力无疑值得肯定,其出走故事的核心是“成长”。而麦琳是未能出走的娜拉,她“既要又要还要”的拧巴状态,以及缺乏自我认同却拼命寻求他人关注的行为,都让人反感。这又何尝不是每一个觉醒女性曾经经历过的状态?既没有勇气和能力真正出走,又无法停止地“控诉”自己未能获得娜拉所应得的尊重。
麦琳的行为具有一种模糊的双重性:一方面,作为家庭主妇,麦琳似乎缺乏出走的实际理由,正如网友所批评的:依赖丈夫,享受着富足的物质生活;另一方面,她的“控诉”虽然缺乏逻辑,但也可能是一种出走的前奏。或许,我们可以以“成长”的眼光来看待这类“控诉”。公众号“别的女孩”对“摩门娇妻”的分析放在这里同样适用:“当我们把‘独立女性’当作标准时,可能会忘了这个世界上还有多少人正在尝试从无数性别枷锁中挣脱出来。”麦琳扭曲拧巴的“控诉”,或许正是其成长的起点:她察觉到了问题,却无法理清思路,因此开始了不体面的抱怨、内耗和攻击。这在日常生活中并不少见,但这种情形在当下的影视创作中鲜少被呈现。
《玫瑰的故事》剧照。
同样忽视“成长”的,是大众文化中的“宣判”叙事,它常常直接站在了“出走的终点”上。这也是许多“大女主”影视作品被批评为“悬浮”的原因之一——这些作品中的女性角色实际上并没有经历过真实的出走,外部和内部的成长都被潦草地带过。细看《玫瑰的故事》中新女性代表黄亦玫,会发现她无需为事业和母职劳动操心,社会中女性的舞台好像是天然存在的。此外,当前的叙事还给观众留下虚假的印象:只有世俗意义上的强者女性才值得被赞美与推崇,而那些无法“出走”,或者在出走过程中软弱、挣扎的娜拉,则被视为卑鄙无赖。
《一路朝阳》剧照。
这些问题与鲁迅先生在《娜拉走后怎样?》中所揭示的问题相契合:娜拉能意识到自身困境的存在,意味着她内心已经萌发了独立的人格和情感,但这并不代表她具备独立生存的能力。社会中的性别化经济结构最终只会让娜拉面临两种选择——“不是堕落,就是回来”。如今,困境发生了微妙的改变,在真实世界中,舞台早已初具规模,但是进一步搭建的幸苦和汗水往往是娜拉迈不出第一步的缘由;即便成功出走,社会对传统“好女孩”的嘉奖,也可能导致她们再度回归。于是,独立的人格和情感再度成为问题。在双女主电视剧《一路朝阳》中,李慕嘉和田蓉最初相互鼓励,携手出走,但最终却在恋爱关系中各自以扭曲的方式回归传统女德的框架,成为付出为主导,前后人格不自洽的圣女。
那么我们究竟可以期待一种什么样的叙事?
《山花烂漫时》剧照。
面对不同女性在价值选择上的分裂,我们或许不必在“控诉”和“宣判”二者之间做出选择,而是在理解二者的基础上,探索一种能够兼顾这两种群体诉求的新叙事形式,这种模式着眼于成长。《山花烂漫时》或许是一次成功的尝试。这部围绕张桂梅老师事迹展开的群像剧既没有单纯地陷入受害者的“控诉”姿态,也没有否认女性的弱势处境,而是采用了“理解环境、接纳自己、奔向未来”的叙事角度。比如,剧中的女学生“谷雨”受到侵害时,镜头没有过多强调受害者的绝望,而是聚焦于张桂梅老师如何冷静理智地帮助受害者争取权益。同时,本剧的人物塑造还带有一种来自底层的淘气的自足和自尊。比如,张桂梅老师第一次品尝奶茶后,就用自己的奖金给女孩们每人买了一杯当地最好的奶茶,吃苦耐劳和享受生活并不矛盾,无论境况如何,它们都是人的尊严的体现。“奔向”叙事中的娜拉,坦诚且松弛,风尘仆仆且眼里有光。
“奔向”叙事的难得之处在于它展现了女性的勇气和成长的落地。女性能接受无奈的现实,但它不代表终点,有一个更好的未来值得憧憬。当娜拉们意识到自己能追求更有价值的目标,看到了全新的人生可能性时,她们便从“出走”转而“奔向”。正如影视博主“42手册”所言:追寻自由和自我价值的实现,实在强过日复一日的哀叹千百倍。
“奔向”叙事为那些无需出走的女性提供了行动的理由——存在着那么多种与当下不同的精彩生活方式,更是在娜拉们迈出的每一步中注入了坚韧的乐观主义。作为信念者与行动者,“娜拉”边走边思,在回望中辨认起点,敏锐地感知每一个转折的可能,有时加速奔跑。在这一过程中,女性获得了一种既轻松又坚定、既严肃又充满游戏精神的心态:先做,人总会出错,错了再来;先玩,游戏规则有问题,边玩边改。
然而,为什么当下的大女主叙事中少见“奔向”的身影?关键或许在于缺乏想象力和勇气。大女主叙事的核心困境是,女性的生活常被标签所限制。正如上野千鹤子在《厌女》中所说,女性似乎总在“母亲”或者“荡妇”之间被迫选择,我们是否可以打破这些框架,不是换个刻板印象,而是重新想象一种更自主、更自由的生活方式?这份想象力与勇气,正是“奔向”叙事所呼唤的。

《某种物质》电影剧照。
今年上映的恐怖电影《某种物质》揭示了限制女性想象力的社会机制。片中,社会对女性身体的剥削被利兹——一位50岁的女明星——内化为自我追求。为了重获完美如同商品的年轻美貌,她使用生物制剂,从本体中分裂出一个20岁的“新自己”。随后,她便挥霍无度地透支母体的体液,维系新身体的稳定。影片赤裸呈现了现代女性如何在自我蚕食中沦为资本主义与父权制杂交体的养料。如易洛思在《冷亲密》中对这种情况的形成原理做出了分析。互联网和市场思维的结合让人们始终将自己置于与他人的公开竞争中。市场化渗入人际关系中,制造出一种同质化的“虚假多样性”,每个人都过于看重自己的“个性”,而这些“个性”如同商品,表面琳琅满目,实则价值趋同,通过抽象的市场价值进行交易,真实的个体差异不再被承认和欣赏。竞争心态与市场化的结合进一步压缩了女性探索自我和拓展想象的空间。
想象和出走都需要勇气,那么当下的女性主义叙事是否真正赋予了这种力量?在电视剧《半熟男女》中,表面上每位女性角色似乎都接受了自己的“道德瑕疵”,但剧情依然暗暗强化了情感上的“纯粹”标准。例如,何知南被贴上“脚踏两条船”的标签,但她始终重视真感情,而两位男主角的情感算计远胜于她;看似“上岸先斩意中人”的独立女性韩苏,实际上在关系中更为负责。女性的“瑕疵”似乎只有在“真心错付”的前提下才被宽容。这正是随时代变幻的“好女孩魔咒”,而过于强硬的女性主义也可能无意间成为它的帮凶。娜拉不是因为足够好才有资格出走,也不是出走之后就一定要过得足够好。事实上,在远非理想的现实中,我们更需要讲述女性如何找到真实的主体性,而不是如何成为完美无缺的人。
《半熟男女》剧照。
电影《好东西》就展现出了这种轻巧且柔韧、现实却灵动的女性主义态度。“恋爱脑”歌手小叶的“快乐倒贴”实则是缺爱女孩的自我疗愈:全情投入恋爱,是为了他人的关注,更为了释放自己的真性情;单亲妈妈王铁梅向现实妥协,放弃记者理想和真实报道,却始终以倔强姿态,不屈于生活;敏感而怯懦的小孩王茉莉是新一代的“娜拉”,总是能在“不合时宜”的时刻吐露残酷真相。电影中的一幕可以被视作“女性主义奔向”的极佳隐喻,小叶让王茉莉听声音,王茉莉耳中的“宏大”声音,泥石流、暴雨、鳄鱼冲破水面等,其实是妈妈王铁梅做家务的声响,切菜、拖地、用豆浆机。这里暗藏可能的多重解读:母亲在“寻常琐碎”中的消耗,是女儿心里的“宏伟崇高”。女性所承载“寻常琐碎”不仅是伟大的,也是孕育崇高的土壤,想象和勇气使其生长。《好东西》在向每一个女孩展现多彩的“娜拉”,她们挽着手,舞蹈在妥协与不妥协之间,明亮而深刻。
女性在出走时,并不需要自证出走是“合法的”,即绝对的正确性,出走依据的是“合理性”而非“合法性”。这种合理性就是一种“饱满的自由”,或者说是内在不断涌现的生命力。出走不是出逃,而是奔向。外部的旷野已经在疯狂生长,女性当下的奔向不只是开拓一个更宽广的外部,也是激活女性身体里灵动的、强劲的、不确定的内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