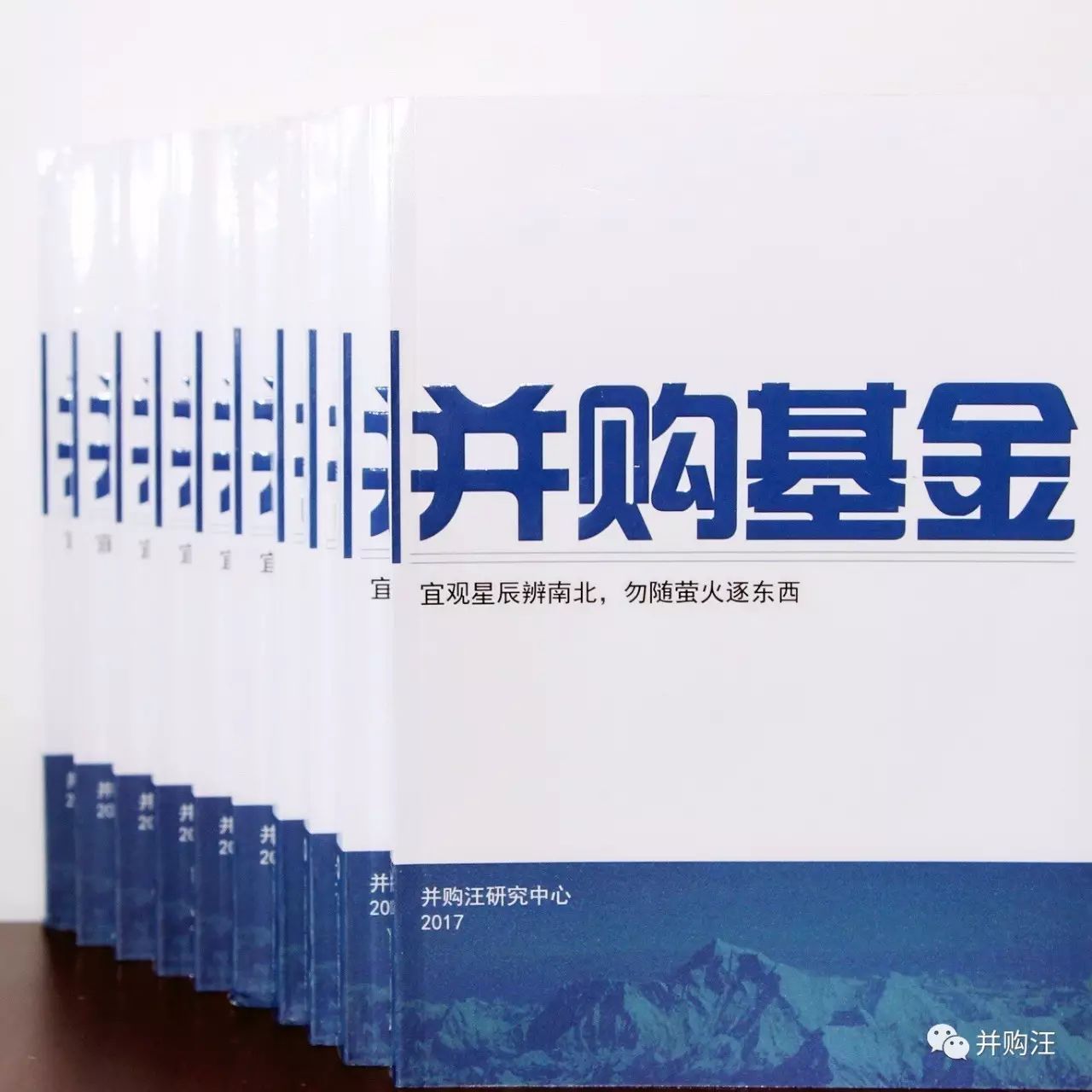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刘光裕先生,于2024年4月2日因病逝世,享年88岁。
刘光裕先生,1936年出生,江苏武进人。中共党员。1959年毕业于山东大学中文系,留校执教。1970年,借调至山东省委宣传部工作。1973年,回到山东大学,任《文史哲》编辑部副主任,全权负责复刊等事务。1975年初,重回山东省委宣传部。1978年,任山东省委宣传部理论研究室副主任。1979年夏,再次回到山东大学,出任《文史哲》编辑部主任。《文史哲》发行量在1982和1983年居全国同类刊物之首。1984年冬,辞去行政职务,回中文系任教。1996年退休。
刘光裕先生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知名的、具有广泛影响的编辑学专家和出版史名家。他关于编辑概念的论述,引发学界广泛关注与长期讨论;他是《中国出版通史》的发起人;他的中国古代出版史研究具有开创性,在出版史学界产生强烈反响。在经学、柳宗元研究、汉字文化等领域,刘光裕先生的研究也产生过重要影响。半个多世纪的学术生涯中,刘光裕先生出版了《编辑学论稿》《柳宗元新传》《编辑学理论研究》《历史与文化论集》《先秦两汉出版史论》《蔡伦造纸与纸的早期应用》等著作,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刘光裕先生两度主持《文史哲》编辑部的工作,对《文史哲》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而突出的贡献。
刘光裕先生的辞世,是学术界的重大损失。我们将永远纪念他。
刘光裕先生千古!

《文史哲》创刊于1951年5月,至今已有半个多世纪。创办《文史哲》的关键人物是华岗。华岗(1903-1972),浙江省龙游县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党内宣传部门高级职务。抗战初期,因公开指斥王明错误而被王明撤掉《新华日报》总编辑之职;以后历任中共中央南方局宣传部长、中共上海工作委员会书记等职,并任云南大学社会学教授。1949年9月,华岗应召从香港赴北京参加政协会议,途中因健康原因滞留青岛,经中共山东分局向中央请求暂留青岛工作。接着,担任山东大学校长、党委书记,直至1955年蒙冤入狱。他任山大校长之前,有重要著作如《1925-1927年中国大革命史》《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社会发展史纲》等,都早为国人熟知。林默涵在1982年著文说:“中年以上的人对华岗同志是很熟悉的,许多人跟他一起工作过,更多的人读过他的著作。他是一个革命活动家,又是著名的史学家、哲学家。”华岗既是党的高级干部,又是著名学者。他任山东大学校长的五六年间,成为山东大学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创办《文史哲》,是华岗对山大的重要贡献之一。
《文史哲》自1951年5月创刊,到1953年第2期以前,共11期,一直是山东大学文学院与历史语文研究所部分教师的同人刊物。1951年,山东大学部分教师发起成立《文史哲》杂志社,共同推举校长华岗为社长,副校长陆侃如教授、文学院院长吴富恒教授为副社长,又邀历史系著名学者杨向奎教授任杂志主编;以杨向奎为首组成编辑委员会,负责日常工作。因为是同人刊物,《文史哲》具有“自治”性质,办刊方针及其他事务由杂志社同人自己研究确定。当年商定的办刊宗旨是,通过刊载应用新观点、新见解的研究文章,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与学术水平,推进学校文科的教学与科研。办刊经费主要靠同人自筹;参加办刊的教师都拿了钱,其中以华岗个人支持经费较多。学校也曾从科研经费中给点资助,但数量不多。编辑部的后勤工作,由历史系与历史语文研究所的两个工友兼做。编委会中没有一个专职人员,主编杨向奎是兼任,具体做编辑工作的编委成员也都是兼任。早期编委如童书业、王仲荦、赵俪生、殷焕先、卢振华、孙思白、孙昌熙、刘泮溪等,后来都是著名学者,当时还很年轻,他们大多跑过印刷厂,做过校对。从组稿审稿,到校对印刷,到刊物发行,这些工作都是教师兼做的,没有报酬。本校教师发表文章包括华岗校长的文章都不给稿费,当时也没有人想拿稿费。校外的稿子给少量稿费,最早是每千字3万元,即3元。1952年夏天以后,葛懋春从历史系毕业留校做助教,他成为《文史哲》第一个专职编辑。专职编辑只有葛懋春一人,忙不过来,许多编辑工作仍由教师兼做。刊物开办时,没有在邮局或书店发行。主编杨向奎回忆说:“热心的同志们都不懂出版发行业务。第一期出版了,既然没有邮局或新华书店发行,我们如何发行,把它们卖出去?只好采用原始的办法,给全国各大学的朋友们寄出,请他们代售。这当然不是办法,连累了朋友,许多是他们自己拿钱买下,把钱给我们寄来。我记得郑鹤声先生对我说,这不是办法,他的朋友来信说这办法太原始了。”刊物销路没有打开,不可能不赔钱。大学教师办刊物,最大的问题不是稿源,而是资金。刊物不断赔钱,教师工资非薄,财力有限,所以创刊一年后到1952年,出现严重亏损局面。实在支持不下去了,华岗校长不得不亲自到山东省委统战部和青岛市委请求支持2000万元,即2000元,才渡过难关。从1953年第2期(总12期)开始,《文史哲》确定为山东大学学报之一,经费从此由学校负责,不再需要教师个人支援。不过,从1953年开始,刊物销路也打开了,经费困难实际上已不复存在。到1955年,国内外订户大增,刊物经费自给有余,还积累了上万元资金。
20世纪50年代初期,全国学术刊物只有两家,就是《新建设》与《文史哲》。《新建设》在北京,《文史哲》在青岛。到1957年,上海创办《学术月刊》,学术刊物便形成三足鼎立之势。1951年,正值新政权建立之初,数年内战的腥风血雨之后。这时候,山东大学文科教师为什么创办同人刊物——《文史哲》呢?这件事当然与华岗有关,不过细究起来原因大概有二:
原因之一是,当年山东大学聚集了一批率先拥护新政权的著名学者与青年学者。这一点,主要应归功于华岗以前的山大校长赵太侔。1945年抗战胜利后,国立山东大学在青岛复校,校长便是戏剧家赵太侔。赵太
侔
,是山东籍同盟会员,国民党元老;民国后,弃政而到美国留学,专攻舞台灯光。在新文学家杨振声教授做青岛大学第一任校长时,赵太
侔
任教务长。他长期担任山大领导,学术界名气不大,然而作风稳重,为人正派,在政治动荡中能保持自己的清白与正直,校内外口碑颇佳。在办学方面,赵太侔崇尚教育家蔡元培的兼收并蓄办学思想,故而山大颇有学术自由的宽松氛围,不拘一格招揽人才,再加青岛环境幽美,交通便利,气候宜人,这些因素促使一批学者在抗战胜利后纷纷投奔山大。例如,大后方的著名红色教授赵纪彬、杨向奎,还有因为同情学生运动而上过国民党当局黑名单的陆侃如教授、冯沅君教授,还有对现实甚为不满的青年学者赵俪生、徐中玉、孙思白等,他们都乐意到山东大学工作。抗战胜利后,随着东南沿海各地大学陆续复校,学者教授也纷纷选择自己乐意工作的大学。山东大学借1945年复校的机会,聚集了一大批国内学术精英,文科理科都是如此。在这方面,校长赵太侔起了重要作用。1951年初,山东大学与华东大学合并。华东大学是山东解放区办的大学,学生为革命青年,教师都是参加革命较早的知识分子。与华东大学合并后,校内的革命气氛立即高涨起来。20世纪50年代初期,当全国多数大学的教师惊魂未定、犹豫狐疑之际,山大许多教师已经成为新政权的衷心拥护者,思想包袱较少工作积极主动,热情高涨。山大这样一批教师与华岗出任校长这两方面因素结合起来,就具备了办刊物的条件与勇气,结果就在1951年创办了同人刊物——《文史哲》。
原因之二便是,校长华岗的领导才能与个人魅力。华岗是中共山东分局三人领导成员之一,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史学家,又办过报纸刊物。他的地位,他的经验,他的个性,足以作《文史哲》的强大后盾。《文史哲》所以在1951年创刊,而且越办越好,华岗校长是不可或缺的关键人物。华岗对早期《文史哲》的贡献可从两方面去看,一为领导山大师生学习马列主义,二为亲自领导办刊物。
华岗办大学,始终将教学与科研置于首位。1951年任山大党组副书记(华岗是党组书记)与教务长的余修回忆说:“他(华岗)主持校政,把山大办得生气勃勃,上下一体,培育英才而英才辈出,改革教育而能推陈出新。“余修后来是山东师范学院院长,山东省副省长。华岗坚持“以教学为中心”,要求政治思想工作和总务后勤工作都围绕教学这个中心。与此同时,他又把学习马列主义,作为改造大学与提高教学科研的关键来抓。新中国成立后,华岗是最早领导全校师生系统地学习马列主义的大学校长。他定期在全校作时事报告,亲自作系统讲解马列主义的报告。这类报告的地址,一般在学校广播站前的露天阶梯广场;台下听讲的,有全校师生,从副校长童第周教授、陆侃如教授到普通学生,还有青岛市委、北海舰队司令部的领导与干部。华岗学识渊博,思维敏捷,见解深刻犀利,再兼口才好,所以每一次作报告,都是人山人海,像赶集一般热闹。经数十年至今天,山大还有人津津有味地讲说华岗当年作报告的精彩与热闹。他凭自己的经验与能力,使学习马列显得不那么枯燥与沉重,变得有人情味,生动活泼。因此,学习马列很快成为山大教师的一种时尚。像先秦史学者童书业教授可以背诵《家庭、私有制与国家的起源》,可以背诵《联共(布)党史》“四章二节”,校园里无人不知,可见学习热情之高。前面谈到,山大聚集了一批率先拥护新政权的著名学者与年轻学者,现在他们又掌握了马列主义这个武器,进而想写文章、办刊物,就是合乎逻辑的事。从社会环境看,当时正处于新旧潮流的剧烈变革之中。山大文科在20世纪50年代出现一批应用新观点的科研成果,表明山大文科居于新时代学术潮流的前沿地带,暂时取得了符合时代潮流的一种学术优势。凭借这个优势,《文史哲》充当了弄潮儿的角色,影响或引领全国学术潮流,从而使偏居青岛的一家大学学报,在全国如日中天,独领风骚,创造了一段令人难忘的历史。就刊物本身而言,成功的关键在于能否影响或引领学术潮流。时代潮流后浪推前浪,总是不断演变,不断进步。刊物一旦在时代演变中失去学术优势,不再影响或引领学术潮流,辉煌不再怎能避免?此一时,彼一时,不必同日而语。
在1951年那个特殊的年代,除了华岗敢办《文史哲》,全国大概没有人想办什么同人刊物。华岗是《文史哲》第一任社长。他坚持的办刊方针是将马克思主义渗透到各个领域。每一期文稿,都由主编杨向奎送到他那里作终审。1952年开始做专职编辑的葛懋春回忆说:“每期文章他都亲自审定,通读一遍。每次开常务编委会前,都听取我们对稿件初审的汇报,同时他对送审的稿件提出修改意见;为了赶上出版时间,他往往连夜突击改稿。”审定《文史哲》的文稿,不只要有广博学识,还要有丰富审稿经验与一丝不苟的负责精神。华岗一天到晚很忙。他是校长,是党组书记,还是山大教授。他做山大教授不是靠手中权力,而是靠自己讲课。他为山大学生讲的都是当时大学里的新课,如中国近现代史、中共党史、鲁迅研究等。他一面讲课,一面培养年轻教师。山大中文系研究鲁迅的老师,历史系研究近现代史的老师,最早多是听华岗讲课而渐渐成长起来的。所以,华岗真的是非常忙。可是,他再忙也坚持为《文史哲》终审书稿,此为尽职,此为敬业。如今,兼任学报主编或编委会主任的大学领导,大概已很少像华岗那样亲自终审文稿了。作为大学领导的华岗,颇具个人魅力。对他心悦诚服者,不仅有学生,更有同事与教授,全校上下几乎有一种崇拜心理(后来,果然有人批判华岗在山大的所谓“个人崇拜”)。开始时,人们对写文章顾虑较多。华岗带头写稿,成为解除人们顾虑的好方法。从1951年到1955年蒙冤被捕以前,他在《文史哲》上发表文章40多篇,几乎每一期都有他的文章。他鼓励人们用马列新观点从事科研,经常动员教师写文章,著书立说。山大文科很快出现应用新观点的风气,不断为《文史哲》提供具有新意的文稿。华岗做《文史哲》社长,不是挂名的社长,是脚暗实地做事的社长。诚然,办《文史哲》并非华岗一人之功,但他起了关键作用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文史哲》创刊后给国人的一个突出印象是非常活跃,不断开展学术讨论,不断提出新观点、新见解。《文史哲》早期的重要学术讨论,历史领域有中国古代史分期、中国土地制度、古代农民战争、资本主义萌芽等,文学领域有韩愈柳宗元评论、《红楼梦》评论、鲁迅研究,以及典型问题等。
《文史哲》是学术刊物。华岗是革命家,他办《文史哲》始终坚持宣传马克思主义。他认为马克思主义与学术的关系,是前者指导后者,而不是代替后者。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学术研究,出现不同的理解或不同的见解,是完全正常的事,也是难以避免的事。解决这类不同意见的分歧,只能通过充分的与自由的讨论,此外没有别的好办法。在他看来,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立场与以客观态度尊重学术,两者没有矛盾。在史学领域,华岗并不同意“古史辨”派的观点。众所周知,“古史辨”派并不是马克思主义学派。但是,华岗屡次鼓励原为“古史辨”派的童书业教授搞自己的专业,说“古史辨”作为学派具有自己的价值。相信自己不同意的学派具有学术价值,这样的态度可算是客观尊重学术。充分尊重学术,提供自由讨论,使《文史哲》在“双百”方针提出之前的学术讨论搞得风风火火,有声有色。这成为《文史哲》举世公认的一大亮点。
在刊物上开展学术讨论,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并不容易。真正的学术讨论,必须是也必定是自由的讨论。自由讨论中参与各方都是平等的,彼此可以各抒己见,可以畅所欲言;否则,就不是自由的讨论。从刊物领导方面看,对不同意见必须一视同仁,一碗水端平,特别要注意善待异己,避免一边倒。容忍异己,善待异已,任何时候都是一种雅量,一种风度,也是一种民主作风。以《文史哲》讨论古史分期为例。华岗本人对古史分期所持观点为西周封建说,党内一位著名史学家也持“西周封建”说。可是,山大校内对“西周封建”说存在许多不同意见。古史分期能否在山大讨论起来,华岗本人是否乐见不同意见,这一点非常重要。对此,葛懋春回忆说:“华岗同志在领导《文史哲》工作中,十分重视组织学术上不同意见的争论。中国古史分期是中国史学界的一个老大难问题。当时,有些教授不明确学术与政治问题的界限,不敢同持西周封建论的人争鸣,总想听听他的意见。其实,他在《中国历史翻案》一书中是持西周封建论的,但他总是鼓励持不同意见的人写文章。他多次鼓励童书业教授破除顾虑,发表自己看法。在他领导《文史哲》杂志时,战国封建论、魏晋封建论的文章登了不少。这是《文史哲》能够较早在全国开展奴隶制和封建制分期讨论的重要原因。”当年山大历史系,童书业持“战国封建”说,韩连琪持“两汉封建”说,王仲荦持“魏晋封建”说,皆不以华岗校长的“西周封建”说为意。古史分期的讨论肇始于山大校内,接着反映到《文史哲》。在讨论中,各种意见畅所欲言,针锋相对,激烈争辩。出现这样的自由讨论,华岗具有善待异己的雅量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
华岗认为,马克思主义是真理;宜传真理只能靠说服,不能靠压服,强迫人接受马克思主义是没有用的。说服人们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最好方法与途径是讨论或辩论。他在山大师生中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时,经常有不同意见的讨论。有一次,物理系束星北教授对华岗所讲量变与质变的哲学观点公开提意见,说运动员跳高时一厘米一厘米地加高,哪是质变?哪是量变?有人认为,这是故意抬扛。华岗听说后,亲自到办公室找束星北,听取意见,交换看法,进一步讨论量变、质变等哲学问题。这件事,至今仍是华岗留在山大校园里的美谈之一。华岗与我国许多早期马克思主义学者一样,认为马克思主义与民主是完全一致的;以为马克思主义与民主是对立的,水火不相容,无非是反动派的恶意宣传而已。故而他满腔热情地宣传马克思主义,又在宜传中坚持平等的态度,坚持讨论的方法,坚持以理服人。后来任山大社会学系主任的徐经泽教授,年轻时跟随华岗从事马列主义教学工作。有一次,徐经泽根据自己在人民大学研修班听苏联专家讲课的内容,向校长华岗请教联共(布)党史与国际共运史的关系,请教《联共(布)党史》第四章第二节所讲哲学。这次华岗明确地对他说,马克思主义也不能“定于一尊”。另一次,华岗还对徐经泽说,斯大林也是有错误的。如今徐经泽年届八十,不久前与我讲起华岗这两件事,感慨万分,唏嘘不已。马克思主义不能“定于一尊”,大致代表华岗的真理观。如果真理“定于一尊”,这真理就变成了黑格尔的“绝对理念”。从政治上看,黑格尔的“绝对理念”是非常可怕的。既然不能“定于一尊”,所以马克思主义本身也需要讨论,也需要辩论。马克思主义者不可自以为掌握了一切真理,目空一切,拒绝讨论与辩论。鉴于这样的真理观,他在学术研究中善待异己学派,提倡自由讨论;在政治上,注意平等待人,坚持民主作风。
出于历史方面的复杂原因,当年我国革命队伍中许多人都反对著名学者胡适的思想观点,华岗为其中之一。所以,华岗主持下的《文史哲》,在1955年全国批判胡适之前,早就刊登许多批判胡适的文章,1952年刊出文学史家陆侃如教授的《纪念五四,批判胡适》即为其中之一。不过,华岗领导山大师生批判胡适,是一种思想批判,一种学术批判,至多是教师的一种自我思想改造。以陆佩如为例,他深受胡适学术思想影响,但照样提拔做山大副校长,有职有权。《文史哲》从1954年开始连载陆侃如、冯沅君的《中国古代文学史稿》,这是1949年后第一部文学史专著,立刻声震学术界。1955年以前山大师生批判胡适学术思想,大致是民国以来我国文化界两种对立势力的长期论战在新形势下的继续,它与后来出现的政治批判运动,性质完全不同。了解这样的背景,可以进而了解《文史哲》1954年第7期为何刊载李希凡、蓝翎所撰《红楼梦》研究文章。这篇文章不久便轰动全国,作者也以“两个小人物”闻名于世。从思想渊源看,这篇文章的出现,与两位作者曾是山大中文系学生有关。他们读书时,恰逢华岗领导师生学习马克思主义,批判胡适学术思想。他们的思想受此影响,故而有文章中的进一步思考。不过,《文史哲》刊发这篇文章,就像它在1952年刊发陆侃如的《纪念五四,批判胡适》一样,无非是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针对他们认为一种错误学术观点进行批判。这种批判,限于学术范围或思想范围,并不是政治批判。关于这件事,当事人葛懋春回忆说:“《文史哲》常务编委会发表这篇文章根本没有接到任何上级的指示,当时也不可能预见到它后来在思想界产生多大的影响。文章发表后,连《人民日报》编辑部都不知道作者的通信地址,《文史哲》编辑在接到该报长途电话询问作者通信处时,还不知什么原因。”作者李希凡也说:“当时,党的‘百家争鸣’的方针尚未明确提出,但在华岗同志领导下的《文史哲》,一直坚持学术上的互相商榷探讨的学风,各种意见都可以发表,还希望被批评的参加讨论,进行答辩。当然,有时也由于我执拗、偏激,坚持错误意见,致使有的文章产生坏的影响,但责任不在编辑部,而在我自己。”说《文史哲》上“各种意见都可以发表,还希望被批评的参加讨论,进行答辩”,此为事实,查刊物可证。以后出现的政治批判,是“一言堂”,是一边倒的模式,不准有不同意见的讨论或辩论。所以,无论编辑部还是文章作者,他们的初衷都是批判胡适学术思想的影响,都不是也不可能是发起一场政治批判运动。诚然,学术批判也有差错。特别是当年的学术批判,少心平气和,多出言不逊,但与政治批判的性质不一样,后果也不一样。不幸的是,李希凡、蓝
翎
那篇文章发表后,后来演变成为一场政治批判运动,冤案无数。出现这样的演变,是当年的政治环境与政治斗争造成的。
从学术讨论本身看,其中存在组织领导、方法步骤等一系列具体问题。但归根结蒂,学术讨论关乎学术民主,关乎民主作风。有民主,才有真正的学术讨论;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学术讨论。华岗在《文史哲》提倡自由讨论,说到底是民主作风的一种表现。他在工作中,对待同事,对待不同意见,颇具民主作风。1980年华岗追悼会所致悼词中,特别肯定他“作风民主”。当年在山大担任党组副书记的余修回忆说:“记得那时两位副校长童第周、陆侃如先生都是非党人士,华岗同志很尊重他们的职权,很重视他们的学识和能力。凡学校的重大兴革事项,都召集在一起商量,共同作出决定,由各方分工去办,从不个人包办,从不搞一言堂。华岗同志的民主合作的作风,深得广大党外教职工的信服,他给我们做出良好的榜样,因之他的成信在校内是极高的。”政治上不搞“一言堂”,表现在学术领域就是发扬学术民主,提倡自由讨论。也就是李希凡在回忆中所说:“各种意见都可以发表,还希望被批评的参加讨论,进行答辩。”有学术民主,才有自由的讨论;没有学术民主,就不可能有自由的讨论。在此,容忍异己学派,善待异已学派,最具关键意义。
华岗主持《文史哲》从1951年至1955年,凡四年。《文史哲》在这四年进行的学术讨论,影响之深远非常惊人;像古史分期、农民战争、《红楼梦》问题、典型问题等,一直到改革开放以前的二三十年间,始终是全国学术界热烈谈论的重要话题。华岗办《文史哲》短短四年,结果影响了或掌控了学术界数十年的话语权,可谓期刊史上一个奇迹。这样的辉煌史迄今无法复制,令人羡慕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