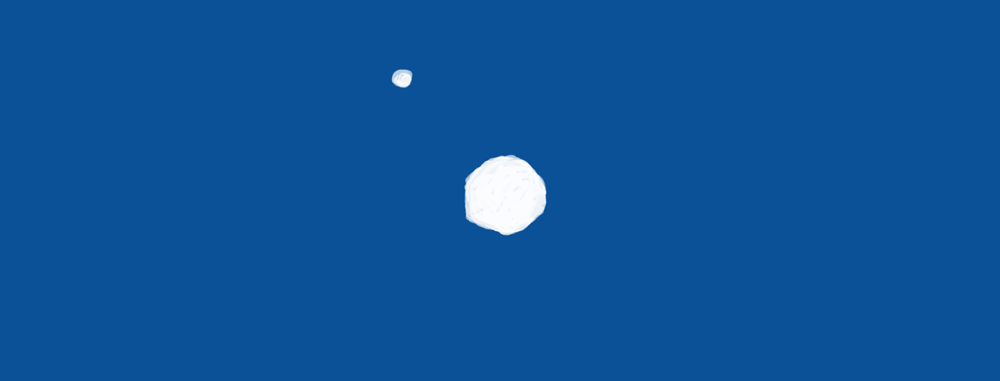
过去、现在与未来之间的区别,仅仅是一种顽固且持久的幻觉。
——出自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写给米凯莱·贝索
(Michele Besso)
家人的信,1955年
当我坐在飞机上跨越时区时,很难想象是在某一个具体的瞬间,时间开始发生变动,我突然变成数小时后的我,而这些时间被地缘界限小心翼翼地存放。
时间取决于经度。地球分为24个时区,每天24小时完成一次360度的自转,在经线上大体上以15度的间距划分。

△ 飞行中的日出。Mark Vanhoenacker / 摄
在航空这件事上,有一个时间规范,这里统一采用同一个时区的时间,这个时间有时被称为“UTC”
(世界协调时间)
,有时被称为“GMT”
(格林尼治标准时间)
,有时又被称为“Zulu”(祖鲁时间,军事通信中用字母“z”来代表时区)。
通常机组人员的出发时间,甚至日期,会和同一班飞机的乘客不同。旧金山的旅客登上飞机时是星期一傍晚对我和其他机上工作人员而言,已是星期二早上。
实际上,为了避免时间的偏差带来的混乱感,在1884年的一次会议上,本初子午线被选定为零度经线,前文提到的
格林尼治标准时
(Greenwich mean time,GMT)
就是本初子午线的时间。

△ 世界时区。每个时区宽约15度,但为了适应政治界限而有些变化。图最下方表示时差,即与以英国格林尼治为中心的时区在中午12时相差的小时数。纽约位处-5区,因此,当格林尼治为中午时,纽约是上午7时。对世界时区系统有多种修正。例如,虽然冰岛和英国不在一个时区,但是冰岛实行和英国一样的时间。西班牙完全在格林尼治标准时间内,但是把时钟定为+1时,而葡萄牙则遵从格林尼治标准时。中国跨越5个时区,但全国都实行北京时间(+8小时)。在南美洲,智利(-5时区)使用-4小时的标准;阿根廷则使用-3小时,而不是它更适合的-4小时。
另一个概念是国际日界线
(Intermational Dale Line,以下简称为“日界线”)
,即新的一天开始的地方,主要沿着180°经线。但是、正如上图所示,有些地方日界线有所偏离,以免一国或一个群岛内有两个不同日期。因而,日界线呈之字形,以便西伯利亚和俄罗斯其他地方有同一个日期,而且使阿留申群岛和斐济岛不致被划分开。新的一天从日界线开始并向西推移,因此这条线以西一般比其东面提前进入新的一天。
了解了平面的时间的差异,我们可以试着把它抽象成一个原点。
而我们对世界,尤其是历史的认知,仰赖一条线性发展的横向时间轴。我们可能会说一个个「序列」,都是按照时间先后进行排列。
若是抛开先入的结论性观念,如何回答“历史”或者说是“地球的年龄”这个问题?
早期,将地质记录转换成地球历史的尝试基于这样一种观点,即各种特定类型的岩石会于过去的不同时期在全球各地形成。
花岗岩、片麻岩等结晶岩被认为是最早的或“第一纪”
(Primany)
岩石。
石灰岩、砂岩等层状岩石则是“第二纪”
(Secondary)
岩石。
半胶结的砂砾沉积物被归为“第三纪”
(Tertiary)
。
而松散的未胶结沉积物属于“第四纪”
(Quaternary)
。
然而,没有证据表明特定类型的岩石的年龄在世界范围内是相同的。
19世纪初,世界上第一张经过良好校准的深时图表的初稿诞生。这归功于从事运河挖掘工作的威廉·史密斯
(WiliamSmith)
的敏锐观察,他观察到英格兰西部的侏罗系地层序列反复出现,他不仅认识到岩层组的存在,还发现每个地层单元都有其特征化石更重要的是,他意识到,对于外观相似的岩石单元,最好的方法是通过化石进行区分辨别。这就是所谓的化石层序律,它是生物地层学的基础,也是通过特有的化石组合来判定岩石年代的理论依据。最终,史密斯无须看到化石采自哪种岩石,仅仅通过观察化石就能判断它所处的地层。

△
威廉·史密斯1815年制成的大不列颠地质图 / 维基百科。
而这些特定类型的贝壳化石以相同的顺序出现在英国各地的地层中。就像药盒帽
(pillboxhat)
与喇叭裤可作为特定年代的文化标志一样,标志化石
(indexfossil)
同样能够指示特定的地质年代。
以上工作的成果便是大众最为熟悉的地质年代表,由今至古分别为:
新生代
(CenozoicEra)
,孕育了各式各样的哺乳动物。
中生代
(MesozoicEra)
,发育令人生畏的爬行动物。
古生代
(PaleozoicEra)
,遍布阴暗的成煤沼泽、呼吸急促的肺鱼和疾行的三叶虫。
大量丰富的化石生命形式使得每个代
(era)
可进一步被划分为纪
(period)
,纪又细分为世
(epoch)
,世再分为期
(age)
。
然而,在古生代岩石底部的贝壳层之下,寒武纪
(Cambrian Period)
的地层下方,岩石变得“沉默”——没有发现化石。生命似乎是在寒武纪期间突然出现的,这一谜团令达尔文苦恼不已。可见的化石是维多利亚时代的地质学家用来划分地质年代的工具,但由于没有发现化石,这些最古老的岩石便成为解不开的“死结”。于是,它们被笼统地归入“前寒武纪"
(Precambrian)
。此后,地质学家花了一个世纪的时间才认识到,前寒武纪实则孕育了大量的生命,而且该时期占据了地球历史近90%的时间。
任何一个提出“现在什么时间了?”的人都知道什么是时间但跟这么多抽象概念,如空间、美或者生命一样,时间的准确概念也非常飘忽,难以捉摸。
在卡罗尔于2010年出版的题为“《从永恒至此》”
(
From Eternityto Here
)
的书中,他曾在序言中向读者承诺:“到了本书的结尾部分,我们将准确地定义时间,这一定义可以用于任何领域。”但这样的承诺是永远无法兑现的。
圣·奥古斯丁
(St.Augustine)
有这样一段名言:“那么什么是时间呢?如果没有人问我,我知道它是什么。如果我想要对向我提问的人解释它是什么,那我就不知道了。”几乎每一天,我们都不止一次地用到“时间”这个概念,却从没认真地考虑过它的准确定义,或者这样一个定义是否真正存在。事实上,我们大量地使用或者见到许多有关“时间”的惯用表达,但是它们与作为物理量的时间有非常不同的含义。

△ 《彗星来的那一夜》(
Coherence
)剧照
时不时地,我们会在生活中经历许多时间段,它们可以是“倒霉的时间”“美好的时间”,甚至可能会是“神奇的时间”,但这些时间都不是通过我们的钟表计量的。时间身上真的带有某种品质,它们能够让不同的时间有所不同并且因人而异吗?
我无法解释,为什么这么多时间的属性看上去如此“自然”但把那些说法赋予空间就会变得如此别扭。或许时间在日常生活中并不具有与空间相同的地位。我们感到,时间在我们的生命中比空间更为重要。这是一种幻觉,因为如果没有空间,我们便无处生存。产生那种错误观念的原因就是我们只拥有“有限的时间”,因此我们一定要最大限度地实现对它的最佳利用。
在斯莫林
(Smolin)
于2014年出版的著作中,他的整本书几乎都用于回答“时间是虚构的还是真实的”这个问题。我个人认为,这个问题在物理学领域内是无法回答的。这是一个哲学问题,与我们利用感官感知到的一切事物——包括我们自己的存在——是否是真实的类似。

△《飞向太空》(
Солярис
)剧照
所以我们对时间的态度,是“感知”。
当时间被划分为一种可感的属性时,我们对环境就有了更细微的体悟。
瓦尔巴群岛
(Svalbard)
,它们在地图上呈现灰色;依据图例,它们“没有官方时间”。我被一种想法迷住了:那些地域拒绝被一分一秒所束缚,完全不受日程表的统治。那里的时问是否像枝头的北美红雀一样被冻结?还是单纯地按照一种更狂野的自然韵律流淌,不受限制,无拘无束?
那片土地确实不受时间的约束。它仍深深地烙印着冰期的痕迹。不同时代的人类历史遗迹(17世纪鲸脂制造者丢弃的鲸骨、叶卡捷琳娜大帝统治时期的猎人坟墓,以及德国纳粹轰炸机的残骸)散落在广袤却贫瘠的苔原上,如同一场策划拙劣的展览。

△ 斯瓦尔巴群岛
这种多段时间的并置带来了一种垂向时间的陌生体验——区别于横向的时间轴,时间作为一个相关联的整体被感知。
虽然我们人类可能永远不会停止对时间的担忧,并学会爱上它
[套用《奇爱博士》(
DrStrangelove
)的副片名]
,但或许我们可以在时间恐惧症与“恋时间情结”
(chronophilia)
之间找到平衡,习惯于“时间无处不在”——清楚地认识到人类在时间中的位置。这既包括人类出现之前的悠久过往,也包含没有人类参与的未来。
不过,我们所居住的这颗星球极为古老、坚韧,而非年轻、未经历练,亦或可能十分脆弱。作为地球公民,我的日常生活也因意识到缤纷的地貌与生物的长久存在而变得丰富多彩。理解某种特定景观的形态成因,如同学习一个普通单词的词源,令人豁然开朗。时间之窗徐徐开启,照亮了遥远却仍可辨认的过去——几乎就像记起了一些早已遗忘的事物。
这赋予了世界多重意义,改变了我们感知自身位置的方式。虽然我们可能会因虚荣心、对存在的焦虑或恃才傲物面强烈地抗拒时间,但无视人类在地球历史中的暂时性便是贬低自己。虽然关于永恒的幻想可能令人着迷,但“时间无处不在蕴含着更深刻且更神秘的美景。

△ 地质学时间螺旋 / 维基百科
地质学是一门认知“命运”的学科:过往的秘密历史支撑着这个世界,将人类罩于当下,并设定了我们的未来之路。过往并未消逝;事实上,我们可以在岩石、景观、地下水、冰川和生态系统中轻易地察觉到其留下的痕迹。比方说,如果一个人事先了解了某座伟大城市的建筑物的历史语境,那么其游览这座城市的体验会变得更为丰富。与此相似,识别出各地质年代的独特“风格”,也会让人深感满足。
人类,同样居住在地质年代之中。
参考资料

《改写地球历史的25种石头》,后浪,2023.10
《地理学与生活:全彩插图第11版》,后浪,2017.3
-Fin-
如需转载请注明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