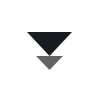作者:田士臣,英国诺丁汉大学国际公法硕士,武汉大学中国边界与海洋研究院博士生。
原文刊发于
《边界与海洋研究》2017年第4期
(本文标题经作者授权有调整)
目前的南海形势,与2016年7月12日南海仲裁案裁决宣布时相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与当时有的学者推测中国可能因为南海仲裁案而“濒临绝境”相反,中国秉持解决南海问题的双轨思路,中菲南海问题双边磋商机制首次会议成功举行,中国与东盟国家在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第14次高官会上就《南海行为准则》框架达成一致,这些都为通过双边和地区规则管控分歧、深化务实合作、维护南海和平与稳定奠定了制度基础,为构建基于地区规则的国际海洋法律秩序做出了实在贡献,南海局势由此复归和平、安宁与良好秩序的积极方向。
在中菲重归和平谈判轨道的背景下,避谈或慎谈南海仲裁案论者有之,惧谈南海仲裁案论者也有之,彻底遗忘南海仲裁案论者更有之。本文认为,南海仲裁案不是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伤疤”或“地雷”,直面相关各方就南海仲裁案对中国提出的批评,向全世界深入阐明中国对南海仲裁案的立场的合法性、中国维持南海和平稳定的信心和决心,回答为什么被西方国家标榜为践行国际法治的南海仲裁案却使南海频生冲突与波澜,才能化解域外国家对中国凭借军事实力和政治影响力解决南海问题的指责。
梳理学者和媒体的言论,指责中国对南海仲裁案的立场主要集中但不限于以下几点:中国签署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下称《公约》)即表示同意接受《公约》第十五部分规定的包括强制仲裁在内的第三方强制程序;按照《公约》第十五部分第288(4)条规定,仲裁庭是否具有管辖权应由其自行裁定;按照《公约》第十五部分第296条规定,仲裁庭的裁判对于争端各方具有确定性和拘束力,中国作为争端一方必须遵守,中国不遵守仲裁裁决就是破坏国际法治。
以上几点是批判者就菲律宾单方面提起的南海仲裁案批评中国政府立场时惯用的逻辑和法律依据。这些表面看来于法有据的论断隐藏了诸多逻辑的混乱和法律适用的错误。它把中国签署《公约》时给予的国家同意无限放大,对仲裁庭超越其法定管辖范围视而不见,事实上刻意模糊了《公约》给予仲裁庭的法定权限的边界,根本无法实现仲裁裁决本应达到的目的和效果,不符合《公约》所体现的国际法治精神,不利于基于《公约》的国际海洋法律秩序的构建。
剥开南海仲裁案的所谓逻辑和“形式合法性”外衣,从国际法治的本源和实质上分析,南海仲裁案临时仲裁庭超越法定权限和管辖范围做出裁决,片面解释和适用《公约》,破坏了国际海洋法的完整性和权威性,客观上造成了国际法的碎片化,损害了包括国际仲裁在内的第三方争端解决机制的声誉和权威,无益于南海争端的和平解决和良好海洋法律秩序的构建。中方对南海仲裁案的不接受、不参与、不承认、不执行的“四不”立场,既是正当行使中国作为《公约》当事国所拥有的合法权利,也符合《公约》所体现的国际法治精神,并在一定程度上防止和减轻仲裁裁决对国际法治造成的负面影响和危害。
一、维护《公约》争端解决机制的声誉和权威,阻止国际法上积极诉讼主义的扩张
国际法上的积极诉讼主义(judicial
activism),抽象讲是指诉讼行为超出了司法审判的边界[1],也有人将其归纳为“对国家强加不符合严格国际法治原则的法律限制的倾向”[2]。南海仲裁案既违背了国家同意这一基本国际法治原则,也超越了《公约》和当事国的授权。特别是,那种认为中国签署《公约》即等同于无条件接受《公约》第十五部分规定的所有第三方强制程序的说法,无视中国根据《公约》第298条所做出的有关排除声明,擅自扩大了中国签署《公约》时所同意承受的国际义务的法定范围。
国际法律体系构建于主权国家平等的原则基础之上,这项原则的后果之一就是任何国际争端解决机制不能未经国家同意行使管辖权。作为整个国际法体系的基石,国家同意原则是国际法具有拘束力的根源所在。这项原则同样适用于有关国际诉讼的法律。正如常设国际法院在“东卡雷利亚案(Eastern Carelia Case)”所述:“在国际法上已经完全确立,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不经其同意,被迫将其与其他国家的争端提交给调解、仲裁或其他任何和平解决方式。”[3]国际法院在“和平条约解释案(Interpretation of Peace Treaties case)”中再次确认:“争端当事国同意是法院在诉讼案件中行使管辖权的基础。”[4]以上是对国家同意原则与管辖权关系的基本理解。
具体到本案,中国政府于2006年根据《公约》第298条做出了就特定事项不接受《公约》第十五部分第二节规定的任何程序的排除声明,这表明中国签署《公约》给予的国家同意是有限制条件的,这个条件的最基本要求就是任何强制程序的争端解决机构必须在法定范围内行使管辖权。展开讲:第一,关于《公约》第298条第1款(a)、(b)和(c)项所述的任何争端,即有关海域划界、历史性海湾或所有权、军事或执法活动等事项的争端,中国政府不接受《公约》第十五部分第二节规定的任何强制程序。因此,不能将中国签署《公约》与中国无条件接受《公约》第十五部分规定的包括强制仲裁在内的所有第三方强制程序划等号,强制仲裁的案件不适用于各当事国排除适用第三方强制程序的案件。曾任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主席、委员的平托(M.
C. W.
Pinto)法官指出,“若争端被‘排除’在《公约》第十五部分第二节之外,只有在‘做出排除’的国家撤销本国根据第三节做出的声明,或该国与其他争端当事国达成协议将争端提交一种或另一种争端解决程序的情况下,才能对该争端适用强制程序。”[5]
换言之,只有那些当事国提出声明的范围以外的事项,如果由某一国家提出强制仲裁,这时候发生的管辖权争议才由仲裁庭自主裁量,仲裁庭不能通过自由裁量权来突破国家同意这项根本原则的限制。
第二,中国签署《公约》给予的国家同意是基于仲裁庭的管辖权是由《公约》法定的,仲裁庭的自由裁量权必须在法定权限内行使,而不是无限制的行使。《公约》对仲裁庭的管辖权限的法定性体现在诸多方面,比如根据《公约》第288条第1款仲裁庭仅对“有关《公约》解释和适用的争端”具有管辖权;根据《公约》第281条和283条仲裁庭行使管辖权应当考虑尊重当事方协商解决争端义务以及当事方履行交换意见义务的前提条件;根据《公约》第三节的规定仲裁庭应当遵守有关适用第二节强制程序的例外和限制;《公约》并不调整领土主权事项等等。换言之,即使中国签署《公约》表示中国同意接受《公约》规定的包括强制仲裁在内的第三方强制程序,仲裁庭在行使管辖权时必须在以上法律规定的诸多限制条件内行使;如果没有这些法定限制或者这些法定限制可以被任何争端解决机制的自由裁量权所任意突破,比如仲裁庭可以任意解释争端事项是否属于当事国声明排除的事项,中国就不会给予《公约》国家同意了。因此,简单和机械地援引《公约》第288(4)条认为仲裁庭享有不受任何限制的自由裁量权是不符合《公约》规定的。
以上构成了对中国签署《公约》给予的国家同意的比较完整的解读,中国签署《公约》给予的国家同意正是考虑到这些法定限制,超出这些限制条件强加给中国法律义务也就超出了中国通过国家同意所承受的国际义务的范围。本案仲裁庭正是超出了《公约》对仲裁庭的自由裁量权所规定的法律限制,通过任意武断的法律解释和适用进行积极的扩权和越权,突破《公约》规定的行使管辖权的前提条件,规避中国提出的排除声明,把本质为领土主权和海域划界的争端包装为法律解释和适用的争端,是一种违反国家同意原则强迫中国接受第三方争端解决机制的激进做法。曾任美国国务院法律顾问的亚伯拉罕·索菲尔(Abraham
Sofaer)撰文指出,“任何法庭都应遵守《公约》条款的限制及中国同意接受《公约》争端解决程序时所提出的声明。”
[6]1927年“荷花号”案也曾明确,“法律规则之所以对国家有拘束力是源于国家签署公约时表达的自由意志......因此对国家独立性的任何限制不能依靠推测得出”。[7]因此,仲裁庭和西方学者不能以推定方式来确定中国签署《公约》时给予国家同意的内容,武断认为中国签署《公约》即等同于接受其规定的任何第三方强制程序,超越《公约》给予它的法定权限裁定对此案有管辖权。
再回到原点,既然按照《公约》第十五部分第288(4)条的规定仲裁庭是否具有管辖权应由其自行裁定,也就是说表面看来仲裁庭是否有管辖权完全由其自己说了算,又如何判定仲裁庭超越法定权限呢。有几点需要说明:第一,《公约》附件七仲裁庭在管辖权上的自由裁量权是有限度的,这一点与《国际法院规约》第36(6)条规定的国际法院在管辖权上的自由裁量权完全不同。[8]但是,为了夸大和强化仲裁庭的自由裁量权,西方学者——包括菲方美国代理律师保罗·雷切尔(Paul
S.
Reichler)——在引用《公约》第288条第4款的时候,实际上是有意无意拿这一条与《国际法院规约》第36条第6款作类比,从而误导普通公众认为仲裁庭在管辖权上享有同国际法院一样的自由裁量权。这些学者作为专业人士内心其实是非常清楚的,这两个条款尽管措辞基本相同,但涵义是完全不同的。《国际法院规约》第36条第6款规定适用于任何争端、任何情势,但第288(4)条规定仅适用于有关《公约》解释和适用的争端,且受到本文前面所提到的缔约国声明、不调整领土主权争端以及第十五部分其他条款等一系列法定限制。其次,由于管辖权受到一系列法定限制,仲裁庭的自由裁量不能是任意的、武断的、主观的。正如《公约》附件七第9条所规定并为仲裁庭《程序规则》第25条所确认的那样:“仲裁法庭在作出裁决前,必须不但查明对该争端确有管辖权,而且查明所提要求在事实上和法律上均确有根据。”本案仲裁庭恰恰是在这一点上出了问题,仲裁庭既没有依据法定管辖范围确定其管辖权,也没有满足在事实和法律上确有依据的法定要求。这一点下文还会做深入分析,其中最能体现仲裁庭的武断性、任意性和主观性的是,仲裁庭认为可以先裁定海洋地形地物的法律性质,而不需要考虑其主权归属,从而使得仲裁庭可以绕开领土主权争端对本案行使管辖权,这一做法没有得到任何国际法渊源的支持,也与国际法院先前的所有判例相反。国际法院在解决关于领土主权和海域划界争端的时候,无一例外都是先判定岛屿主权归属,再依据“陆地统治海洋”的原则判定海域划界等其他问题,而本案仲裁庭的做法恰恰相反,属于典型的本末倒置。仲裁庭在没有法律性权威支持的情况下超越法定管辖范围行使管辖权,必然向中国强加其通过国家同意所承担的《公约》义务之外的法律义务。
从本质上讲,缺少了国家同意这个核心要素,仲裁庭的裁决就失去了合法性(legitimacy),没有法律效力。正如国际法院前法官、国际法委员会前主席阿卜杜拉·卡洛玛在2016年7月19日接受媒体采访时强调:“管辖权的本质就是通过给予国家同意给予仲裁庭裁决案件的权力。如果国家没有给予同意,仲裁庭就没有管辖权。”[9]国际仲裁本身就是一个基于自愿的程序,国家同意是国际仲裁的一项本质特征,其管辖权也是基于当事国的同意,缺少了国家同意仲裁就不是仲裁了。即使是国际法院的管辖权同样基于国家同意。[10]临时仲裁庭不顾中国的明示反对,在没有合意的情况下强制仲裁,这一程序从一般国际法意义上讲已经失去了管辖权的基础,不能再称之为仲裁,只是非法无效的第三方强制争端解决程序。
中国通过排除声明给予《公约》国家同意的做法反映了普遍的国际实践,法国、澳大利亚、泰国、韩国、俄罗斯等许多国家都做出了类似声明。本案是中国被强迫作为南海仲裁案的争端当事方,如果任由这种积极诉讼主义扩张,将来所有同中国一样根据《公约》第298条提出声明的国家都有可能站在被告席上,成为滥用第三方强制程序的受害者,他们提出的合法声明也就会成为一纸空文。从这个角度讲,中国坚持不参与、不承认的立场,正是为了防止积极诉讼主义在国际海洋法领域泛滥成灾,维护《公约》第三方争端解决机制的声誉和权威。
防止积极诉讼主义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处理好司法与政治的关系,真正使其发挥定纷止争的最终目的,而不是沦落成政治工具。南海仲裁庭显然没有打算通过裁判最终解决纠纷和促进和平。相反,在中国已经明确立场的前提下,强行做出的仲裁裁决不但没有解决中菲之间的争议,而且在领土主权争端之外增添了许多新的海洋权益争议。仲裁裁决成为本地区新的政治、外交和军事冲突点,激化了南海海域的不稳定因素,加剧了地区紧张局势,成为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根源。一方面,域外国家可能以非法仲裁裁决为依据挑战中国在南海的主权主张,加强在南海的军事存在,推动南海军事化。域外国家加强南海军事存在反过来又会迫使声索国加强相关岛屿的自卫措施,形成恶性循环。另一方面,其他南海声索国可能会效仿菲律宾提起类似诉讼,或直接片面援引仲裁裁决推进其在南海的政策主张,这些都会成为导致本地区产生冲突和不稳定的新因素。
南海仲裁案之所以未达成定纷止争的目的,反而成为地区和平稳定的负资产,正是因为这个案件受到太多的政治干预,许多学者对此提出了他们的批评意见。郑永年教授在本案实体裁决发布后说:“我一直强调,菲律宾这个案子是政治问题,是美国在背后操作的一个政治问题。”[11]
德国波恩大学教授、国际法和海洋法专家斯特凡·塔尔蒙表示:“中立的观察者会感觉到国际法和临时仲裁庭被菲律宾及其幕后操纵者‘导演’成了一场‘政治官司’,这导致所谓裁决结果不可能执行,从中期来看,将使国际法承受较大打击。”[12]对于将南海问题作为遏制中国的工具,美国总统奥巴马是直言不讳的。奥巴马在2016年4月接受《大西洋》杂志编辑杰弗里·戈德堡(Geffrey
Goldberg)采访时表示:“只需要看一看我们在南海是怎么操作的,我们已经把绝大多数亚洲国家动员起来一起孤立中国,使中国措手不及,坦白讲,这极好地服务于我们加强联盟方面的利益。”[13]结合奥巴马的表态回顾近几年南海形势的发展,在美国推行亚太再平衡战略之前,尽管相关国家之间存在领土主权争议,南海一直是开放的、和平的、稳定的,一切变化始于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开始。
当仲裁案成为美国实现其亚太再平衡战略和地缘政治利益的工具,法律就失去了其应有的独立性和公正性。如果不是中国站在前台坚持自己的立场,任由法律沦落为地缘政治的工具,任由南海被塑造成第二个中东,任由南海原有的开放、和平和安宁状态被打破,那才是《公约》争端解决机制最大的失败和悲哀。从这个角度讲,中国是在维护《公约》争端解决机制的声誉和权威,也是在维护南海地区的和平稳定。
二、维护《公约》的统一性和完整性,反对对《公约》解释和适用的碎片化
2006年国际法委员会第58届会议通过的《国际法不成体系:国际法的多样化和扩展引起的困难》在说明国际法碎片化(不成体系)对国际法一致性造成影响时,专门提到了包括《公约》附件七仲裁庭在内的三个不同机制程序对《公约》通用规则的解释和适用问题。[14]尽管对国际法碎片化的影响及其可控性有不同看法,防止不同机构对同一国际法规则做出碎片化的解释和适用是共识,特别是要警惕那种违反通用规则的“造法”行为。暂时抛开临时仲裁庭对该案没有管辖权不说,其裁决体现了仲裁庭将本案作为国际海洋法“造法”运动试验场的种种“大胆创新和努力”,也违背了《公约》要求仲裁庭依据法律和事实判案的法定要求。
首先,从程序上讲,认真阅读仲裁庭的两次裁决会发现,仲裁庭的裁决更像是基于结果的逆向法律逻辑推理(result-oriented
judging),它不是基于中方的政府声明并以此作为中方初步异议来逐项展开讨论,而是明显基于菲方的诉求且在肯定菲方诉求的前提下逐项展开论证,许多中方的观点仲裁庭或者是有意忽略或者是草草应对,这种程序创新在司法审判或仲裁程序中是极其鲜见的。比如仲裁庭分析中方在南海的活动,一上来就直接援引菲方观点说中方在菲律宾的专属经济区从事非法活动,也就是说在没判决之前就已经先确定相关海域属于菲律宾了,而中菲之间的争议恰恰在于没有划定海上边界。仲裁庭在管辖权问题上的裁决更是如此。仲裁庭不是依据中方关于管辖权的异议进行讨论,而是顺着菲律宾的管辖权诉求进行推理。为突破主权和海洋划界问题对管辖权的限制,临时仲裁庭支持菲方将海洋权益与海洋地物法律地位分开处理的主张,认为主权问题可以和海洋权益分开,争议不涉及主权和海域划界问题。这样本末倒置的逻辑很难解释,既然有关某海洋地物的海洋权益争端与谁对这个地物拥有主权无关,为什么菲方要针对中国提起诉讼呢。最终的裁决结果更是与仲裁庭声称不管辖领土主权问题的主张完全相反。仲裁庭裁决中国部分岛礁不具有完全岛屿法律地位,裁决部分岛礁为不可占有的低潮高地且处在菲律宾的大陆架上,这些内容或者直接剥夺了中方对部分岛礁的主权主张,或者从逻辑上排除了中方与菲律宾海洋划界的可能性,明显超越《公约》对仲裁庭的授权,也违背了仲裁庭不对主权和海域划界问题行使管辖权的承诺。此外,程序上值得注意的另一点是仲裁庭对已有判决的援引方式。通观本案援引的所有案例,仲裁庭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援引少数而非多数的意见,而持有少数意见的恰恰是仲裁庭现任法官,这一耐人寻味的做法为仲裁庭采取实体上的“造法”行为铺平了道路。
仲裁庭在实体上的“造法”行为更是不胜枚举。岛屿制度是《公约》里面的一项重要制度,临时仲裁庭关于“岛礁”法律地位的裁决最引人关注,在没有援引任何法律权威且不顾事实的基础上,其对“岛屿”概念做出了自己独特的狭隘解释,从而认为南海不存在任何享有完全岛屿法律地位的海洋地物,这样的结论为满足菲律宾其他诉求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法律基础。[15]为得出这一结论,仲裁庭不是将作为太平岛主人的中国台湾提供的辩护意见作为证据基础,也没有派任何仲裁员或专家证人进行实地考察(按卡洛玛法官的意见,从程序上来说,他们本该这样做,而且中国台湾方面一再发出邀请),而是完全依据菲方提供的证据展开讨论,这是不符合常理和程序的。专家证人斯科菲尔德教授更是推翻自己原来认为在南海存在完全法律地位岛屿的观点,在庭审实体阶段提供了不同观点,辩称“先前可能的主张与最终结论完全是两回事”。归结到一点,法庭就此做出的裁决并不是依据事实做出的,仲裁庭不去实地考察也正是为了回避这样的事实,从而以“不作为”的方式为其就太平岛法律地位做出“指鹿为马”的裁决扫清障碍。
仲裁庭关于“岛屿”概念的新标准包括但不限于:要求岛屿拥有维持稳定人群的客观能力(objective
capacity which can sustain a stable community of
people);官方人员不包括在维持稳定人群的能力范围之内;经济活动不依赖于外部资源(dependent on outside
resources);等等。这些标准都超出了《公约》原有条款的规定。引用美国佛吉尼亚大学教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评释》主编迈伦·诺德奎斯特(Myron
Nordquist)的话说:“如果引用仲裁庭适用的标准,如此理解产生的结果就是连香港和新加坡都可能是礁。”“如果相同标准适用于美国,比如位于太平洋中间的美属约翰斯顿岛,现在拥有200海里专属经济区,但它的一些基本指标远不及太平岛,所以这对美属岛屿也是非常不利的,根据这个标准它们都将不是岛屿。”[16]塔尔蒙教授在接受德国媒体采访时也强调,临时仲裁庭对岛屿的狭义定义如果得到认可,那么受影响的不仅是中国,美国、加拿大、法国、英国、日本等因岛屿获得海洋区域或主权的国家都将受到影响。[17]可见,临时仲裁庭的裁决是对整个国际海洋法律秩序的冲击。
临时仲裁庭关于“岛屿”的“造法”行为已经在现实中造成理解或适用上的冲突。日本政府发言人在回应有关将该标准适用于冲之鸟礁的问题时明确表示,裁决不适用于冲之鸟礁,冲之鸟礁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在2016年7月13—14日例行记者会上回应关于太平岛法律地位的提问时左躲右闪,甚至没有直接面对问题,最后只能是答非所问地重复《公约》的条文。[18]裁决对现实世界造成的冲突才刚刚开始,随着时间的推移,临时仲裁庭关于“岛屿”的“造法”行为的危害性会越来越凸显。
临时仲裁庭对规定适用管辖权前提条件的《公约》第281条所指的“协议”(无论动词还是名词)的狭义解释也是一项“创新”。仲裁庭认为,无论是中菲之间的双边文件还是《南海各方行为宣言》,都不构成两国之间具有法律拘束力的协议。仲裁庭没有解释裁定协议必须是具有法律拘束力的协议的法律依据,而是简单粗暴地否定中菲根据这些协议所承担的通过谈判解决争端的义务。这样的解释等同于无视所有《宣言》当事国做出的庄严承诺,否定了整个地区国家为维护地区和平所做出的努力。《宣言》当事国是尊重《宣言》的效力,还是默认临时仲裁裁决的效力,这必然会造成规则适用的冲突。从这个角度讲,临时仲裁庭的解释是极不负责任的“造法”行为,中国坚持其立场就是要抵制这种不负责任的行为,维护地区国家的和平稳定和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
此外,一方不出庭就裁定其完全承担不利后果,这种明显“一边倒”的裁决在整个国际司法和仲裁的历史上十分罕见。为了达成这种“一边倒”的裁决,仲裁庭以局外人看起来近乎偏执的态度,或者在设定结论的情况下寻找理由和依据,或者为得出想要的结论不顾最基本的事实,失去了仲裁庭应有的独立性和中立性。以岛礁建设的军事活动属性为例,从最开始的官方表态开始,中方就一再强调南沙岛礁的建设是在已驻守岛礁上开始的建设,并一再明确岛礁建设同时具有防御功能,且事实上在建设之前岛礁驻守人员都是军人。就连美国也一直指责“中国的岛礁建设加剧南海军事化”,声称“中国准备把这些岛礁变为军事前哨”。仲裁庭不做任何实地调查,不顾长久以来中国在所有岛礁上驻军的事实,完全采信菲方主张,裁定中国在南沙群岛的所有岛礁建设不构成军事活动,不受中国根据《公约》第298条做出的排除性声明的限制,这明显违背了最基本的事实,很难令人信服。
临时仲裁庭在本案的“造法”行为无法一一列举。按着司法经济的原则,在可以根据多个法律依据做出判决的时候,法官应当根据引起最小争议的依据做出判决。综合以上分析看,仲裁庭的做法恰恰相反,两次裁决均存在诸多引起争议的“造法性”解释或适用,在许多海洋法的概念和制度上撕裂了《公约》的统一性和完整性。这样的后果是,仲裁庭是在为国际海洋法领域法律适用的碎片化做实实在在的贡献。从这个角度,临时仲裁庭的做法是与国际法院、国际海洋法法庭等权威国际司法机构的努力背道而驰的,后者的诸多判决为国际法的编纂和渐进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比如国际法院在判决中确立的许多关于海洋划界的原则和制度都被吸收到1982年《公约》之中,本案则创立了一个反面的先例。
符合国际法治原则的裁决会被不同的权威司法机构或争端解决机制所援引,不符合国际法治原则的裁决或判例会被扔进历史的垃圾堆。可以预见,随着越来越多的学者深入研究本案对国际法造成的危害和负面影响,当同样的问题再次出现时,权威司法机构就会作出与本案相反的解释,本案的裁决必定会被其他权威裁决或新的国际立法推翻。比如“荷花号”仲裁案确定的船舶刑事司法管辖原则就被1958年《领海和毗连区公约》及其他国际公约所推翻。从阻止本案破坏国际法的统一性和完整性这个角度,中国是在维护基于《公约》的国际海洋法律秩序和国际法治。
三、维护基于共同价值的国际法律秩序,防止“欧洲中心主义”在海洋法律领域的复活
近代国际法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深受欧洲中心主义的影响,客观上讲这与国际法的起源与殖民历史有直接关系。在长久历史时期内,包括中国在内的亚非拉国家并不被视为国际法的主体,因为他们首先不被西方国家视为文明国家,而是被当作可以任意处置的国际法的客体。他们的领土边界往往由殖民主义者来划定、切割,这种不顾民族、文化对领土边界的任意处置到现在仍然是非洲地区战乱不断的根源之一。如果在21世纪的今天,有人仍然抱有这种殖民主义心态,企图在在南海海域的海域划界上对亚洲人指手画脚,这当然应当是所有亚洲国家都应当齐心协力努力防止和避免的。因此,现代国际法编纂与发展的一个很重要任务就是去殖民化和克服这种欧洲中心主义的影响。
国际海洋法领域也是如此。努力防止欧洲中心主义的抬头,使海洋法律秩序反映包括亚非拉国家在内所有《公约》当事国的价值和利益,也是海洋法发展面临的形势与任务。这种努力既应体现在国际海洋法立法方面,也应体现在海洋法的解释和适用上。在立法方面,亚非拉等发展中国家积极参与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创制,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主体作用。在《公约》解释和适用上,仍然要保持这种积极参与和主体作用,防止欧洲中心主义的不当影响。从南海仲裁案看,仲裁庭的组成、运行、后果和各方对仲裁裁决的态度等都说明,防止欧洲中心主义的抬头仍然任重道远。
在南海仲裁案临时仲裁庭的组成上,仲裁庭是由四个欧洲籍和一个非洲籍仲裁员组成,不像国际法院、国际海洋法法庭等国际司法机构那样在法官的组成方面充分考虑了世界不同地区和法系的代表性。尽管表面看来从程序和形式上讲很难对这样的组成提出质疑,但能让几位持积极诉讼主义的少数意见法官凑在一起组成仲裁庭并非易事,而是菲律宾单方面指定仲裁员造成的结果。这种客观上形成的菲律宾能够单方面指定仲裁员的局面更不是出于偶然,作者有理由相信这是美菲处心积虑精心运作的结果。首先,中国不参加仲裁的立场美菲都是非常清楚的,也就是说中国不会指定仲裁员,这在客观上为美菲运作提供了机会。但如何保证所有仲裁员都能够由菲方指定仍然需要运作。其次,菲方提起仲裁的时机很重要,选择日本籍法官担任国际海洋法法庭庭长时提起仲裁为其进一步运作提供了重要抓手,日本籍法官对中国的态度显而易见。第三,平托退出后选择门萨当仲裁员是美菲精心挑选的,因为门萨最开始不在仲裁员名单里面,是为了这个仲裁案临时匆忙加到仲裁员名单里的,这一点如果留心仲裁员名册不难发现。这些方面加之其他因素共同造成菲方单方面指定仲裁员的局面,为仲裁庭做出“一边倒”裁决提供了可能,也为仲裁员在南海施加欧洲中心主义的影响提供了机会。
但这种“一边倒”的裁决从后果上讲明显受到了欧洲中心主义的影响,特别是最终实现了美国对航行自由的地缘政治需要,根本没有考虑亚洲国家的主权、安全和资源需求。在这一点上菲律宾扮演的角色是非常可悲的,一方面在起诉中国这点上属于“伤敌一千、自损八百”的行为,另一方面仲裁裁决如果有效的话对包括中国、菲律宾、越南在内的所有南海声索国都会产生不利影响。展开来讲,目前的仲裁裁决裁定南海的所有岛礁没有一处具有完全岛屿法律地位,这样的裁定影响到不管任何一方占领的所有岛屿——姑且不论主权归属,最终损害的是包括菲律宾、中国在内的南海所有声索国在相关岛礁的主权。而最大的受益方则是美国,因为从地缘政治角度讲,南海海域没有一处岛屿的情况下美国所能主张的自由航行权利范围是最大的。如果反过来,由南海声索国共同确定岛屿法律标准的地区规则,在不影响各自主权主张的情况下制定共同开发的法律文件,就不会出现目前这种只有美国占到最大便宜,南海各方所有声索国都因仲裁裁决吃亏的局面。这一点更能说明,亚非拉国家一定要争取积极参与《公约》规定的解释和适用,使公约真正反映他们共同的价值观和根本利益。
欧洲中心主义也明显反映在各方对仲裁裁决的态度上。前面提到的美国和日本对仲裁庭认定岛屿标准的态度,明显反映了作为欧洲中心主义核心的例外主义,即只希望为别人设定义务、给自己特殊权利的一贯态度。一方面,美国、日本的政府发言人认为仲裁庭认定的标准不适用于自己国家的岛屿。另一方面,美、日、澳等国家发表的诸多联合声明要求中方尊重裁决。自己国家都不认可的标准,却要求别的国家适用,这种矛盾的作法非常荒谬。如果仲裁裁决认定的岛屿法律地位标准只适用于中国,美国、日本、英国、法国、澳大利亚等其他拥有相似海洋地物的国家都不承认这一标准,这很难说仲裁庭的裁决反映了国际社会的共同价值和普遍的国际法治原则。如果裁决最终成为只是意图对中国南沙岛礁产生影响的特殊和例外规则,而不能被欧美国家乃至整个国际社会所接受,更是说明仲裁庭实际上在欧洲中心主义影响下成为国际政治的工具。作为副产品,仲裁裁决还打击了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对欧美主导的司法和仲裁机构的信心,这对《公约》第三方解决机制而言当然也是一种失败。
南海仲裁案反映的欧洲中心主义还体现在西方媒体的报道和学者的反映上。西方媒体的“一边倒”或选择性报道是媒体自身的价值观和报道倾向。但是,作为以真实客观为职业操守的媒体,却出现大量的集体造假行为。比如,几乎所有媒体在报道这一案件的时候对做出裁决的临时仲裁庭身份做了虚假报道。对于这个形式上根据《公约》附件七成立的依靠常设仲裁法院提供行政服务的临时仲裁庭及其裁决,为了加重临时仲裁庭的权威性、合法性和重要性,路透社、金融时报、美国之音、时代周刊、BBC、华尔街日报、卫报等在报道时称之为“联合国法院/仲裁法院(UN
Court , UN tribunal, UN arbitration tribunal, UN-backed tribunal,
UN-backed arbitration court)”、“联合国支持的常设仲裁法院(UN-backed Permanent Court of
Arbitration)”、“联合国的海事判决(UN sea ruling)” 、“联合国法院/法庭判决(UN court/tribunal
ruling)”、“联合国判决(UN ruling)”或“联合国支持的判决(UN-backed
ruling)”,这明显不符合事实,并导致国际法院专门发布信息进行澄清。再比如,西方媒体在报道中国南海主张时经常在报道结尾背景部分指出“中国对整个南海主张主权”或者“中国宣称南海九段线内90%的水域为中国内水或领土”,中国政府的对外表态中从来没有这样的说法。这样的误导性报道或选择性失明报道还很多,不符合客观事实,有违媒体的道德操守。
从学者的反映看,如前文所列举,确有西方学者专门撰文支持中国政府的立场,但更多的西方学者对本案裁决的具体法律适用保持了沉默。那些就南海仲裁案做出谴责中国表态的西方学者,大多数都是重复南海仲裁案菲方美国代理律师保罗·雷切尔的原则性立场观点,即本文开始部分援引的批评中国对仲裁案的立场的惯常逻辑和法律依据,很少有西方学者结合案件具体法律适用—比如岛礁法律地位标准—批判中国的立场。这些都反映出许多西方学者的欧洲中心主义倾向。
南海仲裁案临时仲裁庭超越法定权限做出的裁决无论从程序还是从实体上都不具有合法性,中国对南海仲裁案的立场本身是符合国际法治原则的合法行为。剥开南海仲裁案的法律外衣,这场案件实际上是围绕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际海洋法律秩序的斗争,即是真正以《公约》为基础建立维护国际社会共同价值和共同利益的国际海洋法律秩序,还是在歪曲解释适用《公约》的基础上建立一个维护特权和例外的欧洲中心主义国际海洋法律秩序。南海仲裁案作为广义上的国际司法实践为我们提供了一次讨论如何通过国际司法维护国际海洋法律秩序的机会。
司法的功能从狭义上讲是为了就事论事地就具体案件定纷止争,从广义上讲也服务于通过个案的法律适用阐述反映共同价值和利益的普遍规则[19],同时在这个适用法律的过程中法律的公平和正义得到彰显。这种对司法功能目的的解释同样适用于仲裁。从南海仲裁结果看,这两个功能都没有实现。仲裁既没有解决中菲之间的争端,更没有通过本案阐释反映国际社会共同价值的普遍规则。案件也许通过“娴熟精致”的法律技术操作实现了对个别或少数国家的单方面正义,但法律技术不能被用来阻止实现对整个国际社会的实质正义。从这个角度讲,南海仲裁案是国际法治实践的反面教材。如何抵消和减轻仲裁案对国际法治产生的负面影响,构建一个基于《公约》规则的国际海洋法律秩序,需要包括中国在内的整个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
[1] Fuad Zarbiyev, "Judicial Activism in International Law—A Conceptual Framework for Analysi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Dispute Settlement, Vol. 3, No. 2, 2012, pp. 247-248.
[2]
Robert Howse, “The Most Dangerous Branch? WTO Appellate Body
Jurisprudence on the Nature and Limits of the Judicial Power”, in Thomas
Cottier and Petros C Mavroidis (eds), The Role of the Judge in International Trade Regulation , Michigan: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03, pp. 11-41.
[3] Status of Eastern Carelia,
Advisory Opinion of 23 Jully 1923, PCIJ, Series B-No 5, p. 27,
http://www.icj-cij.org/pcij/serie_B/B_05/Statut_de_la_Carelie_orientale_Avis_consultatif.pdf,
visited on 18 June 2017.
[4] Advisory Opinion Concerning the Interpretation of Peace Treaties with Bulgaria, Hungary and Romania; First Phas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ICJ), 30 March 1950, http://www.refworld.org/cases,ICJ,4023a17a4.html, visited on 12 June 2017.
[5] 平托:《<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解释与“国际法治”》,http://www.cibos.whu.edu.cn/index.php?id=544,登录时间:2017年5月22日。
[6] Abraham D. Sofaer, ‘The Philippine Law of the Sea Action against China: Relearning the Limits of International Adjudication’,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15, Iss. 2, 2016, pp. 393–402.
[7] The Case of the S.S. Lotus,
Judgement of 7 September 1927, PCIJ, Series A-A10, p. 18,
http://www.icj-cij.org/pcij/serie_A/A_10/30_Lotus_Arret.pdf, visited on
18 June 2017.
[8] 《国际法院规约》第36条第6款规定:“关于法院有无管辖权之争端, 由法院裁决之。”
[9] 深圳卫视直播港澳台专访:《<学问南海>系列专访--国际法院前法官:南海仲裁案裁决无效》,http://www.toutiao.com/a6308698986934354177/,登录时间:2017年5月22日。
[10]
ICJ, “Basis of the Court's Jurisdiction”,
http://www.icj-cij.org/jurisdiction/index.php?p1=5&p2=1&p3=2,
visited on May 22, 2017.
[11] 郑永年、莫道名:《如何面对仲裁结果》,http://news.ifeng.com/a/20160713/49346259_0.shtml,登录时间:2017年5月24日。
[12]冯雪珺:《德海洋法专家谈南海仲裁案:菲方称“全面胜利”令人吃惊》,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503135,登录时间:2017年5月24日。
[13]
Geffrey Goldberg, “The Obama Doctrine”,
https://www.theatlantic.com/magazine/archive/2016/04/the-obama-doctrine/471525/,
visited on 24 May 2017.
[14] See U.N. Doc. A/CN.4/L.682/Corr.1 (Aug. 11, 2006).
[15] 在太平岛具有完全岛屿法律地位的情况下,其本身享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菲方诉状中包括第4—8项以及第11、12、14项等多项诉求将根本无法得到满足。这是因为,一旦太平岛保持原来的完全岛屿法律地位,菲方诉求4至7所宣称的中国相关岛礁不产生专属经济区或大陆架或部分岛礁位于菲大陆专属经济区内或大陆架上的主张,或者根本不成立,或者就没有任何意义。菲方在其他诉求中有关中国岛礁建设及海洋活动违法的指控也根本不再成立,因为仅仅太平岛一个岛屿所辐射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就可以为中方的所有行使主权权利和管辖权的海洋活动提供充分法律依据。
[16] 深圳卫视直播港澳台专访:《<学问南海>系列专访--美海洋法专家:美日勿被仲裁结果冲昏头脑》,http://www.toutiao.com/a6309524875274879490/,登录时间:2017年5月22日。
[17] 美国太平洋凤凰群岛的豪兰岛(Howland Island)、贝克岛(Baker Island)及莱恩群岛金曼礁(Kingman Reef),日本的冲之鸟礁(Okinotorishima)和澳大利亚的麦克唐纳岛(McDonald Island)等等,在自然地理条件上都比太平岛要差许多。
[18] U.S. Department of State, Daily Press Briefing - July 13, 2016, https://2009-2017.state.gov/r/pa/prs/dpb/2016/07/259951.htm, visited on 20 June; U.S. Department of State, Daily Press Briefing - July 14, 2016, https://2009-2017.state.gov/r/pa/prs/dpb/2016/07/260032.htm, visited on 20 June.
[19] Zarbiyev (n 1).
责任编辑:黄伟
美编:江沚珊